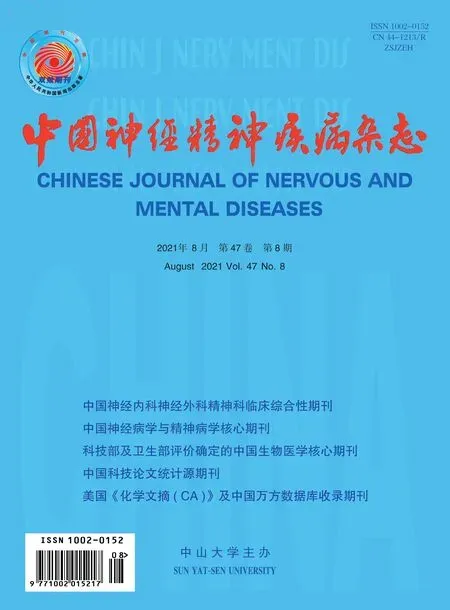四重人格分離性身份障礙1例
袁欽湄 楊峘 曹玉萍
分離性身份障礙(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曾稱多重人格障礙,其特點是至少有兩個且相對持久的身份或互不聯系的人格出現并交替控制個體行為,同時伴隨對重要事件的記憶障礙[1]。DID患病率尚無系統數據,meta分析發現其橫斷面患病率約2%~5%[2]。DID癥狀復雜多樣,常共病其他精神疾病,治療難度大。本文報告1例具有四重人格的DID患者,以期提高對該疾病診治的認識。
1 臨床資料
患者袁某,女,16歲,因“漸起憑空聞人聲、性格改變8年,行為異常1月”于2020年5月至2021年1月先后3次入我院精神科治療。
患者訴8年來可憑空聽到2個聲音,一個是另一自己發出的聲音并可與之對話,另一聲音在這個聲音之后出現,一直存在于患者腦中,可感受和旁觀患者的生活。2個聲音持續存在但不同時出現。此間學習生活如常,性格由開朗逐漸變得孤僻、內向。至2020年1月,患者出現整段記憶缺失,如:堅信自己于2012年11月7日出生(此時實為8歲),此前記憶完全缺失;在學校考試作弊被老師發現當場批評,但過后予以否認;先后3次自殺未遂,分別為過量服用氟伏沙明、夜間入廚房拿刀欲自殺、夜間將頭浸入冷水中,但事后均否認。于2020年5月8日首次入院。
既往體健。個人史無特殊,目前高中在讀,成績中等。自幼與父母同住,父母為政府工作人員,性格均急躁。病前個性開朗,近8年性格漸孤僻。無精神疾病家族史。
體查及神經系統檢查未見異常。精神狀況檢查:意識清晰,接觸交談被動欠合作,問答不切題,自知力喪失;查及言語性幻聽;否認妄想;注意力欠集中,記憶有片段缺失,計算力尚可;情感低落,否認持續情感高漲史;意志行為活動減退,社會功能下降,與人交流少;有自殺觀念。血常規、肝腎功能、電解質、甲狀腺功能、心電圖、腦電圖及頭顱CT均未見明顯異常。小睡實驗:睡眠潛伏期293.5 min,睡眠效率71%。陽性癥狀評定量表23分,陰性癥狀評定量表28分。
診斷考慮:1.青少年情緒障礙?2.精神分裂癥?入院10 d后患者變成自感體內有3個人:自稱“小透明”,小透明系無法忍受“身體里”另外2個人相互控制而出現,表現陽光;第2個人“袁某”(系患者本人),聰明、自律,有自殺傾向,喜歡殘忍的東西;第3個人“崔崔”,熱愛生活,膽小,害怕待在醫院。“小透明”訴因為“袁某”有幾次自殺行為,所以“崔崔”把“袁某”困在身體里,這次住院面對醫生的是“崔崔”,并稱“袁某”在2012年11月7日在回家路上被1名男子猥褻(此經歷患者此前從未與父母反映,具體不詳)。
入院予舍曲林50 mg/d、丙戊酸鈉500 mg/d、喹硫平50 mg/d,配合沙盤治療及支持性心理治療。28 d后出院,患者情緒好轉,仍存在憑空聞聲、記憶缺失等癥狀。出院后接受約每月1次的心理治療,期間休學在家。
2020年7月22日再次入院,表現情緒低落,常憑空聽到嘶吼聲、哭泣聲,感到害怕、痛苦,有自殺觀念。有時用另一人的口吻說話,內容如“我又出來了,袁某的身體里住著3個人,其他2個人在商量著怎么去死”。每次持續幾分鐘,事后完全否認。住院期間,患者堅稱自己體內存在3種完全不同的身份和人格狀態,有各自相對持久的感知、思維及行為方式,并稱自己出生于2012年11月7日,即被“猥褻”當天,對此之前記憶完全喪失。修改診斷為“分離性身份障礙”。
住院期間在“袁某”的人格下予以言語暗示,誘發了患者人格轉換,患者突然轉變口吻,稱“我才是真正的袁某,她們都是不好的”。并突起欲攻擊治療師,抓其母親質問“為什么要殺死我”。予暫停暗示治療并安撫。調整藥物為阿立哌唑20 mg/d、舍曲林125 mg/d,癥狀控制欠佳,住院9 d出院,期間仍存在人格轉換癥狀,未能復學。
出院后,患者接受約2~4周1次的認知行為治療。出院后約 1個月,患者出現第 4重人格,名為“Smile”,患者訴“Smile已經出現七八次,均在情緒爆發時,常有暴力傾向,發作時會掐死身邊所有的活物”。此后,患者能自行轉換人格,每個人格知道彼此的存在。心理治療期間,治療師與患者的每個人格均建立了良好信任關系,幫助患者逐漸認識到每個人格如同一個杯子的不同面,都歸屬于同一個整體。隨著治療推進,患者逐漸接受并希望自己的人格能夠整合。
2021年1月19日,患者以“小透明”的人格身份主動要求第3次住院,訴“小透明”和“袁某”已經完全信任醫生,愿意犧牲自己(即“小透明”)來整合所存在的人格。住院期間,患者展現的“Smile”沉默寡言,用嘶啞的聲音僅發聲個別詞句,并用肢體動作表達信息。艾森克人格問卷評估示:小透明,精神質4分,情緒1分,外傾-內傾性19分,掩飾性13分;袁某,精神質11分,情緒14分,外傾-內傾性3分,掩飾性11分。
入院后予舍曲林100 mg/d、拉莫三嗪50 mg/d、哌羅匹隆12 mg/d治療。進一步幫助患者分析并充分認識每一人格出現的心理意義(可能代表患者所面臨的心理危機),促進各個人格彼此溝通,同時強化人格整合的意義。采用催眠治療處理患者8歲時可能遭遇的創傷性經歷。治療前準備形態各異的布藝玩偶,患者選擇不同玩偶代表自身存在的每種人格。采用想象乘電梯的方式,每層電梯代表相應年齡,誘導患者依次回到既往各年齡階段。當誘導患者來到電梯第8層,患者忽而睜眼,淚盈于睫,渾身顫抖不止,用嘶啞的聲音呼喊“媽媽”。治療師立即予以安撫,將代表性格陽光的“小透明”玩偶放入患者懷抱中,并在潛意識層面提取與抽離創傷性記憶,患者漸漸平靜。此后將患者再次帶至電梯第8層時,其未再出現情緒波動。住院10 d后出院,憑空聞聲已消失,情緒平穩,除主人格之外的其他3種人格均消失。
出院后予舍曲林100 mg/d、拉莫三嗪50 mg/d、哌羅匹隆8mg/d維持治療。3個月后隨訪,患者未再出現人格轉換和記憶缺失癥狀,談及病中表現訴如同夢境。已恢復上學,生活如常,訴感易困倦。
2 討論
97%的DID患者存在兒童期創傷經歷,其中83%是性虐待[2-3]。分離身份可能是患者對童年極端創傷事件的防御機制[4]。本例中,患者報告被“猥褻”經歷后出現熱愛生活的“崔崔”即為患者因創傷事件出現的人格。但兒童期創傷經歷并非DID診斷的必備條件。
有關DID的診斷,《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第11版》(ICD-11)分離性身份障礙的診斷標準中未列入記憶缺失癥狀。而 《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5版》(DSM-5)中注有DID患者可存在反復的記憶空隙,且與普通的健忘不一致。該患者在疾病之初,其他人格多以“聲音”或“感覺”的形式存在,醫師并未觀察到其人格轉變。其次,對于自傷自殺行為,醫師往往首先關注患者的行為動機、情緒狀態及可能需要進行的危機干預等,而非關注患者對此經歷是否知情或存在記憶[5]。因此,患者對既往經歷的階段性遺忘,易被誤認為是抑郁體驗下的記憶力減退、現實解體等癥狀。此外,DID患者的記憶力受損可伴隨執行功能異常,當患者記憶恢復后,執行功能可恢復正常[6]。
DID還需與精神分裂癥相鑒別。擬人化、內部、交流式的聲音可能被誤認為幻覺[1]。患者對自身多重人格的覺知和描述可被誤認為妄想。DID患者存在的身份分化,及無法控制自己的思維、感覺和行為等,難以與思維被插入等思維形式障礙相鑒別。但DID患者更少出現明顯的思維形式障礙,同時DID患者沒有明顯的陰性癥狀[7]。
根據臨床表現,考慮該患者共病抑郁障礙。既往病例報告亦顯示,DID患者常與抑郁障礙、創傷后應激障礙、藥物濫用、邊緣性人格障礙等共病,甚至出現犯罪行為[8-9]。共病增加癥狀的復雜性和治療難度。
DID的治療包括心理治療、藥物治療及物理治療。目前尚無特效藥物,多為對癥治療,但分離的人格狀態可能影響服藥依從性。調節5-羥色胺2A受體和多巴胺D2受體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聯合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抗抑郁劑可用于有侵入性癥狀的復雜創傷病例[10]。電休克治療DID共病抑郁障礙患者的自殺意念療效確切,但是否能促進分離人格的整合仍需進一步研究[11]。
本例心理治療包括認知行為治療、暗示治療及催眠治療。無論何種方式,過快進入創傷處理的治療方法可能會損害治療關系或加重分離癥狀。與患者的主要人格建立信任的治療關系十分重要。如在“袁某”的人格狀態下行暗示治療,意在整合或“驅走”其他幾個人格,在治療過程中雖誘發了人格轉換,卻意外取得了“袁某”的極大信任,有益于后期人格整合;在長程的認知行為治療中,幫助患者分析、認識人格出現的心理意義,激發整合意愿;催眠治療通過退行、記憶提取、創傷性移情、整合等方式進一步對患者進行人格整合,并幫助處理兒童期創傷記憶。既往DID的病例報告顯示采用分階段心理治療獲得可觀療效[8]。也有個案采用穩定(如正念、支持和意象技術)、分離部分和創傷處理 (如促進和鼓勵不同分離部分間的記憶共享和合作)獲得一定療效[12]。另有研究采用系統網絡[9]管理DID合并邊緣性人格障礙的患者,建立個體化心理系統,這為更加科學地監測DID全程治療提供了參考和啟示。
綜上,DID的診斷需要對患者進行詳盡的病史追溯和癥狀辨析。藥物治療在于干預情緒癥狀,長期心理治療在于幫助患者將不同身份整合為一個牢固的自我。建立良好的治療關系后患者以不同的身份進入治療,治療師可因此了解每個身份的特點和關系,最終身份的整合可突然發生或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