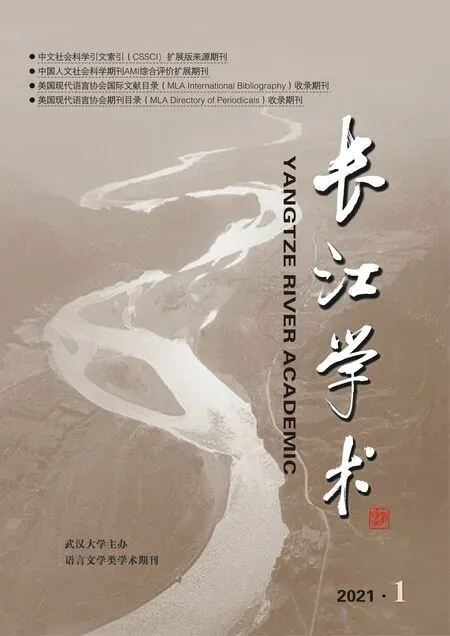作為文化現象的譯者:譯者研究的一個切入點
〔香港〕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學 翻譯系/翻譯研究中心,香港999077)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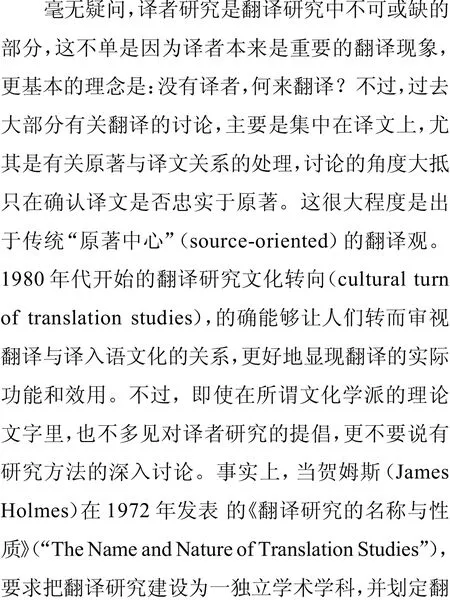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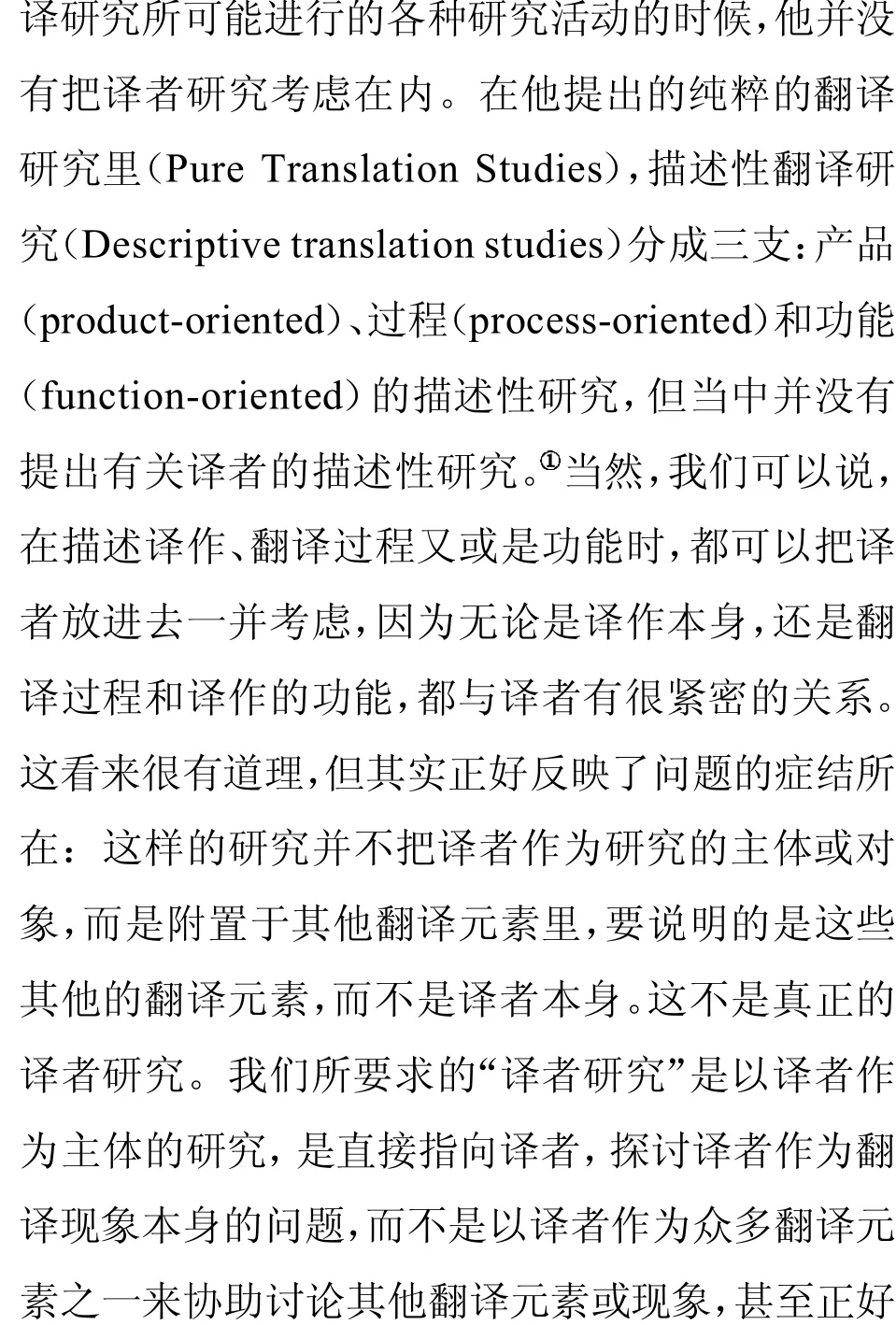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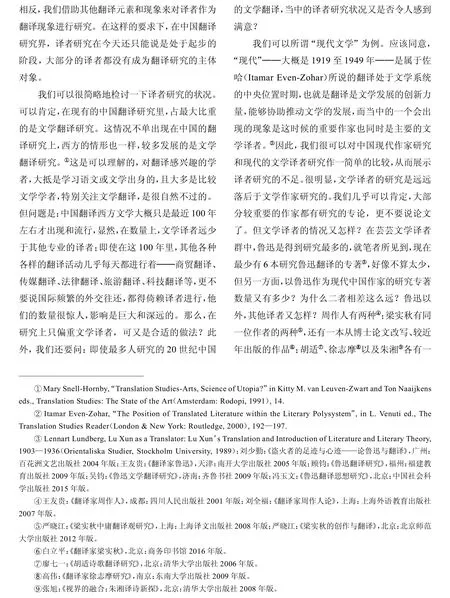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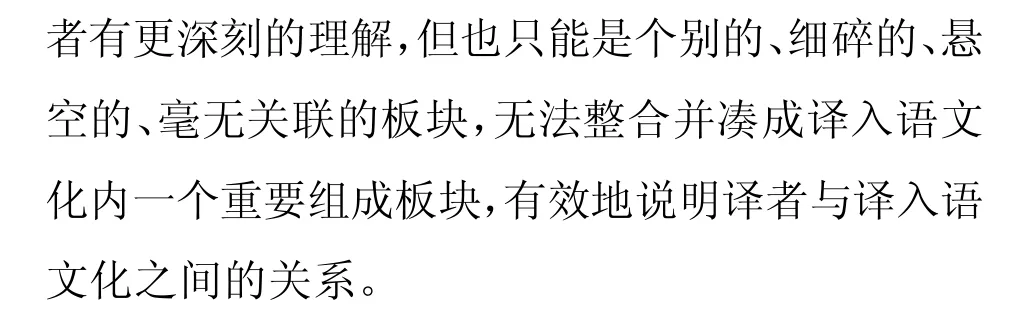
另一方面,這樣的譯者研究集中在他們的翻譯活動上,忽略了譯者的其他文化活動。其實,譯者本身就是文化中的個人,即使最專業或職業化的譯者,他/她的活動不可能只限于翻譯活動,而這些翻譯活動跟其他各方面的活動是掛鉤的、配合的,甚至互動的。文學譯者的例子最易理解,他們的創作跟翻譯是整體性的,不討論他們的文學活動,不可能真正理解他們的翻譯活動。創作以外,他們的出版活動呢?社會活動、教學和學術研究……跟他們的翻譯活動完全沒有關系嗎?文學譯者以外,其他的也一樣。例如清中葉以來廣州貿易體制下的通事,他們除了要負責翻譯工作外,還要處理其他大量商貿事務,更要與中英雙方的官員打交道,協調西方商人在華的貿易以至生活,他們的翻譯活動甚至可以說是附屬于其他活動的。現有的研究大都只集中討論譯者的翻譯活動和翻譯,忽略譯者其他的活動,無法全面展現完整和真實的譯者。
此外,由于這種譯者研究所強調的是個別譯者自身的價值和貢獻,結果是無可避免地集中于一些所謂重要和知名的譯者,上面說過的現代文學翻譯家研究現狀,便能夠很好地說明這一問題。魯迅、周作人、胡適、梁實秋等都是文學翻譯大家,為他們立傳立論,無疑是合適的,但如果譯者研究只是停留在這些重要人物上,那就有很大的局限性,畢竟所謂的大家名家數目不多,占譯者的比例極為微細,即使多做名家研究,也不可能較完整地窺視譯者的真正角色和貢獻。事實上,在人類歷史長河里,很多極其重要的發展都跟一些不知名以至不知道名字的譯者相關,甚至由他們所推動。又以廣州體制的通事為例。在英國東印度公司聘用小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和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為譯員前,中英貿易以及由此而出現的中英各種交往,都是通過這些通事來進行,他們在中英關系史上扮演過極其重要的角色,但他們絕對不是什么翻譯名家,甚至絕大部分連名字也不為人知,以現有的譯者研究模式進行,這些曾對人類發展史產生過重要影響的譯者肯定不會成為研究對象,而我們對廣州體制的翻譯活動便不可能有較完整的理解,從而對錯綜復雜的近代中英關系的理解也不可能完整。這樣的狀況理想嗎?事實上,從廣州通事這個例子可以引伸出來的,就是譯者研究不應該只限于單獨或個別的譯者,譯者群體也應該納入在譯者研究的范圍內。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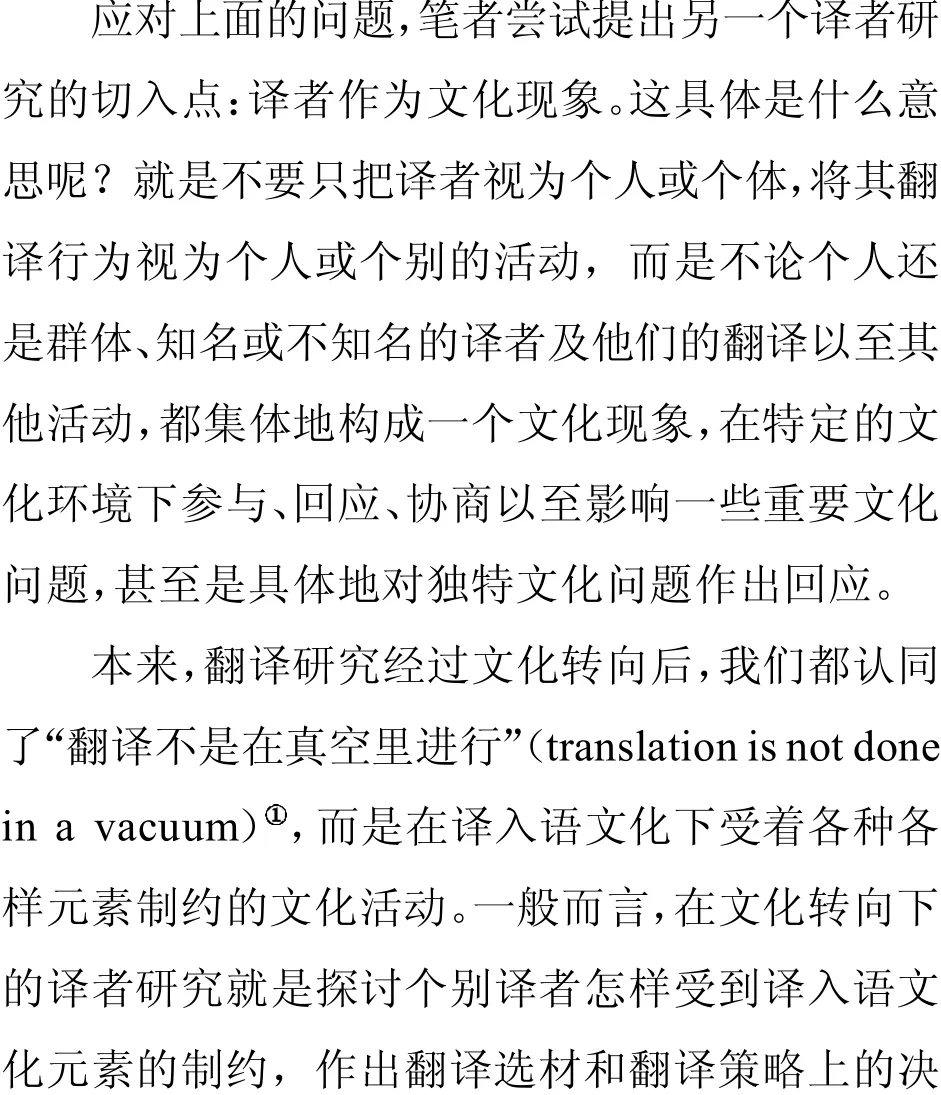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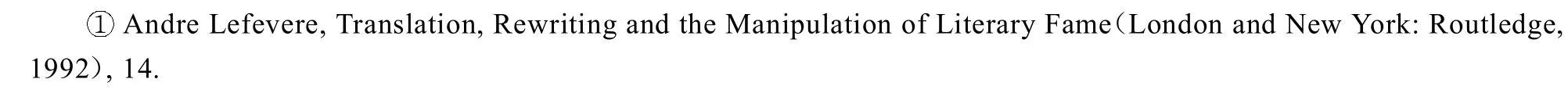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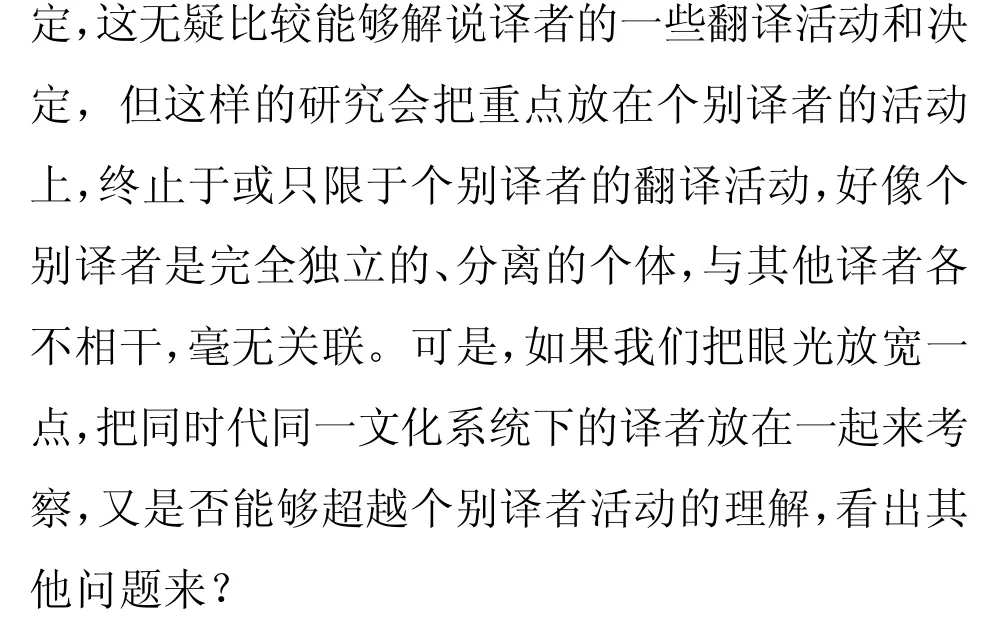
其實,同時代同一文化系統下的譯者面對的,是接近甚至相同的文化元素、文化現象以及文化問題。因此,盡管他們各自進行表面看來很不相同,甚或的確很不相同的翻譯活動,但很多時候是在不同程度上以不一定相同的方式回應著這些文化元素、現象或問題。也就是說,他們的翻譯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集體性的文化行為,有著一種共同性甚至標志性,因而在總體上構成一個文化現象,與他們所處時代的主要文化現象掛鉤和互動。以譯者為文化現象,跟譯入語文化現象關聯進行考察,已經不是個別譯者特定的翻譯行為的研究,而是更大范圍、更整體性的譯者行為研究;同時,這樣的研究不會終止于譯者本身,而是聯系到更大的社會、文化方面去。我們不單以社會和文化元素去解釋或理解譯者的翻譯和翻譯行為,更通過同時代同文化的一些譯者的翻譯和翻譯行為去理解社會和文化狀況,一方面更好地展現譯者在整個文化中的功能和位置,說明譯者與文化的關系,另一方面從一個從來很少人關注的角度——譯者的角度去觀照社會和文化,從而得到更深邃的理解。
必須強調,在我們認定同一文化下進行的翻譯活動具備集體性,不同譯者都在回應相同或接近的文化現象和問題時,并不是說所有譯者的翻譯活動都十分接近,這跟事實不符。我們不應該排除個別譯者的獨特性,因為畢竟不同譯者具有不同的背景,際遇、經歷,以至目標,因此,即使面對相同或接近的文化現象或問題時,也會有不同的體會、思考和反應,結果,盡管整體而言他們是在回應著相同的問題,但他們具體對應的方式,也就是他們的翻譯以及其他相關活動,卻可能有很大的差異。這不單是我們在翻譯史上見到的客觀狀態,更是以譯者為文化現象進行譯者研究饒有意義的地方,因為實際上是探究不同譯者怎樣以相同或不同的方式去應對一個文化問題和現象,既能標示不同譯者的獨特性,增加對個別譯者的理解,又能分析不同譯者的共通性,在更大的文化層面上,更好地展現時代和文化因素對譯者所起的整體作用,有見樹見林的效果。
以譯者為文化現象的譯者研究,具備以下特點:
第一,它并不排除個別譯者的研究,事實上,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會先從個別譯者入手,不過,它不會是所謂的“全面”譯者研究,也沒有必要羅列或說明譯者所有的翻譯成果或活動,只會抽取相關的部分,針對某一個文化現象或問題來進行深入分析,不會停留在所謂“Who- When- What”的表面論述。
第二,它不局限于個別譯者或知名譯者,不論個別知名或不知名的譯者,都會被視為一個譯者群體的組成部分,集體地應對一些文化問題和現象。
第三,在分析譯者的文化位置時,不會只集中或局限于他們的翻譯活動或文本來進行研究,而是集結譯者其他足以說明相關文化問題的各種各樣活動,包括創作、出版、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從這一角度來說,這樣的研究模式能夠對譯者提供更全面的分析及理解。
三
也許在這里可以利用筆者在過去十余年一直構思和撰寫的一本書稿《天朝的譯者:從李葉榮到張德彝》為例子,來說明一下“譯者作為文化現象”的譯者研究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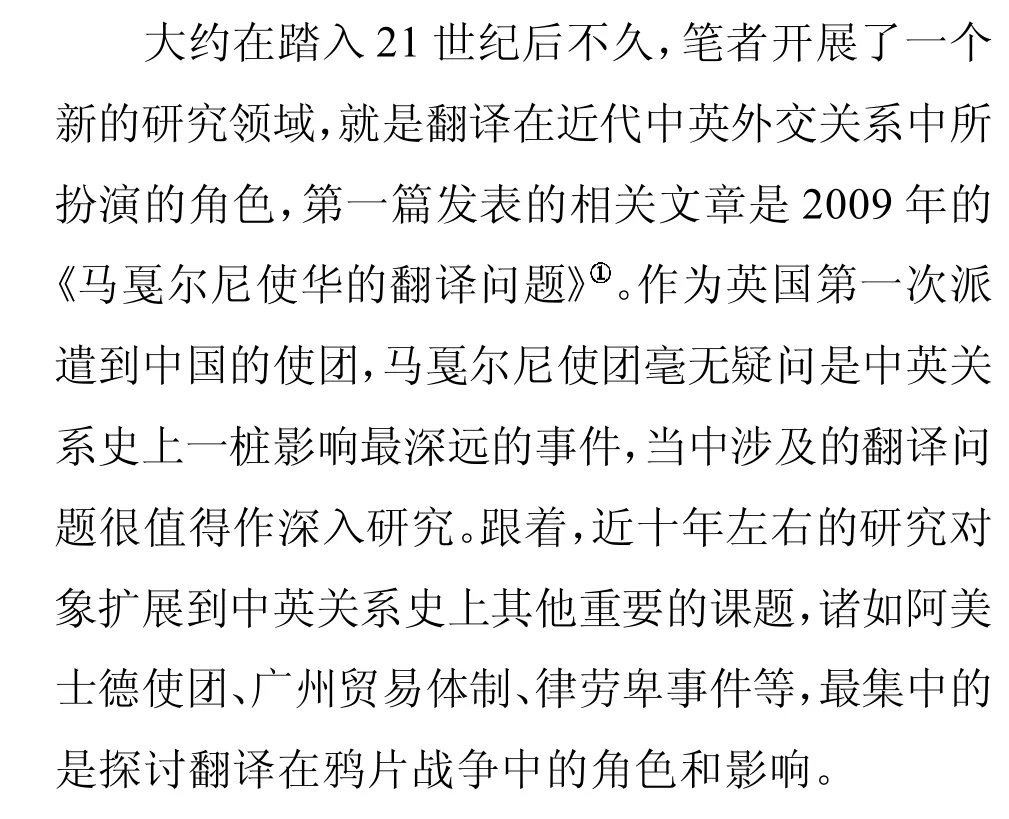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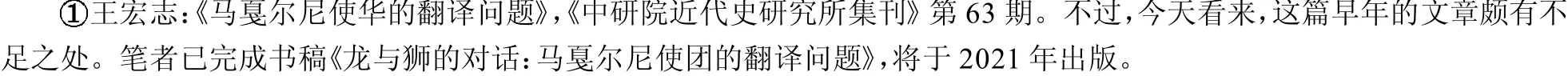
在中英交往過程中出現的重大歷史事件里,譯者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的行為實際上有可能左右歷史的進程,值得深入研究。筆者在研習譯者在這些歷史事件中的活動和位置時,嘗試找出一個貫穿18—19 世紀、長期有力地影響著譯者的文化元素或現象:天朝思想。
毫無疑問,天朝思想本身是一個十分復雜的課題,不可能在這里作深入討論。如果用最簡單的說法,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對待外族外國的一種主流態度和論說,或者更具體一點,中國傳統文化中把外族和外國人看成是文化水平低下,甚至沒有開化的蠻夷。筆者認為,在明末以至清末(最少在1860 年代以前),這樣的文化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中國與西方國家交往其中一個主要元素。筆者正在撰寫的《天朝的譯者:從李葉榮到張德彝》,就是以傳統天朝思想下的蠻夷觀作為整個研究的框架,貫串一系列個別譯者或譯者群,從明末1637 年英國第一次商船隊到達廣州,第一次與華貿易的通事李葉榮開始,至1860—1870 年代在清廷派遣幾次到歐洲的使團出任譯員的張德彝。
要強調的是,這里所謂的“天朝的譯者”,指的是在傳統中國天朝大國思想下,在中英交往過程中活動和運作的譯者,因此不只限于在清廷或為中國官員工作的中國人通事或譯員,實際上可以說幾乎涵蓋了全部在17—19 世紀參與過中英交往過程的譯者,大致可以分為四類:一是剛提過在清廷或為中國官員工作的中國人通事或譯員;二是為英方(東印度公司、英國政府或宗教團體)服務的英國譯者;三是為中國朝廷工作的西方人譯者;四是為西方人聘用提供翻譯服務的中國人譯者。在這段時間里,無論是中國方面還是英國的譯者,不管是中國人還是西方人,盡管服務對象不同,工作環境和待遇很不一樣,工作目標以至性質更是大相徑庭,但其實都無法擺脫這天朝思想的影響和制約,他們的翻譯活動就是在這些制約下進行,而且幾乎無可避免地必須回應這些制約。當然,這不是說他們做著相同或差不多的翻譯工作,又或是以相同或相似的翻譯策略來從事翻譯,剛好相反,正由于不同譯者處于不同的文化和政治位置,他們對于天朝思想的制約會有不同的態度,有些是配合的,有些是抗衡的,有些是調和的,因而產生的回應模式很不一樣,翻譯活動和策略也會有很大的差異。不過,不管是配合也好,抗衡也好,調和也好,這些制約的確存在,也的確發揮很大的作用。如果我們要對明末以來至清中葉以后甚至清末年間參與過中英交往的譯者及其翻譯行為有較準確和全面的理解,便必須對作為翻譯制約力量的天朝思想做深入分析。
同樣地,限于篇幅,我們不可能在這里詳細分析天朝思想對于譯者及其翻譯行為具體的制約是什么。概括而言,天朝思想對譯者及翻譯行為的制約,以及明末以來中西交往的譯者怎樣以一個文化現象作出集體性的回應,大概有好幾種不同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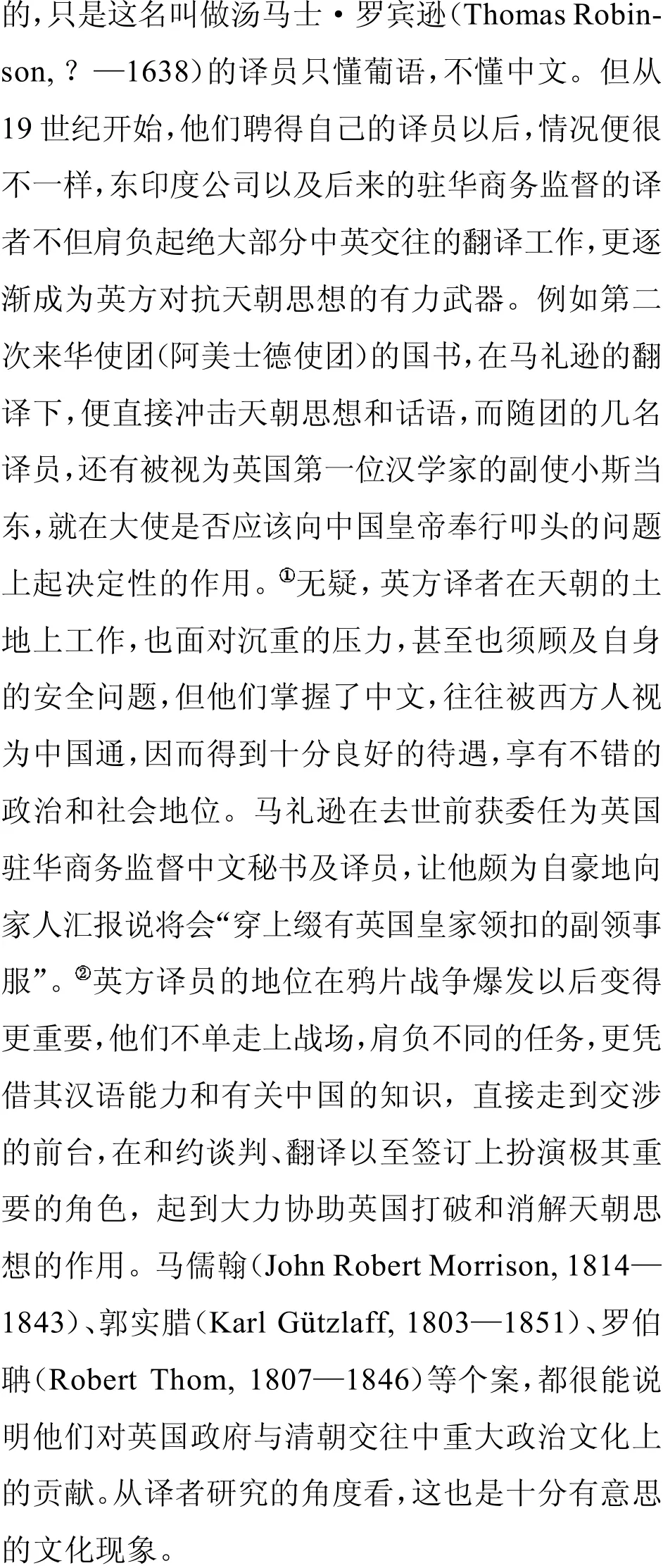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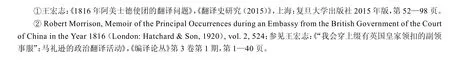
四
其實,天朝思想以外,在漫長的翻譯史中,影響和制約譯者行為的文化元素和問題很多,不少極有意義的課題尚待發掘和處理。以文學翻譯為例,清末民初所翻譯的西方文學作品中,不少具有帝國主義擴張和殖民的思想,放在晚清中國受盡列強侵略的政治背景里,便構成了一個十分獨特的譯入語文化問題。不同的譯者會采用什么方式來回應?他們認識到這些作品中的帝國主義思想嗎?他們刻意回避這些思想嗎?還是視而不見?又或是大刀闊斧地刪除?他們會以“拿來主義”的態度供中國讀者各取所需嗎?怎樣拿來?當頭棒喝嗎?鼓吹模仿嗎?還是若無其事地全盤接受?各種應對方式起什么作用?另外,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以工農兵文藝、階級斗爭為文學主導思想,提出思想改造,摒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學,這對不少從民國時期進入新中國時期的文學作者和翻譯者造成很大的沖擊。在新的文藝和政治思想指導下,尤其經歷過思想改造的過程后,面對嶄新的工作環境和出版條件,他們怎樣調整從前的翻譯活動,從而追上新時代的需要,配合國家的文化政策?不同譯者可能有相近或完全不同的學習過程和應對方法,都清楚地表現在翻譯選材、翻譯策略以至對作品的詮釋、解讀和流播,甚至他們的其他文化活動上。這是很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對不同譯者作個別的個案研究,很能增加我們對個別譯者的理解,但整體地把他們看成是一個文化現象,就更充分地說明新中國的政治文化與翻譯的關系和狀況,更清晰地展現譯者怎樣構成特殊的文化現象。
文學翻譯以外,明末以來來華西方傳教士的一些翻譯活動和行為中,是否也能找出一些重要的文化問題,展示集體的制約和回應?例如不同傳教士在翻譯西方宗教作品,又或是在翻譯中國典籍和文學作品時,怎樣應對傳統中國思想的力量?又或者在19 世紀西方國家在中國的政治活動加劇后,作為主要掌握中文能力的傳教士,又怎樣在世俗與宗教之間作出取舍,為西方國家擔任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譯員,尤其當時中外政治交往涉及不少諸如鴉片販賣等道德問題?這都是以文化問題入手來考察譯者的有趣課題。
總而言之,現有的譯者研究幾乎完全集中于個別的譯者。在現階段譯者研究還很不足的時候,這不但無可厚非,甚至是有必要的。但如果所有譯者研究都只停留在個別譯者傳記式的書寫,不能從文化的層面展現更具普遍性、更深層次的意義,也明顯是不足的。把譯者視為文化現象,對應某些重要文化問題,審視譯者在這些文化問題上的作用和角色,展現一個時代和文化的譯者們翻譯行為的集體性和普遍性,這也許是進一步推展譯者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