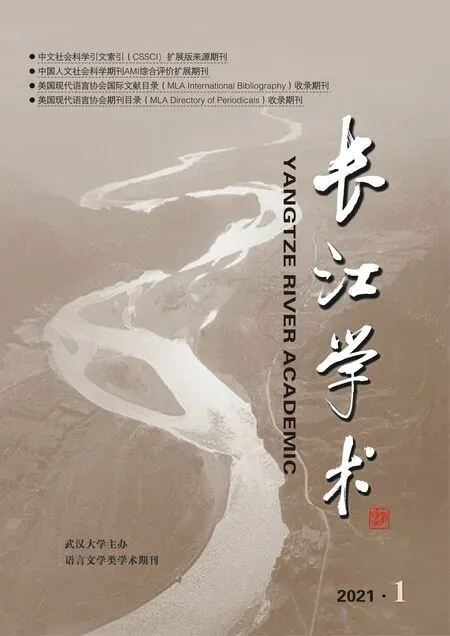中國早期現代文學理論科學性的獨特探索(上)
金永兵
(西藏大學 文學院,西藏 拉薩850000)
我國對文藝理論的科學性追求始于“啟蒙”與“救亡”的雙重壓力,是在現代/落后、東/西、古/今等一系列二元關系中被處置的。與其說它著眼于中國,不如說它更著眼于中國與“西方”之間的斷裂。當時歷史語境下被指認為代表著民主的“德先生”與代表著科學的“賽先生”在古老而落后的中國嚴重缺失,于是指引二位“先生”進入學術語境成為當時知識階層的重要任務。這一現代性追求的目標是彌合東西方之間的斷裂,“自強”“自主”等價值追求都有著“如西方一樣即可自強”“如西方一樣即可自主”的潛臺詞。“民主”與“科學”這兩種核心價值因此常常溢出各自的概念邊界,呈現出一種在啟蒙意義上的概念融通,并以人文主義的方式與個人及民族主體性的確立聯系在一起。
在當時的語境里,“科學”既是價值觀又是方法論。說它是“價值觀”是因為“科學”在啟蒙年代里象征著理性,而理性本身即意味著對啟蒙主義倡導的主體意識、人性自由等價值的張揚;說它是“方法論”是因為這種對理性的象征關系依然要通過“科學方法”來確立。從這兩者的關系上來看,此時“科學”首先是作為“價值觀”的科學而存在的。這是由于“科學性”主要是意在為主體性確立一個普遍有效的人文主義基礎,從根本上來說,它試圖建構的并不只是一套“求真”的科學體系,而且是一套求“啟蒙”、求“救亡”的人文實踐學說。胡適曾這樣概括五四新文化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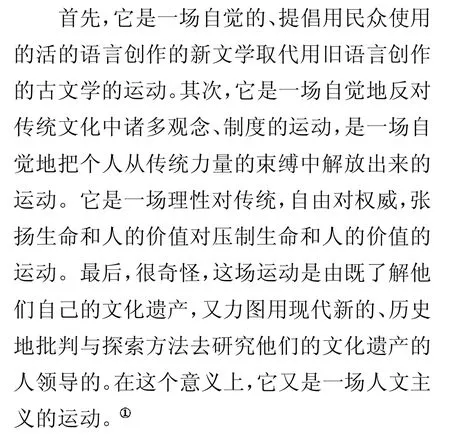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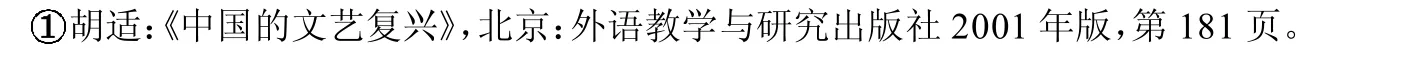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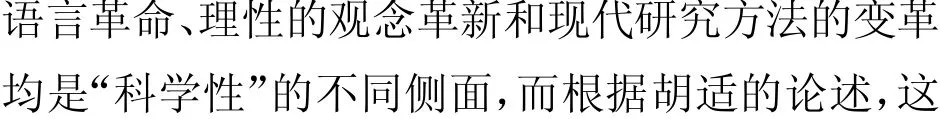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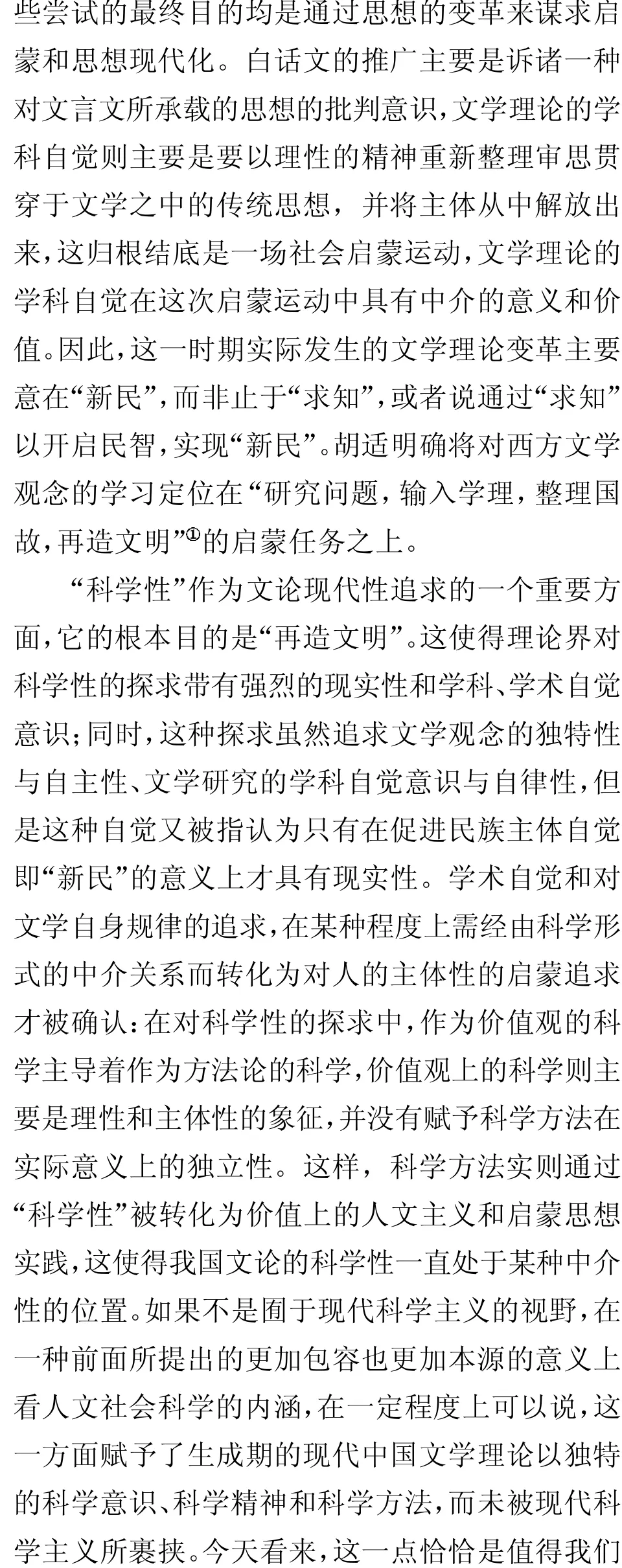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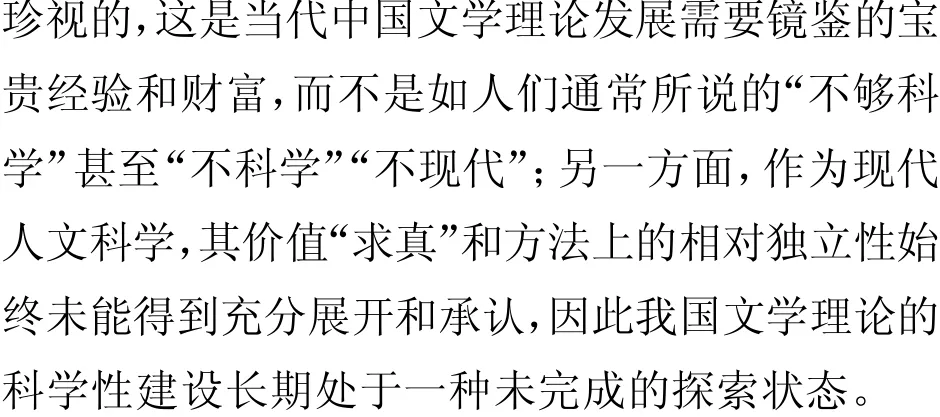
一、語言革命論與文學理論科學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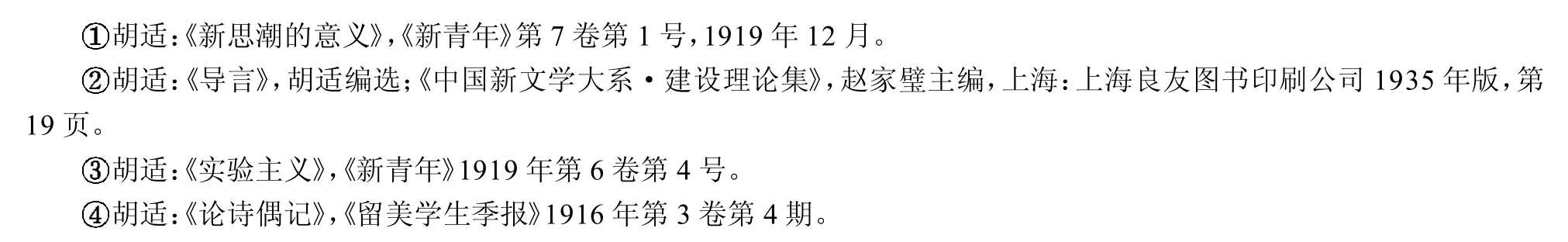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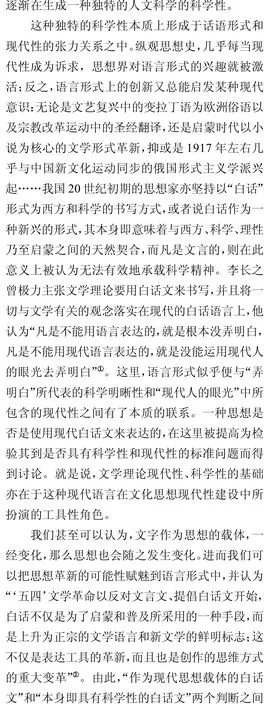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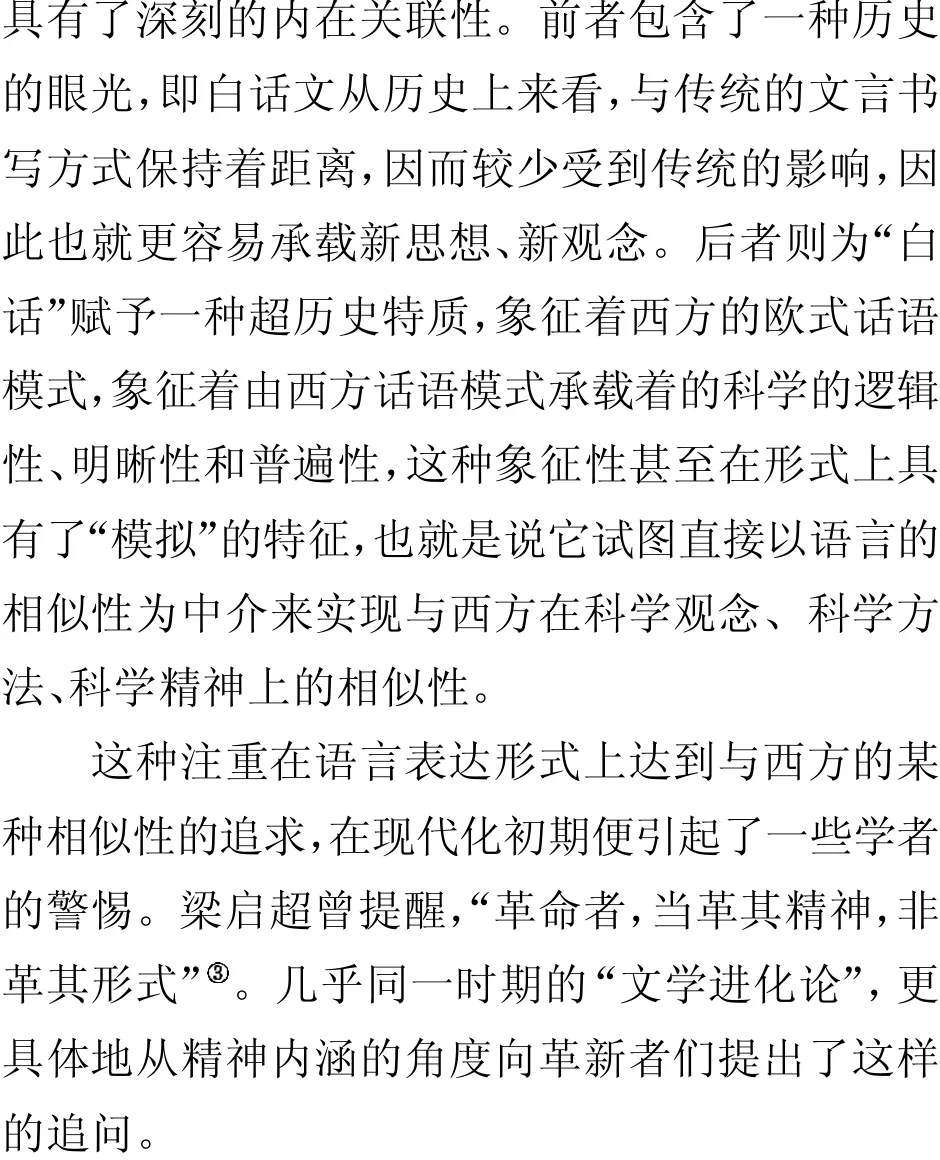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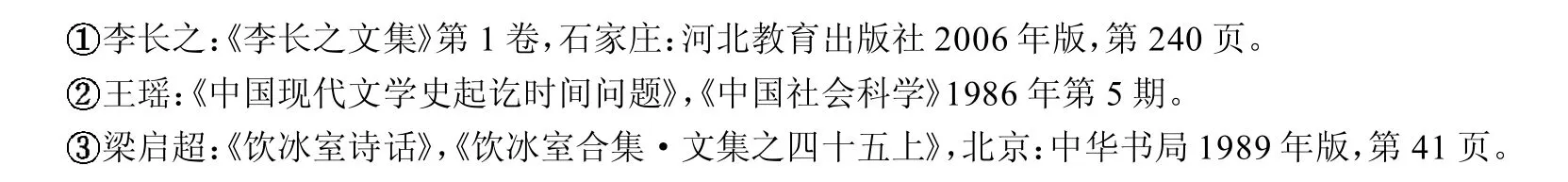
二、文學進化論與文學理論科學性
任何一種有關事物發展變化的理論,只要它與絕對靜止的永恒觀念和“回歸性”的宗教時間意識相對立,堅持一種指向無限未來的、不斷流逝的線性時間,并認為種種事物在這一無限流逝中必將一并向前發展,都可以在廣義上稱為“進化論”。換言之,只要是以現代性的時間觀念為內在法則的目的論,都可以稱作“進化論”。達爾文的進化論并不因其中有關事物向前進化的觀念而著名,因為這是所有現代性理論的共性,就拿黑格爾有關藝術、宗教、哲學三者演進的判斷來說,它也是一種“進化論”的思想,達爾文思想的特性在于強調進化要依循“自然選擇”或“適者生存”的法則,正是這套法則在我國現代化的起始階段與中國思想家們產生了共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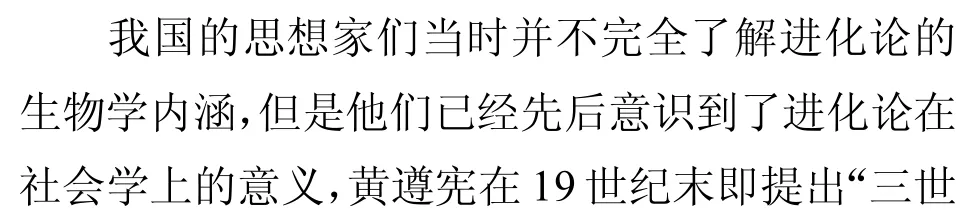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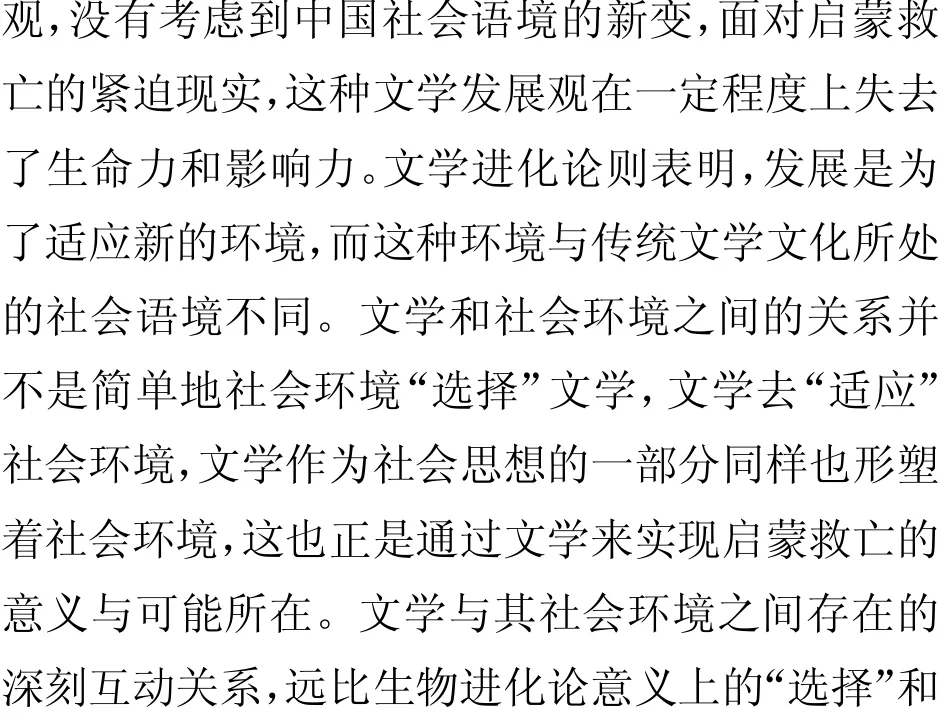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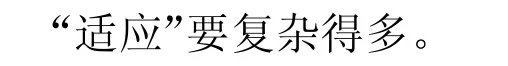
文學進化論重視文學與現實環境的互動關系,重視探尋文學發展規律,重視文學與人的內在關系,這種提問和致思方式無疑受益于自然科學的進化論思想,是借科學理論為人文思想賦權。換句話說,它是從科學角度論證人文價值選擇,從而將科學與人文結合起來,雖然難免生硬、抽象,但歷史表明,這種結合的努力對中國文學理論現代性的生成具有重要意義:人文的價值與力量需要科學的支撐。(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