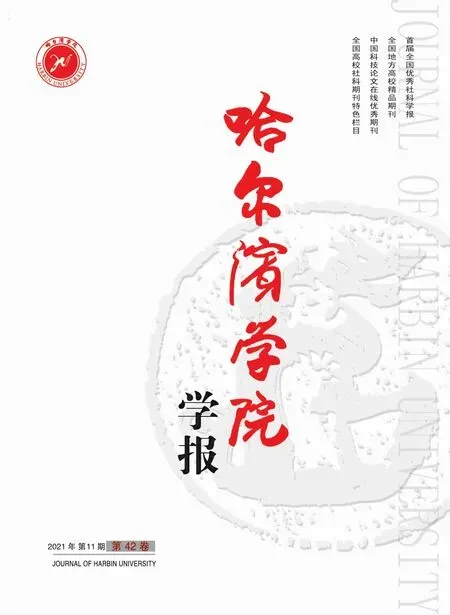雙重敘事進程中圓形人物的建構
——重讀經典小說《外婆的日用家當》
劉 潔
(華中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愛麗絲·沃爾克是當代美國女作家、女權主義者、政論家。她曾投身于民權運動,其很多作品都反映出她對黑人生活的關注。短篇小說《外婆的日用家當》是沃爾克以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為背景書寫的短篇小說,小說中母親Mrs Jones、大女兒Dee(后改名Wangero)和小女兒Maggie三位主人公都是在美國社會成長起來的黑人女性。小說分成兩部分,一是大女兒到家前,母親回憶小時候的大女兒和想象自己在電視上與功成名就的大女兒見面的情景;二是大女兒到家后告訴母親自己改名為Wangero,向母親索要攪乳器蓋子、攪乳棒,與妹妹爭奪百納被不成負氣離開的三個情景。在目前諸多評論中都認為小女兒Maggie深諳黑人縫被子技能,熟悉家庭歷史,應該是百納被的傳承者,而大女兒Dee是思想膚淺和愛慕虛榮的人,筆者認為此觀點有失偏頗。雙重敘事進程理論是申丹教授在發現眾多對于同一文本出現不同解讀的現象后提出的敘述學概念,她認為雙重敘事進程常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本文以雙重敘事進程理論為指導,以小說中爭議最大的大女兒形象為藍本,分析其性格和品質特征,探討顯性進程和隱性進程及兩者的關系,展現大女兒圓形多面的形象。
一、顯性情節與人物形象
整篇小說的敘事者是母親,在第一部分;大女兒在第一部分并未出場,她的形象是由母親的回憶和想象構成。就顯性進程而言,敘事者想象自己在電視節目上與事業成功的大女兒相見時,展現出一個積極進取、令母親感到自豪的大女兒形象。當母親認為是大女兒燒了老房子時,讀者開始領會到敘事者母親的態度,并與敘事者開始站在一邊。讀者對大女兒的形象開始修正,她憎恨貧窮的家庭,憎恨懦弱無知的母親和妹妹。形成這種認識后,提到她好打扮,她要什么東西時都不顧一切地拼命地得到,不達目的不罷休,這些描述也都在先前認識的作用下顯得她愛慕虛榮、自私自利,從側面都折射出她的負面形象。
第二部分介紹了大女兒到家之后與家人發生過三次沖突。第一次沖突是大女兒擅自改名。當母女兩人談論改名時,讀者了解到大女兒Dee的名字是根據姨媽等人的名字來取的,母親甚至可以根據家譜把這個名字的源頭追溯到美國南北戰爭時期,讓讀者感覺大女兒改名的行為是忘祖背宗。第二次沖突是大女兒向家里索要攪乳器蓋子和攪乳棒。大女兒詢問它們的歷史并要求拿走來做裝飾品,而小女兒Maggie清晰地記得攪乳棒出自誰手,相比之下,大女兒膚淺自私的形象被進一步加深。第三次沖突是大女兒跟小女兒爭百納被,這也是故事的高潮部分。母親當初在大女兒上學時要把家里的兩條百納被送給她,但大女兒卻認為被子太土氣而拒絕接受。而小女兒會縫被子,熟悉黑人家族的傳統技能,當姐姐與她爭百納被時懂事的她讓媽媽把百納被給姐姐,并說自己不用被子也能記得外婆,展現出一個懂得謙讓、熟悉縫紉技巧、勤勞本分的黑人女性形象。兩者比較,讀者更堅定了對敘事者母親的認同——小女兒應該是百納被的傳承者。
總之,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三個沖突,加劇了大女兒的負面形象,尤其是最后母親沒有把百納被給她這個選擇,更加堅定讀者對大女兒的認識,她是一個不尊重家人、自私自利、愛慕虛榮的人。
二、細節碎片與隱性進程下的人物形象
在意義的海洋里,顯性情節猶如表面的洋流,隱性進程猶如海底不同深度涌動著的或逆或順的暗流。申丹教授認為:“敘事的隱性進程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和間接性,往往在很大程度上由一些看上去瑣碎離題的細節組成。”因此,為解決大女兒真正形象的問題,本文將從文本細讀入手,發現細節碎片,解讀細節碎片,進而發掘與顯性情節雙軌并行的隱性進程。通過整理被顯性情節忽略的一些文本細節,可以看出一個不一樣的大女兒形象,她其實是一個時尚美麗、綽約多姿而且勇敢、不畏困難的黑人女孩。
大女兒回家后的第一次沖突是有關她改名的部分。通過查閱資料,發現Wangero原來是一個非洲黑人的名字。在Dee看來,改名為Wangero才是尊重祖先、牢記祖先的行為,這是符合黑人民權運動要求的。但對于缺乏認識的母親和妹妹,Dee覺得向她們解釋也是徒勞,因而并沒有向不知情的敘事者講述出來。
第二次沖突是向母親索要攪乳器蓋子和攪乳棒。Dee認為它們可以作為藝術品來展示,這說明Dee具有相當的審美能力,能夠認識到這些東西的藝術價值。結合隱性進程對大女兒改名行為進行理解,其具有為黑人爭取合理權利的意識,大女兒其實是一名具有政治意識和藝術審美能力的新時代黑人女性。
第三次沖突是與妹妹爭奪百納被。Dee認識到百納被是無價之寶,她期望通過百納被向眾人展示黑人的智慧,以及團結和家族意識等黑人文化傳統,進而消除白人對于黑人的偏見和誤解。而小女兒和母親卻無法認識到這兩條被子的政治價值。故事的最后,從隱性進程來看,臨行前,大女兒告訴母親這兩條被子的真正價值,在隱性進程中大女兒的形象是了解時局、奮發向上的年輕美麗的黑人女性形象。
三、雙重敘事進程的關系
通過發掘隱性進程,讀者會發現故事中的人物由扁平人物變成了圓形人物,進而發現小說厚重的蘊意。從隱性進程中,看到作品建構的另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同一個文本表達出不同的意義,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當作品中存在明暗相映的兩個敘事進程時,我們還需要關注這一明一暗的兩股敘事流之間的關系。”[3]受此啟發,筆者將進一步探討小說里這兩條一明一暗、雙軌并行的敘事進程之間的關系。
顯性情節暗藏玄機,隱含作者將小說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大女兒并未出場,讀者只能單從敘事者的講述去了解大女兒的形象特征。第二部分在大女兒出場之后,雖然有更多的文本細節發現大女兒另一面的人物形象,但顯性情節依然是主導地位。敘事者母親是一位世代生長在美國、深受白人思想影響的美國黑人,他從骨子里認為黑人是下等公民,黑人的形象不可能像白人一樣擁有光鮮亮麗的外貌,不可能跟白人一樣妙語連珠、自信幽默,甚至不敢去直視一位陌生白人。在這樣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下,敘事者母親代表了白人的思想認識。因此,她口中的大女兒同樣也是一個負面形象。大女兒的形象被敘事者講述出來的寫作手法仿佛模擬了黑人形象一直以來都是由白人來講述的模式。在白人的講述中,黑人一直以來都是愚昧無知的“野蠻人”。她認為大女兒好打扮、擅自改名等行為都是不對的,而認為小女兒樸實無華、尊重祖先,應該成為家中百納被的傳承者。
但是,隱性進程進一步補充了顯性情節中未能言盡的豐富蘊意。通過發掘大女兒的言行細節,發現了隱性進程下一個有難言之隱的人物形象。大女兒年幼時所表現出愛顯示自己的文化,愛打扮自己,實質是更加顯示出她因過度自卑而迫切需要證明自己的內心;她回家后沒有向母親解釋自己的行為初衷,是因為她認為母親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深受白人階級的愚弄,因而感到辯解也是徒勞;她改名為非洲名字Wangero實質上是想改變自己受壓迫、被他人書寫的命運;她爭奪日用家當將其展示出來,實質上是想將黑人的智慧和創造力展示出來;她離開前對妹妹說的最后一句話顯示出她對于時局的認識,體現了她期望黑人同胞一起努力推翻白人壓迫的先進思想。
小說中的顯性進程與隱性進程是相互補充、相互照應的關系。如果僅關注顯性進程,大女兒就是負面的形象,以至于她自己的母親都不愿把百納被交給她來傳承,而百納被的傳承應該由深諳縫被子技能,熟悉家族歷史的人將其用于日常生活中來繼承。但如果能洞察到文本暗藏的隱性進程,讀者就會發現大女兒也是具備百納被繼承品質的,她能認識到百納被所代表的政治意義,了解時局,致力于黑人民權運動,應該是黑人文化政治上的繼承者。這兩股敘事進程各行其道,并行不悖,共同抵達一個主題——小女兒應該是黑人文化的歷史繼承者,大女兒應該是黑人文化的政治繼承者,黑人優秀的傳統文化應該由整個家族成員一起齊心協力,共同繼承發展。
小說的題目“Everyday Use”在小說最后的高潮部分,即與妹妹爭被子這一沖突中出現。讀者通過發現雙重敘事進程,題目的寓意便更加厚重、更加具有語義密度。從顯性情節來看,這個題目暗示著作者的態度,即百納被的價值在于放在日常生活中來傳承,所以應該給熟悉家族歷史、深諳縫被子技能的小女兒。從隱性進程來看,這個題目“日用家當”喻意厚重——黑人的日用家當就是黑人的政治歷史文化遺產,它們凸顯了黑人富有創造力的智慧結晶,有力地批判了白人的偏見。
總之,這部短篇小說蘊含著似波濤翻涌般的雙重敘事運動——顯性進程聚焦于“百納被”的傳承問題,大女兒是一個憎恨貧窮的家庭、愛慕虛榮、自私膚淺的女性;而在隱性進程中,讀者發現長大后大女兒回來探望母親和妹妹,期望將家里的一些日用家當帶走向人展示出來并不是愛慕虛榮的表現,而是認識到家中日用家當的政治意義,因而是她積極投身黑人民權運動洪流之中的表現。因此,這篇小說中隱性進程里大女兒的人物形象與顯性進程中的形象是相互補充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