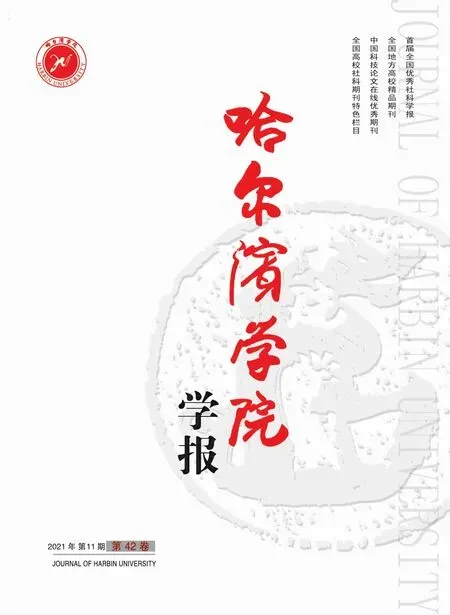《達洛衛夫人》中的“醫療烏托邦”書寫
徐 晗,夏忠玉
(云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弗吉尼亞·伍爾夫是20世紀享譽英國文壇的女作家,《達洛衛夫人》是其1925年創作的長篇意識流小說。對于《達洛衛夫人》的研究,學者們多從文本中意識流手法、女性主義、兩性共存意識、心理敘述等方面入手,而對于通過分析作品中人物經歷分析現代人對烏托邦的渴求卻鮮有提及。本文以《達洛衛夫人》中的塞普蒂默斯為研究對象,從塞普蒂默斯的醫療經歷入手,挖掘那個時代的人們對于“醫療烏托邦”的向往,以及出現這種社會現象的淵源。
一、烏托邦與“醫療烏托邦”
烏托邦文學的源頭可追溯到人類早期出現的神話,在古希臘古羅馬時代的戲劇作品中也有呈現,我國東晉詩人陶淵明也曾描述過一個烏托邦社會,但具體提及“烏托邦”這一概念的是16世紀英國人文主義作家瑪斯·莫爾(Thomas More,1478—1535)。莫爾在其作品《烏托邦》中,借一個敘述者之口描寫了一個充滿暴力和陰謀的社會和一個寧靜、和諧的社會,以此形成對比,用現實中的丑惡現象來凸顯出烏托邦社會的美好和純潔。
“廣義的烏托邦理解一般把‘烏托邦’等同于一切人類理想社會……從功能或實際功效出發,分析烏托邦是用來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和意義。”[1](P3)德國思想家恩斯特·布洛赫從烏托邦的實現路徑出發,強調了烏托邦的功能性,他認為烏托邦表達了對美好生活的希冀和向往,是一個發揮積極意義的概念。
布洛赫和蒂里西都將烏托邦視為人的可能性或者是期望的范疇。名詞“醫療烏托邦”出自布洛赫,他認為,在我們稱之為烏托邦的社會,夢想存在于人類的一切表達形式中,包括非文本的表現形式,比如“醫療烏托邦”“建筑烏托邦”等。但早在莫爾的《烏托邦》中,當他描繪理想社會時,他特別指出,烏托邦人的健康狀況是良好的,醫藥需要的不多,但他們十分重視醫藥知識,重視有關這方面的著述。對于身體的快樂的說法,烏托邦人認為是在于身體的安靜以及和諧,即每個人享有免于疾病侵擾的健康。同樣,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中,航海家描繪的太陽城:“他們那里沒有痛風、手痛病、加答爾、坐骨神經痛等,因為這些疾病是由于濕氣和分泌不良造成的……”[2]在太陽城里,每種疾病都有治療秘方,城里的人通過鍛煉、飲食、草藥、祈禱來治療疾病,無一不靈。可見,在早期的烏托邦社會的描述中,就表現出人們對高超醫療技術的向往和訴求。德國學者諾爾曼認為:“醫學的核心是社會科學。”德國病理學家維爾蕭認為:“政治從廣義上來講就是醫學。”可見,人類社會離不開醫療,作家在創作過程中,通過其經歷和時代背景有可能在作品中呈現這一訴求。
伍爾夫生活的20世紀,各領域都呈現出多元、開放和復雜的特點,人們對于社會生活中的烏托邦態度也趨于復雜。或許是因為19世紀的人們對于烏托邦實踐的失敗,使20世紀的人們不再熱衷烏托邦,一些思想家和文學寫作中都呈現出對烏托邦的批判,反烏托邦寫作的趨勢蔓延開來與反烏托邦思想相互映襯。但在將烏托邦視為政治之惡的20世紀,布洛赫、保羅·蒂利希等思想家在反烏托邦的逆流中重新詮釋了烏托邦的內涵,賦予烏托邦以積極的意義,力圖把烏托邦從罵名中拯救出來。
在布洛赫的強調烏托邦功能性的觀點中,烏托邦具有沖破現實的需要,表達了對美好世界和生活的希望,能有效排除虛無主義,發揮的是一種積極的作用。對于一生飽受精神疾病的折磨的伍爾夫來說,她的病歷和塞普蒂默斯有相似之處,在《達洛衛夫人》中,塞普蒂默斯的醫療悲劇遭遇或許是伍爾夫通過對“醫療烏托邦”書寫來尋求對醫療的期望。
二、作品中“醫療烏托邦”書寫的建構
“在《烏托邦精神》中,布洛赫對烏托邦沖動持一種完全肯定的態度,認為所有的訝異、所有打破黑暗瞬間的希望都指向了救贖和自由王國。”[3](P158)但布洛赫在法西斯興起后意識到,烏托邦也有可能帶來毀滅。伍爾夫在《達洛衛夫人》對于塞普蒂默斯醫療的過程,展現的正是這種對于烏托邦思想態度的矛盾性,霍姆斯大夫的誤診甚至利用病人的弱點,對其進行語言攻擊,使塞普蒂默斯痛苦不堪。但似乎伍爾夫更傾向于積極的一面,因為威廉爵士的出現,給患者帶來了一絲光明,盡管塞普蒂默斯最終還是走向了死亡,但至少威廉爵士在給他治療過程中,正確診斷了他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還給予他關懷。
(一)霍姆斯大夫的誤診和偽善
在伍爾夫構建的“醫療烏托邦”中,霍姆斯大夫是作為反面烏托邦存在的。在他正式出場前,文中曾做過幾次鋪墊,每次他對塞普蒂默斯的診斷都是“他沒有病”,并建議塞普蒂默斯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或者在睡覺前服用溴化劑,他認為塞普蒂默斯的頭痛、失眠和亂夢是神經質。塞普蒂默斯體重只要減輕,僅僅只是半磅,他也要讓塞普蒂默斯的妻子雷西婭在早餐中多加一份燕麥片……這些診斷和治療,在之后威廉爵士的再診時表明,都是錯誤的治療方式。而塞普蒂默斯不僅要承受精神和身體上的不適,還要面對霍姆斯大夫的冷嘲熱諷。“總之,人性——這個鼻孔血紅、面目可憎、殘暴透頂的畜生抓住他了。霍姆斯抓住他了。……塞普蒂默斯在一張明信片背面寫道:一旦你失足走入歧途,人性便會纏住你不放。”霍姆斯大夫并沒有按照塞普蒂默斯的實際病情進行治療,而是抓住他的弱點,對他進行身體和心理上的雙重折磨。
霍姆斯大夫長期混跡于貴族階層,他的名聲并不是由他的醫術得來,而是靠在上流社會層層介紹和推薦。正如威廉爵士提到的,這些普通開業的醫生!他一半時間都是花在糾正他們錯誤上,而且有一些根本無法彌補。霍姆斯大夫是典型的小市民形象,他貪圖錢財,愛慕虛榮,在給塞普蒂默斯治病時拿他家的墻壁和什么爵士的墻壁做比較;在治療病人時總是把精力轉到搜羅古董式的家具上來……他用最溫柔的語氣說著冷冰冰的話,當人們質疑他的醫道時,他冷嘲道,如果他們很有錢的話,可以上哈利街去求醫。對塞普蒂默斯病情的誤診以及對他心靈的摧殘,使塞普蒂默斯的身體和神經全面衰竭,成為一個醫療悲劇。
(二)威廉爵士的再診和人文主義關懷
威廉爵士是伍爾夫建構的“醫療烏托邦”中最理想的醫生,他和霍姆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威廉爵士一看到塞普蒂默斯就斷定是一個極為嚴重的病例,每個癥狀都表明病情嚴重。他在和病人的交談中注意到病人賦予“戰爭”象征性的含義,就建議病人離開親人去鄉下療養院休養;他不會稱病人為“瘋狂”,而是用喪失平衡感來代替。威廉爵士有著專業的知識,其地位是因為他的能力得來的,他熱愛這一行,并努力工作:“當病人走進你的診所……那醫生就得運用平穩的手段:命令病人臥床休息,獨自靜養,安靜和休息;休息期間不會見朋友,不看書,不看通信……”威廉爵士醫治時的專業和霍姆斯大夫的拙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除此之外,威廉爵士具有人文主義關懷精神。他曾駕車六十英里,去鄉間給窮人出診,只恰如其分的收取病人能支付得起的診費。威廉爵士不僅醫術高明而富有同情心,善于洞察人心。“平穩,神圣的平穩,乃是威廉爵士的女神。”威廉爵士在診斷過程中,把平穩作為他的宗旨。他曾說平穩的姐妹就是感化,對于病人應去感化,而不是讓他屈服。在這值得一提的一個人物雷西婭,她也是造成塞普蒂默斯醫療悲劇的重要人物,她一直逃避問題,自我麻痹,當霍姆斯說她丈夫沒病時,她感到寬慰,“多么善良、多么好心的人啊!”當威廉爵士診斷了病情并給出醫療方案時,她選擇逃避,覺得他們被醫生拋棄。正如在威廉爵士心中的雷西婭形象一樣,她不過是披著合情合理的偽裝,潛伏在愛情、職責和自我犧牲的冠冕堂皇的名稱之下,在很多時候,她不會露出真面目。她只考慮自身的利益,而不顧丈夫的健康,體現了病人家屬的自私和愚昧。
塞普蒂默斯的醫療悲劇,不僅涉及到醫療本身的誤診,還有作為大夫本身的霍姆斯的偽善,再者就是雷西婭的自私。威廉爵士用他精湛的醫術和善于洞察人心的能力,還有他的人文主義關懷精神,把霍姆斯和雷西婭照得無處遁形。這個在人性的黑暗面下造成的悲劇,帶來的是塞普蒂默斯的自殺和毀滅,但威廉爵士的出現也表明了在作者建構的“醫療烏托邦”中,還是寄予了希望和積極的意義。
三、“醫療烏托邦”書寫建構的淵源
(一)社會根源
牛紅英在《西方烏托邦文學研究》第七章中提到:“20世紀被普遍解讀為烏托邦已死的時代。”烏托邦文學在19世紀中葉達到高潮,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盛轉衰。此時,西方資本主義開始向壟斷帝國主義過渡,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階級矛盾日益突出,宗主國和殖民地的關系日益惡化,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席卷全球,19世紀建構的烏托邦世界已經幻滅,而此時的英國已經走向了衰敗。
在世界大戰爆發前夕,英國面臨國內的自由民主即將解體的危險,政府已經沒有能力控制緊張的局面。在達成參戰的共識后,接下來的年歲里,從心理和道德上給英國人的記憶和人生觀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影響了一代文學作品,塑造了此后20年英國人對于外來戰爭威脅的反應。盡管當時反戰宣傳者統計了觸目驚心的數據,在帕森達勒的戰爭中,共有75萬人犧牲,250萬人受傷,但很少有人意識到,戰爭給英國的工業和社會領域帶來了極大的變化,它使國家權力高度集中,集中控制權高度膨脹。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場造成大規模生命損失的戰爭,促使國內對生命更加重視,主要表現為改善醫療環境、關注兒童和老人、重視哺乳期母親,以及像建立醫學研究學會那樣的醫療創新。到了20世紀20年代,似乎和平時代已經到來,一切恢復了平靜,之前的集中主義機制像是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英國政府甚至為了表明其人道主義面孔,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動。但人們很快注意到,這一切不過是假象,根本無法回到戰前的經濟和社會狀況,當時的首相勞合·喬治只是一個軀殼,他沒有自己的政黨,其私人生活奢侈、浪費,無法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愛戴。其后的暴力血腥執政和欺騙煤礦工人,引發了大罷工,這一系列活動對英國社會造成了巨大的沖擊。而這一切追根溯源都源自于戰爭帶來的后遺癥。
伍爾夫塑造塞普蒂默斯的醫療事故時,是與克拉麗莎的宴會一起進行的,當宴會達到高潮時,塞普蒂默斯走向了死亡。塞普蒂默斯是戰爭的受害者,是戰爭這部絞肉機中的小小縮影,當英國上層社會的貴族享受著五光十色的宴會時,那些被戰爭殘害的人只是他們茶余飯后的談資而已。盡管戰后的英國開始重視人的生命,改善醫療環境,但霍姆斯大夫這樣的醫生仍然存在,他正如當時的英國政府一樣,外表披著人道主義面具,其實他偽善、自私,善于抓住人性的弱點來滿足自己的私欲。在這動蕩不安的時代背景下,伍爾夫塑造了威廉爵士的形象以諷刺那些弄虛作假的醫生,同時從另一方面表現出其對于醫療方面的理想化構想。
(二)個人經歷
英國著名作家伍爾夫幼年時,就失去了母親。伍爾夫說“她的死”“是可能發生的災難中最沉重的”。[4](P44)在她的傳記中,她認為母親的去世,只不過是一次摧毀性的喪親,根本沒有達到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但是,幼小的伍爾夫失去了母親的庇護,才使得同父異母的哥哥喬治有機可乘。姐姐瓦奈薩和伍爾夫對于喬治的暴行選擇了長期沉默,因為她們所受的教育就是保持一種無知的純潔,而不是用行動去反抗暴行。這是伍爾夫體內毒瘤的源頭,她深知,毒瘤會再次復發,甚至比以往都可怕。這心智毒瘤以一種精神上的腐壞在她13歲時襲擊了她,在她的余生里,它一直就在某個地方不停活動著,永遠懸而未決。這讓她的心智結出一種傷疤,在一定程度上愈合并掩飾她持久的傷口。在后來的歲月中,伍爾夫一直被所謂的“躁狂”所折磨。
在《達洛衛夫人》中,威廉爵士給塞普蒂默斯診斷時,曾建議他到鄉下療養院休養,并遠離和他親近的人。在《伍爾夫傳》中有提到,1910年伍爾夫在特威肯哈姆住到8月份,然后去了康爾沃的鄉間,這是她最喜歡的,對她的健康很有益處。另外,威廉爵士對于“瘋病”用“失衡感”來替換,在傳記中也有提及,瓦奈薩清楚伍爾夫的糟糕處境,她在對生病的伍爾夫進行描述時是用了“病人”而避免用“發瘋”這個令人恐懼的詞。在創作《達洛衛夫人》期間,伍爾夫遭受了一次短暫但猛烈的精神震顫,但這件事對她沒有產生有害的影響,因為那時她正在寫塞普蒂默斯的瘋癲。13歲種下的精神毒瘤,使伍爾夫一生都在焦灼不安中度過,因為她不知道這個魔鬼什么時候會跳出來抓住她。正如塞普蒂默斯被霍姆斯大夫折磨時所說的那樣:一旦你失足走入歧途,人性便會抓住你不放。威廉爵士被賦予了伍爾夫身邊美好人的品質。在寫完塞普蒂默斯的瘋癲之后,伍爾夫再也沒有提到過《達洛衛夫人》的進展。而后,伍爾夫決定搬家,從里士滿搬到倫敦,她又恢復了,對丈夫充滿愧疚,覺得欠了他很多。到此,我們能感受到伍爾夫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在作品中她塑造了威廉爵士精湛的醫療者形象,也是她的希冀,她覺得自己也會和塞普蒂默斯一樣幸運,或者更幸運。
伍爾夫從13歲起就和她的精神疾病作斗爭,或者說更早,因為其父有躁郁癥,有遺傳的可能性。從開始發現有聲音在和自己說話時的“死亡療法”,到后來的傷口結痂又復發,她這一生都在和精神疾病做斗爭,盡管有丈夫和瓦奈薩的照顧和陪伴,但最終還是被毒瘤吞噬。在這個過程中,伍爾夫對生活抱有希望,對文學異常熱愛,在忍受疾病折磨的同時堅持創作,到后來和丈夫的相濡以沫以及對她無微不至的關懷家人和醫生等,都是她與疾病斗爭過程中的希望,這也表現出伍爾夫頑強的生命力。對《達洛衛夫人》中醫療烏托邦的建構,也是來自于伍爾夫自己的經歷,盡管在她那個時代,英國社會充滿了政黨之爭、戰爭的騷亂等,醫療設施的完善也只是戰后的附屬品,但伍爾夫仍構建了一個醫療的烏托邦,對未來寄予了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