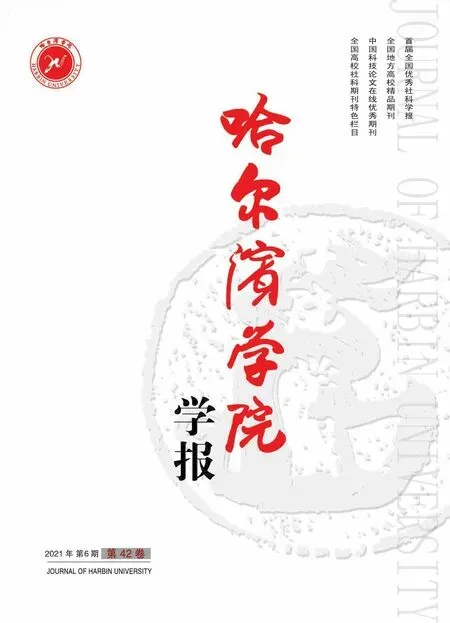鮑勃·迪倫詩中的黑人形象
何轉紅
(廣西民族大學 外國語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6)
黑人形象是美國文學討論的焦點之一,隨著社會的變革,美國文學作品中的黑人形象經歷了一系列嬗變:從被奴役、被壓迫的無奈的逆來順受者,到有獨立自主意識的覺醒者,再到反對種族隔離與歧視、積極爭取民主權利的社會運動參與者。這些改變得益于黑人的抗爭和美國文壇為了扭轉黑人形象和命運發出的聲音。其中,美國歌手詩人鮑勃·迪倫用詩歌的方式展現了當時社會中黑人的形象,推動了民權運動浪潮,為社會變革帶來了可能性。
一、迪倫筆下的黑人形象
《只是棋局里的一枚卒子》《埃米特·希爾之死》和《海蒂·卡羅爾孤獨地死去》是迪倫為數不多的為黑人而作的作品。三首詩均源自真實的社會事件,反映了美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黑人的境遇。
1.麥迪加·埃文斯:“國王”般的民權斗士
麥迪加·埃文斯是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密西西比州的土地秘書,知名的非裔民權人士,長期受到恐怖威脅,于1963年6月12日被刺殺身亡,兇手逃脫定罪,直到幾十年后新證據的發現兇手才被審判,于1994年伏法。《只是棋局里的一枚卒子》是針對黑人麥迪加遇害一事寫的抗議詩。
詩歌第一節描述了一起看似普通的兇殺案:“灌木叢后方射出的一顆子彈”“一把槍柄”預示了不為人知的陰謀;“一根手指”“兩只眼睛”這些描寫兇手的詞作主語,被放在施動者的位置,突出兇手的主動,反映兇手作為施暴者策劃和實施了陰謀。而黑人麥迪加作為受害者形象,被放在賓語位置,“……取了麥迪加·埃文斯的血”“……朝向他的名字扣下扳機”“……瞄準一個男人的腦后”,說明他作為被害人的被動地位,對暗藏的危險一無所知。
詩歌從第二節開始追溯麥迪加生活的社會背景和被害主因:第一,黑人自出生伊始受種族偏見和歧視,白人“比他們命好,生下來就是白皮膚”。第二,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白人“得到的比黑人多”。第三,社會機制固化種族歧視,維護白人利益。學校是神圣的教育機構,但學生從上學起就被灌輸和固化種族偏見;政客代表權威的政府形象和立場,對歧視加以蓋章認定,“假借黑鬼的名義/獲取政客的利益”;軍、警和司法等維護公平和正義的機構在種族平等方面有失偏頗,“法律與他同在/為了保護他的白皮膚/維持他的仇恨”。第四,種族沖突時有發生,白人“被教導如何成群結黨/自背后開槍/緊握拳頭/將人吊死,處以私刑”。可見,麥迪加的死不是偶然的、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整個白人社會精心設計的棋局。他的形象此時逐漸清晰起來,他是一個自出生到死長期遭受歧視和不公待遇的黑人。
全詩共5節,52行,直接描寫麥迪加的詩句僅有3行(第1、44、45行),詩人對他形象的塑造隱身于對白人的描述中。一方面,透過對白人社會及兇手大篇幅的描寫來反襯黑人遭到擠壓、迫害和無生存空間。另一方面,通過褒貶的對比,詩人把麥迪加比作國王,使他“國王”般的光輝形象受到崇拜與褒揚。白人被詩人認為是玩弄人于手掌的人、獲取和維護利益的政客、無名的卒子、“栓了鏈條的狗”、自背后開槍手段殘忍的殺人犯,受到鄙視、唾棄與抗議。透過白人及政客陰險狡詐的、丑陋的形象來反襯黑人麥迪加為自由和平等獻身的英雄氣概。值得注意的是,在讀者未知麥迪加民權斗士身份的認知背景下,這種“國王”般的英雄形象的架構會略顯突兀,畢竟在有限的詩歌空間,從第1行刻畫的普通的受害者跳躍到第45行的英雄形象,中間的過渡所提供的文本信息有限,讀者需要很多的篇外語境信息去補白。
2.埃米特·希爾:被暴虐至死的悲劇少年
《埃米特·希爾之死》是以密西西比州14歲非裔美國少年埃米特·希爾被暴力虐殺的真實故事為基礎創作的第一首抗議詩。希爾的形象是有爭議的,據說,1955年8月,來自芝加哥的希爾在密西西比州訪親時,在雜貨店對著已婚的白人婦女卡洛琳·布萊恩特吹口哨,被認為是在調戲女店員,這成為幾天后他遭到綁架和暴虐的原因。在陪審團看來,兩名白人兇手虐殺希爾是無罪的。而詩人筆下的希爾是一個“可憐的”徹底無過的人,是被施暴者毫無理由虐打至死的,“他們說有正當的理由,但我不記得是什么”,[1](P46)他的經歷是“凄慘的悲劇”。因此,詩人被認為有美化黑人形象之嫌。毋庸置疑的是,詩人對黑人的立場和態度是非常友好的。
詩人在第一節用“年輕的男孩”描述14歲的希爾,突出他青春年少、不諳世事,也似乎在為他作辯護。“踏入”“凄慘的悲劇”蘊含著迪倫對他命運的惋惜。詩歌第二、三節描寫了少年遭受的虐待和痛苦,“拖到谷倉里將他毒打了一頓/他們折磨他,用盡邪惡的招數……/谷倉里聲聲慘叫,街外陣陣大笑”“滾他的身體”“血紅的雨”“把他扔到河里淹沒他痛苦的尖叫”。詩人用對比的手法突出希爾無力反抗的凄慘形象,兩名兇手的行徑類似美國極端種族主義組織三K黨,通過暴力實施私刑和極端手段來宣告種族歧視的勝利,他們“從殺虜中和看著他慢慢死去得到樂趣”,然后在陪審團的無罪宣判后“微笑著走下法院的樓梯”。
希爾的悲劇形象還在于“審判是個玩笑”。在現實中,根據當地陪審團成員挑選規則,由于沒有黑人登記為選民,最終陪審團全部由白人組成。陪審團沒人在意他的基本人權和死亡,即便“高呼審判的抗議聲”不斷,也未能改變他在庭審中得到公正對待的結局。詩歌第四節至第七節把他的悲劇歸根于美國社會嚴重的種族歧視觀念,“希爾的尸體還浮在歧視黑人的南方水土上”,人們對種族偏見的漠視,“雙眼被死人的泥污蒙蔽了,你的心滿是灰……”,以及種族歧視的極端分子,“這類行徑仍存在于幽靈般的三K黨”。
3.海蒂·卡羅爾:社會底層的邊緣人
《海蒂·卡羅爾孤獨地死去》描述了掙扎在社會底層的黑人婦女海蒂·卡羅爾,她具有社會對黑人的傳統印象:第一,生活貧困。海蒂“生了十個小孩”,[2](P49)家庭負擔沉重,養家任務艱巨;她51歲,處于勞動力退化的年齡。現實案件起因是因為在酒店的舞會上白人威廉·贊津格嫌她上酒不夠快,辱罵并打傷了她。第二,身份低微。由于海蒂缺乏良好的生活和社會背景,只能做端盤子、倒垃圾的廚房女傭,從事最不起眼的工作,是社會的邊緣弱者。相反,24歲的兇手出身富裕家庭,親戚在當地政界位居高官。第三,沒有話語權。社會地位低決定了海蒂的人生狀態。生活中,她“從未坐上餐桌的一端/甚至不曾跟用餐的人說話”。而警局里兇手“對自己的行徑的回應是聳肩/咒罵和譏諷,他的舌頭不停叫囂”。第四,無力反抗。海蒂性格溫和,生前她不具備反抗白人種族歧視和階級偏見的能力,她從未對威廉做過任何事,“卻被一記重擊殺害,被一根手杖擊斃”。第五,沒有人權和尊嚴。詩中海蒂被殺“沒有緣由”,兇手“恰好心血來潮,沒有預警”,對人命不以為意。第六,得不到平等、公正的待遇。海蒂無辜死去,威廉被列為一級謀殺嫌犯,被拘幾分鐘后被保釋,最終僅被判六個月監禁作為“嚴厲”的懲罰。白人體制下的司法像兇手威廉一樣,無視黑人平等的權力。
詩中黑人海蒂和白人威廉的形象落差建立在種族歧視環境下的種族心理和發展失衡上。威廉不可一世的心態、舉止和形象建立在優越的經濟基礎和社會背景上。他用“戴鉆戒的手揮轉手杖”殺死了海蒂。鉆戒和手杖代表財富和權勢,“手杖騰空飛越”是種族階層心理力量的抗衡。處于弱勢的海蒂只有恐懼。“將恥辱哲學化且批評所有恐懼的你/把帕子從你的臉上拿開/現在還不是流淚的時候”,這似乎是黑人群體抗爭意識覺醒的宣告,但法庭上的抗爭并沒有迎來平等和勝利。第45行“噢”代表了對人們抗爭過后得到不公正審判結果的驚訝、痛苦和醒悟,“將恥辱哲學化且批評所有恐懼的你/把帕子深深埋進臉里/因為現在該是流淚的時候了。”最后,詩人只能用“lonesome”來形容海蒂的心理狀態和命運。黑人不被社會接納,被隔離、被歧視、孤立無援。作為邊緣底層人,連基本的人權都得不到尊重,死也是孤獨的,生命得不到共鳴。
二、創作因素
詩人拋棄種族偏見和歧視,從白人視角關注黑人問題,為黑人發聲,這與他生活的經歷不無關系。
1.受兒時經歷的影響。迪倫早年被限制的族裔經歷是后來他同情受種族隔離和歧視等不公正待遇的黑人的原因之一。迪倫出生于美國明尼蘇達州的猶太人家庭,當時希賓人歧視外來族裔,猶太家庭被排斥于主流之外。因此,兒時的迪倫經常與窮人的孩子打成一片,嘴里滿是“黑話”;在學校也是過著邊緣的“隱形人”生活。后來迪倫對社會低層人士的同情大概也源于這一生活經歷。20世紀50年代是搖滾發展的時代,此時的迪倫早早接觸了黑人音樂,他常收聽密西西比河沿線的外地電臺播放的布魯斯和搖滾樂,[3](P85)他還演奏過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的音樂。貓王這種打破種族隔離制度的限制,用黑人音樂演繹搖滾歌曲的方式,受到當時包括迪倫在內的許多白人青年的推崇。
2.受自身叛逆性格的影響。迪倫認為自己生在錯誤的家庭,有著錯誤的名字,于是把本名羅伯特·艾倫·齊默曼改為鮑勃·迪倫;他大一輟學到紐約追逐音樂夢想,并對外宣稱自己是孤兒;他喜歡彌爾頓的抗議詩《皮埃蒙特大屠殺》,[4](P41)但不認為自己是抗議歌手,他熱愛反叛歌曲,認為反叛是鮮活的、好的、值得尊敬的;[4](P86)他甚至拒絕出現在諾貝爾頒獎典禮上。這種骨子里的叛逆精神詮釋了身為白人的他為何會脫離主流白人群體,同情支持黑人。
3.受周圍人的影響。伍迪·迦思禮的人生態度,對音樂的態度、創作主題、音樂風格等都深深地啟發著迪倫。在音樂方面,伍迪認為音樂可以記錄社會現實和改革,可以作為階級抗爭的武器,他竭力用音樂消除歧視,倡議平等,鼓勵人們尋找尊嚴和力量。他曾說過:“不論你是什么樣的人、什么樣的膚色,我就是要唱出這些歌讓你對你自己和工作充滿驕傲。”[5](P89)在創作主題方面,伍迪一生創作了許多抗議歌曲,刻畫了底層工人階級的困頓與黑暗,如伍迪創作了抗議國歌《這是你的土地》(This Land is Your Land),而迪倫也創作了在民權運動中廣為流傳的抗議國歌《隨風飄蕩》(Blowing in the Wind)。迪倫認為伍迪的歌唱響了人性,唱出了平等的美國精神。
另外,迪倫關注黑人問題與當時的女友蘇西也有一定關系。蘇西是“紅尿布嬰兒”,父親是共產黨員,也是一名工會領袖。[6](P29)蘇西深受父母政治信仰的影響,對政治運動很積極,高中時曾拿著禁止核彈的請愿書去征集簽名而被留校察看,[6](P48)也曾為結束種族隔離的民權運動募捐,多次參與街頭示威、靜坐、抗議、游行。蘇西和迪倫于1961年相識,1963年分手。在此期間,迪倫變得政治化,為爭取種族平等大會舉辦過一場公益演唱會,[7](P147)并參加了1963年向華盛頓自由進軍的集會。[7](P183)另外,他還寫了不少抗議歌曲,《埃米特·希爾之死》就是當時為美國人權組織“種族平等協會”所作。[8](P52)迪倫在政治或社會事業方面從未表現出太大的興趣,也很少參與政治事件,而蘇西強化了他的社會政治意識。
4.受到社會運動的影響。作為二戰后一代,迪倫的叛逆主要源自美國當時盛大的民權運動和反文化運動的影響。1952年,艾森豪威爾頒布法案宣布消除軍隊中存在的種族隔離。[6](P41)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對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作出裁決,宣布在學校中實行種族隔離行為違憲,終止學校里長久以來的種族隔離制度。然而,南方部分政客依然反對種族融合,動用警衛隊阻止黑人學生入校。因此,民權組織分別在1958年、1959年和1963年發起了“爭取種族平等”游行、“為無種族隔離學校”游行、“為工作和自由:向華盛頓進軍”游行。其中最著名的是1963年的民權游行。馬丁·路德·金在集會上發表了《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彼得、保羅和瑪麗組合(Peter,Paul and Mary)演唱了《隨風飄蕩》。[1](P141)這次集會迫使國會通過了《1964年民權法案》,宣布種族隔離和歧視行為違法。[6](P58)20世紀60至70年代,美國年輕一代掀起了一系列抗議主流社會價值、制度、秩序和文化的反文化運動,如校園民主運動、婦女解放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反戰和平運動、搖滾樂、嬉皮文化和自我主義復興等。迪倫是這場風暴的中心人物之一。
5.受布魯斯音樂的影響。布魯斯起源于非洲,美國南北戰爭后發展成為底層美國黑人奴隸的圣歌、贊美歌、勞動歌曲和頌歌;20世紀20年代,它逐漸在美國興起,與福音歌、爵士鋼琴等黑人音樂被統稱為種族音樂。1942年至1945年美國《公告牌》將此類唱片稱為“黑人區熱歌檢閱”;直到1958年,人們才用“節奏與布魯斯”的稱呼取代了“種族音樂”。[7](P31)迪倫自少年時就對布魯斯音樂產生了興趣,1962年發行的首張唱片就帶有濃厚的鄉村布魯斯色彩,在他后期的音樂中也有跡可循。
綜上所述,童年的經歷、天生叛逆的性格、戀人和師友的影響、社會運動的召喚以及對黑人音樂風格的關注,促使迪倫脫離當時社會白人一貫的種族歧視立場,形成對黑人友好的態度,用同情的視角和態度探討黑人生存問題。
三、結語
較其他作品而言,迪倫筆下的黑人形象看似扁平、不立體、不飽滿,主要表現在:其一,詩人不像其他作家那樣用大量篇幅、正向大肆地敘述黑人事跡,刻畫黑人性格和經歷,塑造和突出黑人形象;而是僅用寥寥數語代入話題,很容易讓人覺得是一筆而過、刻意忽略。其二,黑人不作為詩人寫作的中心卻是重心,三首詩中對黑人的正面描寫均僅有數行。詩歌更像是為抨擊黑人事件背后的社會機制和根源而作。其三,黑人形象隱身于對白人形象的詳細描寫中,透過白人一舉一動來反觀和反襯黑人。然而,從詩歌敘述的內容來看,詩人筆下的黑人和其他作家一樣多樣化,人物描寫有為自由平等而獻身的勇敢的英雄形象,有界限模糊的有爭議的悲劇人物,也有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可憐的邊緣弱者。讀者在有限的詩歌篇幅中,依然能透過對黑人形象外表的描寫深入到內心,感受到他們情緒和心理的變化。從這方面來看,詩人筆下的黑人實際上是飽滿的。因此,無論從創作手法還是表達內容來看,迪倫詩歌中的黑人形象都是別具一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