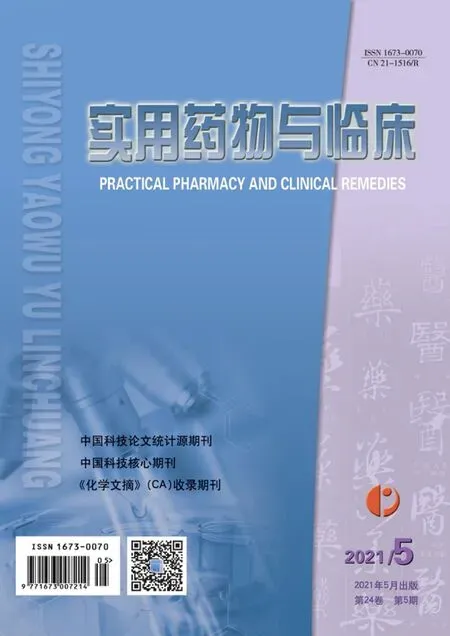英夫利昔單抗治療炎癥性腸病失應答的研究進展
賀小露,周 青,黃曉暉
0 引言
炎癥性腸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主要包括克羅恩病(Crohn′s disease,CD)和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UC)2種疾病類型。英夫利昔單抗(Infliximab,IFX)是首個用于治療IBD的生物制劑,能有效促進腸道黏膜的愈合,減少或避免激素的使用,降低手術風險和住院率。然而,臨床中部分患者出現對藥物的失應答(Loss of Response,LOR),表現為療效欠佳甚至無療效。研究顯示,10%~30%患者對IFX起始治療無應答,稱為“原發性失應答”,起始應答較好而隨著時間推移又失去療效的稱之為“繼發性失應答”,據報道在治療期間出現繼發性失應答的患者高達50%[1]。LOR導致疾病復發、手術率增加、患者經濟負擔加重,是IFX實際應用中的難題。目前LOR發病機制尚不明確,本文主要就LOR的產生機制及應對策略進行綜述。
1 LOR的可能機制
1.1 血清藥物谷濃度 英夫利昔單抗LOR的發生與血清藥物濃度不足相關。Seow等[2]的研究發現,IFX治療的患者血清中,可測得血清谷濃度的患者與無法測得血清谷濃度的患者的臨床緩解率分別為69%和15%,內鏡緩解率分別為76%和28%,結腸切除風險分別為55%和7%,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多項研究表明,無論是誘導期,還是緩解期,更高的IFX血藥濃度與較好的臨床結局密切相關[3]。一項研究分析了728例中到重度UC患者IFX血藥濃度與臨床結局的關系,結果顯示,臨床應答更好的患者的IFX血藥濃度顯著高于未應答的患者,誘導期(8周)血藥濃度大于>41 μg/ml的患者達到臨床應答的可能性低于此血藥濃度患者的2倍,而維持緩解期血藥濃度>3.7 μg/ml可使UC患者獲得滿意的臨床結果。Bortlik等[4]認為,在維持治療前達到3 μg/ml的血藥濃度有助于維持緩解,部分研究則將此臨界值設為2 μg/ml。需要注意的是,“達標治療”的目標不同,所需的血藥濃度也不同,例如黏膜愈合需要更高的血藥濃度來維持。Ungar等[5]根據回顧性分析將6~10 μg/ml設為達到黏膜愈合的濃度窗口。另一項單中心的橫斷面研究發現,使肛周病變型CD患者的瘺管愈合的IFX血藥濃度至少應大于10.1 μg/ml。IFX血藥濃度不足的原因是個體藥代動力學過程存在差異,如男性、高體重、低白蛋白水平等因素均可加速藥物清除,使血藥濃度降低。也有文獻報道,在UC患者用藥1 d后的糞便中檢測出IFX,推測藥物可能經受損黏膜丟失,導致藥物清除過快[6]。
1.2 抗藥抗體 IFX屬于人鼠嵌合的IgG1單克隆抗體,具有較強的免疫原性,可使機體產生抗IFX抗體(Antibodies to infliximab,ATI)。研究發現,不規律地使用IFX的患者中近60%出現ATI,ATI可導致輸液反應以及對IFX的失應答[7]。一方面產生的ATI與英夫利昔單抗結合而抑制英夫利昔單抗的生物活性,另一方面,二者結合形成免疫復合物,加速IFX的自身清除[8]。文獻報道,ATI的形成使IFX的清除增加2.5倍[9]。目前認為,ATI陽性與較低的谷濃度有顯著關系,一項研究發現,77%的患者中IFX濃度在0.00~2.31 μg/ml能檢測到ATI陽性,相反谷濃度在14.98~39.59 μg/ml則測不到ATI[10]。需要注意的是,有一部分ATI的產生是一過性的,稱為短暫性抗藥抗體。短暫性ATI可自行消失且不會導致患者繼發性失應答[11],而持續性ATI與藥物的臨床療效有關,會引起LOR。
1.3 其他因素 疾病本身對IFX的應答是有影響的,孤立性腸道病變及既往無腹部手術史患者更易對IFX產生治療應答,狹窄性病變患者應答率較低[12]。一項納入3 187例CD患者的Meta分析顯示,使用IFX維持治療一年內LOR的發生率為36%,伴有肛周病變、發病年齡小、結腸受累是導致LOR的危險因素[13]。另外,炎癥程度也會影響藥物的應答,Olsen等[14]發現抗腫瘤壞死因子-α(Anti-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水平較高的UC患者達到臨床或內鏡的緩解率更低,原因可能是沒有足夠的藥物去阻斷血清和組織中大量的TNF-α,因此,炎癥程度高以及病情嚴重的患者需要更高的劑量才能達到臨床療效。目前已明確吸煙是CD獨立危險因素之一,相對于吸煙的CD患者,不吸煙者對于生物治療顯示出更好的應答[15]。
2 LOR應對策略
2.1 治療藥物監測與ATI檢測
2.1.1 治療藥物監測 治療藥物監測(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TDM)在探究藥物失應答的機制以及評估IFX的療效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研究顯示,與經驗性調整治療策略相比,以TDM為基礎的IFX的劑量優化更具成本/效益比,同時血藥濃度監測可預測患者臨床結局,與患者生物學、內鏡和組織學緩解密切相關[16]。目前臨床中多為被動的TDM監測,即患者發生失應答后再進行監測,而主動的TDM監測則是對緩解期患者按計劃進行TDM監測。考慮到經濟壓力和遠期的效果,對所有人群進行主動TDM監測目前還存在爭議。也有研究認為,與被動TDM相比,主動TDM可為患者帶來更多的臨床獲益,如TAXIT研究顯示,根據主動TDM監測的結果,調整IFX用量,可提高患者臨床緩解率,或節省治療費用[17]。目前多數的研究顯示,IFX有效的谷濃度為3~7 μg/ml,TAXIT研究對于谷濃度不足3 μg/ml的患者進行了優化治療,經過優化治療,患者的臨床緩解率從65%提高至88%(P=0.02)[4,17]。在有效的谷濃度范圍內,濃度越高臨床結局越好。有文獻建議IFX的谷濃度≥5 μg/ml能獲得較好的臨床結局[18]。So等[19]報道了在兒童IBD患者中,IFX的血藥濃度應>1.58 μg/ml。
2.1.2 ATI檢測 ATI的形成是導致IFX血藥濃度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監測TDM的同時也需監測ATI的水平。ATI可能是一過性的,一般應根據2次的檢查結果進行判斷。此外,抗藥抗體一般于IFX輸注4次后出現,檢測時間不應早于14周[20-21]。對于ATI的檢測值,目前還沒有統一的標準,不同試劑盒的結果有差異。有研究報道了ATI水平為8.0 μg/ml可以作為ATI陽性或陰性的臨界值[22]。
2.1.3 治療策略調整 目前越來越推薦對于IFX失應答的患者采取TDM評估后進行分類處理。IFX谷濃度不足(<3 μg/ml)、ATI陽性,表明患者對IFX產生抵抗,可換用其他的TNF-α抑制劑;無法換用其他TNF-α抑制劑時考慮嘗試強化劑量。IFX谷濃度不足(<3 μg/ml)、ATI陰性,可考慮強化藥物治療(增加IFX劑量、縮短給藥間隔以及聯合免疫抑制劑)。研究顯示,提高IFX劑量至10 mg/kg,或縮短輸液間隔至4周或6周是緩解LOR有效的方法[23]。另外聯用免疫抑制劑如硫唑嘌呤,能通過降低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減輕炎癥負擔等提高IFX的血藥濃度,因為炎癥負擔重和較高水平的CRP均可以加速IFX在體內清除,從而導致其血藥濃度過低[24]。IFX谷濃度足夠(>3 μg/ml)、ATI陽性,提示患者的炎癥過程可能非TNF相關的機制介導,可以考慮換用非TNF-α抑制劑的藥物,如硫唑嘌呤或其他免疫抑制劑、糖皮質激素,或進行外科手術治療。IFX谷濃度足夠(>3 μg/ml)、ATI陰性,提示治療失敗可能與藥物無關,需要尋找其他導致治療效果不佳的原因。
2.1.4 轉換為其他抗TNF-α藥物 IFX谷濃度不足且ATI陽性的患者,轉換為其他抗TNF-α藥物時,可重新獲得臨床應答。GAIN試驗發現,對IFX失應答的中重度CD患者在換用阿達木單抗(首劑160 mg,隨后80 mg/2周)后,在第4周約21%的患者獲得緩解,而使用安慰劑組僅為7%(P<0.001)[25]。隨后,ADHERE試驗(GAIN的延伸試驗)報道了長期應用阿達木單抗96周的緩解率(活動度指數CDAI較基線下降≥100、CDAI<150)分別為39%、26.5%[26]。另一項試驗研究IFX失應答的中重度CD患者換用賽妥珠單抗(400 mg/2周)作為二線治療,在第6周有61%患者獲得臨床應答(CDAI下降>100分),39%患者得到緩解[27]。多項國際多中心研究均已證實,對于抗TNF-α治療失敗的患者,改用其他作用機制的生物制劑如烏司奴單抗(IL-12/IL-23抑制劑)和維多珠單抗(抗α4β7整合素抗體)均有很好的療效[28],但我國目前只有抗TNF-α制劑被批準用于IBD的治療。
2.2 預測LOR的生物標志物 有學者認為,CRP水平能反應IBD患者炎癥的負荷程度,同時高的炎癥負荷能加速TNF-α抑制劑的清除,因此,CRP可能是潛在的預測LOR的生物標志物。Song等[29]發現,基線CRP水平>1 mg/dl與藥物原發性無應答顯著相關(P=0.042),另外在Cox風險比例模型中就多個因素對LOR的影響進行分析,結果發現,CRP水平>1 mg/dl同時CRP較基線下降>70%與1年的LOR顯著相關(P=0.001)。腸道微生物參與IBD的發病及治療是近年來研究的熱點,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腸道微生物多樣性的減少及數量的改變可能與IFX失應答密切相關。有研究對維多珠單抗治療反應不同的IBD患者糞便樣本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維多珠單抗治療反應良好的CD患者在治療前攜帶的腸道微生物多樣性更高,其腸道內的羅斯菌和伯克霍爾德菌明顯高于治療失敗患者[30]。國內研究發現,中國人群IBD患者腸道菌群的改變模式與西方人群相似,并且分析了中國人群CD患者使用IFX前后的糞便樣本,結果發現梭菌目相對較多的患者對IFX反應較好,與單獨使用活動指數CDAI預測IFX療效相比,與CDAI一起可將準確性由58.7%提高至86.5%,因此,作者認為梭菌目可能可以作為預測IFX療效的生物標志物[31]。Nishida等[32]研究了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的比率對UC患者使用IFX的療效預測,結果發現,IFX失應答的患者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的比率顯著高于持續應答的患者,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的比率為4.488可以作為預測IFX藥物失應答的臨界值。可能的機制是中性粒細胞參與IFX細胞膜受體Fc-γ介導的吞噬過程,高的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的比率導致IFX的清除增加,血藥濃度降低。
3 結語
IFX在臨床應用廣泛,但藥物失應答是面臨的巨大挑戰。開展IFX治療藥物監測和ATI的檢測尤為重要,通過優化治療方案尤其是調整谷濃度水平,可使大多數患者重新獲得應答,相較與經驗性的調整用藥劑量或換用二線、三線的抗TNF-α治療藥物更合理,更有利于實現個體化用藥。近年來的研究進展提示,一些指標如CRP、特定的腸道菌群、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的比值可作為潛在的預測IFX療效的生物標志物,但仍需進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