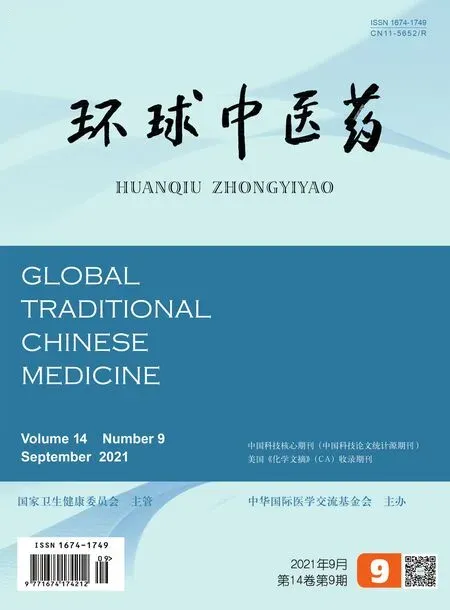從膽郁發熱論治焦慮障礙伴不明原因發熱一例
翟靚帆 鄭瑀 施蕾 許鳳全
1 病例摘要
患者,女,41歲,主因“體溫升高伴緊張焦慮6月余”就診。患者自訴平素思慮重、易緊張不安。患者于2020年7月23日就診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許鳳全門診。刻下癥見:體溫升高,體溫波動在36.1~37.6℃,咳嗽,痰多色白,無惡寒,無汗出。情緒緊張,思慮重,擔心體溫升高,無明顯情緒低落,無自罪自責。頭暈頭痛,入睡困難,胸悶,腹脹,納差,大便溏結不調,每天1~2次,小便正常。定向力、記憶力等尚可,余專科查體未見明顯異常。舌質紅,苔黃偏膩,脈弦滑有力。
2019年底,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全球,患者因2020年1月接觸外省朋友后出現體溫升高,咳嗽等癥狀,懷疑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出現焦慮、恐懼。2020年2月至5月期間反復因低熱就診于北京各三甲醫院呼吸專科門診,多次行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新型冠狀病毒相關抗體、胸部高分辨CT平掃、血常規等均未見明顯異常,并根據相關檢查基本排除肝臟疾病、甲狀腺疾病、結締組織病、感染等導致體溫升高的可能,建議其心理專科就診。患者查焦慮自評量表(self-anxiety scale,SAS)65分,抑郁自評量表(self-depression scale,SDS) 58分,參照CCMD-3診斷標準,診斷為焦慮障礙(中度),予鹽酸帕羅西汀片10 mg,口服2次/日,連續服用7天后體溫未見明顯升高,波動在36.0~37.3℃,因擔心藥物可能出現的不良反應,自行停藥,后出現低熱。
結合患者癥狀、體征及相關檢查結果,西醫診斷為焦慮障礙,中醫診斷為郁病、內傷發熱,辨證為膽郁痰擾證,治以宣熱清膽,方選溫膽湯加減,處方:清半夏9 g、枳實12 g、姜厚樸10 g、紫蘇葉10 g、茯苓12 g、姜竹茹12 g、陳皮12 g、醋香附10 g、郁金10 g、生龍骨30 g、生牡蠣30 g,水煎服,日1劑,早晚分服。并囑患者放松心情,2周后復診。二診(2020年8月10日):患者自述體溫升高癥狀略有緩解,波動在36.0~37.2℃,痰量明顯減少,未訴明顯腹脹,大便成形,每日1次。仍有胸悶,焦慮時加重,時有咳嗽,舌紅苔膩,脈弦。在前方基礎上加用薤白10 g、瓜蔞皮15 g,囑患者繼續放松心情,減少對體溫的關注,2周后復診。三診(2020年9月1日):患者胸悶以及焦慮情緒明顯好轉,對體溫關注減少,最高體溫不超過37℃。咳嗽緩解,痰量減少,二便調,舌紅苔薄白,脈弦。加用黨參20 g、炒白術20 g、茯苓20 g。囑患者放松心情,堅持鍛煉,不適隨診。2020年10月電話隨診,患者發熱癥狀已消失,緊張情緒較7月份明顯緩解。
2 分析與討論
2.1 焦慮障礙發熱屬于中醫內傷發熱范疇
焦慮障礙主要表現為廣泛和持續的焦慮或反復發作的驚恐不安[1],多伴有自覺發熱、頭暈心慌、胸悶氣急、肌肉緊張等軀體癥狀。焦慮障礙患者常以軀體癥狀為主訴就診[2],有研究顯示當患者以軀體癥狀為主訴就診時,診斷出焦慮障礙或抑郁障礙的正確率僅22%[3]。由于焦慮障礙癥狀混雜,易與其他疾病混淆,常常導致誤診誤治,增加了患者負擔,也占用了更多醫療資源[4],隨著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發展,焦慮障礙逐漸受到重視。焦慮障礙所致發熱一般屬于非感染性發熱,多表現為低熱(體溫<38℃)[5],主要與自主神經功能紊亂影響下丘腦體溫調節中樞相關[6]。發熱是臨床常見主訴,作為焦慮障軀體癥狀之一,臨床較為少見,以首發軀體癥狀就診時更不易被識別。
中醫治療表現為體溫升高的焦慮障礙往獲良效,膽郁發熱為其核心病機。焦慮障礙低熱不應參照中醫外感病治療,中醫學認為情志疾病多以郁證概括,郁證引起的發熱屬于內傷發熱范疇。古代醫家對郁證的認識主要分為兩類,氣血津液瘀滯不通而生郁,或情志抑悒而憂郁[7]。七情內傷所致發熱在古籍醫案中多有記載[8],或因驚恐憂思,或因悲哀郁怒。七情過極,氣失疏泄,氣郁化火則為火郁,氣滯血瘀則為血郁,郁久傷脾,蘊濕生痰則為食郁、濕郁、痰郁。朱丹溪謂:“氣血沖和,萬病不生,一有怫郁,諸病生焉。”[9]氣、血、痰、濕、食、火六郁皆可為病,郁而化熱,可以出現發熱癥狀。膽郁也屬郁證之一,孫一奎在《赤水玄珠》中提出臟腑本身自郁,分為心郁、肝郁、脾郁、肺郁、膽郁等證,其云“膽郁者,口苦,身微潮熱往來,惕惕然如人將捕之”。可見七情郁結、氣機不暢可以引起膽郁證[10]。膽為清凈之府,痰氣內阻于膽,郁而化熱,故膽郁證可在臨床表現出頭暈口苦、身體發熱等癥狀。
2.2 膽郁痰擾為焦慮障礙發熱主要病機
氣郁、虛勞、痰飲、瘀血皆可引起內傷發熱,膽郁痰擾乃焦慮障礙發熱的主要病機。膽為奇恒之腑,《靈樞·本輸》中稱之“中精之府”,有藏而不瀉的特點,膽在人體生命活動中占據重要地位,自古有“凡十一臟取決于膽”的說法,認為諸多臟腑雜病均可從膽論治[11]。膽屬少陽,少陽為樞,膽為人體三陰三陽之樞、五臟六腑之界,故內經中稱之為中正之官[12]。中醫認為膽主升發之氣,調節情志,喜柔和惡抑郁,與全身氣機調暢密切相關。《脾胃論》曰:“膽者,少陽春升之氣,春氣升則萬化安。”可見膽氣的條達關系著五臟六腑的有序運化,膽氣順則臟腑順,膽氣逆則臟腑逆[13],膽氣舒暢條達則氣機通調,膽汁藏泄得當則脾胃運化有序。若有情志不遂,氣機郁結,易郁于膽,如《臨癥驗舌法》中云:“膽屬少陽, 其氣尚稚, 膽為甲木, 其質尚嫩, 所以最易被抑, 一抑則其氣悶而不舒矣。”[14]《張氏醫通·郁》亦有 “膽主決斷,氣屬相火,遇七情至而不快,則火郁而不發”的說法,皆表明膽易郁結化火。七情內傷,膽氣郁滯,運化失職,津液聚而生痰。痰與氣結,擾膽腑清凈,郁久化熱,發為內熱。
2.3 溫膽湯清膽化痰治療膽郁發熱
情志抑悒,痰氣膠結,有如《雜病源流犀燭·氣郁》中言:“往往由氣成積,由積成痰,痰甚則氣不得宣而愈郁。”痰是津液在致病因素作用下產生的病理產物,同時也會成為致病因素引起新的病理變化。痰有“有形之痰”和“無形之痰”之分,有形之痰聞之有聲、視之有形,無形之痰停留于臟腑、經絡,隨氣升降流行,形成多種病證,故有“百病多由痰作祟”的說法。膽乃潔凈腑,膽郁痰擾,郁而化熱,發為低熱。患者半年來反復體溫升高,無惡寒等表證征象,屬內傷發熱。患者情緒緊張日久,終致膽氣郁滯,痰濁內擾,郁而化熱,出現體溫升高、咳嗽痰多。低熱和咳嗽在疫情期間加重了患者的焦慮、恐懼情緒,痰氣郁結更甚,導致低熱難以緩解,形成惡性循環。咳嗽痰多、頭暈頭痛、胸悶、納差、腹脹、大便溏結不調乃痰氣互結、痰濕內阻之象。投以溫膽湯,起清熱利膽,化痰理氣之功。溫膽湯來自南宋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氣郁生涎,涎與氣搏,變生諸證”乃溫膽湯所主病機。半夏、陳皮針對痰氣互搏以理氣化痰涎,竹茹清熱化痰,枳實行氣消痰,使痰隨氣下,氣郁隨痰消。佐茯苓健脾化濕以絕痰源。氣結則痰聚,痰壅則氣滯,故加用郁金、香附、紫蘇加強行氣解郁之效。生龍骨、生牡蠣為重鎮安神之要藥,神魂安定則思慮減、心情坦蕩,有助于焦慮情緒緩解。諸藥共起宣熱清膽之功,奏解郁退熱之效,痰濁得化,氣機調暢,情志得以疏泄,膽腑得以安寧。膽郁和痰熱消散,患者低熱減退。后期注重補益脾胃,以防藥力峻猛損傷正氣,加用黨參、炒白術健脾益氣,固本培元。
溫膽湯在臨床使用廣泛,可治療屬于膽郁痰擾、痰氣互結型各類疾病,體現了中醫異病同治的思想。有調查[15]顯示溫膽湯用于治療精神神經系統方面疾病最為多見,用溫膽湯以化精神、神經系統無形之痰往獲得良效。《金匱要略》中言: “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溫膽湯雖名為“溫膽”,實則“清膽”[16],通過清熱化痰,行氣解郁,使痰化熱清,氣機調暢,身熱得退。據相關的現代臨床研究報道[15],溫膽湯具有鎮靜、抗焦慮、放松肌肉作用,調整植物神經功能,從而使大腦興奮和抑制過程協調,改善情感性精神障礙,對于精神煩躁、緊張恐懼、神志異常等癥狀有滿意療效。
3 結語
中國精神健康調查顯示焦慮障礙已經居于中國精神心理疾病首位[17],以軀體癥狀就診的焦慮障礙患者對醫療資源造成了浪費[4],疫情影響下的焦慮障礙更應受到重視[18]。本例焦慮障礙伴不明原因發熱臨床較為少見,應以排除感染等病因為主,針對焦慮障礙治療方是良策。中醫著眼于整體,抓住膽與氣機的關系進行辨治,從膽郁論治焦慮障礙伴隨不明原因發熱在臨床往獲良效[19],溫膽湯是臨床治療焦慮障礙最常用的思路。焦慮障礙首以清膽化痰為要,投以清熱化痰理氣之劑,待膽郁漸散、痰熱漸消增以補脾益腎以絕復辟之患。臨床選用溫膽湯治療情志疾病應用廣泛,效宏力專,醫者需結合臨床之要,相需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