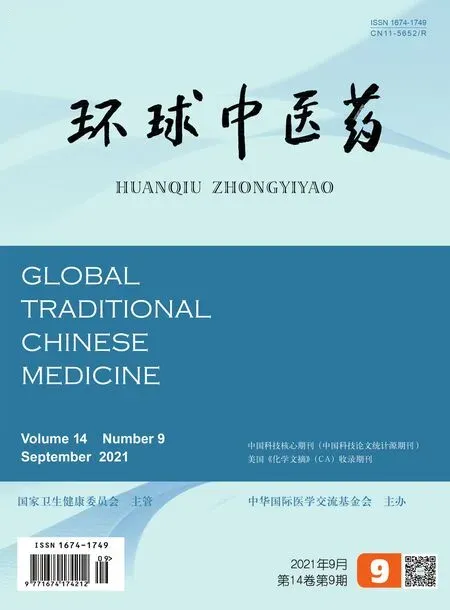谫論《傷寒論》大青龍湯證為風(fēng)寒化熱表證
張楠 許二平
《傷寒論》第38條和第39條論述了大青龍湯證治及其用藥禁忌,前賢今哲對經(jīng)文奧旨及方藥功效闡釋甚豐。傳統(tǒng)認(rèn)識普遍將大青龍湯證之病機(jī)認(rèn)定為“表寒里熱”,然對其“里熱”之具體病位,則長期未有明論。筆者認(rèn)為,《傷寒論》大青龍湯證之“熱”,不在于“里”而在于太陽之“表”,其病機(jī)當(dāng)為“表寒化熱”而非“表寒里熱”。茲谫論如次,以就正于同道。
1 《傷寒論》大青龍湯證病機(jī)的傳統(tǒng)認(rèn)識
《傷寒論》第38條云:“太陽中風(fēng),脈浮緊,發(fā)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fēng)者,不可服之。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第39條云:“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shí),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fā)之。”[1]對于經(jīng)文所論的大青龍湯證之基本病機(jī),學(xué)術(shù)界素以“表寒里熱”立論,并認(rèn)定大青龍湯之功效為外散表寒、內(nèi)清里熱。
《傷寒學(xué)》認(rèn)為:“大青龍湯證為風(fēng)寒束表,衛(wèi)陽被遏,營陰郁滯,內(nèi)有郁熱所致,證屬表寒里熱,表里俱實(shí)”,其病機(jī)為“風(fēng)寒外束,內(nèi)有郁熱”,故“宜表里兩解,重在解表,兼以清熱”[2]。《傷寒論選讀》認(rèn)為,第38條和第39條是“論太陽傷寒兼陽郁內(nèi)熱的證治”,其病機(jī)為“風(fēng)寒外束,兼陽郁內(nèi)熱”,大青龍湯功效為“外散風(fēng)寒,內(nèi)清郁熱”[3]47-48。《傷寒論新釋》指出,第38條之“煩躁”癥狀,既“不能用風(fēng)寒外束,邪郁于表解釋”,也“不能用邪正交爭劇烈解釋”,而從治療上“用麻黃湯加石膏分析”,其“屬于內(nèi)熱所致無疑”;大青龍湯證“屬外感風(fēng)寒而表實(shí),內(nèi)有郁熱而煩躁”,“故用大青龍湯外發(fā)在表之邪,內(nèi)清陽郁之熱”[4]。《傷寒論譯釋》認(rèn)為,大青龍湯證之病機(jī)為“表寒里熱”,大青龍湯具有“發(fā)表清里”功效[5]408。《傷寒論選讀》認(rèn)為,第38條和第39條“論述了太陽傷寒兼里熱的證治”,“本證應(yīng)屬表寒里熱,表里俱實(shí),治宜外散風(fēng)寒,內(nèi)清郁熱”,“大青龍湯在《傷寒論》中(是用于)治療外寒內(nèi)熱證”[6]。《傷寒論導(dǎo)讀》亦指出,第38條是論述“傷寒表實(shí)兼里熱煩躁的證治”,大青龍湯功效為“解表兼清里熱”[7]。
綜上所述,大青龍湯證“外寒里熱”病機(jī)似已取得學(xué)術(shù)界廣泛共識,但對于該證“里熱”之具體病位,各家注釋則均避而未論。
2 《傷寒論》大青龍湯證之“里熱”立論不能成立
筆者認(rèn)為,傳統(tǒng)認(rèn)識將《傷寒論》大青龍湯證之“熱”定位為“里熱”,認(rèn)定大青龍湯功效為“外散表寒,內(nèi)清里熱”,缺乏足夠依據(jù),其論難以成立。
2.1 大青龍湯證之“熱”不在三陽經(jīng)之陽明、少陽
傳統(tǒng)認(rèn)識認(rèn)為大青龍湯證之“熱”屬于“里熱”,就三陽經(jīng)而言,其“里”自非指太陽之“表”,乃是指代少陽或陽明。然從仲景用藥規(guī)律方面仔細(xì)探究,大青龍湯證之“熱”并不位于陽明或少陽。
《傷寒論》陽明病篇治療“煩躁”諸方中,白虎加人參湯含有石膏,其用量為漢制1斤。假若第38條之“煩躁”是由陽明“里熱”所致,則石膏亦當(dāng)使用重劑。大青龍湯中麻黃用量為漢制六兩,約合94 g,“如雞子大”石膏約合56 g[8],石膏劑量低于麻黃。亦有學(xué)者認(rèn)為“如雞子大”石膏約合92 g[9],但其劑量亦只是與麻黃劑量相仿。如此低劑量石膏,實(shí)難既清陽明“里熱”,又抵消麻黃、桂枝、生姜之辛熱對里熱的影響,亦與仲景清泄陽明里熱時(shí)所用劑量不符。因此,認(rèn)為大青龍湯證之“里熱”位于陽明,于理難通。少陽郁熱所致之“煩躁”,《傷寒論》第96條有“心煩”“胸中煩”之謂,仲景予以小柴胡湯治之。大青龍湯中清熱藥只有石膏,并無柴胡、黃芩等疏泄少陽郁熱之品,因此認(rèn)為大青龍湯之“里熱”位于少陽亦無依據(jù)。再者,從第38條和第39條原文分析,仲景以“太陽中風(fēng)”和“傷寒”之語冠于條首,謂脈象為“脈浮緊”和“脈浮緩”,語義所指皆為太陽病范疇,與“陽明病”或”少陽病”無關(guān),且條文中也無少陽病或陽明病之臨床表現(xiàn),故將大青龍湯之“熱”定位于少陽或陽明確為牽強(qiáng)。
或曰,既然大青龍湯沒有清泄陽明或少陽“里熱”之功,那么當(dāng)代臨床上用其治療表寒兼有陽明里熱等證,為何能獲良效?筆者認(rèn)為,當(dāng)代醫(yī)者所用之“大青龍湯”,與《傷寒論》大青龍湯原方藥量配比存在較大差異,石膏用量普遍較大,遠(yuǎn)超麻黃劑量,其清熱作用自非原方可比。有學(xué)者分析當(dāng)代“大青龍湯”臨床驗(yàn)案76例,發(fā)現(xiàn)石膏之平均用量為23~33 g,麻黃之平均用量為4~14 g,石膏與麻黃之比多為6∶1、5∶1、2∶1[10]。察當(dāng)代名老中醫(yī)“大青龍湯”醫(yī)案,石膏用量亦遠(yuǎn)大于麻黃[11]。因此,從藥物劑量配比言,當(dāng)代醫(yī)者所用之“大青龍湯”,已非《傷寒論》之大青龍湯。
2.2 大青龍湯證之“熱”不在三陰經(jīng)之心、肝、肺
太陽風(fēng)寒表證未解又兼有其它證候,傷寒學(xué)界謂之為太陽病兼證[5]14,如桂枝加厚樸杏子湯證為太陽中風(fēng)兼肺氣上逆證、小青龍湯證為太陽傷寒兼水停胃脘證等。相對于太陽風(fēng)寒表證,“肺氣上逆證”和“水停胃脘證”等,亦可稱為“里證”。因此,若大青龍湯證之“熱”位于心、肝、肺,則此“熱”亦可謂之“里熱”。然從《傷寒論》第38條和第39條原文分析,大青龍湯證之“熱”亦不在心、肝、肺。
《傷寒論》第39條明確指出“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fā)之”,說明大青龍湯證與少陰心腎無涉,其“熱”并不在心,其“煩躁”癥狀并非心火所致。肝火擾亂心神亦可導(dǎo)致“煩躁”,但第38條和第39條并無肝火癥狀,況在《傷寒論》中仲景亦不以石膏清泄肝火,故大青龍湯證之“熱”亦不在肝。并且第39條明言以大青龍湯“發(fā)之”,亦說明大青龍湯之作用在于治表而不在于治里。
肺合皮毛,風(fēng)寒襲表時(shí)外邪可以化熱蘊(yùn)肺;肺素蘊(yùn)熱,復(fù)有風(fēng)寒襲表,亦可出現(xiàn)風(fēng)寒表證與肺熱兼夾并存。若大青龍湯證有肺熱存在,則亦可稱之為“里熱”。肺主宣發(fā)肅降,邪熱壅肺當(dāng)見咳嗽、咯痰、喘鳴等,但第38條和第39條并無肺系癥狀,其“發(fā)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shí)”等均屬衛(wèi)表癥狀。因此,大青龍湯證之“熱”亦不在肺。再者,邪熱壅肺出現(xiàn)《傷寒論》第63條和第162條“汗出而喘”時(shí),仲景則出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治之。該方石膏用量半斤,清泄肺熱作用較強(qiáng),自非大青龍湯中“如雞子大”劑量可比。
3 《傷寒論》大青龍湯證之“熱”在太陽之“表”
筆者認(rèn)為,如果《傷寒論》大青龍湯證之“熱”不在三陽經(jīng)的陽明、少陽和三陰經(jīng)的心、肝、肺,則傳統(tǒng)認(rèn)識的“里熱”之說即難成立。既然本證之熱不在三陽經(jīng)的陽明和少陽之“里”,亦不在三陰經(jīng)的心、肝、肺之“里”,則其“熱”只能位于太陽之“表”。
《傷寒論》第48條云:“若發(fā)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郁不得越,當(dāng)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fā)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澀故知也。”[5]425此條言初患太陽病之時(shí),發(fā)汗不徹,汗出太少,致使風(fēng)寒之邪不解,衛(wèi)氣被其郁閉而引發(fā)“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語,是對病人周身不適、似有所苦而難以表述,因而煩躁不安之形象描寫[3]55。“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和“更發(fā)汗則愈”,則強(qiáng)調(diào)了“躁煩”之因在于汗出不徹。由此說明,太陽風(fēng)寒表證若不能得到適度汗解,在某些情況下是可以引發(fā)患者周身不適而出現(xiàn)煩躁的。《傷寒論》第38條“不汗出而煩躁”語,亦說明“煩躁”是由“不汗出”所致。
既然寒邪郁閉肌表可以導(dǎo)致“煩躁”,那么《傷寒論》第35條“頭痛”“身疼”“腰痛”“骨節(jié)疼痛”“無汗”之麻黃湯證,為何未現(xiàn)“煩躁”癥狀?這說明只有身體疼痛并不至于導(dǎo)致病人煩躁,只有在其基礎(chǔ)上再疊加周身異常不適,才能導(dǎo)致病人煩躁不安。結(jié)合第38條和第48條原文精神,病人出現(xiàn)周身異常不適,除與寒邪閉遏有關(guān)外,當(dāng)與衛(wèi)陽郁而化熱之“表熱”有關(guān),此即《素問·調(diào)經(jīng)論篇》“皮膚致密,腠理閉塞,玄府不通,衛(wèi)氣不得泄越,故外熱”[12]之謂。只有衛(wèi)陽化熱,郁于肌表,與寒邪相搏,熱邪外攻而寒邪內(nèi)斂,寒熱錯(cuò)雜糾纏于肌腠,才可能在身體疼痛之基礎(chǔ)上出現(xiàn)肢體憋悶不適、莫可名狀感覺,從而導(dǎo)致病人出現(xiàn)煩躁。魏荔彤[13]在闡釋第38條時(shí)云:“但添一煩,知其非傳里之煩,而仍為表未解之煩也”,指出“煩躁”乃是因于表邪而非里邪,確乃洞中肯綮。驗(yàn)之臨床,確有體質(zhì)壯實(shí)之人罹患風(fēng)寒表證后,寒邪閉塞肌表,衛(wèi)陽郁遏化熱,表寒未解而郁熱已生,從而出現(xiàn)惡寒、發(fā)熱、身體疼痛,欲汗出而不能,周身肌膚肢節(jié)憋悶不適,以致病人心煩不寧,常以速得暢汗為其迫切所求。此時(shí),若病人服藥后果能汗出透徹,確能諸癥消減而“煩躁”頓除。
筆者認(rèn)為,大青龍湯乃麻黃湯倍麻黃用量,減杏仁用量,再加生姜、大棗、石膏而成,方中石膏的主要作用在于清泄太陽表熱。關(guān)于石膏功效,傳統(tǒng)認(rèn)識多強(qiáng)調(diào)其清泄里熱之功而不言其清泄表熱之效,而《別錄》則早有石膏“解肌發(fā)汗”之論,《藥性論》亦有“解肌出毒汗”之謂。張錫純《醫(yī)學(xué)衷中參西錄》云:“石膏之質(zhì),中含硫氧,是以涼而能散,有透表解肌之力,外感有實(shí)熱者,放膽用之,直取金丹”,對石膏辛涼透表之力推崇備至,進(jìn)一步發(fā)揮了《別錄》《藥性論》對石膏解肌清熱功效的論述[14]。孔伯華先生亦認(rèn)為石膏性涼微寒,氣輕能解肌表,宣散外感溫邪之實(shí)熱,使其從毛孔透出[15]。由于石膏體重氣輕,辛涼開腠,用于外感表證而有熱象存在時(shí),主要是取其氣輕和衛(wèi)之性,故在大青龍湯中的用量較小[16]。
4 風(fēng)寒化熱表證應(yīng)確立為獨(dú)立的外感病證型
常見的外感表證以風(fēng)寒與風(fēng)熱最為常見,前者以麻黃湯、桂枝湯為其主方,后者以銀翹散、桑菊飲為其主方。風(fēng)寒化熱表證既非單純之風(fēng)寒表證,亦非單純之風(fēng)熱表證,乃介于兩者之間者,主方為《傷寒論》大青龍湯。若將風(fēng)寒化熱表證作為獨(dú)立的外感病證型,則與風(fēng)寒表證和風(fēng)熱表證構(gòu)成了外感病三證鼎立格局,風(fēng)寒表證、風(fēng)寒化熱表證、風(fēng)熱表證三者序列完整,涇渭分明。
臨床實(shí)際中,感受風(fēng)寒之邪而呈現(xiàn)風(fēng)寒表證者固為多見,但感受風(fēng)寒之后迅速化熱,形成風(fēng)寒之邪未解而表有郁熱之證者,亦非少見。此證之臨床表現(xiàn)多見寒熱錯(cuò)雜,如鼻流清涕與咽喉腫痛并見,咳吐黃痰與惡寒無汗并見等[17]。臨床上也有部分小兒感冒,常見惡寒、發(fā)熱、頭痛、鼻流清涕,但痰液稀稠并見,痰色黃白互見,辨證既非單純風(fēng)寒,也非單純風(fēng)熱,細(xì)辨之下,實(shí)屬寒熱錯(cuò)雜之證。此時(shí)單獨(dú)予以辛涼解熱藥,往往汗出不透,單獨(dú)予以辛溫祛寒藥,往往汗出熱不解,但若采用辛溫與辛涼并舉之法,則能取得滿意療效[18]。從以上臨床實(shí)際情況分析,感受風(fēng)寒之邪后衛(wèi)陽郁閉化熱,從而形成風(fēng)寒化熱表證,確屬客觀存在。
風(fēng)寒化熱表證多由風(fēng)寒表證演變而來,此從《傷寒論》第38條可以得到印證。第38條“脈浮緊,發(fā)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等為寒邪郁遏肌表所致,而“煩躁”癥狀則反映了寒邪化熱,寒熱糾纏于肌表病機(jī)。因“煩躁”是寒熱錯(cuò)雜于肌表導(dǎo)致患者周身異常不適所致,故風(fēng)寒化熱表證除具有第38條和第39條癥狀外,尚應(yīng)具有類似于《傷寒論》第48條“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等癥狀。結(jié)合臨床實(shí)際,此多表現(xiàn)為肌體憋悶煩熱,周身躁擾不適,莫可名狀等。由于風(fēng)寒化熱表證為寒邪與熱邪交互并存,故其臨床表現(xiàn)具有寒熱錯(cuò)雜特征,表現(xiàn)為鼻涕清濁互見,咯痰雖多清稀色白但有時(shí)卻粘稠色黃,雖然惡寒無汗但卻咽紅咽痛等,治宜辛溫解表兼以清泄表熱,可予大青龍湯加蟬蛻、僵蠶、浮萍、牛蒡子等化裁治之,亦可將麻黃湯、桂枝湯等辛溫解表劑與銀翹散、桑菊飲等辛涼解表劑化裁聯(lián)用。
5 結(jié)語
綜上所述,《傷寒論》第38條和39條所述之大青龍湯證當(dāng)屬太陽病風(fēng)寒化熱表證,并非傳統(tǒng)認(rèn)識所認(rèn)定的“表寒里熱”證;其主方大青龍湯為辛溫解表兼清表熱之劑,并非傳統(tǒng)認(rèn)識所認(rèn)定的“外散風(fēng)寒內(nèi)清里熱”之表里雙解劑。風(fēng)寒化熱表證由風(fēng)寒表證演變而來,風(fēng)寒在表而熱已成,表熱雖存而寒未盡,其病機(jī)特點(diǎn)為寒熱錯(cuò)雜,臨床表現(xiàn)為寒熱兼見,治宜辛溫解表與辛涼解表并用。因本證與風(fēng)寒表證和風(fēng)熱表證存在明顯差異,故應(yīng)將其確立為獨(dú)立的外感病證型,以體現(xiàn)外感病常見證型之多樣性和復(fù)雜性。筆者認(rèn)為,進(jìn)一步深化對風(fēng)寒化熱表證之系統(tǒng)研究,對于外感病診療理念的全面確立以及臨床分型施治,具有重要的啟發(fā)作用和指導(dǎo)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