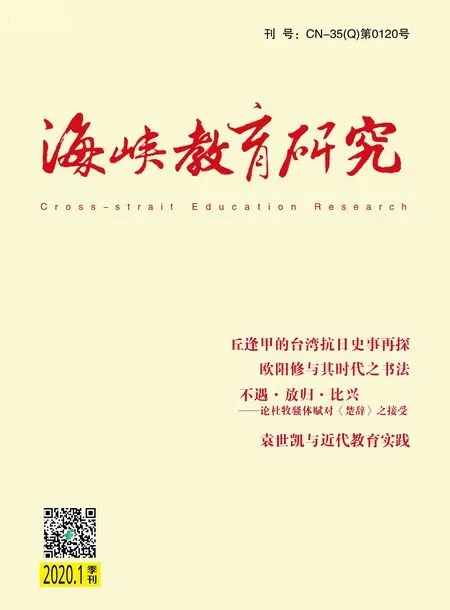今天我們如何讀《論》《孟》
——《讀〈論語〉〈孟子〉法》的啟示
■ 唐東輝

孔子的思想集中體現在《論語》一書,孟子的思想集中體現在《孟子》一書。我們要研究孔孟的思想,應從《論語》《孟子》入手。那么我們該如何閱讀二書呢?朱子所撰的《讀〈論語〉〈孟子〉法》,收集二程(程顥、程頤)論述如何閱讀《論語》《孟子》的九條語錄,對我們閱讀《論語》《孟子》頗有啟示意義。
一、《論》《孟》為本
朱子的《讀〈論語〉〈孟子〉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1]讀書求學的人要把《論語》和《孟子》當作治學的根本。《論語》和《孟子》研究好了,那么六經就可以明白了。
程子之所以說學者要以《論語》《孟子》為本,反映了儒學從漢唐到宋明的新發展。漢唐時期,儒學以經學(以五經為研究文本)的方式呈現與發展。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至東漢光武帝時已立十四家博士。兩漢時期,不僅有今文經學,還有古文經學。東漢末年鄭玄綜羅百家,遍注群經,集古今文經學之大成。唐代的《五經正義》,又集鄭玄以來經學發展之大成,是經學的又一高峰。而宋明時期,儒學以理學(以四書為研究文本)的方式呈現與發展。北宋時期,儒學正從經學向理學過渡,所以程子才如此推崇《論語》《孟子》二書。面對“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面,理學家們以四書為本,發展出了一套足以抗衡佛道的形上之道,如程朱的天理,象山的本心,陽明的良知,奠定了儒家的內圣之學。南宋時,朱子的《四書集注》漸漸取代五經的地位,成為科舉考試的教科書。
然而,對程子所說的《論語》《孟子》既治,六經可不治而明,這句話需要審慎對待。這既是一種夸張的修辭,突出《論語》《孟子》的重要性,也是一種客觀的陳述,表明通過《論語》《孟子》也可以“見道”“明道”。從義理的角度說,《論語》《孟子》(或者說“四書”)與六經寓含著同一的大道,讀六經可以“見道”“明道”,讀《論語》《孟子》也可以“見道”“明道”,所以說《論語》《孟子》既治,六經可不治而明。當然,從知識的角度說,《論語》《孟子》既治,六經也可謂不明,如我們通過讀《論語》《孟子》,知道禮以敬為本,但如果我們不去學習實踐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仍然是不知禮的野人。
二、全本為上
《讀〈論語〉〈孟子〉法》第六條曰:“或問:‘且將《論》《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浹洽耳。’”所謂挑“緊要處看”,其實就是讀選本。只是這個選本的選者是自己而不是別人。可見,不只是現代人,古人也愛看重點,讀選本,挑“緊要處看”。而在程子看來,《論語》《孟子》讀選本、挑“緊要處看”固然是好,但終不如讀全本那樣來得融會貫通。
關于選本的弊端,魯迅早就指出,“選本所顯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眼光愈銳利,見識愈深廣,選本固然愈準確,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殺了作者真相的居多”。[2]這可以細分為兩端,一是所謂的“緊要處”,受到選編者眼光與見識的局限,具有極大的主觀性。選編者眼光越銳利,見識越深廣,挑選出來的選本就越能反映“作者真相”或作品原意;反之,選編者所挑選的部分,則未必就是作品的精華,甚至有遺珠之憾。二是一葉障目,難窺全貌。既然是選本,自然就有未選之處,讀者若以此為據去了解作者或整個作品,難免有失偏頗。如陶淵明其詩,魯迅就指出,不僅有“悠然見南山”之類的“飄飄然”,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又如李清照其人,不僅有“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的兒女柔情,也有“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的鐵骨錚錚。如果選本不能兼顧各種類型,自然容易導致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因此,閱讀《論語》《孟子》,要想融會貫通,還得讀全本。
如果從教材的角度來看,則像《論語》《孟子》這樣的經典,應該屬于王榮生所界定的“定篇”[3]。所謂“定篇”,就是沒有經過任何刪改的完整的經典之作,是要讓一批一批、一代一代的學生徹底理解與領會的作品,是要讓學生通過最權威的解說來學習這些經典作品豐富的文化內涵。《論語》《孟子》作為“定篇”,是每一屆學生都要經過學習而徹底理解與領會的文化經典。
三、熟讀玩味
古人讀書,講求熟讀玩味。《讀〈論語〉〈孟子〉法》第四條曰“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熟讀玩味:熟讀是玩味的前提。熟讀,才能了然于胸。不能熟讀,便不能記憶,離開書本就空空如也,便不能隨時隨地地玩味。“玩味”一詞最妙,玩者,把玩之謂也,像把玩古董一樣細細把玩文字,味者,品味之謂也,像品味茶酒一般細細品味文字。只有熟讀玩味,才能讀出自己獨特的心得體會,才能與作者的心靈相契合。

《讀〈論語〉〈孟子〉法》第五條曰:“程子曰:‘《論》《孟》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我們閱讀《論語》《孟子》,只是去讀原文,意思便自足,若用語言去解說,意思便不足。讀書與吃飯有相通之處。眼前一桌子美味佳肴,如果只是聽別人說如何如何好吃,自己卻不曾動筷子親自去品嘗一番,終究不知好吃在何處;讀書也一樣,前人的解說再妙再精彩,但自己都不曾將原著仔細品讀玩味,終究是隔了一層。書讀百遍,其義自現,只有去讀原文,才能促使我們去思考去玩味,才能讀出自己獨特的心得體會,才能與圣人的心靈相契合,若以語言來解經,通過別人的翻譯和注解來解讀經典,便覺意味不足。當然,這并不是說不能看翻譯和注解,翻譯和注解是我們理解原著的幫手,是通往圣人之意的津梁,但與我們自己閱讀原著相比,這畢竟是第二步的工作,而且,如果只看翻譯和注解而不去閱讀原文,就會缺少自己的閱讀體驗,成了人云亦云,道聽途說。
熟讀玩味的前提是先通曉文義。《讀〈論語〉〈孟子〉法》第二條曰:“程子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在程子看來,閱讀文字,先要通曉文義,然后才去探求深意。所謂“曉其文義”,就是理解文字表面的意思。我們在閱讀中碰到不懂的字詞時,翻查字典以確定其準確的含義,就是做的“曉其文義”的工作。當然,“曉其文義”只是第一步,進一步還要“求其意”,探求文字背后的深意。如《論語·述而》篇說:“子之所慎:齊,戰,疾。”如果不知道“齊”通“齋”,怎能準確理解這句話的文義呢?進一步就是要探究文字背后的深意:為什么孔子對齋戒、戰爭、疾病格外謹慎呢?原來,齋戒關乎神明饗與不饗,戰爭關乎國家的存亡,疾病關乎一身的生死,所以孔子才如此謹慎。
熟讀玩味的方法便是字斟句酌,晝誦夜思,平心易氣,闕疑存惑。《讀〈論語〉〈孟子〉法》第一條指出,讀書要“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圣人之意可見矣。”在讀書的過程中,要涵泳諷誦,字字而求,句句而思,晝而誦之,夜而思之,念茲在茲才可能一旦豁然貫通;要平心易氣,心浮氣躁則不能沉潛細思;要闕疑存惑,強不知以為知只能是自欺欺人。只有做到這樣,才能得見圣人之意。
熟讀玩味的最高境界便是能分辨孔子與孟子兩位圣人語言風格的差異。《讀〈論語〉〈孟子〉法》第七條曰:“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所謂“自然”,就是渾然一體,自自然然,如孔子說自己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諾大的胸懷與志向,說來卻是如此平淡自然;所謂“事實”,就是事實如此,實話實說,如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是因為人性本善,所以人人都有成圣成賢之可能,這是一句大實話。
四、切己體察
《論語·子張》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切問而近思”,就是說要切己體察。朱子與呂祖謙將合撰的理學入門讀物命名為《近思錄》,正是取“切問而近思”、切己體察之意。在《讀〈論語〉〈孟子〉法》中,朱子也特別強調要切己體察。
《讀〈論語〉〈孟子〉法》第四條曰:“程子曰:‘凡看《語》《孟》……須將圣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二書切己,終身盡多也。’”在閱讀《論語》《孟子》的過程中,如果只是把圣賢所說的當作一場話,聽完就過去了,就是不能切己;切己就是要關切自身,圣人所說的話,就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一般,促使自己深刻地反思自己、省察自己。圣人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里仁》),自己是否做到了見利思義?圣人說,“先行其言,而后從之”(《論語·為政》),自己是否做到了言顧其行?一個人若能如此切己體察地閱讀經典,將終身受益無窮。
《讀〈論語〉〈孟子〉法》第一條曰:“程子曰:‘讀書者當觀圣人所以作經之意,與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圣人與凡人雖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人生的境界卻有天壤之別。“圣人,人倫之至也。”(《孟子·告子下》)圣人是理想人格的典范,達到了人生的完美境界,而我們則處于普通人的境界,所以才需要讀書學圣賢。因此在讀《論語》《孟子》時,就要本著這樣一種心態,切己體察:圣人為什么達到了圣人之境,而我為什么還是一介凡夫?如此才能反求諸己,觀照自身,完善自身,向著圣人之境邁進。
《讀〈論語〉〈孟子〉法》第三條曰:“程子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圣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于《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很幸運,我們都生在孔孟文化的中國;不幸的是,我們都不是生在孔孟之世,無緣親眼目睹圣人的風范,無法親耳聆聽圣人的教誨;所幸的是,古圣人發明了文字,將圣人所說的道理記錄了下來,使我們得以通過文字和圣人晤面。文字凝結的《論語》,使孔子和他的弟子們仍然栩栩如生地展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如果能把《論語》中孔子諸弟子的疑問當成自己的疑問,那孔子對諸弟子的回答不就等于是對自己的回答嗎?自己和圣人不就是在面對面地交流嗎?就算圣人復生,也不過是用那些道理來教導人。雖然每個人的生命境遇不一樣,所遇到的困惑也不一樣,雖然孔孟與群弟子討論的是兩千多年前的事情,而我們現在面對的則是當下的事件,但這并不妨礙我們透過千差萬別的事件,去探索事件背后永恒的真理,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一以貫之”之道。正因如此,我們才需要對孔孟與諸弟子的對話“深求玩味”,切己體察,去求得那“一以貫之”之道。
五、學以明道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讀書人學習《論語》《孟子》的目的,不是為了在人前吹噓炫耀,也不是以之作為求取功名利祿的敲門磚,而是為了修身明道,行道弘道。
學習《論語》《孟子》,首先要知道、明道。《讀〈論語〉〈孟子〉法》第九條曰:“程子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在程子看來,如果讀了《論語》《孟子》而不能領悟圣道,就算讀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雖多,亦奚以為”典出《論語·子路》篇:“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熟讀了《詩經》三百篇,如果在國內還辦不通政治任務,出使外國也不能獨立談判酬酢,縱然讀得多,又有什么用處呢?讀書是為了學以致用,閱讀經典是為了通經致用,而不是做一架博聞強識的“活書櫥”。可見,讀圣賢書以明道為終極目標。如果書讀了很多,卻不能見道、明道,不能領會圣賢的用心,豈不悲哉!進而言之,若真能悟道、明道,則自然能以一顆不容已的仁愛之心,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自覺地去弘揚此道,使人人都明心見道。孔子就是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周游列國,以求知遇,孟子就是以舍我其誰的精神,游說諸侯,宣揚王道。
明道、見道的標準,就是以《論語》《孟子》為尺度權衡去評判天下事物,去處理日常事務。《讀〈論語〉〈孟子〉法》第八條曰:“程子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在程子看來,《論語》《孟子》就是量度事物的尺度稱錘。求學之人讀了《論語》《孟子》,明心見道,就如同有了尺度稱錘一般,用它去稱量事物,自然就能見出長短輕重。正所謂“權,然后知輕重;度,然后知長短。”(《孟子·梁惠王上》)評判事物的是非曲直需要一個標準,這個標準就是我們所常說的道理,說得文雅一點叫做理性。《論語》《孟子》所載千言萬語,約而言之,無非就是這個道理或理性。學習了《論語》《孟子》,有此把柄在手,自然能夠量度事物的長短輕重,而不是受私欲或物欲的煽動而有失偏頗,或受外界情勢的裹挾而不由自主。
《論語》《孟子》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經典,朱子所撰《讀〈論語〉〈孟子〉法》,強調讀《論語》《孟子》要以《論語》《孟子》為本,要以全本為上,要熟讀玩味,要切己體察,要學以明道,對于我們今天學習《論語》《孟子》仍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