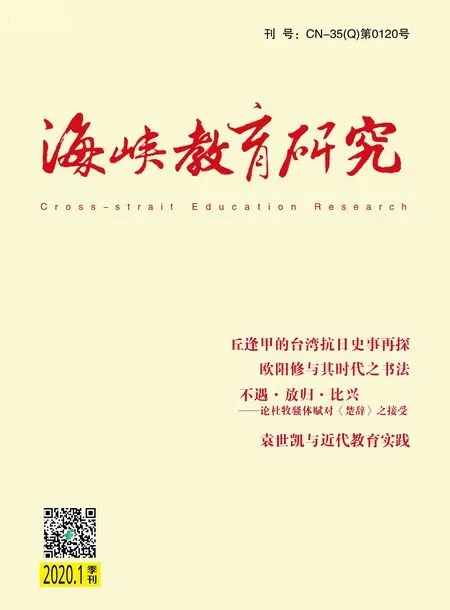不遇·放歸·比興
——論杜牧騷體賦對《楚辭》之接受
■ 張鑫誠
一、前言
《文心雕龍·辯騷》稱屈騷“雖取熔經(jīng)旨,亦自鑄偉辭”[1]64,通古變今,在繼承《詩經(jīng)》同時獨創(chuàng)《楚辭》特有之風格。馬積高《賦史》談到騷體賦之流變:“騷體賦本身的變化較少,只是后世有的騷賦間或插入‘兮’字的散文句或整齊的對偶句、排比句。”[2]8騷賦發(fā)展至唐,雖在句式上皆循屈賈遺則,又受他體影響,句式靈活、情感亦趨于多樣化之作。體式頗為穩(wěn)定的騷斌,實也處于不斷發(fā)展變化之中。[3]111

屈原
在杜牧現(xiàn)存三篇辭賦中,《阿房宮賦》蔚為名篇,馬積高將之界定為新體文賦。[2]344杜牧另外兩篇騷體短賦《望故園賦》《晚晴賦》不限于形式,在精神內(nèi)涵與藝術手法上均對《楚辭》有所繼承發(fā)揚,有其文學與社會價值。然目前對杜牧賦的研究只停留在《阿房宮賦》上,尚未有單篇或?qū)W位論文對此二篇賦進行過針對性的討論。在《唐賦分體研究》《中晚唐賦分體研究》兩本唐賦論著中,于論述騷體賦的章節(jié)內(nèi),均未提及杜牧的《望故園賦》《晚晴賦》,頗有遺珠之憾。
受唐代文學環(huán)境之影響,杜牧兩篇騷體賦中又融合律賦之寫法,添加對偶之四字有韻腳之句。又杜牧作為繼承韓愈古文運動的散文家,在《晚晴賦》中,加入了新文賦以散文句式入賦的筆法,一定程度上形成騷體賦與文賦合流現(xiàn)象。①晚唐騷體賦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作家不僅以騷體抒情,且用以指斥社會上的不平現(xiàn)象,同時晚唐人重視塑造情景交融的優(yōu)美意境[4],杜牧之《望故園賦》《晚晴賦》可謂此特點之典范。另杜牧評李賀有言“蓋《騷》之苗裔”[5],此語歷來為研究者所關注,并以此分析李賀對《楚辭》之接受,由此亦可側(cè)面觀照杜牧與《楚辭》關系密切。對杜牧騷體賦進行深入探析,有助補充杜牧賦研究及晚唐賦對《楚辭》接受研究之不足,并可管窺晚唐文士在賦體中的失意書寫。是以本文以杜牧騷體賦對《楚辭》之書寫主題、意象運用與比興手法作為主要觀照點,探尋杜牧騷體賦對《楚辭》之接受。
二、“才高者菀其鴻裁”——對《楚辭》書寫主題之紹繼
《文心雕龍·辯騷》敘《楚辭》各篇的情感表達云:“故《騷經(jīng)》《九章》,朗麗以哀志。……其敘情怨,則郁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1]65總體觀之,騷體賦情感柔美,情調(diào)幽怨。清程延祚《騷賦論》即謂“騷則長于言幽怨之情。”[6]774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云:“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zhí)履忠貞而被讒邪,憂心煩亂,不知所訴,乃作《離騷經(jīng)》。”[7]1這樣的寫作背景奠定了《楚辭》哀怨的寫作風格。茲從情感書寫上分為兩個主題,分析杜牧辭賦對《楚辭》哀怨情感之熔鑄。
(一)嗟小人嘆不遇
《離騷》中屈原潔身自好修立品行“紛吾既有此內(nèi)美兮,又重之以修能”[7]3,然而當時政治環(huán)境昏暗,人皆求利而無所不為,“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nèi)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7]7是當時政治社會之寫實。《漁父》中亦通過描繪塑造的“漁父”形象揭示黑暗時代下時人之隨波逐流:“世人皆濁,何不渥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欲其釃。”[7]107在這樣的昏昧環(huán)境下,奸佞小人嫉賢妒才,曲意逢迎,卻受君王重用,如《離騷》中“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7]5,而屈原這樣的忠貞之士則遭逢奸邪讒毀:“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7]9。
觀杜牧賦可見其與《楚辭》精神內(nèi)涵相似之處。牧于大和二年(828)登科,半年后隨外放江西觀察使的沈傳師做幕僚,然此后并無甚大作為,由其賦中所言還受到同僚攻擊。大和四年(830)冬,陸沉下僚的杜牧由宣城進京,道經(jīng)秦地而生不得志與思歸之意,遂將其個人生命際遇下所生出的情感熔鑄在《望故園賦》中。而賦中有諸多篇幅直接地痛斥小人之黨同伐異,與自身之有技無售,從而表達出鮮明激烈情感,試引文觀之:
既操心之大謬,欲當時之奏技。技固薄兮豈易售,矧?qū)碇畾q幾。人固有尚,珠金印節(jié),人固有為,背憎面悅,擊短扶長,曲邀橫結。吐片言兮千口莫窮,觸一機而百關俱發(fā)。嗟小人之顓蒙兮,尚何念于逸越。[8]12-13
杜牧開頭即自敘“欲當時之奏技”,有心為朝廷建功立業(yè),然不能得。正是由于當時黑暗的現(xiàn)實社會“擊短扶長,曲邀橫結”,人人唯利是圖,黨同伐異,打擊弱小的政敵,攀附勾結權勢炙手可熱者。杜牧不僅建立功業(yè)之理想不能達成,反而受讒佞百般攻擊:“吐片言兮千口莫窮,觸一機而百關俱發(fā)。嗟小人之顓蒙兮,尚何念于逸越。”字里行間皆可明顯感受到杜牧同屈原一般,其既有對君王不用賢良之怨,更表達對群小結黨營私,讒害忠良之悲憤,使得哀怨成為其騷賦中激烈涌蕩的風格。

楚辭
賦末“生既不足以紉佩兮,顧他務之纖小”,化用《離騷》“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7]3之語,意又近乎《懷沙》“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7]83表明即使不被重用,仍要修養(yǎng)自身品德,沒有完全放棄希望。非無才也?實不遇也。《晚晴賦》則運用比興手法書寫小人:“雜花參差于岸側(cè)兮,絳綠黃紫,格頑色賤兮,或妾或婢”,以雜花之繽紛而掩紅芰,比擬奸邪烏合得勢,書寫自己之不遇。杜牧騷賦中對小人之丑行與不遇困頓的書寫主題,皆承襲自《楚辭》。
(二)傷孤身思放歸
“望歸”和“懷古”這兩大人性主題在中國文學史的起源,其實可以說由屈原首先加以展示。[9]96且自《哀郢》觀屈原放歸江南的之悲吟: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
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
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7]76
屈原遠離故都而一路東行,身體上的放歸與內(nèi)心之眷留,呈現(xiàn)出相反的方向。此以地理位置上的距離遠隔為開端的書寫,但是卻步步環(huán)繞著以自我生活為中心的種種身份階級、社會政治、歷史文化等相關變動脈絡。[10]59“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7]92表達了失意文人那種矢志之愁、故鄉(xiāng)之思。《望故園賦》中,杜牧既受小人讒毀而不遇,而生放歸之意:
余之思歸兮,走杜陵之西道,巖曲天深,地平木老。隴云秦樹,風高霜早,周臺漢園,斜陽暮草。……悵余心兮舍茲而何去?憂豈無念,念至謂何?憤慍凄悄,顧我則多。萬世在上兮百世居后,中有一生兮孰為壽夭?生既不足以紉佩兮,顧他務之纖小。賦言歸兮,余之忘世,徒為兮紛擾。[8]12-13

“余之思歸兮,走杜陵之西道。”杜牧遂生退卻之心,描寫沿杜陵西道之景致,既然無法在朝政上有所作為,不如安心享受這高峻雄起的秦地美景。這與屈原之對現(xiàn)實失望而心生退卻“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相似。[7]10“隴云秦樹,風高霜早,周臺漢園,斜陽暮草。”杜牧就眼前的地理景觀書寫出一種懷古傷今的歷史思維。前朝地景一方面標示著實質(zhì)地點,一方面也充滿著個人情志或是已經(jīng)內(nèi)化了的集體想象。因此它們不是單純的風物景觀,而是奠基與自我追尋、社會意識的地理認同。[10]65
“賦言歸兮,余之忘世,徒為兮紛擾。”杜牧在文末流連于彷徨何往,產(chǎn)生出不如歸隱田園、與世隔絕之隱逸念想。遙遙呼應了屈原在放歸原野、遨游仙界之放歸與懷沙沉江之堅守間徘徊狂亂。最終杜牧“中有一生兮孰為壽夭”之嘆,正呼應了屈原《涉江》“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7]76之千古同悲的孤寂。“賦言歸兮,余之忘世,徒為兮紛擾。”《晚晴賦》在文末亦與表現(xiàn)出《望故園賦》相似的孑然放歸之幽,“若予者則謂何如,倒冠落佩兮,與世闊疏。敖敖休休兮,真徇其愚而隱居者乎。免眾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其中“倒冠落佩”又化用《離騷》“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以示無意仕宦而有意“退將復修吾初服”。
然而不同于屈原杜遨游仙境之放歸,杜牧之放歸是帶有人間煙火氣息的:“遠林雞犬兮,樵夫夕還。織有桑兮耕有土,昆令季強兮鄉(xiāng)黨附。悵余心兮舍茲而何去?”[8]13山村人家仍可為杜牧提供心靈安寧之所,而屈原只能在迷幻的仙界中找尋自我意識的滿足,呈現(xiàn)出二人不同的社會意識。面對喪失希望的社會,失意下的屈原與杜牧的離世遠游或歸隱,也許無用于改造社會,然放歸成為他們自我超脫的一種方式。
三、“吟諷者銜其山川”——對《楚辭》意象運用之承創(chuàng)
《文心雕龍·神思》言意象云:“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1]515意象指作家為文構思時,意想中的形象,或作品中呈現(xiàn)的整體形象。關于“意象”之塑造,唐庚《唐子西文錄》記:“謝玄暉詩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橋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意象殊窘。”[11]447物象隨作家喜好、生活環(huán)境,影響心理而有所揀擇,以建立作家個人意象群。物象有時表現(xiàn)民族文化特性,賦予意象以特定意義。
杜牧《晚晴賦》中,取用花草意象描繪秋日池景:“雜花參差于岸側(cè)兮,絳綠黃紫,格頑色賤兮,或妾或婢。”[8]15《離騷》:“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7]6游國恩之評可資參考:“因念此輩茍保芳草之質(zhì)。雖至枯萎凋落,亦復何傷;乃竟相率而變?yōu)槭彿x,與惡草同其禍害,此則深可哀痛者也。”[12]95杜賦“格頑色賤”,也即《離騷》之“蕪穢”,“雜花”意象流露出對當時人才制度不公社會的深刻諷刺。此外《晚晴賦》以雜花間草意象比擬小人,《望故園賦》則直斥小人之“顓蒙”,二賦在對小人之書寫上可互相映照。賦中又有“倒冠落佩兮,與世闊疏。”[8]15“冠”“佩”之意象亦繼承自《離騷》,與在朝仕宦有關,“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屈原用以表示自身美好修養(yǎng)與高潔質(zhì)量。“倒冠落佩”表達自身仕途偃蹇,有意歸隱。
在山川意象上,杜牧騷體賦亦可見對《楚辭》意象承襲之處。杜牧《望故園賦》“寂寥四望,蜀峰聯(lián)嶂,蔥蘢氣佳,蟠聯(lián)地壯”中“山”之意象投射出杜牧受困與無人見知政治困境下的自我意識,與《楚辭》呈現(xiàn)出緊密聯(lián)系。《涉江》:“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7]76《楚辭》中“山”意象呈現(xiàn)出連綿、晦暗之特點,“失志遷客”望之生悲,處之心危,內(nèi)心之情感體驗與外在之困境此時相互映照。正合王夫之言:“云嵐垂地,檐宇若出其上。江北之人,習居曠敞之野,初至于此,風景幽慘,不能無感,被讒言失志之遷客,其何堪此乎!”[13]72
《望故園賦》在記敘西陵野景時用到“水”意象,“長煙苒惹,寒水注灣”[8]12之表達效果亦繼承《楚辭》中“水”意象。《離騷》中有“汨余若將不及兮”[7]6句,洪興祖評曰:“言我念年命汩然流去,誠欲輔君,心中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歲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耄也。”[14]17此可與“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7]7相互照映。《抽思》亦有:“臨流水而太息”句。煙霞之“苒惹”與時間密切相關,又特言“寒水”表達心境,寄托對歲月荏苒而自身不遇之感傷。

杜牧
“隴云秦樹,風高霜早。”[8]12杜牧此用一“云”一“霜”意象之語境心境與《楚辭》中用到云霜之意境相似。《楚辭》以云意象寄寓自身遭逢,如《思美人》:“愿寄言于浮云兮,遇豐隆而不將。”屈原遠放沅湘,欲托情浮云而不得,失落失望滿懷。而杜牧其放歸,在杜陵西道上回顧上一段失敗的仕宦旅程,自我意識則產(chǎn)生如浮云飄忽之感,意與《楚辭》略同。有取及霜、雪所造成的萬物凋零之效果者,如《楚辭》以霜意象溫度低、意涵生命凋零之特點,切合騷客遭遇讒毀以至被流放千里之遭逢下所抒發(fā)的凄涼、感傷之內(nèi)心感受。《惜往日》:“微霜降而下戒”[7]89,汪瑗注云:“霜降而芳草夭,喻讒言入而君子殺也。”[15]222照應了《望故園賦》前文“嗟小人之顓蒙”。
杜牧在意象選取上除紹繼《楚辭》,亦有創(chuàng)新之處。如騷體賦中懷古意象之運用,是杜牧的創(chuàng)新,這應也與杜牧的懷古詩成就有關。“周臺漢園,斜陽暮草。”“繚粉堞于綺城,矗未央于天上。”[8]12杜牧用歷史之滄桑感寄托自身不遇,懷古是文人對生命時間與生存空間的反省[9]96,杜牧放歸過程中將自身遭逢寄托于古人古跡,借以抒懷。另外,在諷刺小人之結黨營私時,《離騷》直述之:“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7]7而《晚晴賦》則勾勒了群木之意象來表意。“木勢黨伍兮”,以木之伙同而生,暗喻小人“擊短扶長,曲邀橫結”之黨同,這亦是意象運用的創(chuàng)新之處。
四、“童蒙者拾其香草”——對《楚辭》比興手法之熔鑄
比興之義為《楚辭》代表性的特色。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16]475比興每每蘊含諷諫之旨,《文心雕龍·辯騷》即言:“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guī)諷之旨也。”[1]64此為后世辭賦家所繼承,杜牧亦不例外。②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云: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讬君子;飄風云霓,以為小人。[7]1

《楚辭》比興寄托之傳統(tǒng),已然成為后代文士創(chuàng)作中有意無意都帶有的一種特定文化意涵,而于《晚晴賦》表現(xiàn)尤為明顯。《文心雕龍·比興》即言“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制《騷》,諷兼比興。”[1]667《辯騷》亦云:“虬龍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1]64對屈原《離騷》有極高的評價,認為它繼承《詩經(jīng)》諷喻時政之意涵,故而《文心雕龍·辯騷》謂“虬龍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1]65如《離騷》以惡草比興“薋菉葹以盈室兮”,薋菉惡草盈室,豈非諷刺奸佞之蜂聚楚國,而代表忠貞之士的“香草”則被遠棄。吳仁杰《離騷草木疏》即謂:“《離騷》以薌草為忠正,蕕草為小人。蓀、芙蓉以下凡四十有四種,猶青史忠義獨行之有全傳也。薋菉葹之類十一種,傳著卷末,猶佞幸奸臣傳也。”[17]998《望故園賦》雖多用直抒寫法,而偶可見比興之寄,如“巖曲天深”連綿峰嶂,如同當時社會,仕進無門,宦途雪塞,興寄晚唐士大夫階級進退維谷之苦楚。
至于《晚晴賦》則充分發(fā)揮騷賦“比體云構”[1]667之特點,通篇運用比興之表現(xiàn)手法。馬積高即言《晚晴賦》通篇用比喻,且什九是以人喻物,這是杜牧的一種創(chuàng)造。[2]335陳巖肖稱此賦不流于表羽,乃“善比興者”③,蓋其得《風》《騷》比興精髓而切中實弊也。茲引文觀其比興之寄:
木勢黨伍兮,行者如迎,偃者如醉,高者如達,低者如跂,松數(shù)十株,切切交峙,如冠劍大臣,國有急難,庭立而議。竹林外裹兮,十萬丈夫,甲刃摐摐,密陣而環(huán)侍。豈負軍令之不敢囂兮,何意氣之嚴毅。
杜牧為中唐名相杜佑之孫,生逢藩鎮(zhèn)割據(jù)的戰(zhàn)亂年代,曾研究兵法,注解《孫子》十三篇,并在李德裕對藩鎮(zhèn)用兵時提出了有效建議。④“如冠劍大臣,國有急難,庭立而議”隱含諷諫之意,暗刺晚唐中央衰弱,藩鎮(zhèn)煩亂頻繁,而朝廷則宦官主政,士大夫忙與黨爭,國有難而空議不能除。牧又值牛李黨爭之時,他處在夾縫中,牛黨重其人而不用其謀,李黨用其謀而不重其人。是故雖負長才,終不得重用,無法將胸中韜略真正實現(xiàn),無奈以松竹為兵,透出濃濃的悲哀。
復觀《晚晴賦》承襲《離騷》“香草”與“惡草”比興意象一段:
復引舟于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奼然如婦,斂然如女,墮蕊黦顏,似見放棄。白鷺潛來兮,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雜花參差于岸側(cè)兮,絳綠黃紫,格頑色賤兮,或妾或婢。間草甚多,叢者束兮,靡者杳兮,仰風獵日,如立如笑兮,千千萬萬之容兮,不可得而狀也。[8]14-15
杜牧將自己比作“紅芰”,雖有得重用之時,然更多時候是“似見放棄”。正如他在會昌二年寫的《上李中丞書》:“至于俯仰進趣,隨意所在,希時徇勢,不能遂入。是以官途之間,比之輩流,亦多困躓。”[8]464“紅芰”是香草的一種,第一層意涵以表忠貞之志,《離騷》中即有“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7]10將“紅芰”比作女子,則用“宓妃佚女,以譬賢臣”之義,是第二層意涵,以賢臣自況。“白鷺潛來兮,邈風標之公子”,正乃牧以白鷺自況,愿追逐賢君。“窺此美人兮”,正是《楚辭》中“美人”文化傳統(tǒng),用以比擬君王。白鷺之窺“紅芰”,公子之窺美人,正如杜牧希望朝廷能夠注意到自己,使得自己能完成揚聲紫微的抱負,然最終“墮蕊黦顏,似見放棄”,在現(xiàn)實中暗淡。而“雜花參差于岸側(cè)”“間草甚多,叢者束兮,靡者杳兮”則比喻奸佞結黨營私,政治環(huán)境昏暗。放在歷史社會環(huán)境下,則矛頭直指操弄權勢、欺君罔上的宦官集團。“或妾或婢”亦隱指妾婢奪去了正室之寵。此皆切《文心雕龍·辯騷》“每一顧而掩涕,嘆君門之九重,忠恕之辭也。”[1]64總體而言,通篇充斥著小人奸邪的痛斥與不遇之感懷,而在比興手法的運用及比體喻體的選取上,杜牧騷體賦熔《楚辭》而鑄新。
五、結論
在《楚辭》之影響下,杜牧在《望故園賦》《晚晴賦》兩賦中以騷體書寫了面對外部政治環(huán)境困厄、小人讒毀不絕的處境而產(chǎn)生士不遇的感懷。孤身與放歸是杜牧騷賦中另一重要主題,面對冷峭的社會現(xiàn)實,杜牧在屈原身上找到了認同感。在現(xiàn)實壓迫下,流連彷徨后,杜牧與屈原同樣選擇了放歸遠游的人生超越。這是杜牧騷體賦對《楚辭》在書寫主題與內(nèi)容上之趨同。在意象運用上,兩賦在“山川”“花草”等意象上皆可見紹繼《楚辭》之特色,而杜牧以懷古意象入騷體賦,是其創(chuàng)新之處。在比興手法之熔鑄上,以《晚晴賦》為主,此賦“比體云構”,以通篇可見的比興之義含蓄流露出自身懷美質(zhì)而不遇之哀、對小人結黨之恨等感懷,同時熔鑄了《楚辭》“香草”“美人”“惡草”之傳統(tǒng)文化意涵。是知《楚辭》確實對杜牧之騷體賦有著深厚之熏染,由此亦可鑒照《楚辭》對唐代騷體賦影響之深遠,《文心雕龍·辯騷》中“衣被詞人,非一代也”確為的言。

注釋:
①關于新文賦,可見馬積高《賦史》:“新文賦是伴隨唐代古文運動而產(chǎn)生的一種賦體,因為它的語言基本上同唐宋古文相似,只是大體押韻,成了所謂‘押韻之文’。”頁9。
②鄭毓瑜先生《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于頁122論屈騷之諷諫功能:“任何源出或祖紹屈騷的作品都被社會預期應該達成諷諫功能。”又于頁184補充“諷諫”云:“‘直諫’不能僅僅理解成對君王的勸諫或?qū)ι缛旱挠栒],反而偏重于透過知識分子自身所折射出的一切困難的怨懟、苦悶或是隱微的渴望與蒼茫的失落。……‘直諫形式’因此超越言說策略作用于他人的目的性,說服自己多過說服君王,啟發(fā)自我多過改造社會。”其說詳當,可資參考。
③宋·陳巖肖《庚溪詩話》:“眾禽中,唯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閑野不俗。……《易》與《詩》嘗取之矣。后之人形于賦詠者不少,而規(guī)規(guī)然只及毛羽飛鳴之間。……至于杜牧《晚晴賦》‘復引舟于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奼然如婦。斂然如女,墮蕊黦顏,似見放棄。白鷺潛來兮,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雖語近纖艷,然亦善比興者。”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xù)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8 月,冊上,頁182)。
④后晉·劉眴等撰:《舊唐書·杜牧傳》:“武宗朝誅昆夷、鮮卑,牧上宰相書論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間,盛夏無備,宜五六月中擊胡為便’。李德裕稱之。(牧)注曹公所定《孫武十三篇》行于代。”(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5月,卷179,頁3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