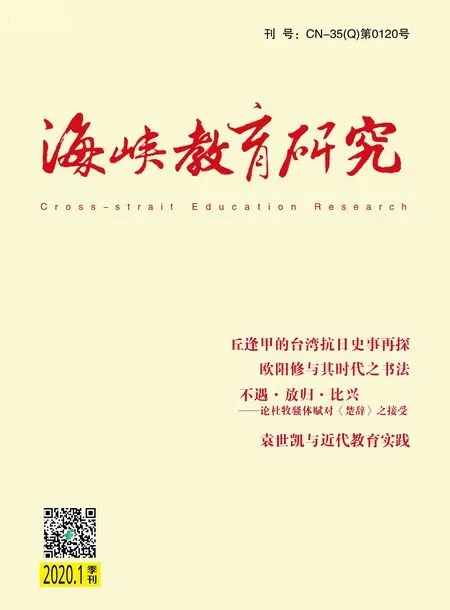歐陽修與其時代之書法
■ 孫漢生
歐陽修是有宋一代文宗,文章、詩詞卓絕一時,為后世所宗,但學習書法,未聞有宗之者。史有歐體,其先人蘭臺率更公也,非永叔也。然而,翻閱今人所著之中國書法史論著,歐陽修都占據重要篇章。古今學者對歐陽修書法方面的貢獻和影響力,論之詳備,今欲再論,幾乎無從置喙。但是,相較于歐陽修文章詩詞研究之為顯學,歐陽修書法研究領域,仍有書法史家所未到而有待拾遺補缺者。歐陽修在中國書法史上的貢獻和影響力,何以發生影響,本文試圖在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略作分析。
上篇:歐陽修的文化自覺、文化焦慮及其書法追求

歐陽修畫像(三才圖會)
蘇軾《評楊氏所藏歐蔡書》:“歐陽文忠公書自是學者所共儀刑,庶幾如見其人者,正使不工,猶當傳寶。況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1]黃庭堅《跋永叔與挺之郎中及憶滁州幽谷詩》:“歐陽文忠公書不極工,然喜論古今書,故晚年亦少進。其文章議論,一世所宗,書又不惡,自足傳百世也。”[2]蘇黃師徒的上述評論,最具代表性,皆承認歐陽修在書法方面的影響力。蘇軾作為直接弟子,更為含蓄和尊重,而黃庭堅是再傳弟子,語氣就更為銳利:書不極工,晚年少進;百世宗傳,因其喜論書法,更因道德文章,一世所宗。這很符合中國傳統的德藝觀念,藝因人傳,而不是人賴藝傳。歐陽修自己有此方面的言論,近人弘一法師談藝,也很強調這種德藝關系。

歐陽修自書詩《夜宿中書東閣》
歐陽公《世人作肥字說》:“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然后世不推此,但務于書,不知前日工書隨與紙墨泯棄者,不可勝數也。使顏公書雖不佳,后世見者必寶也。非自古賢哲必能書也,唯賢者能存爾,其余泯泯不復見爾。”《集古錄跋尾·唐湖州石記》:“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后世而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后不朽。”此論大體同于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之意,后世之弘一法師論書法,因承之。但若深論,顏魯公書法若不卓絕,其名固亦能傳之后世,所傳乃道德英雄之名,非書家之名。道德之名固然比書家之名更值得崇尚,但并不能代替,也不能相混。書家須講究道德,成為君子,否則書名必遭詬辱,蔡京書雖不亞于蔡襄,但其書跡不如蔡襄之書流播后世之廣遠,是亦一證。如此看來,歐陽公書史留名,仍因德藝雙馨。
一、歐陽修的文化自覺及其心系書法的時代焦慮
歐公在《集古錄跋尾》中反復多次嘆息宋人書法不如唐人,僅舉幾例。跋《范文度模本蘭亭序三》:“自唐末干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圣宋興百余年間,雄文碩學之士,相繼不絕,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獨字書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蹤唐室,余每以為恨。”以三代和唐朝為楷模的文化自覺,體現其全面振興當朝文化的責任感。跋《唐武盡禮寧照寺鐘銘》:“余得唐人書,未嘗不嘆今人之廢學也。”跋《唐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其筆畫遒勁,不類婦人所書。余集錄亦已博矣,而婦人之筆著于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常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于唐,書之廢莫廢于今。蓋唐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為而。唐人書見于今而名不知于當時者,蓋不可勝數也,非余錄之,則將遂泯然于后世矣。余于《集古》,不為無益也夫。”跋《唐植柏頌》:李潮書,“為僅有,亦皆后人莫及也。不惟筆法難工,亦近時學者罕復專精如前輩也”。跋《唐夔州都督府記》:“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婦人、武夫皆善書法;時人“忽而不為”。歐陽公很有緊迫感,而前人墨跡又有泯滅失傳之憂,所以歐公十分焦慮。
歐陽公認為,甚至五代干戈之際,書法都比宋代強。跋《徐鉉雙溪院記》:“鉉與其弟鍇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為學者所宗。蓋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能自奮然為當時名臣。而中國既苦于兵,四方僭偽割裂,皆褊迫,擾攘不暇,獨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君者優游其間。及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得為王臣,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采。蓋亦有以過人者,故特錄其書爾。若小篆,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其筆甚精勁,然其人無足稱也。”跋《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五代干戈之際,學校廢,是謂君子道消之時,然猶有如忠恕者。國家為國百年,天下無事,儒學盛矣,獨于字書忽廢,幾于中絕。今求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故余每與君謨嘆息于此也。”他感嘆:“五代干戈之際,士之藝有至于斯(徐鉉、王文秉“字畫之精”)者,太平之世,學者可不勉在!”(《集古錄跋尾·王文秉紫陽石磬銘》)。勉勵時人重視書法為其集古之動因之一。
張家壯、鄭薇文章認為,歐陽修《集古錄》展示了古意盎然的那一部分資源,對三代兩漢多數銘文所傳遞出來的高古簡質極盡推崇。[3]其實,從《集古錄》篇目來看,唐代碑帖占十之七八,主要是因為唐代為時不遠,碑帖留存尚多,但歐陽修在跋尾中對唐人碑帖的推崇、贊嘆,也是能體現他的主觀意向:如果說有三代情結,那也有濃重的唐代情結。
宋代書法為何不如唐人,甚至不如五代?跋《唐辨石鐘山記》曰:“(唐人)至于書畫,亦皆可喜。蓋自唐以前,賢杰之士,莫不工于字書,其殘篇斷稿為世所寶,傳于今者,何可勝數。彼其事業,超然高爽,不當留精于此小藝。豈其習俗承流,家為常事,抑學者猶有師法,而后世偷薄,漸趣茍簡,久而遂至于廢絕歟?今士大夫務以遠業自高,忽書為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而間有以書自名者,世亦不甚知為貴也。至于荒林敗冢,時得埋沒之余,皆前世碌碌無名子,然其筆畫有法,往往今人不及,茲甚可嘆也。”歐公認為,宋人偷薄茍簡、忽書不學。今人潘伯鷹承襲歐陽公觀點,談宋人蘇黃米蔡書法時說:“整個北宋和南宋的書法遠不及唐朝的標準,其所以衍成這樣事實的原因,大概有兩方面。其一,由于五代以來的喪亂,作為當時社會當權派的士大夫階級已經只注意一些政治和理論的大事,其余一切,只好付之茍簡,對于書法藝術都不大崇尚了。”[4]
歐陽公并不全廢宋人書法,對當時書法特出者,不吝贊美之詞。首推當朝皇帝:“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玩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歸田錄》卷一)但是,歐陽公并沒有推皇帝書法水平當朝第一;歐公自己身為文壇領袖,老實承認自己書法不行,沒有自封書壇盟主,而是推蔡襄為盟主,但蔡襄謙讓。《蘇子美蔡君謨書》:“自蘇子美死后,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溯激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余年,竟如何哉?”從傳世的文字可見,歐陽公對蔡襄書法贊不絕口。《跋茶錄》:“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錄目序》橫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為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粗識其一二焉。”

蔡襄畫像

蔡襄《自書詩》

蘇舜欽畫像

蘇舜欽《游山五古帖》
跋《唐鄭澣陰符經序》曰:“公權書《高重碑》,余特愛模者不失其真,而鋒芒皆在。至于《陰符經序》,則蔡君謨以為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鋒,與余之說正相反。然君謨書擅當世,其論必精,故為志之。”對碑刻鑒賞,雖人各異,歐公能夠尊重他人,見其虛懷若谷。歐公年齡、官位、文名皆高于蔡襄,但不以為事事高于他人,他一再揄揚蔡襄書法當時第一。
跋《唐虞城李令去思頌》:“今世以小篆名家,如邵不疑、楊南仲、章友直。”記錄當時書法名家。《六一詩話》贊摯友:“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于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為世所珍。余家嘗得南唐后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以此紙書其《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絕,真余家寶也。”《跋杜祁公書》:“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為十卷而藏之。公筆法為世楷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世人莫若余得之多也。”幾十年后,《宣和書譜》著錄的歐陽公同時代人物,差不多僅此幾位,不知與歐陽公的表彰是否有關。
對于當時書法中出現的不良傾向,歐陽公則毫不留情地直率批評,哪怕是最好的朋友。《與石推官》兩函,驚駭于石介的字“何怪之甚”,“特欲與世異”,有違君子中庸之道。石介復書辯解[5],歐陽公亦不發寬宥之言。歐陽公將為書與為人為學并談,要求法古而能為后世法,如鐘王虞柳。藝術評論從書法形態、技藝上升到道德的高度和儒家價值觀層面,可見歐陽公振興書法的迫切心態,其實關乎儒學復興,不單單是為文藝。
二、歐陽修的書法生活:學書修身,帶動風氣
歐陽公不僅僅“喜論古今書”,更是一位身體力行的書法練習者,終身不輟,老而彌篤,到了癡迷成瘋的程度,自言“每見筆輒書”,江休復比之為“風法華(瘋和尚)”。(《試筆·風法華》)看來是個“筆霸”,十足的書癡。
歐公隨筆《筆說》《試筆》《集古錄跋尾》記載了他的學書生活、學書感受和書學觀念。作為文壇領袖、朝廷重臣,他的書法生活,對那個時代,一定具有引領作用。
《筆說·夏日學書說》:“夏日之長,飽食難過,不自知愧,但思所以寓心而銷晝暑者……當其揮翰若飛,手不能止,雖驚雷疾霆,雨雹交下,有不暇顧也。古人流愛,信有之矣。”沉酣其中,大有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之勢。
《試筆·學書消日》說:“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已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為,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于學字,為于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賢留意于此,不為無意也。”
《試筆·學書為樂》:“蘇子美嘗言:‘明窗凈幾,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為樂,則自足有余。”歐陽公另有詩《試筆》:“試筆消長日,枕書遣百憂。余生得如此,萬事復何求?”當然,在歐公看來,寫字也不僅僅是打發日子,尋求快樂,也有一定的現實功用。《筆說》中有《李晸筆說》“付發”,《誨學說》“付奕”,寫便條教育兒子。《試筆·學書作故事》一則說,“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為故事”,這是記事本的功能。“學書勿浪書”,也不是隨便就亂寫。
《筆說·夏日學書說》:“字未至于工,尚已如此(愛、樂),使其樂之不厭,未有不至于工者。使其遂至于工,可以樂而不厭,不必取悅當時之人,垂名于后世,要于自適而已。”本段筆記透露出幾個信息:一、直到晚年,歐陽修認為自己的書法尚不夠好,但不減其樂。二、只要樂而不厭,總會學好的,那時會得到更多的樂趣。三、學書的非功利性,不為討得同時代人之歡心,也不求留名后世,只求自得其樂,是自己的一種生活方式。另一則筆記《李晸筆說》云“求悅俗以取媚,茲豈復有天真耶?”強調堅持自己、永葆個性“然后能名于后世”“古人各自為書,用法同而為字異”“唐所謂歐、虞、褚、陸,至于顏、柳,皆自名家,蓋各因其性”。《李晸筆說》是寫給兒子歐陽發的,時在嘉祐四年夏,“學書盈紙”,從談毛筆談到用筆,再談到個人個性,將自己習字的體驗向兒子現身說法。
《試筆·學真草書》:“自此已后,只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倦,當得書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書法悟道。由學書而感悟人生之理,萬事皆累,但心有所寄,則可樂。《學書工拙》:“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稍可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銷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于此,遂成一役之勞,豈非人心蔽于好勝耶?”我們似乎看到,歐公通過學書習書,體悟先秦哲人思想。《荀子·修身》云:“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役物而不役于物也”。如果役于書法,役于工拙,役于好勝之心,則有違君子之道。學書,本為修身成為君子,役于書法,則是異化。《莊子·外篇·山木》:“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
《試筆·李邕書》:“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事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為字絕不相類,豈得意而忘其形者耶?因見邕書,追求鐘、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余。余偶從邕書而得之耳。”此則筆記反映了歐公書法生活之一面,記錄了歐公學書的路徑。歐公通過學書體會了后發致遠、難能可貴、得意忘形、觸類旁通等學書和人生至理。道理是常理,貴在自己體悟,不體悟,即是不知。
跋《唐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余為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后二十余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于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殆今蓋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謂富哉!”此則說明歐公學書路徑,幼年學虞世南。

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黃庭堅說歐陽公“喜論古今書,故晚年亦少進”,其實是對歐陽公自我評價的發揮。歐陽公自己說,正是集古博覽讓自己的書法水平得以提高。跋《唐興唐寺石經藏贊》稱“余初不識書,因集古著錄,所閱既多,遂稍識之,然則人其可不勉強于學也!”跋《唐玄靜先生碑》稱:“余以集錄古文,閱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稍識字法。”
《試筆·蘇子美論書》從蘇舜欽書法所達到境界與其本人書法言論的差距,體會“非知之難而行之難”。歐公強調,“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不過多用力于空想空談書法理論,而是更多用力于書寫實踐。且古之人“方其幼時,未有所為,時專其力于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學漸近于用”,以致于“熟”,故能精。古人幼時學書,“今人不然,多學書于晚年”。此言有趣,我們二十一世紀的“今人”更是常覺不及古人,嘆不及古人學書于幼年,練就童子功。此則筆記記于官署,“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顧見案上故紙數幅,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聊聊數語,我們可以相見歐陽公為官與寫字的情境。其時在1060年秋天,大宋立國百年,歐公時任樞密副使(國家最高軍事領導機構副長官)。歐公以國家領導人之尊,號召學書法從娃娃抓起,無疑能夠帶動風氣。
跋《唐顏魯公法帖》記:顏帖為刑部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云“拙于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煎”,蓋其貧如此。此本墨跡在予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出于相家,而清苦甚于寒士,嘗摹帖刻石以遺朋友故人,云:“魯公為尚書,其貧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此則跋語揭示了古人書法作品內容的教育、勵志意義。學書求為“至人”“君子”,道德的體驗,讓其樂在其中。《筆說·學書靜中至樂說》:“有暇即學書,非以求藝之精,直勝勞心于他事爾。以此知不寓心于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于有益者,君子也;寓于伐性汩情而為害者,愚惑之人也。學書不能不勞,獨不害情性耳,要得靜中之樂者為此耳。”此段筆記透露出幾個信息:一、老年學書不輟,并且,雖身為文壇領袖,朝廷重臣,并未自命為書法家,仍然自我定位為“學”;二、學書目的主要在修身養性,成為君子;三、學書為人生樂事,足以遣興度日。
歐陽公不是理學家,但他以古文和書法活動,與理學家一樣具備文化自覺,承擔起北宋社會道德和價值建設的使命,推動思想文化發展,匯入北宋儒學復興的時代洪流。
下篇:《集古錄》對其時代書法的意義
歐陽公身體力行帶動風氣、推動北宋書法事業發展,起作用的最主要因素,尚非其自家的書法作品,而是歷時十八年之久的集古創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集古錄》書影
在歐陽公之前,早有古人對古器銘、古碑刻感興趣而尋訪、研讀。五代、宋初畫家李成畫《讀碑窠石圖》所畫情景,據說是東漢蔡邕觀讀曹娥碑,也有人說是曹操、楊修訪求曹娥碑。五代書法家楊凝式也常常于野外訪古尋碑,拓帖題壁。但是,更為刻意搜求,拓碑收藏,堅持不懈,整理集錄上千卷,編目題跋四百余篇者,唯有歐陽修。他因此一舉創立了中國金石學這門新學科。

李成《讀碑窠石圖》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
歐陽修的創舉,完全出自天性——君子仁心,不忍美與善的消逝;出自天然的悟性——文化自覺、文化使命感和緊迫感,自覺搶救文化遺產,學習、追蹤前人,直接目標是唐人書法(前文已述)。歐陽公天生一種好古癖,對不朽、永恒的美好事物的珍惜和追尋,非常癡迷和執著,《江鄰幾文集序》云:“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綱羅,至困厄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于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為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說,早在寶元元年(1038)為乾德縣令時,“縣有古碑一片”,碑文有不解之字,請教于王源叔(王洙),嘆曰:“漢之金石之文存于今者蓋寡,惜其將遂磨滅。”他在《集古錄跋尾》中反復感嘆,恐前人遺跡朽沒不存。跋《后漢無名碑》:“夫好古之士所藏之物,未必皆適世用,惟其埋沒零落之余,尤以為可惜,此好古之僻也。”跋《敦銘》(周姜寶敦,張伯煮):“古之人之欲存乎久遠者,必托于金石而傳,其湮沒埋沉、顯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然岐陽十鼓今皆在,而文字剝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銘在者皆完,則石之堅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銅,取其不為燥濕寒暑所變為可貴者,以此也。古之賢臣,名見《詩》《書》者,常為后世想望,矧得其器,讀其文,器古而文奇,自可寶而藏之耶!”器古文奇,令歐陽公魂牽夢繞。《與劉侍讀書(二七)》說:“昨日進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書,竊承動履清勝,兼復惠以古器銘文,發書,驚喜失聲。群兒曹走問乃翁夜獲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好惡之異如此,安得不為世俗所憎耶!其窮達有命爾,求合世人以取悅,則難矣。自公之西,《集古》屢獲異文,并來書集入錄中,以為子孫之藏也。”得古器銘文,欣喜若狂之態,躍然紙上。
歐陽公學書和集古,不單純是藝事,同時是感悟人生、體認圣賢和弘揚盛德,是一種道德修煉。歐陽公認為,古人書法承載的是圣人之學、君子之品。跋《衛秀書梁思楚碑》:“書譬君子,皆學乎圣人。”跋《唐顏魯公書殘碑二》:“余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跋《唐郎穎碑》“是以君子貴乎博學。”可以想見歐公集古行為,欲以成博學君子。歐公集古,亦是君子多見博聞理想之踐履:《叔高父煮簋銘》并錄劉敞、蔡襄對《煮簋銘》的解讀,“以見君子之于學,貴乎多見而博聞也”。
歐陽公在《集古錄跋尾》中喋喋不休反復多次說他的集古行為“不為無益”。例如,《后漢西岳華山廟碑》說“余之《集錄》不為無益”;《后漢孫叔敖碑》感慨“謂余集古為無益,可乎?”說話聽音,我們推測一下,他為何要不斷叨嘮此意,無非是世人不理解、不贊同,他才表白;自己對其價值,不夠自信;或者自己自信,而社會還沒有接受,才反復申說。從這個角度,說明其集錄行為的開拓性,為前人之未有。《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佐證:“自慶歷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唯恐不及,是又可笑也。然則字書之法,雖為學者之余事,亦有助于金石之傳也。為仆不朽之托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與馮章靖公書(七)》:“承惠寄碑刻,既博而精,多所未見,寡陋蒙益,而私藏頓富矣。中年早衰,世好漸薄,獨于茲物,厥嗜尤篤。而俗尚乖殊,每患不獲同好,凡如所惠,僅得二三,固已為難,而驟獲如是之多,宜其如何為喜幸也。”《后漢樊常侍碑》跋說:“初不見錄于世,自予集錄古文,時人稍稍知為可貴,自此古碑漸見收采也。”此亦可見其集古行為帶動風氣。
集古到底有何益處?本文認為,大體有以下幾種:
(一)文獻價值與史學意義
今人余敏輝教授說:歐陽修的《集古錄》具有很高的歷史資料價值與書法藝術價值,尤其是利用金石銘刻“與史傳正其闕謬”。余敏輝其價值歸納幾條:證史之誤、補史之闕、糾史之妄、考索典制、評議人物。[6]余著于此敘論甚為詳盡,本文從略。
(二)文學價值與古文意義。
歐陽公推崇唐代書法,但并不認為當代(宋)事事不如唐人,比如,對于文章的盛衰,他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而有深入思考。他認為盛唐時社會達于致治,而文章不振。從集古發現文運與國運、文化發展與經濟發展不一致,文運具有漸變性,不可一蹴而就。跋《隋太平寺碑》:“南、北文章至于陳、隋,其弊極矣。以唐太宗之致治,幾乎三王之盛,獨于文章,不能少變其體,豈其積習之勢,其來也遠,非久而眾勝之,則不可以驟革也?是以群賢奮力,墾辟芟除,至于元和,然后蕪穢蕩平,嘉禾秀草爭出,而葩華美實,燦然在目矣。此碑在隋,尤為文字淺陋者,疑其里巷庸人所為。然視其字畫,又非常俗所能,蓋當時流弊,以為文章止此為佳矣。”此段文字簡評南朝至唐元和年間文運,言簡意賅,至為的當。又如跋《唐元次山銘》:“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代(應指南朝和隋朝)之弊。既久而后,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又難也。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可謂特立之士哉!”跋《唐德州長壽寺舍利》亦有以上言論,還從碑文“浮云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發現王勃《滕王閣序》“落霞、秋水”乃初唐流行句式。跋《唐辨石鐘山記》:“覽三子之文,皆有幽人之思,跡其風尚,想見其為人。”這些文字說明,歐陽公集古的關注點是多方面的,不僅僅在字的藝術,更在其所承載的內容和意義。
就書法與文章之關系而言,歐公認為,文因直接載道,處于本之位,書法為末藝。跋《陳張慧湛墓志銘》:“陳、隋之間,字書之法極于精妙,而文章頹壞,至于鄙俚。豈其時俗弊薄,士遺其本而逐其末乎?”
跋《田弘正家廟碑》:“昌黎先生撰。余家所藏書萬卷,惟《昌黎集》是余為進士時所有,最為舊物。自天圣以來,古學漸盛,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為善本。及后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者如《羅池神》《黃陵廟碑》之類,以校余家集本,舛繆猶多,若《田弘正碑》則又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余以碑校集印本,與刻石多同,當以為正。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讎之際,決于取舍,不可不慎也。”此則可見古文運動趨勢。從集古數量看,歐公集古最為集中的是三代銘文、顏真卿書碑和韓愈文章。集錄文字,歐公多稱“古文”,其所倡“古文運動”當與此相關聯。跋《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集》今大行于世,而患本不真。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為正,然時時得刻石校之,猶不勝其舛繆,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為玩好而已。”歐陽公發現先秦古文,質直簡古,例如,稱《敦銘》“器古文奇”。此“文”,既是文字,亦是文章。
從以上例文可知,歐陽公集錄古文,是在為古文復興尋找資料借鑒,他的集古行為是北宋古文運動承續先秦古文、韓愈古文的實踐。
《集古錄跋尾》不少篇堪稱精美雋永的小品文,是被忽略的古文作品。
(三)思想價值與儒學意義
歐陽公是一位醇儒,一生堅持儒家信仰,辟佛批道。他極力推崇顏真卿,正是基于儒家價值觀。他集古不棄佛道碑帖,非為信其內容,而是出于好古癖,出于對史料的保存和書法藝術的珍惜。他在含有佛道內容的題跋中總是急急表白此意,跋《唐司刑寺大腳跡敕》:“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刑獄慘烈)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有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歐陽公將此碑銘作為反面教材,起警示作用。跋《唐鄭預注多心經》:“釋氏之書,因字而見錄者多矣。”跋《唐徐浩玄隱塔銘》:“嗚呼!物有幸與不幸者,視其所托與其所遭如何爾。《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圖、老子以托于字畫之善,遂見珍藏。余于《集錄》屢志此言,蓋慮后世以余為惑于邪說者也。”此二則,強調好的書法,有利于思想的保存和傳播。不忘撇清自己集錄有關佛老的字,不是因為惑于佛老,而僅僅是為留存其字。他感慨“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病畏死,則歸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往往如此也。可勝嘆哉!”跋《唐磻溪廟記》批判高駢迷信道教,“貪心已動于內,故邪說可誘于外,內貪外誘,則其何所有而不為哉?”
史上韓柳并稱,但是歐陽公出于捍衛儒家思想,尊韓而抑柳,因為柳宗元有佛家色彩。跋《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后世稱為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為道不同,猶夷夏也。”跋《唐南岳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后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
(四)碑帖保存與考辨價值
《集古錄》第一屬性,是書法史料的集成,保存了自古至北宋初年很多書法真跡。若不是歐陽公的集錄,很多器銘碑刻我們今天看不到了,就連歐陽公時代的北宋人,學習書法也少了很多優秀范本。本文僅舉其大端。
金石學本來建立于劉敞、歐陽修二人。劉敞著《先秦古器記》收錄“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使工模其文,刻于石”。[7]可是,今天在劉敞的文集《公是集》里所見《先秦古器記》僅僅幾百字,大約是序言,刻工所模刻之科斗書皆不見,大約失傳。而劉敞贈送給歐陽修的古器銘文字,尚存于《集古錄跋尾》,前幾篇皆是:《古敦銘(毛伯敦、龔伯彝、伯庶父敦)》《韓城鼎銘》《商雒鼎銘》《叔高父煮簋銘》等。尚有一些前漢銘文碑刻,歐陽公尋求不得,也得自劉敞饋贈,得以集錄傳世。今言金石學,必祖于歐陽公,實賴公是之助。
跋《唐吳廣碑》:“碑字稍磨滅,世亦罕見,獨余《集錄》得之,遂以傳者,以其筆畫之工也。故余嘗為蔡君謨言,書雖學者之余事,而有助于金石之傳者,以此也。”此則最典型地說明歐陽公保存古人書法之功。
《后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即今流行之《乙瑛碑》。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漢乙瑛碑》稱:“自歐陽修《集古錄》以后,此碑迭經著錄,對后世影響很大。”跋《隋龍藏寺碑》“字畫遒勁,有歐、虞之體”,古吳軒出版社2009年版介紹,此碑首次著錄于歐公《集古錄》。由此,又可見歐陽公存古之功。

《乙瑛碑》

《隋龍藏寺碑》
跋《唐王師乾神道碑》記載一段當時學書故事,頗能代表歐陽公集古搶救保存古人書法資料對于其時代書法學習的影響:“張從申書。余初不甚以為佳,但怪唐人多稱之,第錄此碑,以俟識者。前歲在亳社,因與秦玠郎中論書,玠學書于李西臺建中,而西臺之名重于當世。余因問玠,西臺學何人書?云學張從申也。問玠識從申書否?云未嘗見也。因以此碑示之,玠大驚曰:‘西臺未能至也!’以此知世以鑒書為難者,誠然也。從申所書碑,今絕不行于世,惟予《集錄》有之者,《吳季子碑陰記》《崔圓頌德碑》并此才三爾。”搶救瀕臨失傳之碑,供當時人臨習,使時人之師法從宋人前輩直追唐人,探本究源,進入更高境界。

李建中《貴胄帖》
歐陽公《集古錄》著錄唐人碑帖最多,跋《唐陽武復縣記》:“余家《集錄》千卷,唐賢之文,十居七八。”歐陽詢為其祖上先賢,尤為偏愛,跋《唐歐陽率更臨帖》:“吾家率更蘭臺世有清德,其筆法精妙,乃其余事。豈止士人楷模,雖海外夷狄,皆知為貴。而后裔所宜勉旃,庶幾不殞其美也。”跋《唐辨法師碑》:“其書有筆法,其遒勁精悍,不減吾家蘭臺。意其當時必為知名士,而今世人無知者……蓋其不幸湮沉泯滅,非余偶錄得之,則遂不見于世矣。乃知士有負絕學高世之名,而不幸不傳于后者,可勝數哉!可勝嘆哉!”于此又可見其集古行為,是出于對美好事物的哀憫憐惜之心。
著錄張旭楷書《唐郎官石記》,稱“可愛”,罕見珍貴。此帖今尚印行。著錄《唐孔子廟堂碑》《唐九成宮醴泉銘》《唐孟法師碑》,今日尚流行。

張旭《唐郎官石記》

褚遂良《唐孟法師碑》
著錄《唐大照禪師碑》《唐崔潭龜詩》,皆言唐朝八分書(隸書、分書)名家四人而已:韓擇木、李潮、蔡有鄰、史惟則。前者惟則書,后者蔡有鄰書。《唐植柏頌》為李潮書,“為僅有,亦皆后人莫及也。不惟筆法難工,亦近時學者罕復專精如前輩也”。這些,今日大約失傳,今人感覺陌生,但歐陽公為宋人保存唐人作品,豐富宋人藝術寶庫,為宋人學書提供更多可以借鑒的風格。
唐人碑帖集錄最多的,還是顏真卿的,如《唐顏真卿書東方朔畫贊》《唐畫贊碑陰》《唐顏魯公題名》《唐顏真卿麻姑壇記》《唐中興頌》《唐杜濟神道碑》等,有的今日尚存,有的已經失傳。

顏真卿《東方朔畫贊》
大量唐代著名文人碑帖及其文字,歐陽公著錄之,今雖失傳,但讓我們有所了解,例如:顏師古、李百藥、唐玄宗、元結、韓愈、柳宗元、歐陽詹、陸贄、陸羽、李白、楊炎、樊宗師、李德裕、李宗閔、李紳、劉禹錫、裴休、令狐楚、權德輿、高駢,等等。
歐陽公在經學上持疑古態度,信經疑傳,對于古碑刻亦不輕信。例如《石鼓文》,他存疑,“退之(韓愈)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對于《秦嶧山碑》,歐陽公跋曰:“(鄭)文寶云是(徐)鉉所模。文寶又言,嘗親至嶧山訪秦碑,莫獲,遂以鉉所模刻石于長安,世多傳之。余家《集錄》別藏泰山李斯所書數十字尚存,以較模本,則見真偽之相遠也。”此則說明,歐陽公通過持疑辨偽,集錄了更為原本的碑帖,有存古之功。
歐陽公發現,當時流行的所謂晉人法帖,應是唐人所臨摹,不可能是晉人真跡。這又是疑古一表現。例如跋《晉王獻之法帖》:“獻之帖蓋唐人所臨,其筆法類顏魯公。”《瘞鶴銘》:“《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黃庭經》:“書雖可喜,而筆法非王羲之所為。余非學異說者,哀世人之惑于繆妄爾。”《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偽也,蓋唐世寫經手
其實,《集古錄》首先是一部歷代碑帖集,是一部書法作品總集;《集古錄跋尾》在廣收博采的基礎上考證、鑒別和鑒賞,進而發評論,是一部圖文并茂的書法簡史,或曰書法史評論集,其價值在于書法理論和書法史論方面的獨特貢獻。黃庭堅說歐陽公“喜論古今書”,《集古錄跋尾》可謂正是集中表現。
歐陽公在《集古錄目序》中說:“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后,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但我們今天看到的《集古錄跋尾》和《集古錄目》依朝代先后編目,次序井然。今人知識視野中的書法史上重要碑帖,按照朝代先后赫然在目。筆者所依據版本,《集古錄跋尾》為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和巴蜀書社版李之亮《歐陽修集編年箋注》;歐陽棐編《集古錄目》為清朱記榮編刻《行素艸堂金石叢書》本。有序編目與歐陽公自己所云“無時世之先后”不一致。
《集古錄跋尾》并非專門的書法評論,而是對歷史人物、事件、文獻、人情風俗等隨筆式即興點評或者考辨,但對書法藝術的片言只語的點評,往往能抓住特征,讓人對書法作品有一種大概的認識,受到審美的啟發;將其連串起來,能對書法的時代風格有一些形象記憶,對書法史輪廓有一些印象。
歐陽公對先秦器銘和兩漢碑刻的題跋,注意力主要在史跡考證、人物考辨、文字辨識上,對于文字藝術的評論,極為簡略,如評先秦器銘,“器古文奇”(跋《敦銘》)可以概之;評漢碑“文字古質”(跋《后漢郭先生碑》)、“筆畫頗奇偉”(跋《后漢秦君碑首》)、“體質淳勁”(跋《后漢殘碑》)、“近古簡質”(跋《后漢泰山都尉孔君碑》),皆能抓住主要特征。
評六朝及隋書法。跋《晉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其轉相傳模,失真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耶?”跋《宋文帝神道碑》:“南朝士人氣尚卑弱,字書工者,率以纖勁清媚為佳,未有偉然巨筆。”跋《陳張慧湛墓志銘》:“陳、隋之間,字所書爾。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書者,皆于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即知寫經手所書也。”今日坊間尚傳《遺教經》,有的版本仍標王羲之書,大約是為便于售賣,明知故犯。
(五)書法史評論和書法理論意義
書之法極于精妙,而文章頽壞,至于鄙俚。豈其時俗弊薄,士遺其本而逐其末乎?”皆能點明一個時代的總體風格。
評北朝書法。跋《后魏神龜造碑像記》評魏碑“患其文辭鄙淺,又多言浮屠,然獨其字畫往往工妙”“意其夷狄昧于學問,而所傳訛謬爾,然錄之以資廣覽也。”跋《魏九級塔像銘》“碑文淺陋,蓋鄙俚之人所為,惟其字畫多異,往往奇怪,故錄之以備廣覽。”跋《北齊石浮圖記》:“筆畫清婉可愛。”跋《后周大像碑》:“宇文氏之事跡無足采者,惟其字畫不俗,亦有取焉,玩物以忘憂者。”甘中流教授《中國書法批評史》認為,歐陽公是“北碑、隋碑之美的最早發現者”“《集古錄》對北朝碑刻書法給予的關注成為碑派書法潮流的前奏”。甘著也列舉了一些歐陽公跋語,可以參考。[8]
評唐朝書法。歐陽修對歐陽詢、虞世南、薛稷、顏真卿、柳公權、李邕、李陽冰,等等多有評點。前一節已談及,再看幾例:跋《唐玄靜先生碑》:“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為之篆額,時人必稱為二絕。”跋《唐滑州新驛記》:李陽冰篆,銘曰:“斯(李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后來者誰?后千年有人,吾不知之;后千年無人,當盡于斯。”歐公談經學時,曾言二千年后,有人知之,其語氣頗類于此。可見其集古所得,對于其思想、文章的影響。
《集古錄》著錄、評論柳公權碑頗多。跋《唐高重碑》:“唐世碑刻,顏柳二公尤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于臨時,而亦系于模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則常在也。此碑鋒力倶完。”跋《唐山南西道驛路記》:“公權書往往以模刻失其真,雖然,其體骨終在也。”這些跋語十分精彩。跋《唐鄭澣陰符經序》本文上篇已引述,還保留了與蔡襄的討論顏柳,十分珍貴。
歐公尤其推崇顏真卿。跋語對顏字推崇備至,跋《唐顏真卿麻姑壇記》:“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或疑非魯公書,余初亦頗以為惑,及把玩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后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志之,以釋疑者。”跋《唐杜濟神道碑》:“藝之至者,如庖丁之刀,輪扁之斫,無不中也。”
今人王鎮遠《中國書法理論史》論及歐陽修推崇顏真卿:歐陽修在唐代書法家中最重顏真卿,顏真卿的書法魅力,首先在于其人忠臣烈士之品格,其次在于具備法度。“歐陽修對唐人書法的肯定,尤其是對顏字的推重開啟了宋四家由唐溯晉的風氣,四家均取法顏書的事實足以說明歐陽修的理論不無啟導之功。”[9]此說不無道理,但太過絕對和夸張了。蔡襄雖然比歐陽公年輕五歲,但是同年進士及第,他的書法歐陽修佩服得五體投地,肯定不是受歐陽公的影響。歐陽公之前五代的楊凝式書法就是學過顏體,張世南《游宦紀聞》卷十記載:楊凝式“筆跡遒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10]石曼卿年長歐陽公十三歲而英年早逝,歐公評石書“多得顏柳筆法”(《唐辨正禪師塔院記》跋),說明崇尚顏書,也并非啟導于歐陽公。當然,宋太宗命翰林侍書王著編纂的《淳化閣帖》沒有收錄顏真卿書法作品,此部歷代書法總集代表國家意志,也能反映宋初社會審美趣味,說明歐陽修之前文人總體傾向確實不崇尚顏真卿。顏真卿在北宋中期以后成為中國書法史上偶像級人物,與歐陽修近乎崇拜的表彰,不無關系。
評五代書法,尤見其時代風貌。例如,跋《王文秉小篆千字文》評論、比較分析前人書法:“文秉在江南,篆書遠過徐鉉,而鉉以文學名重當世,文秉人罕知者。學者皆云:鉉筆雖未工,而有字學,一點一畫,皆有法也。”跋《楊凝式題名》,“自唐亡道喪,四海困于兵戎。及圣宋興,天下復歸于治,蓋百有五十余年。而五代之際有楊少師(楊凝式),建隆以后稱李西臺,二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為一時之絕,故并錄于此。”此實為簡明書史,此段評論,《宣和書譜》照錄之,[11]可見歐陽公《集古錄》和書法評論的影響力。《宣和書譜》錄歐公之文,卻不列歐公為書家,亦見其列名標準之嚴。

楊凝式《新步虛詞十九章》
曹寶麟《中國書法史·宋遼金卷》論曰:歐陽修“提醒世人更需要注重比書法遠為重要的道德修養問題,歐陽修的這個思想,后成為蘇、黃等人評判前代書家的主要標準。”“宋朝到后歐陽修時代出現了尚意書風,絕非偶然,它與歐公導夫先路的理論貢獻有著明顯的因果關系。”[12]尚意尚德的書學思想,對后世產生重大影響。其實尚德尚意的理論,也非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近人弘一法師談書法,也很重意興逸氣,更重視道德及佛法。歐公為何尚意,如何尚意,曹著語焉不詳。
尚意,在歐公有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追求神似;一是講究逸興神會,感性之意無意為之。我們細讀《集古錄跋尾》,會發現,歐陽公是在廣覽、比對模刻的碑帖中發現“意”的。歐陽公發現,如果不領會碑刻背后書家之意,是不能欣賞書法之美的,因為刻工技法有工拙。跋《雜法帖五》:“古今事異,一時人語,亦多不同,傳模之際,又多轉失,時有難識處,惟當以意求之爾。”《跋尾》中對刻工模刻走形失真屢次談及。刻工傳模書家墨跡,或多或少總會走形,后世學習前人碑帖,如果拘于形似,難得古人真形,不如求古人之意。跋《唐高重碑》:“柳公權書。唐世碑刻,顏柳二公尤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于臨時,而亦系于模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則常在也。此碑鋒力倶完。”跋《唐山南西道驛路記》:“公權書往往以模刻失其真,雖然,其體骨終在也。”
歐陽公通過研讀晉人碑帖,發現書法總是率性而為更佳。如跋《晉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敘暌離、通訊問,施于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余興,淋漓揮灑,或妍或丑,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燦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后世得之,以為奇玩,而想見其人也。至于高文大冊,何嘗用此?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跋《唐僧懷素法帖》:“予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于家人、朋友,其逸筆余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跋《千文后虞世南書》:“虞世南所書,言不成文,乃信筆偶然爾。其字畫精妙,平生所書碑刻多矣,皆莫及也。豈矜持與不用意,便有優劣耶?”
德,也是一種“意”,決定著書法作品的體骨和品位。這是歐陽公欣賞顏真卿書法的體驗和發現。跋《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斯人忠義出于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跡,挺然奇偉,有似其為人。”跋《唐顏魯公書殘碑》:“余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他評南朝書法《宋文帝神道碑》:“南朝士人氣尚卑弱,字書工者,率以纖勁清媚為佳,未有偉然巨筆。”這是德與意的另一種氣質,書法作品呈現另一種形態。

薛稷《信行禪師碑》
跋《唐薛稷書》:“薛稷書刻石者,余家集錄頗多,與墨跡互有不同。唐世顏、柳諸家刻石者,字體時時不類,謂由模刻人有工拙。凡世人于事,不可一概。有知而好者,有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畫之為物,尤難識其精粗真偽,非一言可達。得者各以其意,披圖所賞,未必是秉筆之意也。昔梅圣俞作詩,獨以吾為知音,吾亦自謂舉世之人,知梅詩者,莫吾若也。吾嘗問渠最得意處,渠誦數句,皆非吾賞者,以此知披圖所賞,未必得秉筆之人本意也。”此篇含義豐富,是文藝鑒賞論的絕佳史料。碑刻與墨跡之不一致,俗謂走樣;懂得與愛好、欣賞,也不是一回事;欣賞(接受)與作者不一致。似此種種,都是各種“意”在起作用。
(六)集古行為的時代影響和歷史作用
《集古錄》對北宋書法的直接影響,更主要的在于歐陽公行為、活動本身:與一大批名公巨卿就書法之事密切聯系,廣泛交流,帶動社會風氣。歐陽修之集古,是非一人之功,多有朋輩之襄贊;集古的過程,亦收集了很多友誼和溫情;歐公將其事皆記于《集古錄跋尾》,共有32人。歐陽公在書信中還談及與集古相關的人物,如編《集古錄目》就是聽取友人徐子春意見而為之。《與劉侍讀書(二)》:“愚家所藏《集古錄》,嘗得故徐子春為余言:集聚多且久,無不散亡,此物理也。不若舉取其要,著為一書,謂可傳久。余深以其言為然,昨在汝陰居閑,遂為《集古錄目》,方得八九十篇。不徒如許之說,又因得史傳相參驗,證見史家闕失甚多。”他們討論的是書法,但不局限于書法,而是與文史、道德問題相關聯,擴大了書法作品的功能和意義,使書法與生活、學術融為一體,更易深入人心,更易傳播,產生影響。
最多最大的幫助來自大學問家劉敞。《古敦銘》跋記:“嘉祐中原父(劉敞)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讀古文銘識,考知其人事跡。而長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予方集錄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模其銘文以見遺。原父為予考按其事。”《敦銘》跋云:“余家《集古錄》自周武王以來皆有者,多得于原父也。”《前漢二器銘》跋記:“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求之久而不獲,每以為恨。友人劉原甫每以其銘刻為遺。既獲此二銘,由是始有前漢時字,以足余之所闕,而大償其素愿焉。余所集錄既博,而為日滋久,求之亦勞,得于人者頗多,而最后成余志者,原甫也,故特志之。”
太常博士楊南仲能識古文,幫助也很大,《韓城鼎銘》跋記:“原甫(劉敞)既得鼎韓城,遺余以其銘,而太常博士楊南仲能讀古文篆籀,為余以今文寫之,而闕其疑者。原甫博學,無所不通,為余釋其銘以今文,而與南仲時有不同。故并著二家所解,以俟博識君子。”《古器銘》跋云:“自余集錄古文,所得三代器銘,必問于楊南仲、章友直。”幫助歐公收集、模寫古文,或幫助考辨釋讀古文,多是博學通古的士人,或是高官顯宦,地位最顯赫的是三朝宰相韓琦。《唐顏真卿射堂記》“今仆射相公(韓琦)筆法精妙,為余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余。”《與韓忠獻王(韓琦)書(一〇)》:“前在潁,承示碑文甚多,愧荷之懇,已嘗附狀。今者人至,又惠《宋公碑》二本,事跡辭翰,可令人想慕。《張迪碑》并《八關齋記》,此之所有,聊答厚賜。”甚至有人主動將自己的藏品送給歐陽公,以求傳之久遠,可見歐陽公集古已經深入人心。《黃庭經四》跋:“得前本于殿中丞裴造。造,好古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于家,不若附見余之《集錄》,可以傳之不朽也。”
歐陽公求碑帖態度十分謙恭,真正不恥下問。《后漢橐長蔡君頌碑》記:“天章閣待制楊畋嘗為余言,漢時隸書在者此為最佳。畋自言平生惟學此字。余不甚識隸書,因畋言遣人之常山求得之。”討論、請教最多的是蔡襄,跋《隋丁道戶啟法寺碑》:“蔡君謨,博學君子也。于書尤稱精鑒,余所藏書,未有不更其品目者。”他自認蔡襄比他水平高,更內行,總是采納蔡襄的意見;《集古錄》收錄了蔡襄多篇題跋。
歐陽公跋《晉賢法帖》云:“把玩欣然,所以忘倦也。”跋《雜法帖四》云:“吾有《集古錄》一千卷,晚又得此法帖,歸老之計足矣。寓心于此,其樂可涯?”歐陽公聲名顯赫,幾十年孜孜不倦向人廣泛征求銘文碑刻,虛心求教書法問題,晚年更以讀碑賞帖、題跋習字作為人生精神歸宿,其行為、其人生觀對當時和后世書法時尚產生深遠影響,理在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