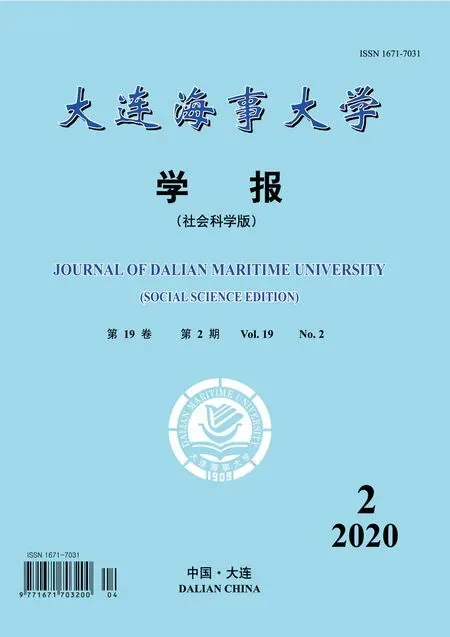危害人類罪的心理要件與成立邏輯探微
——兼論國際刑法研究的兩種思維誤區
馬永強
(北京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871)
在國際刑法中,危害人類罪不僅是“最惡之罪”,更是一類貫徹人道主義原則、維系人類良知底線的犯罪。2002年7月1日生效的《羅馬規約》在對傳統習慣國際法梳理和整合的基礎上,對于危害人類罪的概念和構成要件做了明確的界定。雖然我國并非國際刑事法院的成員國,但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羅馬規約》在國際刑事法院審判實踐中的反復適用,《羅馬規約》的內容將會發展成一種國際習慣法,從而對我國產生約束力。[1]因此,對《羅馬規約》中的危害人類罪進行理論探討具有重要意義。
對于國際刑法的解讀,可能存在兩種思維方式上的誤區。其中之一是以國內刑法的視角來研究國際刑法,另一誤區是,徑直以大陸法系的刑法思維來理解國際刑法。但實際上,《羅馬規約》對于危害人類罪的規定,在譜系上更多地承襲于英美刑法。喬治·弗萊徹教授曾指出,《羅馬規約》拒絕了德國理論發展的影響。[2]因此,僅僅以大陸法系刑法傳統視角來思考,可能會導致誤讀。尤其是在心理要件方面,《羅馬規約》延續了美國《模范刑法典》的要素分析法,這與大陸法系所采用的整罪分析法存在巨大差異。
本文試圖跳出上述兩種思維誤區,將文本分析與判例梳理相結合,遵循國際刑法與英美刑法的思維方式來審視危害人類罪。首先從心理要件這一角度切入,對心理要件的客觀要素以及心理要件的具體內容展開分析。而后進一步闡明危害人類罪的成立邏輯及保護法益,由精微處達致廣大,歸納危害人類罪的本質。
一、危害人類罪的心理要件概述
《羅馬規約》第7條第1款中對危害人類罪的心理要件做了界定,“危害人類罪是指在廣泛或有系統地針對任何平民人口進行的攻擊中,在明知這一攻擊的情況下,作為攻擊的一部分而實施的下列任何一種行為”。應如何理解本條規定,危害人類罪的心理要件僅僅是明知嗎?對此,有學者指出,關于危害人類罪的心理要件,《羅馬規約》第7條的規定并不完整,因為其對行為人的意志因素只字未提;第7條中的“明知”僅指行為人對非法行為及危害結果之外的某些背景、情節或者大環境(行為背景)的認識。至于對其意志因素的要求,應當遵循第30條的一般規定。[3]這一見解雖然仍是從大陸法系的整罪分析視角來理解《羅馬規約》,但其結論值得肯定。這一觀點正確地指出,第7條只是對危害人類罪的部分心理要件的規定。
如果運用要素分析方法,將危害人類罪的客觀要素拆分為行為要素、結果要素和情狀要素(包括但不限于背景要素),再來思考第7條的規定,會很明顯地發現,本條只是對于背景要素的心理要件的規定。根據國際刑事法院《犯罪要件》(Elements of Crimes)“一般性導言”第2項中的解釋,對于第7條沒有規定的部分,應當適用《羅馬規約》第30條。因此,本罪中的行為要素的心理要件是故意,結果要素的心理要件是故意或明知。這樣來看,在危害人類罪中,不同的客觀要素可能適用不同的心理要件,而非簡單的大陸法系意義上的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的區分。
《犯罪要件》也是按照這一方式展開的。首先,《犯罪要件》“一般性導言”第7項中對犯罪要件的組織順序做了明確。“犯罪要件一般按照下列原則組織:犯罪要件強調與每種犯罪相關的行為、后果和情況,因此一般按此順序開列;必要的心理要件,在受影響的行為、后果或情況之后列出;相關的背景情況在最后列出。”這一規定明確指出,心理要件在相對應的客觀要素(要件)之后列出。其次,危害人類罪具體罪行的犯罪要件中的最后兩項要件均為“實施的行為屬于廣泛或有系統地針對平民人口進行的攻擊的一部分”和“行為人知道或有意使該行為屬于廣泛或有系統地針對平民人口進行的攻擊的一部分”。(1)國際刑事法院《犯罪要件》第6條。《犯罪要件》第6條“危害人類罪”導言部分的第2項對此做了解釋:“每項危害人類罪的最后二項要件描述行為發生時的必要背景情況。二項要件明確規定參加且明知系廣泛或有系統地針對平民人口進行的攻擊為構成要件……”由此可見,最后兩項要件分別為危害人類罪的背景要件以及背景要件相對應的心理要件的規定。
以下,筆者結合國際刑事法院在Germain Katanga案判決書中對于相關法律問題的分析,以要素分析的方式,對每個客觀要素的心理要件進行細致探討,同時,對危害人類罪各客觀要件進行簡略介紹,以初步闡明危害人類罪的成立邏輯。
二、行為人實施的具體罪行的心理要件
(一)危害人類罪的具體罪行
在討論危害人類罪時,必須明確的是,危害人類罪規制的是具體行為人所實施的具體行為。因此,背景要件是成罪的必要條件,但卻遠遠不是充分條件。在危害人類罪的判斷方面,行為人所實施的具體行為才是討論的重心。并且,不應將行為人實施的具體罪行與背景要件混淆(2)W. Van Der Wolf: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International Courts Association, 2011, p25.:危害人類罪的具體行為不必是針對“平民人口”的攻擊,完全可以是針對一個平民的攻擊,只要行為人的行為屬于廣泛或系統的攻擊的一部分(3)Prosecutor v. Tadic (IT-94-1-A), Appeal Chamber, Judgment, 15 July 1999, Tadic Appeal Decision, para. 644-658.;整體攻擊行為需要與政策具有關聯性,但并不要求每一具體行為都與政策具有關聯性(4)Prosecutor v. Germain Katanga, Trial Chamber II, ICC-01/04-01/07,7 March 2014, para. 1115.;在特征上,具體行為也不必符合廣泛性或系統性的要求(5)Kunarac ICTY Appeal Chamber, 12.6.2002, para. 96; Blaskic ICTY, Appeal Chamber, 29.7.2004, para. 101.。在Germain Katanga案中,辯護人就試圖混淆行為人具體罪行和背景要件的特點,辯稱行為人實施的具體行為本身也必須是廣泛的或系統的,與政策相關聯的。(6)Prosecutor v. Germain Katanga, Trial Chamber II, ICC-01/04-01/07,7 March 2014, para. 1092.但是這一觀點顯然沒有正確理解危害人類罪各構成要件之間的邏輯關系,因而未被法庭采納。
《羅馬規約》具體規定了包括謀殺、滅絕、奴役、驅逐出境或強行遷移人口、嚴重剝奪人身自由、酷刑、性暴力、迫害、強迫人員失蹤、種族隔離、其他性質相同的不人道行為等11種危害人類罪的具體行為形態,指控行為人的行為成立危害人類罪,必須首先證明行為人實施了11種具體行為形態的一種或多種。(7)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第7條。然后,證明危害人類罪的背景要件的存在且行為人的行為可以被評價為該背景要件的一部分。在Germain Katanga案的判決書中,就首先對Katanga實施的五項具體罪行的客觀要件和主觀要件分別加以論證,而后討論行為人涉嫌的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的背景要件(其中判斷關鍵是有無廣泛或有系統地針對平民的攻擊,以及具體行為與背景要件的關聯性),最后對其個人應負的刑事責任加以論證。(8)Prosecutor v. Germain Katanga, Trial Chamber II, ICC-01/04-01/07,7 March 2014.
(二)具體罪行的一般心理要件剖析
1.《羅馬規約》第30條的內涵再詮釋
《犯罪要件》在對每一具體罪行的犯罪要件的界定過程中,也將背景要件加以列舉。在討論各個具體罪名共同的背景要件的心理要件之前,有必要先考察每個罪名中的具體罪行的心理要件。如前所述,如果在犯罪要件中沒有對具體行為形態的心理要件加以界定,則說明該行為的心理要件適用《羅馬規約》第30條的規定。亦即,對于行為要素,要求行為人存在故意;對于結果要素,要求行為人存在故意或明知;對于附隨情狀要素,要求行為人明知。
其中容易令人困惑的是為何對于結果要素要求故意或明知。原因在于,在《羅馬規約》第30條中,存在對于故意與明知的重疊立法,第30條第3款中對于結果要素的明知,實際上是包括在結果要素的故意之中的。因此,《羅馬規約》對于結果要素的要求可以被理解為故意或明知。(9)有觀點認為,關于故意與明知定義的重疊,僅僅是立法技術問題,在適用過程中并無障礙。具體參見文獻[4]。筆者贊同這一觀點。
Germain Katanga案中,國際刑事法庭對于結果要素的心理要件做了進一步的分析。國際刑事法庭認為,結果要素的心理要件包括兩個層次:一種是《羅馬規約》第30條第2款b項規定的,要求行為人有意造成該結果,這相當于大陸法系中的犯罪目的;另一種故意則是“意識到事態的一般發展會產生該結果”(10)Prosecutor v. Germain Katanga, Trial Chamber II, ICC-01/04-01/07, 7 March 2014, para. 774.。
一個重要問題是,這里的故意是否包括大陸法系故意理論中的“未必故意”(dolus eventualis)?對此,Lubanga案預審分庭認為,《羅馬規約》第30條除了意圖和直接故意以外,也包括明確屬于間接故意的情況。“即行為人已認識到發生結果之風險,卻聽任或同意結果發生”,但這一見解在國際刑事法院2009年審理的Bemaba案中被推翻。(11)可進一步參見Lubanga (PTC1), Confirmation of Charges, 29.01.2007, para. 352; Bemba (PTC II), Decision Pursuant to Article 61(7)(a) and (b)of the Rome Statue on the Charges of the Prosecutor Against Jean-Pierre Bemba Gombo, 15.06.2009, para. 360.[5]427-428在2014年的Lubanga案中,國際刑事法庭指出,由于第30條第2款b項旨在提供對于心理要件的另一條界定路徑,這一問題很難得出確切結論。(12)Prosecutor v. Germain Katanga, Trial Chamber II, ICC-01/04-01/07, 7 March 2014, para. 775.但從文本出發可以得出結論,這里的意識到事態的一般發展會產生該結果,指的是近乎確定但并非一定(near but not absolute certainty)會發生。因此標準是virture certainty,或者oblique intention。因此,這種形式的犯罪意圖的前提是,行為人知道其行為必然會引起該后果,除非有意外或突發事件干預或防止其發生。換句話說,行為人設想的結果不會發生幾乎是不可能的。(13)Prosecutor v. Germain Katanga, Trial Chamber II, ICC-01/04-01/07, 7 March 2014, para. 776-777.由以上國際刑事法庭對于結果要素的故意或明知的界定可知,無論是在《羅馬規約》還是在國際刑事審判實踐中,對于心理要件的界定都是極為審慎的,尚無充分理由表明《羅馬規約》第30條中的故意包括間接故意。
2.謀殺罪的心理要件:窄于習慣國際法
根據《犯罪要件》,謀殺行為是指,犯罪行為人殺害一人或多人。此外,謀殺罪《犯罪要件》的腳注部分指出,“殺害”一詞與“致死”一詞通用。本腳注適用于所有使用這兩個概念之一的要件。謀殺罪的犯罪要件并沒有進一步對謀殺行為的心理要件進行界定,由此可見,對于謀殺的心理要件,應該沿用第30條的規定。但是,根據習慣國際法,謀殺的心理要件可能更為寬泛[6]94。比如在“阿卡耶蘇案”中,謀殺的心理要件被定義為:在實施殺害行為時,被告或其下屬明知侵害身體的行為會導致被害人的死亡,卻不顧死亡是否發生;有意地殺害或者嚴重地傷害被害人的身體。(14)Prosecutor v. Akayesu (ICTR-96-4-T), ICTR(Trial Chamber), 2 September 1998, para. 589-590.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存在放任(recklessness / doluseventualis),也可以滿足謀殺罪的心理要件。
在Germain Katanga案中,法院認為行為人必須故意(deliberately)或者故意不采取行動,意圖使一人或者多人死亡,或者行為人意識到事態的一般發展會產生該結果。(15)Prosecutor v. Germain Katanga, Trial Chamber II, ICC-01/04-01/07, 7 March 2014, para. 781.由此可見,國際刑事法院完全依照了《羅馬規約》的心理要件的界定,排除了放任的情況可以滿足心理要件的問題,其在范圍上要窄于習慣國際法的規定。對此細微變化不可不察。
(三)具體罪行的特殊心理要件
對于某些具體罪行的成立,還要求《羅馬規約》第30條以外的特殊心理要件,包括犯罪目的、放任、特殊故意(special intent / dolus specialis)等。這些要件都被明確地規定在規約文本或者《犯罪要件》之中,主要包括以下類型。
1.特殊心理要件的要求與不要求
在國際刑法中,所謂的特殊故意,是指除了要求意圖通過實施某種行為引起一定結果(比如通過謀殺而致死亡),同時還要求行為人在超出結果之外追求一特定目的。這里的“特殊故意”與國內刑法中的犯罪目的沒有可比性。國際刑法中的特殊故意實質上并不是行為人對行為的“主觀”心理態度,這種態度主要表現在這一組織或政權的政策或計劃中。[7]
2.迫害罪中的歧視性理由
迫害罪中的歧視性理由是典型的特殊故意。在1994年的《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規約》第3條中,歧視性理由則成為一項針對所有危害人類罪具體罪行的普遍性要求。這就產生了歧視性理由是否屬于一般心理要件的問題。受到《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規約》的影響,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塔迪奇案”初審分庭采納了歧視性理由列入背景要件的做法。(16)Prosecutor v. Dusko Tadic (IT-94-1-T), Trial Chamber, Judgment, 7 May 1997, para. 652.在1999年上訴分庭的判決中,則又否定了這一見解,認為歧視性理由僅僅是針對迫害行為而言的。(17)Prosecutor v. Tadic (IT-94-1-A), Appeal Chamber, Judgment, 15 July 1999, Tadic Appeal Decision, para. 305.在“阿卡耶蘇案”中,盧旺達刑事法庭援引了“塔迪奇案”上訴分庭的意見,并在對一系列習慣國際法的梳理以后得出結論:不要求《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規約》第3條中的所有罪行都必須基于歧視意圖而實施。(18)Prosecutor v. Akayesu (ICTR-96-4-T), Trial Chamber, 2 September 1998, para. 447-469.因此《羅馬規約》將歧視性理由僅僅定位為迫害罪的要求,符合習慣國際法的發展趨勢。
三、危害人類罪的背景要素的心理要件
(一)背景要件:構成要素與判斷邏輯
危害人類罪與普通國內犯罪的核心區分乃是二者在時空特征上的不同。在危害人類罪中,所實施的具體行為必須是“廣泛或有系統地針對任何平民人口進行的攻擊的一部分”。如果在不具備這一時空特征的情況下就可以成立危害人類罪,可能涉及主權與人權的緊張關系問題。這一時空特征,對于危害人類罪、戰爭罪和滅絕種族罪的區別也有重要意義。[8]
正因為此,《羅馬規約》第7條第1款規定:“危害人類罪是指在廣泛或有系統地針對任何平民人口進行的攻擊中,在明知這一攻擊的情況下,作為攻擊的一部分而實施的下列任何一種行為。”第7條第2款進一步指出,“針對任何平民人口進行的攻擊”是指根據國家或組織攻擊平民人口的政策,或為了推行這種政策,針對任何平民人口多次實施第1款所述行為的行為過程。《犯罪要件》對此也做了進一步解釋。(19)參見國際刑事法院《犯罪要件》第7條導言部分第3項。因此,在《羅馬規約》中危害人類罪的成立,在背景要件(contextual element)上的要求是:存在廣泛或者有系統地針對任何平民人口進行的攻擊。攻擊還應同時具備政策關聯性。[9]與習慣國際法相一致,在《羅馬規約》的背景要件中,取消了危害人類罪與戰爭罪或者武裝沖突的關聯性(20)《紐倫堡憲章》與《東京憲章》要求危害人類罪與戰爭罪的關聯性,但隨后的習慣國際法中取消了這一要求;《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規約》中要求危害人類罪與武裝沖突的關聯性,《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規約》則并未要求,在前南國際刑事法庭的審判實踐中,也在實質上取消了關聯性要件,武裝沖突只是管轄條件而非實體性要件。具體可參見Prosecutor v. Tadic (IT-94-1-A), Appeal Chamber, Judgment, 15 July 1999, Tadic Appeal Decision, para. 249.。
在國際刑事法院審理的Germain Katanga案中,國際刑事法院對于如何判斷背景要件做出了明確闡釋:應當從三個邏輯層次來判斷是否符合背景要件。第一,存在一個根據國家或組織攻擊平民人口的政策,或為了推行這種政策,針對任何平民人口的攻擊;第二,這一攻擊在特征上是廣泛的或有系統的;第三,行為人具體行為與攻擊的聯系以及行為人的明知。(21)Prosecutor v. Germain Katanga, Trial Chamber II, ICC-01/04-01/07, 7 March 2014, para. 1097-1099.
判斷流程的第三個層次表明,行為人的具體行為應當與攻擊背景存在聯系,即應當區分整體攻擊行為與行為人實施的具體行為——整體攻擊未必都是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人只要參與了這一攻擊行為,并實施了《羅馬規約》第7條所列的具體行為,就可能成立危害人類罪。一言以蔽之,苦心孤詣地認定背景要件的關鍵意義在于,判斷行為人實施的具體行為能否被評價為攻擊的一部分,因為孤立的個人行為不可能成立危害人類罪。(22)具體可參見ICTY, Kunarac et al. Appeal Judgement, para. 99; Prosecutor v. Tadic (IT-94-1-A), Appeal Chamber, Judgment, 15 July 1999, Tadic Appeal Decision, para. 271-272; ICTR, Prosecutor v. Kajelijeli, Case No. ICTR-98-44A-T, Trial Judgement and sentence, 1 December 2003, para. 866; ICTR, Semanza Trial Judgement, para. 326.
(二)背景要件的心理要件:行為人對背景要素的明知
1.對于“攻擊”的明知程度及其判斷
之所以要求明知,是因為《羅馬規約》中采用的是個人責任原則。國際刑事法院認為,行為人對背景要件的明知是對行為人以危害人類罪追責的基礎,因為這說明了在攻擊背景之下的行為人個人責任。(23)Prosecutor v. Germain Katanga, Trial Chamber II, ICC-01/04-01/07, 7 March 2014, para. 1125.關于心理要件的證明,根據《犯罪要件》“一般性導言”第3項的規定,明知和故意的存在,可以從相關事實和情節推斷。關于明知的程度,根據《犯罪要件》,對于攻擊的明知,不要求必須證明行為人知道攻擊的所有特征,或國家、組織的計劃或政策的細節。(24)國際刑事法院《犯罪要件》第6條導言部分第2項。這一規定旨在減輕控方證明責任,如果危害人類罪要求行為人知道整個政策的細節,還會不當限制成罪人員的范圍。因為對于一項政策的具體細節,往往是直接參與政策制定的決策層人士才會知曉。
值得思考的是,行為人是否需要知道存在一項針對平民的政策?在背景要件方面,確實需要政策性要件的存在。但在背景要件的心理要件層面上,《羅馬規約》僅僅要求行為人明知存在攻擊。因而只要能證明行為人知道攻擊的存在,就不需要進一步證明行為人知道政策的存在。事實上,《犯罪要件》中對于政策要件的界定也是極為寬松的。《犯罪要件》規定,以平民人口為攻擊對象的政策一般由國家或組織的行動實施。在特殊情況下,這種政策的實施方式可以是故意不采取行動,刻意以此助長這種攻擊。不能僅以缺乏政府或組織的行動推斷存在這種政策。(25)國際刑事法院《犯罪要件》第7條導言部分第3項。因此,在政府不作為的情況下,只要行為人明知攻擊的存在,并且政府未采取行動,就足以滿足對于背景要件的明知,而不需要行為人具體明知政府不作為行為背后的政策。
此外,還需要考察,是否要求行為人明知攻擊是廣泛的或系統的?第7條中的明知僅僅針對攻擊的存在與否,而不針對攻擊的特點。因此,只需要證明存在對攻擊的明知即可,并不要求證明行為人明知其攻擊行為具備廣泛性或系統性的特點。[10]
2.對個人行為與攻擊的關聯性的明知
必須指出,第7條中的明知不僅要求對“攻擊”這一背景的明知,還要求明知自己的行為屬于攻擊的一部分或者自己的行為與攻擊這一大背景的關聯性。[6]99行為人的行為不能僅僅是出于純粹的個人動機而實施的。(26)Prosecutor v. Dusko Tadic (IT-94-1-T), Trial Chamber, Judgment, 7 May 1997, para. 656-659.換句話說,只要是行為人知道自己的行為屬于攻擊的一部分,即便是出于個人動機而實施該行為,也可以成立危害人類罪。由此可見,動機并非心理要件的內容,而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與背景要素的關聯性,則是背景要素的心理要件中最為核心的內容。對于這一問題,“塔迪奇案”上訴庭做了充分的論證。在“塔迪奇案”中,上訴庭援引了德國二戰期間的“K女士和P先生案”。在本案中,P先生出于擺脫妻子的個人動機,向蓋世太保告發其妻子K女士的反納粹言論,導致其妻受迫害致死。但德國聯邦法院認為,行為人的這一動機并不影響其符合危害人類罪的心理要件,動機與心理要件無關。在對一系列判例和習慣法的梳理之后,“塔迪奇案”上訴庭認為,要證明危害人類罪的成立,必須要證明行為人的具體罪行與針對平民人口的攻擊具有關聯性,并且被告人知道他的個人行為與攻擊之間具有關聯性。(27)Prosecutor v. Tadic (IT-94-1-A), Appeal Chamber, Judgment, 15 July 1999, Tadic Appeal Decision, para. 258, 271.在Germain Katanga案中,國際刑事法庭也指出,需要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具體罪行屬于攻擊的一部分,但不需要行為人完全認同該攻擊。僅僅需要證明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屬于攻擊的一部分,行為人的動機對于判斷其行為是否與背景要件有關聯性無任何影響。(28)Prosecutor v. Germain Katanga, Trial Chamber II, ICC-01/04-01/07,7 March 2014, para. 1125.
3.攻擊為新出現的情況時的心理要件
此處出現了一個重要的解釋學問題:《犯罪要件》中規定,如果廣泛或有系統地針對平民人口進行攻擊為新出現的情況,最后一項要件的故意要素是指,行為人是有意推行這種攻擊的,即具備這一心理要件的該當性。(29)國際刑事法院《犯罪要件》第6條導言部分第2項。這是否意味著,攻擊為新出現的情況時,行為人需要對攻擊具有故意?如果僅僅從文義解釋來看的確如此:如果要求當攻擊為新出現的情況時,行為人僅僅對該情況明知是不夠的,還需要對于該攻擊具有故意才能夠滿足主觀要件的要求。但這一解釋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界定“新出現的攻擊”?這種解釋顯然抬高了心理要件的入罪標準,會大大提升檢察官的證明責任。
對于《犯罪要件》的這一文本還可以做另一種解釋。即在這種情況下,與其說行為人對于攻擊具有故意的要求,不如說是行為人實施的具體行為有故意就已經足夠,因為只要行為人故意實施具體行為,就說明其是在有意推進整體攻擊過程,為整體攻擊過程“加功”。從目的解釋上來看,之所以《犯罪要件》如此規定,并非旨在抬高入罪門檻,而是為了說明:在通常情況下,不僅需要證明行為人明知攻擊的存在,還需要證明行為人的行為屬于攻擊的一部分。但在“攻擊為新出現的情況”時,只需要證明存在攻擊即可,而不需要證明行為人的行為屬于攻擊的一部分。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正以自己的具體行動表明,自己的行為與“廣泛或系統的攻擊”是緊密聯系的。國際刑事法庭在最近的判決中實際上也認同這一看法,其指出,雖然《犯罪要件》中提及了這一情況,但實際上不要求證明行為人意圖使自己的行為成為針對平民人口的攻擊的一部分。(30)Prosecutor v. Germain Katanga, Trial Chamber II, ICC-01/04-01/07,7 March 2014, para. 1125.
對比《羅馬規約》第7條第1款與第30條中的“明知”內涵,會發現在對背景或情狀的認識方面,前者具有更寬的范圍。第7條中的明知不僅是對背景情況的明知,還包括對于具體罪行與背景要件的關聯性的明知,這種理解是習慣國際法對于危害人類罪一般心理要件的一貫要求[11]。雖然第7條第1款對此表述并不明晰,但《犯罪要件》在每一具體罪行的最后一個要件中均載明:行為人知道或有意使該行為屬于廣泛或有系統地針對平民人口進行的攻擊的一部分。因此,在教義學上應當與習慣國際法和《犯罪要件》相一致,在理解第7條中的明知時應注意到其在明知范圍方面的特點。
四、危害人類罪的成立邏輯與保護法益
以上,從危害人類罪的各個客觀要素出發,完成了一場危害人類罪的心理要件之旅。至此,有必要進一步理順危害人類罪的成立邏輯。首先,依據個人責任原則,危害人類罪解決的是對于具體行為人的定罪問題。因此,首先需要行為人實施第7條第1款所列舉的11種行為的一種或多種;其次,行為人的行為必須是在第7條第1款中所規定的時空特征(針對平民的廣泛或系統的攻擊)之下實施的,并且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屬于攻擊的一部分,即滿足背景要件的要求。
如圖1所示,將危害人類罪的此種成罪邏輯與國內刑法中的構成要件相比較,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發現:國內犯罪的構成要件是單層次的,而危害人類罪的構成要件則是復合構造。在危害人類罪中,不僅要判斷個別犯罪行為(einzeltat)是否存在,還需要判斷該個別犯罪行為是否屬于整體行為(gesamttat)的一部分,后者是危害人類罪成立的前提要件。[5]488
在筆者看來,危害人類罪構成要件的復合構造,與危害人類罪所保護的法益相契合。根據《羅馬規約》序言部分,國際刑事法院建立的目的在于,有效懲治罪犯,使“危及世界的和平、安全與福祉”的“整個國際社會關注的最嚴重犯罪”的罪犯不再逍遙法外,從而有助于預防這種犯罪。由此可見,《羅馬規約》所保護的法益是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福祉。所謂福祉,是指人類的基本價值,即人類對于良好生活的美好向往和追求。在這一理想中,最為基本的理念是: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人的基本權利,人之作為人的生命、身體、自由以及人格尊嚴不容踐踏。在危害人類罪中,不僅世界的和平、安全受到了侵擾,更為重要的是,危害人類罪嚴重侵害了人的最低限度之尊嚴(尤其是生命、身體不受傷害和自由)。[12]
但仍須詳細辨別,作為危害人類罪保護法益的人的福祉,針對的是個人抑或是全體人類?對此,Satzger教授認為,危害人類罪是直接針對個人的犯罪。不過,個人只是危害人類罪的次要保護對象,因為這類犯罪之所以具有國際刑法上的重要性,在于其違反方式乃是“廣泛或有系統地攻擊平民”。在這種犯罪規模下,行為人單一行為造成的并非僅是一個個人法益受害而已,行為人以其犯行所侵犯的,乃是全球人類的最低人權標準。因此,全體人類才是危害人類罪的首要保護法益。[5]488韋勒教授也指出,對于危害人類罪來說,對世界和平、安全和福祉的威脅,就存在于對平民人口的基本人權進行有系統或者廣泛的攻擊之中。這種有組織暴力的背景,對人類本身提出了懷疑——在一種“人類共同存在的規則的最低標準”意義上。因此,這種犯罪不僅影響了個人被害人,而且影響了國際社會整體。除了這些超個人的價值之外,這個規范還保護個人的權利,也就是說,個人被害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尊嚴。[13]
結合成罪條件,危害人類罪立法保護的法益主要在于維護人道主義的最低人權標準,其次才是保障個人的權利。因此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不能是孤立的犯行,而是較為廣泛或者有系統地針對平民人口進行攻擊的行為。由于這些行為規模龐大且殘酷,或受害者眾多,抑或發生的時間及地點不同,卻重復同樣的攻擊模式,如此侵害的結果往往造成為數眾多的人喪失共同基本權益,影響甚大,才能構成國際法上的危害人類罪。[14]這正是為何危害人類罪比國內犯罪要多出一個背景要件的理由。
晚近以來,在學術討論中,也有基于人道主義立場的反對聲音認為背景要件的存在缺乏必要性:根據通說觀點,同樣的罪行(比如虐待或者強奸)構成一項普通罪行還是危害人類罪僅僅取決于這是否屬于廣泛或有系統的攻擊的一部分。而事實上,只要實施了這些具體罪行,無論是否屬于背景要件的一部分,都應該成立危害人類罪。這是因為,此類罪行均否定了被害人之作為人類的存在。[15]在筆者看來,這一觀點給人們的啟示在于,從性質上看,強奸、殺人的行為確實都是違反人道、危害人類的行為。但是,從規制方式上看,這些罪行并不需要動用國際刑法加以規制,只需要國內刑法加以處罰即可。危害人類罪的管轄范圍及認定標準要求犯罪必須是“廣泛或系統地攻擊”的一部分。在實踐中,只有大規模計劃犯罪或實施犯罪時才會受到起訴。[16]《羅馬規約》中危害人類罪的范圍不宜過分擴大,否則可能過分干涉一國的刑事管轄權。(31)梅爾教授指出:危害人類罪是針對基本政治體制的犯罪,其往往出現在失敗的國家或犯罪的國家。前一種情形中國家無法阻止這種攻擊,后一種情形中國家本身就在犯罪。由此,存在補充干預的需要。危害人類罪的概念作為一種標準,對如下情形是起作用的:只有在最嚴重罪行未被審理時,才允許國際法庭受理。[17]如果無視背景要件的要求,極有可能打亂國內刑法和國際刑法的不同分工,并影響國際刑法的實操性與國際刑事法院的權威。
五、結語:國際刑法研究的視角轉換
行文至此,再來重溫弗萊徹教授的觀點,或許會有一番新的體悟。弗萊徹教授指出,法律的思維也許是用個人主義的語言陳述,但是它的重心在于厭惡集體行為與集體罪責的想法。浪漫主義的思維與我們同在,即使她的聲音是微弱的并經常受到歧視。[18]學者們在構建國際刑法大廈時也面臨著這種糾結——國際刑法針對的是集體行為造成的災難,但歸責的主體卻是個人,在歸責根據方面,個人主義思想與浪漫主義思維相互纏繞。因此,國際刑法一方面需要確立個人責任原則,另一方面需要將個人具體行為評價為背景要件的一部分。正因為此,危害人類罪的構成要件才會是復合構造,心理要件對應的客觀要素不僅是具體行為,還必須包括背景要件。
綜上所述,通過對危害人類罪的心理要件與成立邏輯的剖析,會發現國際刑法的研究亟待我們轉換研究視角。一方面,國際刑法是不同法系、具有不同知識背景的法律學者共同創造的結晶,因而不能僅僅以單一的大陸法系視角來進行解讀。正如本文所述,《羅馬規約》中更多地呈現出英美刑法的影響。另一方面,與國內刑法的個人責任不同,雖然國際刑法也規定了個人責任原則,但此一國際刑法上個人責任的承擔,離不開特定的集體行為。因此,僅僅以國內刑法的單層次構成要件來理解國際刑法中各類犯罪的構成要件,難免會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對于國際刑法,應當超越自身的前見,從更廣泛更高遠的視角來審視它的本來面目,以洞悉其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