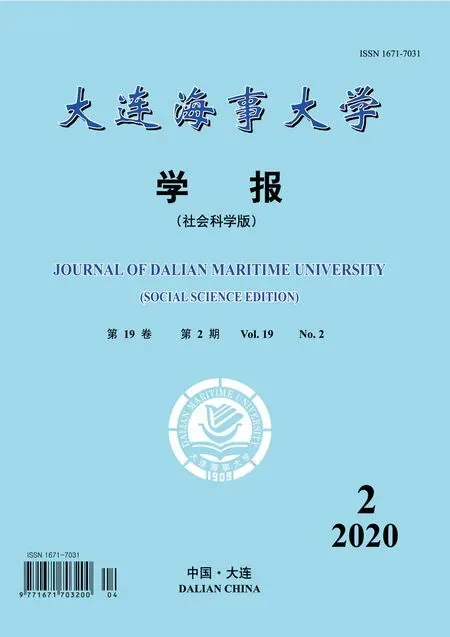國際法的形式淵源與實質淵源的重新審視
談晨逸
(華東政法大學 國際法學院,上海 200042)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西方社會發展出不同的學派來解釋國際法的效力根據問題,而這些學派對國際法淵源的解釋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例如,17至18世紀的自然法學派把上帝法、“理性”、“正義”、道德準則等描繪為國際法的淵源;到了19世紀,實在法學派取代自然法學派成為主流,認為國際法的淵源主要是慣例和條約,其次是一般法律原則,司法判例和“法學家”的學說也可作為輔助之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復興的社會連帶法學派和規范法學派也對國際法的淵源做出了不同的解釋。[1]52-74不同學派對“國際法淵源”的不同解釋直接影響了有關國際法淵源的一系列問題。本文將從實在法學派的角度出發,重新審視國際法的形式淵源與實質淵源之間的關系。
一、國際法淵源的內涵
任何法律都有它的淵源,但是,“法律的淵源”這個詞卻不是一個明確的、劃一的概念。[2]47在國際法上也一樣,不同的國際法作者像一般法律的作者一樣,使用“法律的淵源”一詞是有不同意義的。[3]17歸納起來,學界對“法律的淵源”的理解可以分為兩類。
從比較法的觀點出發,法律的淵源可以有幾個方面的含義:法律的歷史淵源;法律的理論或思想淵源;法律的本質淵源;法律的效力淵源。[2]47第一類學者認為“法律的淵源”一詞包含上述幾種含義。例如,詹寧斯指出法律的淵源的四種意義:(1)歷史意義的淵源;(2)作為識別法律規則的標準的技術意義的淵源;(3)法律的可接受的和被承認的有形證據;(4)制定、改變和發展法律的方法和程序。[2]47-48日本法學者廣部和也教授也提出過類似的觀點,認為法律淵源大體上有四種含義:(1)給予法律以拘束力的事物;(2)法律的產生和發展的主要原因;(3)法律的存在形式;(4)認識法規的資料。[4]但是,正如凱爾森所指出的,這種把“淵源”界定得如此寬泛的理解最大的弊端在于,法律的“淵源”一詞的含混不清似乎使這個術語變得不具什么用處。[5]由此,第二類學者認為,法律的淵源即指法律的效力淵源,而不包括其他非法學的意義。《奧本海國際法》(第八版)將“法律的淵源”定義為“行為規則所由發生和取得法律效力的歷史事實”。在其經典的“泉源”之喻中,法律規則被比喻成一股水,這股水從地面自然地流出的地方是它的淵源;同樣地,也可以說我們看到法律規則流在法律領域上,如果我們要知道這些規則是從哪里來的,就必須溯流而上,直到它們的起點,我們找到這些規則發生的地方,那就是它們的淵源。[3]17-18
筆者認為第一種觀點對“淵源”的理解遠離了這一概念提出的本意,淡化了它的法律意義。在國際法體系中,淵源的作用是提供組成這一體系的法律規則;如果沒有淵源能被找到證明某一規則的存在,那么就可以得出結論——這一所謂的規則并不存在。[6]13因此,國際法的淵源是用來認定國際法體系中的規則的:只有當某一規則被一項或更多的公認的國際法淵源所證實存在時,它才能被接受為國際法的一部分。[7]這正是法律規則的“淵源”這個概念的重要之處。它使法律規則得到認定并與其他規則相區別(特別是與應有法規則相區別),而且也涉及確立新的行為規則的法律效力和變更現行規則的方式。可見,法律效力是“淵源”這一概念不可或缺的一種特性。Schachter教授曾直接指出,“淵源”的理論是證明法律效力的客觀標準。[8]這就使國際法的淵源這一法律概念與影響國際法規則產生的其他非法學意義的因素相區別,避免在尋找某項規則的淵源的過程中對于應當追溯到何處存在不確定性,并使這種追尋具有法律意義。[9]基于上述原因,筆者認為對法律淵源的理解局限于法律的效力淵源更為恰當,贊同把“國際法淵源”定義為“國際法作為有效法律規范的表現形式”,即國際法淵源作為有效的法律規范表現為國際條約、國際習慣和一般法律原則。[10-11]
二、國際法的形式淵源與實質淵源的理論誤區
(一)國際法的形式淵源與實質淵源的內涵
一些國際法學者提出過國際法的形式淵源和實質淵源之間的區別,但不同的學者在使用這兩個概念時對它們的理解各不相同,主要爭議點集中在實質淵源的含義上。對于形式淵源的理解,盡管表述略有不同,但學界基本已形成一致觀點,認為它是指產生對特定對象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普遍適用的規則的法律程序和方法。(1)參見文獻[7]。同時參見文獻[12],“所謂國際法的淵源可以有兩種意義:其一是指國際法作為有效的法律規范所以形成的方式或程序”。文獻[13]第52頁,“國際法的形式淵源是指國際法規則由以產生或出現的一些外部形式或程序”。文獻[14],“形式淵源是法律規則取得其法律效力或拘束力的方式或途徑”。文獻[15]第23頁,“[The formal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law] is the source from which the legal rule derives its legal validity.” 文獻[16],“[The formal sources]consist of the acts or facts whereby this content, whatever it may be and from whatever material source it may be drawn, is clothed with legal validity and obligatory force.” 文獻[17]第71頁,“[Formal sources] confer upon the rules an obligatory character.”論及實質淵源,大多數學者認為它的作用是提供證明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普遍適用的規則已經存在的證據,(2)參見文獻[7],同時參見文獻[14],“實質淵源是某一國際法規則存在的證據,換言之,這些淵源提供了法律規則產生的背景資料,法律的制定者會根據這些淵源確定法律規則的內容和其背后的理念”。表明該規則的實質內容的出處。(3)參見文獻[15]第23頁,“[The material source] denotes the provenance of the substantive content of that rule.”文獻[17]第71頁, “[Material sources] comprise the actual content of the rules.”文獻[16],“[Material sources] represent, so to speak, the stuff out of which the law is made. It is they which go to form the content of the law...”按照這種觀點,當某一規則的形式淵源是習慣時,它的實質淵源可能是許多年前締結的雙邊條約、國家的單方聲明、司法判例等。[18]其他學者對于實質淵源的內涵還存在一些較為零星的不同認識。例如,李浩培教授認為“國際法的實質淵源是指在國際法規則產生過程中影響這種規則的內容的一些因素,如法律意識、正義觀念、連帶關系、國際互賴、社會輿論、階級關系等等”[13]52;趙理海教授則認為,實質淵源是指“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1]51。
前國際法院法官Fitzmaurice認為區別實質淵源與形式淵源的本質在于,前者是法律規則的內容產生的基礎,強調它對法律規則內容的形成所具有的影響;而后者是賦予該內容法律效力的方式,側重點是某項規則經過形式淵源的程序即具備了法律拘束力的特性,而不論該規則的內容為何。[16]之所以上述學者會對實質淵源的內涵存在分歧,主要是因為影響國際法規則內容的因素的范圍不確定,傳統理論把它局限于在法律領域影響國際法規則的內容的資料,而當代則有學者把實質淵源的外延擴展到道德和社會領域,如權力影響、文化沖突、意識形態的張力等。誠然,以上因素對國際法規則的內容都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后一種觀點中的道德和社會因素不屬于國際法學討論的范疇,反而把實質淵源與國際法的根據、起因、形成過程等概念相混淆,背離了區別形式淵源與實質淵源的目的。(4)參見文獻[6]第4頁,“Sometimes the word ‘source’ is used to indicate the ba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sometimes it is confused with the social origin and other ‘causes’ of the law; at others it is indicative of the formal law-making agency, and at others again it is used instead of the term evidence of the law... The distinction formal/ material is directed to avoiding this confusion.”因此,筆者贊同第一種觀點,認為實質淵源是國際法規則的實質內容的出處。而影響國際法的產生和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是國際法的起因(cause),并非實質淵源;[2]49國際法原則、規則和制度產生和發展的過程是國際法的形成過程,而國際法的淵源則是這一過程的最終結果;[19]44國際法的根據(basis)是國際社會的共同同意。[15]14
(二)形式淵源和實質淵源不是國際法淵源的分類
多數學者在區分了形式淵源和實質淵源后,很少提及它們與國際法淵源的關系。例如,周鯁生教授僅指出,“所謂國際法的淵源可以有兩種意義:其一是指國際法作為有效的法律規范所以形成的方式或程序;其他是指國際法的規范第一次出現的處所”[12],但并未闡明這兩種意義之間的關系,它們到底是國際法淵源的分類、組成部分還是另有其他關系。在討論到這個問題的學者中,大多數觀點認為,形式淵源和實質淵源是國際法淵源的分類。例如,李浩培教授提出“國際法的淵源主要可以區別為實質淵源和形式淵源兩類”[13]52。賈兵兵教授也將形式淵源和實質淵源認定為國際法淵源的分類。[14]但是,筆者認為將形式淵源和實質淵源認定為國際法淵源的分類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將形式淵源和實質淵源理解為國際法淵源的分類最明顯的瑕疵在于,這種分類是存在矛盾的。倘若形式淵源和實質淵源是國際法淵源的分類,那么它們首先必須都是國際法的淵源,可是,這一前提并未滿足。如上文所述,法律效力是國際法的淵源必備的一項特性,即所有的國際法淵源都必須是有法律拘束力的。但是,實質淵源僅僅提供證明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普遍適用的規則已經存在的證據,用以表明該規則的實質內容的出處,它只是在某一項國際法規則的淵源的形成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法律資料,并不具備其相對應的淵源所要求的法律拘束力。具體地說,對于“國際習慣”這一淵源而言,條約、司法判例、國家實踐、聯合國大會的決議等都可以是它的實質淵源,但是,在這種情形中,它們都不具備習慣作為普遍國際法的淵源所擁有的普遍拘束力。因此,如果將實質淵源理解為國際法淵源的一個種類,就會與淵源“法律效力”的特性產生矛盾,進而不難得出實質淵源其實不屬于國際法淵源的結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拘束力是相對于特定情形中的淵源而言的,而不是極端地認為實質淵源沒有任何拘束力。這個問題從淵源的作用的角度出發就能很容易理解了。由于淵源在實踐中的作用是判斷某一國際法規則對于特定的當事國是否有拘束力,因此,在上例中,盡管條約對于締約國是有拘束力的,但是,相對于具有普遍拘束力的國際習慣而言,它作為實質淵源不能約束第三國;(5)《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4條:“條約非經第三國同意,不為該國創設義務或權利。”反過來看,如果當事國就是條約的締約國,那也就沒有必要費力地證明某項國際習慣是所涉國際法規則的淵源了,直接以該條約作為淵源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第二,這種分類導致的一個后果是把形式淵源作為國際法的淵源,進而把國際法的淵源降級為淵源的種類。按照這種分類,有些學者便認為“國際法學者所注重研究的主要是國際法的形式淵源,因為只有研究這種淵源才能辨別一個規則是否是國際法規則”,進而把《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第1款前三項的規定視作國際法的形式淵源。[6]5[13]52但是,《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所列舉的國際條約、國際習慣和一般法律原則都是國際法院在裁判時所主要適用的淵源,而國際法院的作用是對提交給它的爭端依據國際法做出判決。由于根據《聯合國憲章》第93條,聯合國各會員國為《國際法院規約》之當然當事國,非聯合國會員國也可在滿足一定條件后成為《國際法院規約》當事國,因此,對于《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表達了它是國際法淵源的列舉這一普遍觀點的說法,學界基本沒有爭議。[17]70-71例如,布朗利和勞特派特都承認它是“國際法淵源的權威性定義”,[20-22]布賴爾利也認為它是關于國際法淵源的具有“最高權威的文本”。[22-23]所以,《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是國際法淵源的權威性說明,而不是國際法的形式淵源。[24]可見,如果把形式淵源和實質淵源作為國際法淵源的分類,就會使國際法的淵源這個上位概念降級為形式淵源這個下位概念,造成混亂。
第三,從分類的意義上說,也沒有必要對國際法的淵源進行分類。作為國際法的淵源,條約、國際習慣和一般法律原則并不依其列舉的次序而有等級的意義,這可以從《國際常設法院規約》草案第38條“依下列次序”的字樣在正式定稿中被刪去看出;事實上,這個次序只是為了敘述的方便,[13]54同時也代表著法官的邏輯階段,而并不表明淵源的層次的存在。[2]53所以,它們在被適用時對相關國際法主體具有相同的法律拘束力。既然它們在適用時沒有差異,那也就沒有必要對它們進行分類,又何存形式淵源和實質淵源是國際法淵源的分類一說?
三、國際法的形式淵源與實質淵源的理論辯證
既然形式淵源和實質淵源不是國際法淵源的種類,那它們與國際法淵源究竟是什么關系呢?筆者認為,形式淵源和實質淵源是國際法淵源的構成要件,它們不但組成了國際法的淵源,而且還確立了判斷某一規則的載體是否是國際法淵源的標準。
首先,重新回顧一下《奧本海國際法》(第八版)對“法律的淵源”的理解,該書認為“法律的淵源”這個名稱“用以指行為規則所由發生和取得法律效力的歷史事實”。[3]17-18這句話包含三層含義:第一,“行為規則所由發生的歷史事實”和“取得法律效力的歷史事實”分別對應的是“實質淵源”和“形式淵源”,前者表明了法律規則實質內容的出處,后者則是行為規則變為法律規則、取得法律拘束力所必經的法律程序;第二,“和”字前后的內容是遞進關系,即某一做法先經過國家實踐、國家的單方聲明或聯合國大會決議等過程形成行為規則,此時實質淵源已經產生,在此基礎上,這一行為規則須經過一定程序,在取得國家的同意后才能成為對其有拘束力的法律規則,這便是形式淵源所發揮的作用;第三,行為規則變為法律規則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這也是法律的起因與法律的淵源之間的區別。因此,從“法律淵源”這一概念本身出發,可以發現形式淵源和實質淵源并非為國際法淵源的種類,而是它的構成要件,只有當這二者都滿足后一項國際法規則的淵源才能正式形成,并且,它們在構成國際法淵源的過程中也是有先后順序的,實質淵源形成在先,形式淵源作用在后。
其次,將形式淵源和實質淵源作為國際法淵源的構成要件具有很強的實踐意義。一方面,對于條約、習慣這些已被公認的國際法淵源,形式淵源和實質淵源可用于證實(confirm)這些淵源的存在。例如,“滅絕種族是國際法上的罪行”這一規則的淵源是國際習慣,它的實質淵源包括1946年12月11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第96(I)號“關于滅絕種族罪的決議”、1948年12月9日通過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1993年《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規約》第4條、1994年《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規約》第2條、1998年《羅馬規約》第6條等。它們都表明滅絕種族是國際法上的一種罪行,必須予以懲治,是該規則實質內容的出處。最終使這一規則具有習慣法的普遍拘束力的因素是各國都認為其有法律義務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的事實。截至2019年11月,已有152個國家批準或加入《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6)參見文獻[25]。另外,“普林斯頓普遍管轄原則”(Princeton Principles on Universal Jurisdiction)第2條將滅絕種族罪列為國際法嚴重犯罪中的一項,也間接表明滅絕種族罪已被視為習慣法中的一部分。形式淵源的條件也已滿足。因此,懲治滅絕種族罪的習慣法規范確實存在。更為重要的是,《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不能被認為任何時候都必然是國際法淵源的詳盡陳述。過去50年來國際社會的最重要的變化是國際組織數目的增加和任務的發展,它們對國際法的淵源有很大的影響。[19]45國際組織的決議是否是國際法的淵源即是一個爭論較大的熱點問題。[26-28]此時,形式淵源和實質淵源作為構成要件可用于判斷《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之外的表現形式是否是國際法的淵源。以聯合國大會的決議為例,在考察時可以先看某一規則的出處,它可能是雙邊條約、國家實踐、國家的單方面聲明等,也可能是該決議本身。接著需看該規則是否已經經過一定的程序取得了法律效力。根據《聯合國憲章》,大會對于聯合國內部行政、財務事務等方面做出的決議有拘束力,換言之,將涉及聯合國內部行政、財務事務等方面的規定以大會決議的形式做出即能使其成為有法律效力的國際法規則,符合形式淵源的程序性要求。所以,關于聯合國內部行政、財務事務等方面事項的國際法規則,聯合國大會的決議可以成為其淵源。
四、結 語
國際法淵源是國際法體系的一個傳統理論問題,對國際法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有著重要的影響。通過重新審視形式淵源與實質淵源的內涵及其關系,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形式淵源與實質淵源是國際法淵源的分類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國際法淵源”這個概念本身是沒有必要進行分類的,而且,如此分類后不但存在邏輯上的矛盾,還造成了國際法淵源與形式淵源這兩個上、下位概念之間的混亂。第二,形式淵源和實質淵源可以被理解為國際法淵源的構成要件,這樣既符合淵源的內涵,也有助于發揮其實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