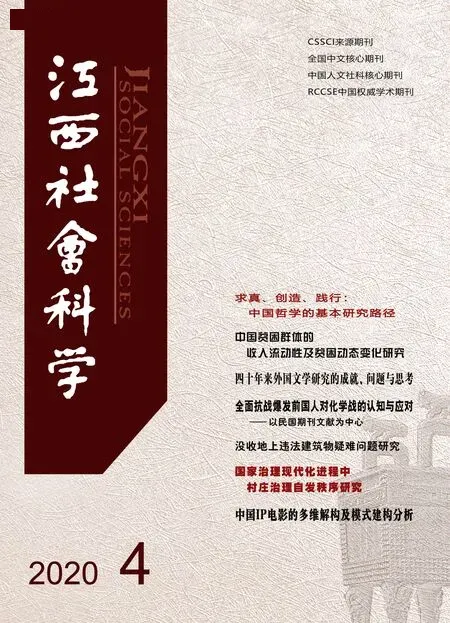中國貧困群體的收入流動性及貧困動態變化研究
■姚 嘉
在收入流動性視角下考察貧困問題,能夠更好地把握貧困群體的貧困動態變化及與社會整體收入變動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在1989年至2015年的20余年里,中國城鄉收入流動性出現兩個拐點,首先以2000年為拐點,收入流動性先上升后下降,其次以2010年為拐點,收入流動性表現出反彈上升趨勢。中國城鄉貧困群體的收入流動性與社會整體收入流動性表現一致,貧困粘性在21世紀初期經歷增加之后,2010年起呈下降趨勢,且絕對貧困人口大幅下降;但是貧困群體收入向上流動幅度低于整體經濟增長幅度,相對貧困持續率較高,社會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因此,在未來精準扶貧工作中,促進社會收入流動性增加,讓貧困群體有更多機會提升收入,實現收入向上流動,是高質量脫貧的關鍵。
一、引言
隨著我國脫貧攻堅戰以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推進,我國絕對貧困發生率大幅下降至4%以下,6000多萬貧困人口實現穩定脫貧;人均可支配收入穩定上升,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8228元,實際增長6.5%。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人民生活質量得到大幅提升。①但同時,中國基尼系數約在0.46左右,高的年份甚至接近0.5,處于國際慣例中的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區間;大量貧困群體雖實現了以絕對收入衡量的貧困-非貧困“量”的脫貧,但未實現“質”的脫貧,即雖然摘了“貧困帽”,但脫貧者生活質量仍然較低。未來長期內相對貧困問題將持續存在,我們需要警惕脫貧者脫離絕對貧困后再次返貧,個體及家庭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誰實現了“質”的脫貧?貧困者長期收入發展趨勢如何?貧困群體的貧困是暫時性的、持續性的還是已經實現了穩定脫貧?傳統基于基尼系數、泰爾指數等衡量方法的貧困研究將貧困人口作為一個整體,在某一時點上,對貧困群體的人口數量、群體分布,收入差距、貧困發生深度等進行測算,多為靜態研究[1],無法描述貧困的動態變化及發展趨勢,無法體現微觀群體(家庭或者個人)處于貧困狀態的時間長短、貧困進入與退出情況,以及前后兩期貧困群體是否為同一批人等。[2]收入流動性研究視角認為,如果貧困群體一直為同一批人,他們一直處于社會收入底層,無法實現收入向上流動,即使他們已經成為非絕對貧困者,但并不意味實現了真正的“有量有質脫貧”。
筆者基于收入流動性視角,考察貧困群體的貧困動態變化及與社會整體收入動態變化之間的關系,試圖為整體把握中國收入分配問題及貧困問題提供支撐,對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參考。收入流動性研究分析個體或家庭在觀察期間內,從前一時間段到下一時間段的經濟狀態變化。[3]收入流動性理論認為,即使一個地區或國家,在觀察的一段時間內,有較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但是如果社會有更大的收入流動性與這種不平等收入分配同時存在,且貧困群體具有提升自身相對收入地位、實現收入向上流動的機會及渠道,那么從長期來看,該社會的收入不平等性不一定會增加,其仍可能是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的社會。[3]因此,研究中國貧困群體的收入流動性,能夠為轉型發展中社會收入分配問題、貧困問題研究提供一個新視角。[4]研究中國社會收入流動性,尤其是貧困群體收入流動性,并將貧困群體收入性與社會整體收入流動性以及其他收入群體收入流動性進行比較,能夠為判斷貧困群體收入流動性是否合理[5][6],貧困群體是否實現了“質”的脫貧,社會成員是否公平地分享了經濟發展果實提供更多依據。[7]將收入流動性與貧困問題結合,在收入流動性視角下分析貧困動態變化,有助于避免特定戶或個體形成持久性貧困、代際貧困等各種貧困均衡狀態[8-10],是面對貧困發展新趨勢,推進當前脫貧攻堅戰的一個有效突破口[11]。
二、數據和研究方法
(一)數據及數據處理
筆者采用2015年發布的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CHNS調查每2至4年進行一次,包括從1989年到2015年,跨度20余年的10次調查數據,調查年份依次為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2009年、2011年、2015年,是中國目前追蹤調查跨度時間最長的大樣本數據庫,并且家庭追蹤情況良好,人口和家庭信息豐富,面板數據質量高,該數據能為本文研究微觀家庭長期內的貧困動態變化和收入流動性提供支撐。
為準確分析微觀家庭貧困動態變化情況,參照已有文獻數據處理方法[5],對CHNS(2015)數據進行如下處理:一是為去除極端異常值的影響,刪除人均收入位于最低1%與最高1%的家庭樣本。二是刪除缺乏地區信息、家庭人均收入、家庭成員信息等關鍵變量的家庭樣本。三是為使平衡面板數據中的歷年觀測收入數據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將CHNS歷年調查收入數據根據CPI折算到2015年獲得可比家庭人均收入變量,以計算城鄉家庭收入流動性及貧困動態變化。四是2011年調查和2015年調查因增加了省(市),導致樣本量有較大增加外,其余CHNS歷年調查樣本戶數比較平衡,城鎮調查戶數在1000~1300戶左右,農村調查戶數在2400~2900戶左右。2011年城鎮調查戶數增加為2450戶,農村戶數為3362戶;2015年城鎮調查樣本量為2413戶,農村樣本量為3314戶。
分析微觀家庭的收入流動性及貧困動態變化,需要構建平衡面板數據,本研究將CHNS相鄰兩個調查年份均出現的調查家庭的數據進行匹配,形成了9個平衡面板數據,每個平衡面板數據跨度在2至4年,將平衡面板數據中前后出現的相鄰兩個調查年份分別稱為起始年及終止年。
(二)研究方法
馬爾科夫轉換矩陣是收入流動性測度公理化的重要基石。[12]用轉換矩陣測度收入流動性時,需要將平衡面板數據調查時間分為前后兩期(起始年、終止年),每期收入從高到低分為若干組,從而形成具有不同等分位數的矩陣。矩陣中的Pij值代表在調查起始年位于某一收入分位的個體或家庭在調查下一期(終止年)流向其他收入分位的概率,本文采用的五分位數轉換矩陣如式(1)所示:

基于轉換矩陣,收入流動性測度公理化指標設置為[13]:


平均流動率是反映整體收入流動程度的指標,是同一調查對象的收入在前后兩期不同收入分位間流動的概率之和,平均流動率越小,收入流動性越小。
本研究基于轉換矩陣測度收入流動性,同時測算以上幾個指標,以確保測度結果的一致性與穩健性。
三、實證測度分析
(一)收入流動性測算及城鄉比較
基于轉換矩陣的城鄉收入流動性指標結果見表1,為進行直觀比較,繪制了中國城鄉收入流動性趨勢圖(如圖1所示)。結果表明,第一,從1989年至今,農村和城鎮地區收入流動性均出現了兩個拐點,一個拐點出現在2000年,另一個拐點出現在2010年。以2000年為拐點,城鄉收入流動性在1989年至2010年間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可能的解釋是隨著社會經濟高速發展,這一時期富有者因為原始資本積累及已有周邊資源變得更加富有,而貧窮者因缺乏機遇和政策難以實現收入向上流動,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收入分配有一定的固化傾向。但是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戶籍制度的放開以及脫貧攻堅戰略的開展,以2010年為拐點,中國城鄉收入流動性表現出反彈上升趨勢。收入流動性兩個拐點的出現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相吻合。第二,農村地區的收入流動性一直大于城鎮地區的收入流動性。城鄉收入流動性差距呈現出先擴大又縮小的趨勢。這是一個好的信號,說明城市發展更加開放包容,經濟社會發展更有活力,城鎮居民在經歷了收入分配固化傾向后,迎來了更多實現收入流動的機遇,給更多的低收入階層提供了收入向上流動的機會。

表1 1987—2015年中國城鎮和農村地區收入流動性

圖1 中國城鄉收入流動性趨勢圖
(二)貧困群體收入流動性及相對貧困動態性
2010年以來中國收入流動性增加的良性趨勢,是因為貧困群體的收入流動性增加了,還是因為其他收入群體的收入流動性在增加?回答這個問題能夠幫助我們分析貧困群體是否實現了可比收入的增長及“質”的脫貧。
本研究將處于五等收入分位中最低分位的群體作為貧困群體,分析處于這一收入分位群體的收入流動性變化趨勢及實現收入向上流動的概率,以判斷貧困群體的長期貧困動態性及貧困粘性的變化趨勢。
首先,農村及城鎮地區貧困群體收入流動性與前文分析的社會整體收入流動性表現一致,也存在兩個拐點。如圖2所示。一是進入21世紀后,伴隨著城鄉社會整體收入流動性下降,城鄉貧困群體的收入流動性也在降低,表現為圖中2000年至2010年間,位于收入最低分位的貧困家庭長期處于貧困狀態的概率加大,貧困粘性增加,貧困群體在這一時期難以實現收入向上流動,“質”的脫貧難以完成,而這種貧困粘性,很可能通過家庭行為、家庭脆弱性,家庭決策影響到代際發展,使子代重復貧困狀態。[14]二是以2010年為拐點,貧困群體收入流動性也在增加,表現為貧困群體長期處于收入最低分位的概率降低、貧困黏性降低,部分貧困群體實現了“質”的脫貧。為減少貧困群體長期貧困及貧困粘性上升,應瞄準長期持續相對貧困家庭進行干預,給予政策上的幫扶,尤其是給予貧困家庭能夠阻隔代際貧困傳遞的相關措施,如對子代的早期正規教育、心理干預、非認知能力提升、就業幫扶等,避免家庭持續貧困或者返貧狀況的發生。

圖2 貧困家庭貧困持續情況
其次,處于社會收入最高20%的富裕家庭的收入流動性變動也與社會整體收入流動性變動一致(見圖3),富裕粘性的變動與貧困粘性表現一致。即21世紀的初始十年,似乎呈現出社會各界擔心的窮者愈窮,富者越富的趨勢,在城鄉收入流動性降低的同時,位于收入分位兩端群體的收入階層也更加固化,收入粘性增加。但從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開始,我們能看到富裕粘性和貧困粘性均大幅下降,貧困群體實現了較好的收入向上流動,富裕群體長期位于收入頂端的固化情況也在改善。

圖3 富裕家庭富裕持續情況
最后,城鄉間收入流動性比較表明,在整體收入水平更高的城鎮地區中,城鎮貧困家庭持續停留在最低收入分位上的概率更高,即城鎮貧困家庭的貧困粘性和富裕家庭的富裕粘性均高于農村地區同等收入分位家庭。2010年起,隨著城鄉收入流動性的增加,城鎮富裕家庭收入持續停留在最高收入分位的比率下降幅度較大。但是,基于2015年CHNS數據,本研究測算的基尼系數為0.447,并且,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續增長的同時,農村地區仍有60%左右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農村平均收入水平,城鎮地區有55%左右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城鎮平均收入水平,人均收入被高收入者平均的現象反映了雖然貧困群體收入向上流動性在增加,但是收入流動性低于社會整體的收入流動性及經濟增長幅度,在整個經濟增長蛋糕中,貧困群體獲得的收入增長蛋糕份額少,相對持續貧困仍然存在,收入分配差距較大。以上人均收入的比較,未包括家庭所擁有的住房等財產,如果考慮存量,尤其是房產,城鎮收入分配差距將大幅增加,而農村地區因缺少可衡量的商品房等大型資產,分配差距將會更大。并且房產等固定資產具有很強的傳遞性,如以此衡量,社會財產收入流動性將大幅降低,貧困者難以實現財產性收入向上流動,將影響高質量脫貧的實現。
以上結果表明,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全體國民收入的大幅提高,城鄉社會收入流動性均有改善,但是收入流動性改善程度不同,貧困群體在整體經濟發展中,分享到的果實較少,貧困群體收入向上流動性滯后于社會整體收入流動性的增長幅度。并且,相較農村地區,城鎮貧困家庭在其所處的社會中,更難實現相對收入的向上流動,這與城鎮地區生活成本普遍較高,尤其是高住房成本有關,這也導致了城市外來人口難以融入城市生活,難以擺脫自身收入階層在城市實現收入向上流動。因此,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要實現高水平脫貧,政府應給予外來務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更多的廉租房、教育、平價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保障。城鎮居民內部收入差距如無法縮小,則外來人口特別是貧困人口將更難跨過門檻進入城市發展。提高城鎮地區收入流動性,促進外來人口融入城市發展、實現新市民對城市經濟發展果實的分享,是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構建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
(三)絕對貧困的動態變化
上文在收入流動性視角下,考察了相對貧困的動態變化,下文在給定以2015年不變價2300元界定的可比統一絕對貧困標準下,貧困家庭絕對貧困的動態變化。
研究將貧困家庭的絕對貧困變動狀態分為三種類型:一類是暫時性貧困(調查初始年時為貧困、調查終止年時非貧困),該類型貧困也稱為脫貧;二類是返貧(調查初始年時非貧困、調查終止年時陷入貧困);三類是持續長期貧困(調查初始年時貧困、調查終止年時也貧困)。第三類貧困家庭或群體,應成為未來精準扶貧工作中給予重點關注的對象。上述三類貧困群體的參照對象為“在調查前后兩期(長期中)”均為貧困群體。

表2 1989—2015年中國城鄉家庭貧困與非貧困的動態變化(%)
表2是1989年至2015年間城鄉家庭貧困與非貧困的動態變化情況。結果表明:第一,我國的絕對貧困主要發生在農村地區,農村地區的絕對貧困率和長期貧困率較高。第二,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農村地區貧困家庭的貧困形式主要為長期貧困,在所有貧困類型中,農村長期貧困家庭占比高達50%。第三,近10年來,隨著扶貧開發的推進,我國絕對貧困問題得到了極大改善,城鄉貧困比率都大幅下降,長期絕對貧困發生率也呈現快速下降趨勢,城鎮家庭長期貧困情況基本消除。第四,無論是城鎮地區還是農村地區家庭,在觀察的20余年里,家庭未發生貧困的概率均呈現上升趨勢,這與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及扶貧工作的開展,中國社會整體絕對貧困發生率下降相一致。第五,城鎮地區家庭返貧狀況逐年改善,城鎮貧困家庭脫貧比率呈上升趨勢,城鎮地區絕對貧困情況改善良好。相比城鎮地區家庭,農村家庭返貧情況的變動有所波折反復,農村地區家庭的絕對貧困發生狀態易呈現反復態勢,在扶貧過程中,對處于貧困線附近徘徊的農村家庭或剛脫貧、脫貧不久的家庭而言,相關部門更應警惕其因病、因殘等情況再次陷入貧困的問題。
綜上,不論是城鎮地區家庭還是農村地區家庭,長期絕對貧困發生率均呈現出下降趨勢,表明在整體收入增長及流動性改善的情況下,絕對貧困發生率下降,扶貧工作成效良好。但是需要注意,一是絕對貧困發生率受國家和當地貧困線的影響,隨著國民經濟水平提高,即使有些地區家庭或人口脫離了絕對貧困,但家庭購買力可能并未真正提高;貧困群體收入向上流動性雖在增加,但改善幅度滯后于社會整體向上收入流動性,貧困群體脫貧的“質”還有待提高,需警惕再次返貧的風險。二是雖然目前我國絕對貧困群體的貧困狀態以暫時性貧困為主,但是農村地區長期絕對貧困在總貧困中占比仍有10%,這表明在精準扶貧過程中,應瞄準長期貧困人群,攻堅長期持續貧困、代際傳遞貧困仍任重道遠。
四、結論
研究基于2015年CHNS數據,在收入流動性視角下,分析了1989年至2015年的20余年間,我國城鄉地區整體及貧困群體收入流動性的趨勢、特點、貧困的動態變化以及貧困群體收入動態性與社會整體收入變動的關系。研究表明,第一,從1989年至今,城鎮和農村地區收入流動性均表現出了兩個拐點,一個拐點出現在2000年,另一個拐點出現在2010年。以2000年拐點界線,城鄉收入流動性呈現出在1989年至2010年間,先上升而后下降的趨勢,即在1989年至2000年間,中國收入流動性呈上升趨勢,2000年至2010年間中國城鄉社會收入流動性呈下降趨勢。但是從21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即以2010年為拐點,中國城鄉收入流動性表現出反彈上升的趨勢。第二,農村地區收入流動性始終大于城鎮地區,城鎮內部收入分配差距更大。第三,城鄉貧困群體的收入流動性趨勢與城鄉收入流動性整體表現一致,近幾年貧困粘性降低,表明貧困群體的收入流動性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以及精準扶貧的開展開始反彈上升,貧困群體有更多機會實現收入向上流動,社會發展更加包容,經濟發展更具活力。第四,以絕對貧困線衡量的絕對貧困動態性結果表明,我國微觀家庭絕對貧困、返貧和長期貧困持續性均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絕對貧困消除率高。第五,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的動態變化結果綜合反映了,一方面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絕對貧困率大幅下降,絕對貧困治理效果好;但是另一方面,城鄉地區貧困群體的收入流動雖在增大、發展向好,但低于社會整體收入流動性的增加幅度及經濟增長幅度,社會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相對貧困持續率較高,尚未實現高質量的脫貧。第六,城鄉收入流動性及貧困動態變化比較結果表明,相比于經濟發展水平較弱的農村地區,城鎮地區的貧困粘性和富裕粘性更大,即在城鎮地區,富者越富,窮者一直窮的趨勢更明顯,貧困家庭更難在其所處的社會中實現收入地位向上流動。
在我國尚未形成擁有龐大中產階級的橄欖型社會之前,不僅要關注當前絕對貧困的消除,更要長遠考慮相對持續貧困問題及高質量脫貧。通過轉移支付使貧困人口暫時實現“量”的脫貧并非長久之道,應提高貧困群體可行的經濟獲取能力,內生發展動力,并給予其可實現收入向上流動的環境、政策。不僅要關注貧困群體收入上的貧困,也要注意就業能力、金融能力、身體可行能力等因素。對此,政府應該通過多渠道路徑進行貧困干預,如擴大基本公共服務覆蓋范圍,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城市應用各種有效手段和方式支持與扶持農村,特別是支持與扶助貧困地區和農村貧困人群。[15]只有多管齊下,促進社會收入流動性增加,讓進城務工群體、城市周邊人群更好融入城市生活,使貧困群體能夠通過外力作用和自身努力結合實現穩定脫貧,讓貧困群體有機會有渠道實現收入向上流動,公平合理地分享社會經濟發展果實,才能實現高“質”的脫貧。
注釋:
①資料來源于國家統計局2018年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