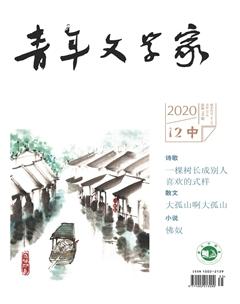《爾雅》在日本的傳播和影響
基金項目:江蘇大學2019年大學生實踐創新訓練計劃項目,項目編號: 201910299074Z。
摘 ?要:日本過去是漢字文化圈內的一員,曾將漢字作為本國的通用文字,漢字辭書也因此在日本流傳。其中,流傳到日本的《爾雅》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詞典,最早收錄于《漢書·藝文志》,在文字訓詁學方面有著重要的地位,對日本也有著廣泛而持久的影響。本文從爾雅的傳播歷史以及傳播影響方面入手,證實中國古代辭書對周邊地區文明的深遠影響力。
關鍵詞:《爾雅》;中國古代辭書;日本;傳播;影響;雅學
作者簡介:陳倩(1999.3-),女,漢族,江蘇南通人,江蘇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本科在讀。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35-0-02
引言:
日本與中國隔海相望,《山海經·海內北經》云:“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其中的倭就是日本,《原始秘書》言:“高麗之學始于箕子,日本之學始于徐福,安南之學始于漢立郡縣而置刺史,被之以中國之文學。”說明在公元前三世紀日本與中國就有了往來。
根據《爾雅》在日本傳播時代的不同,主要分為三個階段:傳播伊始——持續發展——再次發展。時間段主要是從日本的平安時代到近代。傳播伊始方面表現為被統治者所推崇;持續發展階段表現為各種模仿《爾雅》編纂的辭書出現以及雅學的萌芽;到再次發展時期,日本學者對于《爾雅》的整理、研究已經趨于成熟,形成了日本獨有的雅學氛圍。
一、《爾雅》在日本的傳播
(一)傳播伊始
《爾雅》傳入日本的時間至今眾說紛紜,有史可考的是,《爾雅》最遲在奈良時代已經傳入日本。日本元正天皇養老二年(718年),藤原不比等根據《大寶律令》修訂了《養老律令》,而《養老律令·課考令》中就保留了相關的史料:
凡秀才。試時務策二條。帖所牘,《文選》上秩七帖,《爾雅》三帖。其策文詞順序、義理懂當,并貼過者,為通。有義有滯,詞句不倫,及帖不過者,為不。帖策全通為甲。策通,帖過六以上,為乙。以外皆為不第。
由此可見,當時的日本社會將中國的經典著作作為選拔人才的重要標準。作為優秀文獻典籍之一的《爾雅》,則變成了培養和選拔人才的核心科目。當時,日本學者為了能夠讀懂漢字典籍,采用漢文訓讀的方式學習經書,從頭開始練習中文發音,教授發音的學者就被稱作“音博士”。
庚寅,玄蕃頭從五位上袁晉卿賜姓清村宿禰。晉卿,唐人也。天平七年隨我朝使歸朝,時年十八、九,學得《文選》《爾雅》音,為大學音博士。[1]
奈良時期,日本剛剛進入封建時代,為了鞏固天皇的統治,天皇下令編纂史書。和銅五年,太安麻呂獻創作《古事記》,養老四年,《日本書紀》完成。《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之后,日本雖說有了史學著作,但是產量還是不豐,急需修史的人才。
因此天平元年文章科就變成文學教育與史學教育的綜合。所學教材有三史,學教材有三史,即《史記》、《漢書》、《東觀漢記》,另有《三國志》、《晉書》為輔助教材以教修史之筆法,以《爾雅》、《文選》以教屬文之方法。
用《爾雅》來教授撰寫文章的方法,其道理在于爾雅中含有大量的詞匯,修史的學者只有在積累了一定詞匯量的基礎之上,行文時才能得心應手。尤其當時推崇唐詩的音韻以及對仗,遣詞造句的要求極為嚴格,學習《爾雅》就更為必要。
(二)持續發展
大同三年大學寮設立專門的紀傳科,將紀傳科從原先的文章科中獨立出來,選取《史記》、《漢書》、《后漢書》、《文選》、《爾雅》作為紀傳科的必學教材。
為了進一步的學習和認識雅學,日本的學者對雅學文獻開展了收集和整理工作,平安中期學者藤原佐世在《本朝見在書目》(又稱《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一書中共整理出雅學類書目11種。[2]這是日本雅學的開端。
日本平安時代中期,中國已經從盛唐變成了五代十國,氣象大不如前,日本也漸漸與中國疏離,官方外交越來越少,只有民間的僧人和中國還有所往來。因為外交的放緩,中國語的教學也受到了打擊,所幸的是,當時的日本典籍多為漢字書寫,雖然音讀已經衰退,但是《爾雅》作為解釋詞義的經典辭書,其地位猶在。
平安時期昌泰年間,日本僧人昌住用漢語寫成字書《新撰字鏡》,這也是日本第一本漢和字典。編排的體制跟中國舊日的字書頗有不同。既按偏旁部首排列文字,而又取同類事物的名稱編在一起,別為一部,和偏旁部首并列。[3]其取同類事物的名稱編在一起,和《爾雅》后十六篇按照事物的類別分別解釋事物名稱的方法有相似之處。
此外,在內容上,《新撰字鏡》引用了爾雅的釋義。比如《爾雅·釋訓》中的:“明明,斤斤,察也”在《新撰字鏡》中寫為:“明斤并察也”;“諸諸便便辯也”寫為“諸辨也”。
平安時代承平年間,源順應勤子內親王的要求編纂了《和名類聚抄》。其編纂方式受到了《爾雅》的影響,共分32部249門。書云:“卷中分部,部中分門,廿四部百廿八門,名曰《和名類聚抄》。”《和名類聚抄》除了借鑒《爾雅》的編纂方式,還直接引用了《爾雅》注釋共計101處[4]。《和名類聚抄》是日本的第一部類書,這說明在日本辭書編纂之初,主要還是依賴于中國的《爾雅》來進行編寫,《爾雅》辭書之祖之稱名不虛傳。
(三)再次發展
19世紀60年代末,日本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沖擊,開始進行明治維新改革。而后,日軍制定了《戰時清國寶物收集方法》和《敵產管理法》,規定收集到的圖書文物要立刻運回日本國內進行收藏。[5]在這樣的要求下,日本對于雅學的研究發了了改變,從將《爾雅》作為教科書和模仿《爾雅》編纂辭書變成了整理《爾雅》相關圖書和研究《爾雅》本身的價值。
日本在《爾雅》文獻整理方面主要在于保存和刊刻中國雅書,如后來被黎庶昌收入《古逸叢書》的高階氏所藏《爾雅》、羽澤石經山房刻景(影)宋本《爾雅》、神宮文庫藏南北朝刊本《爾雅》。
在刊刻方面,日本的著名文獻學家長澤規矩編有《和刻本經書集成》、《和刻本辭書集成》及《和刻本漢書分類目錄》,其中在《和刻本漢書分類目錄》,經部小學類訓詁下收18鐘和刻本雅學書目,其中《爾雅》6種,《爾雅注疏》6種,《小爾雅》4種,《廣雅》2種。[6]
二、《爾雅》在日本的影響
從奈良時代到近代,《爾雅》在日本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具體表現在科舉制度、辭書編纂和整理校勘和雅學研究等方面,其中雅學研究方面的影響最大,也最有意義。
(一)科舉制度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派遣遣唐使學習隋唐文化,645年大化改新之后,日本開始引進唐朝的律令制度。為了使唐朝的律令制度在日本得以實施,就必須培養大量的官吏人才,因此,公元670年左右,日本引進了唐朝的學令。
《大寶律令》的注釋書《古記》上記載:
“學生先讀經文”,謂讀經音也。次讀《文選》、《爾雅》音,然后講義。其《文選》《爾雅》音,亦任意耳。
平安初期的《穴記》則說:
“讀文”,謂讀訓亦帖耳。《考課令》進士條:“帖所讀,《文選》上秩七帖、《爾雅》三帖”,謂讀音帖也。醫生、大學生等之讀者,讀訓也。
結合以上內容可以知道,作為辭典的《爾雅》,依附于當時的學令,對學者的學習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后來日本考進士科的人漸漸變少,音讀慢慢式微,訓讀仍然挺立,這也為爾雅在引用和辭書編纂方面產生影響埋下了伏筆。
(二)辭書編纂
在辭書編纂上,日本的辭書編纂時喜歡應用《爾雅》的編寫體例,對事物進行分類,從而進行編纂。如寫于日本平安時代承平年間的《倭名類聚抄》,書中包羅萬象,引用了中國古代的詞匯訓釋方面的書籍。《玉篇》和《方言》也借鑒了《爾雅》的編寫結構,按照事物的分類來進行編纂,同時保留了自己的特點,添加了許多日本本土的解釋。
此外,日本辭書偏好借用《爾雅》的名稱來命名,如貝原好古編《和爾雅》(8卷),1694年刊行;新井白石編《東雅》(2卷),1717年刊行。當時這些日本辭書編者是把《爾雅》等作為辭典的同義語使用。[7]
除了仿制《爾雅》編纂辭書,日本還會在辭書中直接引用《爾雅》,如《倭名類聚抄》、《新撰字鏡》、《玉篇》、《和爾雅》等。日本平安藤原明衡編寫的《本朝文粹注釋》和日本第一部文學作品《古事記》中還直接用爾雅解釋文本。
(三)雅學研究
日本的雅學研究主要是從20世紀開始的,較為出名的由內藤湖南的《爾雅的新研究》,文中內藤湖南提出了兩種研究《爾雅》的新方法,并選取其中一種進行研究,得出了《爾雅》最早成書時間在七十子以后的結論。
此外,日本學者還對《爾雅》中的文化和物產也進行了相關的研究。在文化方面,日本學者根據《爾雅·釋親》中的解釋,對中國的家族制開展了研究,主要論文有諸橋轍次的《支那的家族制》、加藤常賢的《支那古代家族制度研究》。在物產方面,主要依附于《爾雅·釋木》進行研究,研究成果有松本洪《上代北支那的森林》和井坂錦江的《東亞物產史》。
除了對于《爾雅》本體的研究,對于注釋爾雅刊物的研究也有很多。其中,對郭璞注《爾雅》的研究為主,研究學者有加賀榮治,立石廣男等。
這些研究突破傳統,引入了西方語言學的研究方法,這些研究方法在后來傳入中國,為中國的學術開拓新思路。但日本的雅學研究和中國的雅學研究始終處在兩個獨立的圈子里,并沒有相互交流融合,這反映出中日學者交流較少的問題。
三、結語
《爾雅》的日本的傳播,最早可追溯到奈良時代,雖然在平安時代陷入了即將衰微的局面,但仍在文人學者心中占有一席之地。《爾雅》的生命力,主要表現在本身作為傳世辭書的優越性和對其他辭書的影響中。后期的《爾雅》則很少以原著的形式露面,大多是被引用和注釋在其他著作里。雅學在日本的傳播,不僅傳承了中國原本的文字訓詁學研究,而且在此基礎上加以創新,用社會學、語言學的視角去剖析《爾雅》。而今中日雅學的互相交流,也使雅學開拓了新的方向,反映出《爾雅》在漢字文化圈幾千年來不變的魅力。
參考文獻:
[1][日]菅野真道、藤原繼繩等《續日本紀》卷第三十五,雕龍一中國日本古籍全文檢索數據庫網路版,國內:古籍在線,日本:漠字情報HTTP://WWW.fan.co.JP/chis/).
[2]侯立睿.日本雅學研究綜述[J].語學教育研究所創設30周年,滕原印刷株式會社, 2015.
[3]周祖謨.日本的一種古字書《新撰字鏡》[J].文獻,1990(02):219-224.
[4]陳晨. 日本辭書《倭名類聚抄》研究[D].2014.
[5]農偉雄,關健文.日本侵華戰爭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破壞[J].抗日戰爭研究, 1994(3):84-101.
[6]侯立睿.日本雅學研究綜述[J].語學教育研究所創設30周年,滕原印刷株式會社, 2015.
[7]徐時儀.漢字文化圈與辭書編纂[J].江西科技師范大學學報,2015(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