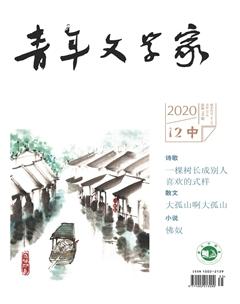詩歌翻譯的“信”與“美”
摘 ?要:“信”與“美”作為審美體系的重要理念,在詩歌翻譯中也具備重要意義。通過對比劉文飛與戈寶權對詩歌《囚徒》的兩種大相徑庭的中譯本,不僅有利于深入解讀《囚徒》的情感價值,還有利于闡釋“信”與“美”的深刻內涵,體驗二者之間的復雜關系,對詩歌的翻譯提供借鑒意義。
關鍵詞:信;美;《囚徒》;普希金
作者簡介:趙秋玲(1995.7-),女,漢族,四川攀枝花人,哈爾濱師范大學斯拉夫語學院碩士在讀,研究方向:俄羅斯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35--02
一、“信”與“美”
“信”與“美”源于中國的審美體系,古代翻譯家常用“信”與“美”的概念來評判譯文的優劣,揭示過程中內容與形式之間的對立統一。[1](70)“信”起源于中國傳統的“忠信”觀念,即強調誠信、忠實。此觀念引申到文學翻譯中,則強調翻譯要忠實于原文,保持原文的原汁原味,使讀者能夠深切體會到原文的風格意境。“忠信的”譯者強調“極大限度地貼近原作,‘言直理旨,不加潤飾”。[1](72)
“美”則強調譯文的整體效果,翻譯活動要達到“美”的效果具有一定的難度。在不同的語言文化和歷史背景下,要再現原文的“美”,并使讀者有所感悟,這對于譯者而言都存在一定難度。對于“美”的理解鄭海凌指出:“一是指文辭的華麗,二是就譯作的效果而言,指美好,完美”。[1](73)譯者會對譯文進行藝術性地再創作,改善其譯文效果,使其更貼合于讀者的閱讀習慣。
“信”與“美”作為兩種范疇,二者之間的關系模糊不定。但是早期二者之間的關系呈現相互對立的狀態,“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者”則講究語言的真實可靠,“美者”則講究語言的優美華麗,二者不可兼得。在中國,對于“信”與“美”的認識理解也是逐漸發展的,由重“信”開始意識到“美”的重要性,從馬建忠的“譯文與原作之間不得有絲毫出入”[1](75)到嚴復的“信、達、雅”理論,再到錢鐘書將“達、雅”包括進“信”,由此可看出,“信”與“美”的關系逐步由對立走向融合。對于二者的關系,筆者認為其不可割裂,譯者在講究“信”的同時也并未忽略“美”的存在,只是這種“美”與原文的整體更相似。同時,強調“美”的翻譯者也并未背離原文進行再創造。
本文旨在針對俄國著名詩人普希金的抒情詩《囚徒》,對比分析劉文飛與戈寶權的不同譯本,闡釋“信”與“美”在詩歌翻譯中的價值意義,并引發對詩歌翻譯的思考。
二、《囚徒》譯本對比分析
亞歷山大·謝爾蓋維奇·普希金(1799—1837)俄國著名詩人、作家。《囚徒》(?Узник?1822)屬于普希金創作晚期的作品,在沙皇專制的社會背景下,普希金敢于發表向往自由的詩作,因此觸怒沙皇,流放南方。詩人在流放時期遭到監禁,面對此情此景,詩人寫下《囚徒》詩篇:
Сижу за решёткой в темнице сырой.
Вскормлнный в неволе орёл молодой,
Мой грустный товарищ, махая крылом,
Кровавую пищу клюёт под окном,
Клюёт, и бросает, и смотрит в окно,
Как будто со мною задумал одно;
Зовёт меня взглядом и криком своим
И вымолвить хочет: ?Давай улетим!
Мы вольные птицы; пора, брат, пора!
Туда, где за тучей белеет гора,
Туда, где синеют морские края,
Туда, где гуляем лишь ветер... да я!..?
1822
普希金的詩歌在中國廣為流傳,諸多學者將其詩歌譯成中文,由于譯者之間的差異性,使得詩歌譯本也呈現不同的效果。我國學者劉文飛、戈寶權、谷羽等人都翻譯過《囚徒》,本文選取劉文飛(以下簡稱劉)與戈寶權(以下簡稱戈)的不同譯本進行對比分析,探討詩歌翻譯中的“信”與“美”的關系。以下為兩位譯者的譯文:
劉譯:我坐在潮濕的牢房的鐵柵旁。一只年輕的鷹,在監禁中被喂養,我憂郁的同伴啊,你在窗下,啄著帶血的食物,拍打著翅膀。∕它啄著,扔著,它望著窗戶,好像在與我想著同樣的心事。它在用目光和叫喊把我呼喚,它想說:“讓我們一同飛去!∕我們是自由的鳥兒;是時候了,兄弟!飛去云外那白雪皚皚的山岡,飛去那閃耀著蔚藍色的海洋,飛去那只有風兒……和我散步的地方!”[2](176)
戈譯:我坐在潮濕的牢獄的鐵柵旁,一只在束縛中飼養大了的年輕的魔鷲,它是我的憂愁的同伴,正在我的窗下,啄著帶血的食物,拍動著翅膀。∕它啄著,扔著,又朝著我的窗戶張塑,好像在和我想著同樣的事情。它用目光和叫聲召喚著我,想要對我說:“讓我們一同飛走吧!∕我們都是自由的鳥兒;是時候啦,弟兄,是時候啦!讓我們飛到那兒,在云外的山崗閃著白光,讓我們飛到那兒,大海閃耀著青色的光芒,讓我們飛到那兒,就是那只有風……同我在游逛著的地方!……”[3](33)
顯而易見,劉與戈的翻譯風格完全不同,下面通過對二者的譯文細節對比分析,發現兩位譯者的差異所在,感受詩歌翻譯的“信”與“美”的深刻內涵。
在第一節詩中,針對“неволе”的理解二者有所不同。劉譯為“監禁”,戈譯為“束縛”,二者皆有“失去自由”之意。但是,兩種譯法的情感效果不同。結合該詩的創作背景,詩人正在南方流放,身陷囹圄,用“監禁”一詞主要表現的是詩人的處境,同時也描繪出“鷹”被禁錮的狀態。“監禁”是貼合作者的現實環境,而“束縛”則偏向于“鷹”的角度進行描寫,隱約帶有一種“失去自由”之感。除此之外,對于句式的處理二者也有所不同,劉傾向于簡潔的語言,在忠實于原文的基礎上對其加以改造;而戈尊重原文,注重“信”,使譯文盡量貼近原文。劉將其斷為兩個小句,句式顯得簡單凝練。戈則用多個形容詞連為一個長句,譯文讀起來更具異域特色。
二者對第一節詩后兩句的翻譯大同小異,但是情感表達效果稍顯差異。對于“Мой грустный товарищ”,劉在原文的基礎上添加了自己的情感體驗,將其處理為呼語“我憂郁的同伴啊”,使句子增加詩人與“鷹”對話的效果,進而拉近兩位“被監禁者”的距離。同時,也生動地表現了詩人內心的孤獨。戈采取直譯的方法,譯為“它是我的憂愁的同伴”,陳述句句型所表現的是詩人的自述,利用平鋪直敘的方式將其所見所聞描寫出來。
詩歌最后一節出現了兩個“пора”,劉省略了一個,直接譯為“是時候了,兄弟”,而戈貼合原文,“是時候啦,弟兄,是時候啦”。劉的譯文因省略一詞顯得短小精煉,貼合譯文整體簡潔的句式特征,符合中文的閱讀習慣。但是,在感情上劉的譯文則主要傳達出一種“堅定明確”之感,使詩歌充滿對未來的向往,表現詩人對生活依舊充滿信心。戈與原文相同,用兩個“是時候啦”重復使用升華情感,詩人內心積極昂揚的心理狀態被隱藏起來,而更增添了一絲愁緒。
詩歌最后采用了三個排比句式,這也是表達詩歌情感的關鍵之處。戈采用三個“讓我們飛到那兒”的句式,與第二節詩最后一句“讓我們一同飛走吧”共同構成排比,句式整潔,有利于增強情感色彩,詩歌整體的情感效果顯得單調樸實。而劉采用的是“飛去”,與前文的“讓我們一同飛去”形成遞進關系,遞進句式擴大了詩歌的空間感——由近及遠,給讀者營造出一種堅定、積極的情感氛圍。
對于“за тучей белеет гора”以及“синеют морские края”,戈是逐字逐句翻譯,尊重原文,他譯為“在云外的山崗閃著白光”與“大海閃耀著青色的光芒”,與“讓我們飛到那兒”相斷開,陳述的語調使讀者的視野停留在近處,營造出“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覺。而劉的譯文“飛去云外那白雪皚皚的山岡”與“飛去那閃耀著蔚藍色的海洋”在原文的基礎上加以創造,不僅使句式簡單輕快,而且轉變讀者的視野,把讀者從“牢房”帶到“山岡”和“海洋”,猶如身臨其境一般,將詩歌蘊含的積極自信表現得淋漓盡致。
劉與戈的譯文分別代表了“美”與“信”兩種不同的翻譯方法,呈現的效果也有所不同。顯而易見,劉更加注重在原文的基礎上加以改造,融入自身對詩歌的情感體驗,他在忠實于原文的基礎上結合中文的遣詞造句習慣,使譯文達到“美”的效果。而戈的譯文注重落實原文,逐字逐句翻譯,使譯文更具異域詩歌的特征。
三、詩歌翻譯的思考
在翻譯外文詩歌的過程中,筆者主要從以下幾點展開對詩歌翻譯的思考:意象選取、句式結構、標點符號。
首先,詩歌中充滿具有象征意義的意象,但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相同的意象可能會具備不同的象征意義。因此,在翻譯詩歌時我們首先要關注原文使用的意象、象征意義及整體詩歌所想表達的情感,結合自身文化背景,正確選取意象,使讀者能深切體會詩歌的情感。但是意象選取卻不是盲人摸象,要有所依據,不能偏離原文。
其次,所有詩歌都注重抑揚頓挫、韻腳、韻律等。但在翻譯詩歌時往往面臨著譯文失去了原文的音律美,尤其采用直譯的方法,譯文的句式結構顯得雜亂冗長,不符合中文詩歌對仗工整,整齊劃一的句式特點。因此,在詩歌翻譯時,要明確譯文的目標讀者,適當地修改譯文的句式,使其不僅保持原文的韻律美,還切合讀者的閱讀習慣。
最后,標點符號屬于易被忽略的問題,但在詩歌翻譯中扮演重要角色。感嘆號、省略號、問號等標點的使用對于描繪詩歌情境有著重要作用。外文詩歌的標點符號使用比較自由,時而省略,時而連用。翻譯外文詩歌時,標點符號的取舍也是一道難題。對此,黃燦然指出:“譯者不應隨便增減標點符號;不應把長短詩行譯成整齊詩行,或把整齊詩行譯成長短詩行”。[4]尊重原文的行文結構與標點使用,這也是“信”的體現。而主張“美”的譯者倡導對原文進行再創造,通過增刪標點符號,使其符合中文詩歌的結構特點。
結語:
詩歌翻譯一直是翻譯界的重難點,是注重“信言”還是“美言”成為翻譯的難題。筆者認為,針對兩者的關系,我們不能固守傳統,將其完全對立,正如錢鐘書所言:“譯事之信,當包達、雅”。[1](76)外文詩歌在創作時也是具備優雅、和諧的特征,譯者在翻譯時不能使譯文失去原文的優美雅致,而應在“信”的基礎上講究“美”,幫助讀者賞析外文詩歌。“信”與“美”的關系錯綜復雜,理解二者的內涵交織對于詩歌翻譯有著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鄭海凌:文學翻譯學[M].文心出版社,2000。
[2]劉文飛:劉文飛譯文自選集[M].漓江出版社,2013。
[3]戈寶權 劉文飛:普希金名作欣賞[M].中國和平出版社,1995。
[4]黃燦然:黃燦然:譯詩中的現代敏感[EB].http://www.zgshige.com/c/2016-11-17/2075192.shtml, 17.11.2016.
[5]谷羽:“囚徒”不墜凌云志——囚徒三首賞析[J].名作欣賞,2002年第1期。
[6]趙燕蕊:詩歌翻譯的“真”與“美”——試比較歌德<游子夜歌>的中譯本[J].山東農業工程學院,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