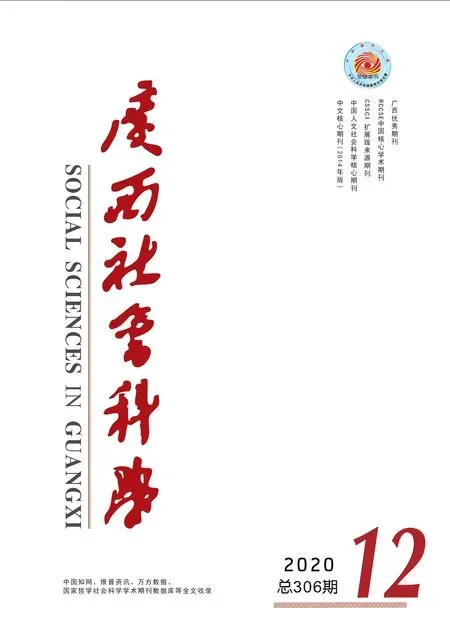“真理的發現”與現代國家想象
——論中國文學史編纂中的進化論思想
2020-03-11 05:51:59
廣西社會科學
2020年12期
關鍵詞:語言
(貴州民族大學 文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雖然進化論與中國文學史書寫的關系已得到較多關注,但已有研究仍有諸多不足,如忽略進化論在文學史著作中所發揮的“真理的發現”與現代國家想象,尤其忽略了進化論在古代文學史著作中發揮的作用。進化論認為宇宙和社會是不斷進化的,這種以宇宙進化論和社會進化論為核心的進化論思想是進化文學史觀念形成的基礎。進化論對晚清以后的中國啟蒙運動甚至革命運動,對文學史理論建構與文學史書寫實踐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成為中國文學史的重要話語類型。最早出現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如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和黃人《中國文學史》等內含進化論的痕跡,尤其是胡適于1922年3月為上海《申報》創辦五十周年紀念而作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被學者認為“二三十年代寫作的諸多文學史,都自覺不自覺地認同胡適這篇文章所描繪的新舊文學轉型的圖景”[1]。在本文看來,“任何歷史書寫者都屬于特定的歷史時代”[2],文學史書寫也不例外,在追求現代民族國家的時代進程中,進化論促進了中國知識分子關于聲音、人的精神和革命等“真理的發現”,即語言進化論促進聲音的發現、歷史進化論促進人的精神的發現、社會進化論促進革命的發現。實際上,“真理的發現”也就是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真理的發現”與現代國家想象是相互統一的。
一、語言進化論與聲音的發現
在20世紀以前,中國文字與聲音一直處于分離狀態,胡適甚至認為言語與文字的分離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華詩詞(2023年8期)2023-02-06 08:51:28
文苑(2020年4期)2020-05-30 12:35:30
小學生作文(中高年級適用)(2018年3期)2018-04-18 01:24:47
瘋狂英語·新策略(2017年8期)2017-05-31 08:13:46
新聞傳播(2016年10期)2016-09-26 12:15:04
玉溪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1期)2015-08-22 02:51:58
少兒科學周刊·少年版(2015年4期)2015-07-07 21:11:17
語文知識(2014年10期)2014-02-28 22:00:56
中學生英語高中綜合天地(2009年10期)2009-12-29 00:00:00
作文周刊·小學一年級版(2008年51期)2008-12-31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