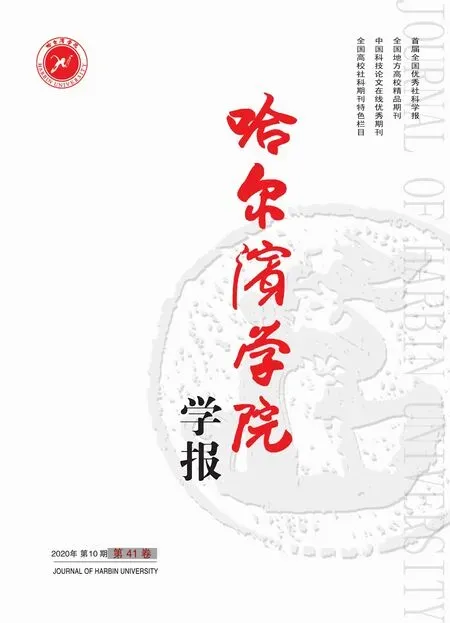國家治理視域下的貧困問題及對當代中國貧困治理的啟示
李華平,武余芹,陳 剛
(蚌埠醫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人類社會發展史,就是一部致力于擺脫貧困,追求美好生活的文明史。從蘇格拉底的省察人生、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神性生活,到空想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從陶淵明的“桃花源”、《禮記》中的“大同世界”,到孫中山“天下為公”的政治理念,都體現了古今中外仁人志士對幸福生活的向往與追求。確切地說,真正意義上的擺脫貧困,只有在人類進入工業社會才具備現實可能性,唯有工業文明,才能超越農業文明的生產局限,借助科學技術的耦合作用,調動各生產要素,形成現代生產力,從而實質性的推進物流、人流、信息流的全球涌動,開辟“世界歷史”。正是資本主義社會造成的市民社會貧困現實,形成了黑格爾政治構建必須直面的疑難:現代社會的苦惱。[1](P245)由此,貧困問題進入現代意義的議程,成為現代社會無法回避的現代性問題。
一、悖論:黑格爾市民社會貧困的苦惱
眾所周知,按照黑格爾政治哲學設置,君主與市民、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形成矛盾辯證法,貧困問題成為溝通黑格爾法哲學兩大主要領域(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主要樞紐。黑格爾將市民社會的貧困歸結于偶然的、自然的、外部的因素,中斷了更深層次的經濟學追尋,而寄望于普魯士專制國家化解貧困的矛盾,建立倫理共同體,結果在實踐中瀕于破產。應當肯認的是,黑格爾對貧困問題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義。
其一,突破了此前盛行的以市場至上原則為基礎的樂觀主義社會政治理論。在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理論看來,按照自由市場原則組織生產,造就社會財富的最大化,全體成員都能享受社會福祉,即貧困問題為市場運行的邏輯自行消解。黑格爾則堅決否棄市場邏輯對市民社會貧困的解決方案,揭示了市民社會內在對立結構關聯及其內源性緊張關系。
其二,從思想范式上對現代社會政治進行深度批判。與黑格爾倚重理性、強調總體、普遍性的理性主義自由主義有別,洛克、斯密等基于原子論思維路向,認為獨立的個人是政治活動的基本單元,從而個體優先于國家,國家則淪為個體的附屬,對私人利益進行保障。當兩者產生抵牾時,私人權益具有絕對優先性。貧困作為個體活動的結果,主要在于個人主觀不作為或偶然性所致。黑格爾敏銳意識到財富過剩與市民社會財富不足(貧困),不能僅歸于個體,而是在市民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產生的,因此,推究貧困問題的產生,社會政治秩序難逃其咎。而作為貧困治理的國家、同業公會,具有更高的整體原則,無法進行原子論還原。只有超越洛克式私人所有權,才能在普遍倫理共同體中找尋個人發展的真實場域與現實依歸。
其三,黑格爾沿著自由主義啟蒙政治哲學理路,試圖提出貧困問題的解決方案。在對待貧民問題上,黑格爾嘗試提出三重解決途徑:富人或私人團體救濟、海外殖民與同業公會,但出于更強調貧民“喪失廉恥和自尊心”“懶惰和浪費”等主觀責任,因此上述途徑均無力解決現代政治的“賤民難題”。易言之,黑格爾方案不過是學理層面的倫理籌劃,而非現實的政治解決,只有從哲學批判轉向政治經濟學批判,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現實途徑,這一理論進路歷史地落在馬克思身上,并由其實質性地完成。
二、重構:悖論性貧困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馬克思為人類解放和幸福奮斗的“初心”,可以追溯到中學時期對職業選擇的思考。馬克思個人貧困經歷與對貧困現象的獨特關注,是指引他從事政治經濟學的一條隱性線索。
早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撰寫的系列政治論文,就圍繞著貧困群眾生活問題,試圖為他們吶喊疾呼。在《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一文中,對當局將窮人撿拾枯枝定性為盜竊行為表示嚴重不滿;《在摩澤爾記者的辯護》中,將葡萄種植的貧困破產現象,上升到法與國家制度的批判高度,從國家治理層面深度挖掘貧困原因。這一時期,馬克思秉承自然法哲學立場,對法的“自由主義”信念仍然深信不疑,以理性批判活動作為解決貧困的主要方案。但是,馬克思自覺這種解決貧困問題的方式,是面對“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要退回書齋,進行理論研究,解決這一苦惱的現實問題。
如果說《萊茵報》時期的工作經歷動搖了此前對黑格爾法哲學的信仰,那么,以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為支點,馬克思開啟了對貧困問題的深度研究,一方面,對黑格爾法哲學進行直接批判,《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轉向經濟學的最初嘗試,雖然開始突破黑格爾法哲學理論框架,將市民社會—國家進行結構性倒置,但思想方法尚未發生根本變革。另一方面,深化經濟學研究,進一步批判黑格爾法哲學。黑格爾將國家視為超越市民社會的定在,馬克思依據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國家、法的關系只能從市民社會中探求,因此對黑格爾法哲學理論的批判,轉換成直接解剖市民社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在《資本論》中,黑格爾關注的現代社會的貧困問題,成為馬克思關注的核心議題,通過詳實的社會學資料和實地調研,馬克思對資產階級工業化造成的工人階級的赤貧現狀進行了深入勾畫,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深掘致貧的制度根源。
第一,深入經濟運行機制,揭露資本與貧困的悖論性。將貧困主體由“市民”界定為“無產階級”,指出與資產階級貧困出于偶然性不同,無產階級的貧困是普遍的必然性,是制度性宿命。工人的貧困與其勞動、勞動生產力成正比,表明悖論性貧困是工人階級的必然宿命。
第二,深入雇傭勞動式的生產關系批判,揭示無產階級貧困的制度性根源。如果說貧困不過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表現,那么深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馬克思發現了工人生產貧困的自身性。為他人生產財富,為自己生產貧困的悖論根源,在于勞動與所有權的分離。
第三,從資本主義生產前提看,雇傭勞動制是悖論性貧困產生的社會根源。結構化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經濟關系是資本能夠貫徹強制邏輯的依據,因而表現為一種制度性貧困。破除現代性貧困的根本出路在于無產階級革命實踐,尋找社會主義制度性替代方案。資本積累必然引起經濟和社會紊亂,大量的剩余人口為了生存的尊嚴而戰。“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2](P874)無產階級的覺醒,認識到貧困的社會物質根源,發現資本主義經濟規律是造成工人階級苦難的淵藪。這時,無產階級革命斗爭意識就會爆發,斗爭的結果是,在生產資料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實現貧困的社會制度性和解,造就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
第四,指明無產階級整體脫貧的方向和途徑。首先,資本主義制度是無產階級貧困的內源性矛盾,無產階級貧困的解決必須在資本主義根基處推倒重來,完成制度性顛覆,繼而重建社會主義制度;其次,階級剝削引致貧困化,必須通過剝奪“剝奪者”,消滅階級及其統治;最后,生產力發展是貧困治理的根本出路。如果人們陷入生活必需品的斗爭,一切腐朽的東西就會死灰復燃。因此,發展才是硬道理,才是解決貧困問題的根本治理之道。
三、突圍:我國貧困治理的制度性建構
馬克思以人類解放和人的全面發展為旨歸的貧困治理理論,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各國共產黨解決貧困難題的根本理論依據,也是國家制度體系構建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根據馬克思的經典理論,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結構性貧困,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安排,勞動與資本的緊張關系得以消除,無產階級貧困問題可以從根本上加以解決。當前我國貧困問題不是制度性貧困,而是生產力不夠充分和平衡的生產性貧困,需要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生態等方面協調發力,綜合施策。
首先,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消除了產生與解決貧困的制度性阻礙。為探究救國救民之路,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種制度方案與救國方略,大多歸于失敗。主要原因在于脫離了中國國情,沒有形成以人民為中心的先進性政治組織,來解決一盤散沙分崩離析的治理亂局。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伊始,以消除貧困,致力于民族獨立與人民幸福為初心和宗旨,在艱苦卓絕的偉大斗爭中,領導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砸碎了腐朽的上層建筑,使中華民族獲得獨立與解放,繼而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為消除貧困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撐。社會主義工業化、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為人民脫貧致富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實踐證明,新中國的制度探索和治理效能十分有效,迅速擺脫了一窮二白的落后狀況,貧困治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其次,以改革開放為主軸的中國道路,極大地釋放了生產力的發展活力,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歷史性轉變。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為思想解放前奏,以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序幕,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從農村向城鎮延伸,由東南沿海向中西部推進,從經濟向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各領域深化。正如鄧小平指出,“中國要謀求發展,擺脫貧窮和落后,就必須開放。”[3](P266)改革開放突破了造成貧困的制度性瓶頸,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的發展,使幾億人實現了脫貧,為貧困問題的根本解決奠定了現實基礎,提供了中國方案。與此同時,極大地激發了各類市場主體創造活力,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提升了國人的綜合素質,提振了人民告別貧困走向富裕的美好生活自信。
最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是解讀中國化貧困成功之謎的政治密鑰。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發展,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鄧小平指出反貧困(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從計劃經濟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經濟運行機制變化理順了基本制度優勢與人民主體性的暢通渠道,農業勞動必要時間釋放出的時間節余,轉化為其他社會勞動時間,鄉鎮企業迅速發展,農民收入結構優化與收入來源多樣化。市場經濟大步邁進,國家財富累積與貧困人口收入同步增長,生產要素配置作用進一步強化。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中國道路以追求經濟發展為優先目標,與傳統救濟式反貧困不同,開發式反貧主要發展投資經營,如基建擴容,社會公共領域與公共產品供給擴大。進入新世紀,中國貧困線隨經濟發展而水漲船高,扶貧更強調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教育等內生性造血式扶貧。
四、攻堅:新時代精準扶貧的治理之道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行進在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中國道路上,繼續創造中國之治的人類發展的歷史奇跡;實現全體人民的小康,讓每一個中國人擺脫貧困,成為共產黨人的莊嚴承諾,精準扶貧成為新時代貧困治理的重要議程。
其一,共產黨人的“初心”決定了脫貧致富達成美好生活是其使命和初衷。判斷一個政黨的成色,主要看他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中國共產黨沒有狹隘的個人私利,他僅遵循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形形色色政黨的根本標志。既然人民利益就是黨的利益,那么治理貧困就是黨治國理政題中應有之義。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到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都莊嚴履行著為人民謀幸福的神圣使命,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準確定位中國道路的時代坐標和制度準星,精準把脈社會主要矛盾,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目標提上治理議程,[4](P70)脫貧攻堅。實現全面小康成為新時代共產黨人的莊嚴承諾和治理效能的實踐標尺。
其二,構建我國貧困治理的“四梁八柱”,完成了治貧的上層建筑頂層設計。在目標上,確保2020年現行標準下所有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既體現了收入標準和國際貧困線接軌,又體現了貧困度量的多維性,涵納了基本生活、教育、衛生等要求。在責任方面,發揮黨和社會主義的政治優勢,簽署責任書,由上而下,層層壓實,實現了政治與制度優勢,進一步轉化為國家貧困治理的現代化與效能化。在工作體系上,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做到“六個精準”“五個一批”“四個問題”的頂層設計與“十大精準扶貧行動”“十項精準扶貧工程”具體對接。在政策配套方面,十八大以來,“中辦”“國辦”出臺了13個配套文件,制定了200多個扶貧政策,覆蓋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產業就業、生態建設等領域。投入與動員上,發揮政府主體投入與主導作用,轉向投入、涉農資金、金融投放、小額貸款、資本扶貧、保險助力協同發力,形成專項、行業、社會三位一體大扶貧格局。在監測方面,建立中央巡視、民主黨派監督、檢察審計、資金監管立體化監管體系。實行建檔立卡精細識別、動態管理精準退出,用最剛性的扶貧政績考核倒逼各地落實脫貧攻堅責任,實施第三方評估、省際交叉考核、媒體暗訪考核,讓貧困治理暴露在社會陽光下,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和檢驗。
其三,精準扶貧的當代價值。一是,豐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開發理論。從改革開放肇始的反貧困,到開發式扶貧、綜合扶貧,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將扶貧開發上升為國家戰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形成了以“精準扶貧”為核心的扶貧思想體系。二是,這一思想成為了當代中國脫貧攻堅指導思想,有力地指引了當代中國貧困治理實踐。三是,為全球減貧貢獻了中國力量與中國智慧。消除貧困是人類的共同使命,中國致力于消除自身貧困的同時,支持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致力于國際減貧交流,讓國際社會分享中國方案和智慧。中國扶貧偉大實踐是對世界減貧事業的有力支持,也是中國制度為世人所認同的重要方面。精準扶貧作為民生工程的一個方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和國家治理優勢,是國家治理體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標志。
其四,有效回應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公平價值觀。西方學者羅爾斯提出差異原則,要求財富分配向最不利者傾斜,促使分配正義更為有效。[5](P48)麥金泰爾對“誰之正義”的追問,切中了公平正義主體的多元性,但卻選擇性的遺忘或無視階級利益的根本差異。而后現代主義更關注多元、差異的公平正義,但對多元主義的差異化過度關注,走向了相對主義,對現實利益選擇性回避。可見,公平正義離開背后的階級利益,不具備獨立的價值實體衡量尺度,造成理論與實踐抽離化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