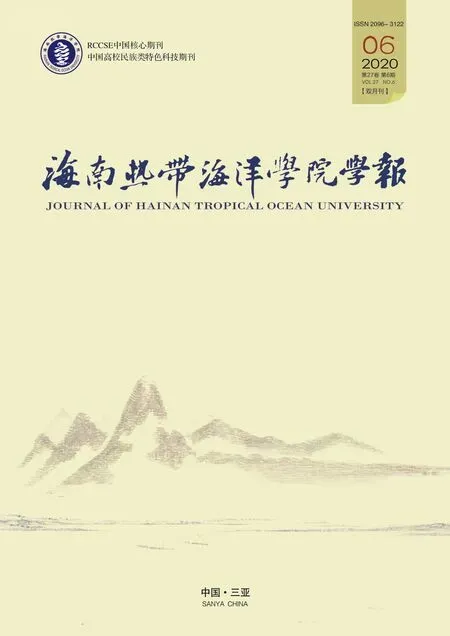宋詞的讀者“粉絲化”現象及“粉絲”傳播效應
柯繼紅,盧和妤
(海南熱帶海洋學院 a.人文社科學院; b.圖書館,海南 三亞 572022)
讀者即受眾,受眾“粉絲化”現象在唐代詩壇也有,如白居易,“童子解吟長恨曲 胡兒能唱琵琶篇”[1],“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2]。到了宋詞,受眾“粉絲化”現象愈演愈烈,形成了更為深廣的粉絲傳播效應,為宋詞流行的深度擬態環境貢獻了重要一環。
宋詞作為融媒形式,具有非常寬闊的受眾基礎。其受眾上自帝王,下至市井,涵蓋了各個層次,但無論是哪一層次的受眾,無論是其作為文學文本的閱讀者,還是作為音樂文本的傳唱欣賞者,在融媒形式及作者意見領袖化雙重影響下,都呈現出了明顯的“粉絲化”現象,伴隨而來的則是“粉絲”們的傳播效應。善歌者是詩歌受眾的重要一環,也是最容易吸“粉”的一群人,但是,在宋詞文化中,身份更顯貴,更具有演偶像意味的,還要算那些占據詞壇中心、具有詞牌創作能力的詞人們。這些詞人們一方面接受來自普通歌女市民的崇拜,另一方面還接受來自較高層面的本集團其他文人的激賞和吹捧,有時候還能贏得來自最高統治者們的贊賞。
一、 市民成為“粉絲”形成傳播口碑
普通市民階層在詞人面前“粉絲化”,是很容易理解的。柳永“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3]121,蘇軾《水調歌頭》“都下傳唱”[4]43,萬俟詠“每一章出,信宿喧傳都下”[3]435,都能說明這一點。市民階層中,一些在傳統文獻中不大登場的女性,也偶爾獲得了機會,出現在詞家視野中。
《古今詞話》“秦觀”條記載了兩則官宦婦人“粉”上詞人秦少游的故事,如“素不善飲”的寵姬碧桃愿意為“學士拼了一醉”[4]25;還有一則:
秦少游在揚州,劉太尉家出姬侑觴。中有一姝,善擘箜篌。此樂既古,近時罕有其傳,以為絕藝。姝又傾慕少游之才名,偏屬意,少游借箜篌觀之。既而主人入宅更衣,適值狂風滅燭,姝來且相親,有倉卒之歡。且云:今日為學士瘦了一半。少游因作《御街行》以道一時之景曰:“銀燭生花如紅豆。這好事、而今有。夜闌人靜曲屏深,借寶瑟、輕輕招手。可憐一陣白萍風,故滅燭、教相就。 花帶雨、冰肌香透。恨啼鳥、轆轤聲曉。岸柳微風吹殘酒。斷腸時、至今依舊。鏡中消瘦。那人知后,怕你來僝僽。”[4]25
《古今詞話》還記載了一則士人江致和以詞吸引“女粉”的故事:
江致和 崇寧間,上元極盛。太學生江致和,在宣德門觀燈。會車輿上遇一婦人,姿質極美,恍然似有所失。歸運毫楮,遂得小詞一首。明日妄意復游故地,至晚車又來,致和以詞投之。自后屢有所遇,其婦笑謂致和曰:今日喜得到蓬宮矣。 詞名《五福降中天》:“喜元宵三五,縱馬御柳溝東。斜日映朱簾,瞥見芳容。秋水嬌橫俊眼,膩雪輕鋪素胸。愛把菱花,笑勻粉面露春蔥。 徘徊步懶,奈一點靈犀未通。悵望七香車去,慢輾春風。云情雨態,愿暫入陽臺夢中。路隔煙霞甚時遇,許到蓬宮。”[4]27
《綠窗新話》引此文較《廣記》為詳,更具小說家筆法:
云崇寧間,輦下上元極盛。太學生江致和,一夕在宣德門前看燈。適會車輿上見一婦人,姿色絕美,與致和目色相授,至夜深乃散。致和似有所失,遂作五福降中天一曲,具道其意。明日,致和以此詞妄意于前日之地待之,至晚,車又來。婦人遙見致和,益增歡喜。致和密令小仆,以此詞投之。自后致和屢見所遇,約致和于曲室,以盡繾綣。婦人笑曰:“今日喜得君到蓬宮矣。”[5]88
二、 歌妓成為“粉絲”直接推動宋詞傳播
宋詞的創作者多為男性,而宋詞歌妓多為年輕女性。歌妓在詞人面前“粉絲化”,失去抵抗能力,是可以預料的。
《古今詞話》記載一個妓女追隨善詞的滬南營知寨云:
瀘南營二十余寨,各有武臣主之。中有一知寨,本太學士人,為壯歲流落隨軍邊防,因改右選,最善詞章。嘗與瀘南一妓相款,約寒食再會,知寨者以是日求便相會。既而妓為有位者拉往踏青,其人終日待之不至。次日又逼于回期,然不敢輕背前約,遂留《駐馬聽》一曲以遺之而去。其詞(《花草粹編》題作“留別”)曰:“雕鞍成漫駐。望斷也不歸,院深天暮。倚遍舊日,曾共憑肩門戶。踏青何處所。想醉拍春衫歌舞。征旆舉。一步紅塵,一步回顧。 行行愁獨語。想媚容、今宵怨郎不住。來為相思苦。又空將愁去。人生無定據。嘆后會、不知何處。愁萬縷。憑仗東風,和淚吹與。”亦名《應天長》。妓歸見之,輒逃樂籍往寨中從之,終身偕老焉。[4]35
《能改齋詞話》記載澶淵營妓喜歡唱李和文《望漢月》詞:
李和文公作詠菊《望漢月》詞,一時稱美。云:“黃菊一叢臨砌。顆顆露珠妝綴。獨教冷落向秋天,恨東君、不曾留意。 雕欄新雨霽。綠蘚上、亂鋪金蕊。此花開后更無花,愿愛惜、莫同桃李。”時公鎮澶淵,寄劉子儀書云:“澶淵營妓,有一二擅喉囀之技者,唯以‘此花開后更無花’,為酒鄉之資耳。”“不是花中惟愛菊,此花開后更無花”,乃元微之詩,和文用之耳。[4]53
又《古今詞話》分別記載了詞人張先、柳永、李之問等人與“粉絲”交往的故事:
張先 張子野往玉仙觀,中路逢謝媚卿,初未相識,但兩相聞名。子野才韻既高,謝亦秀色出世,一見慕悅,目色相授。張領其意,緩轡久之而去,因作謝池春慢以敘一時之遇。詞云:“繚繞重院,靜聞有、啼鸞到。繡被堆余寒,畫幕明新曉。朱檻連天闊,飛絮知多少?徑莎平,池水渺。日長風靜,花影閑相照。 塵香拂馬,逢謝女、城南道。秀艷過施粉,多媚生輕笑。斗色鮮衣薄,碾一雙蟬小。歡難偶,春過了。琵琶流韻,都入相思調。”[4]18-19
柳永 柳耆卿嘗在江淮惓一官妓,臨別,以杜門為期。既來京師,日久未還,妓有異圖,耆卿聞之怏怏。會朱儒林往江淮,柳因作《擊梧桐》以寄之曰:“香靨深深,孜孜媚媚,雅格奇容天與。自識伊來,便有憐才心素。臨歧再約同歡,定是都把身心相許。又恐恩情,易破難成,未免千般思慮。 近日書來,寒暄而已,苦沒刀刀言語。便認得、聽人教當,擬把前言輕負。見說蘭臺宋玉,多才多藝善詞賦。試與問、朝朝暮暮,行云何處去?”妓得此詞,遂負□竭產,泛舟來輦下,遂終身從耆卿焉。(《綠窗新話》上引《古今詞話》)[4]19-20
聶勝瓊 李公之問儀曹解長安幕,詣京師改秩。都下聶勝瓊,名娼也,資性慧黠,公見而喜之。李將行,勝瓊送之別,飲于蓮花樓,唱一詞,末句曰:“無計留君住,奈何無計隨君去。”李復留經月,為細君督歸甚切,遂別。不旬日,聶作一詞以寄之,名《鷓鴣天》曰:“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花草陽關后,別個人人第五程。 尋好夢,夢難成。況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簾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李在中路得之,藏于篋間。抵家為其妻所得,因問之,具以實告。妻喜其語句清健,遂出妝奩資募,后往京師取歸。瓊至,即棄冠櫛,損其妝飾,奉承李公之室以主母禮,大和悅焉。(《綠窗新話》下引《古今詞話》) 按:上闋又引見花庵《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十、《花草粹編》五、《古今女史》十二,茲并校之。《粹編》題作“別李之問”,女史同。[4]32-33
歌妓成為粉絲,在各種場合對歌曲進行演繹和鼓吹,對宋詞的傳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 詞人之間“互粉”擴大了傳播效應
詞人集團內部的互粉,則是另一個普遍的現象。在宋詞文化中,詞人不僅僅承擔著創造者角色,同時也是詞作最主要的受眾之一。在宋詞融媒的魅力下,文人士大夫們也大都未能免俗,紛紛走上了“粉絲化”道路。這種“粉絲化”,一方面表現為對歌妓等的激賞吹捧,更多的時候則表現為對詞人、詞作的喜愛和推崇。這后面一種情況乍看起來,倒很像是文人之間的相互吹捧,但如果仔細分析,則可以看出,除了部分意見表達具有較多理性成分外,許多的時候,詞人們在他人好的作品面前,表現得更像是“粉絲”而不是“批評家”身份。
(一)揚此抑彼
“粉絲”最容易揚此抑彼,后者即所謂的“互掐”。宋詞的許多大批評家們在這一點上都沒能免俗。
大詩人陳師道,推崇秦觀、黃庭堅的詞作,不惜以批評自己的老師蘇軾為代價:
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迨也。(《后山詩話》)[3]280
文學家晁補之論詞,高度推崇秦少游,嚴厲批評黃庭堅“著腔子唱好詩”,卻網開一面,為另一位提倡“詩人的詞”的蘇軾辯解,令人摸不著頭腦:
蘇東坡詞,人謂多不協音律,然居士詞橫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晁補之《評本朝樂府》,錄自《復齋漫錄》)[4]11
苕溪漁隱胡仔愛蘇詞,貶柳詞,作《苕溪漁隱詞話》揚蘇抑柳,極其所能。他表揚蘇軾,推翻前人對蘇詞的負面評價,極盡其力。他表揚蘇軾詞時說:
苕溪漁隱曰:“東坡大江東去赤壁詞,語意高妙,真古今絕唱……”(《苕溪漁隱詞話》卷一)[4]78
苕溪漁隱曰:“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余詞盡廢……” (《苕溪漁隱詞話》卷二)[4]82
對于前人對蘇詞的批評意見,他一一加以反駁。如針對《后山詩話》謂蘇軾“要非本色”的言論,苕溪漁隱曰:“余謂后山之言過矣,子瞻佳詞最多……《后山》乃比之教坊司雷大使舞,是何每況愈下?蓋其謬耳。”(胡仔《苕溪漁隱詞話》卷四“東坡”條)[4]96-97甚至對于有損蘇軾高大形象的哪怕褒揚意見,他都不放過:
《古今詞話》云:“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秀蘭收淚無言,子瞻作《賀新涼》以解之……子瞻真所謂風流太守也,豈可與俗吏同日語哉?”苕溪漁隱曰:“野哉,楊湜之言,真可入笑林。東坡此詞,冠絕古今,托意高遠,寧為一娼而發耶……”(《苕溪漁隱詞話》卷二)[4]87-88
王灼《碧雞漫志》,亦是極力崇蘇抑柳的調子。與胡仔不同的是,他不僅注意到柳永,也注意到了與蘇軾意見不同的李清照,連帶著李清照也作了最嚴厲的批評。他表揚蘇軾時極盡其高:
東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碧雞漫志》卷二“各家詞短長”條)[4]108
其批評柳永、李清照時努力做出貌似公正的態度,實則貶抑更甚:
柳耆卿《樂章集》,世多愛賞……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脫村野,而聲態可憎。(《碧雞漫志》卷二“樂章集淺近卑俗”條)[4]110
易安居士……若本朝婦人,當推詞釆第一。趙死,再嫁某氏,訟而離之,晚節流蕩無歸。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縉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忌也。 (《碧雞漫志》卷二“易安居士詞”條)[4]112
其對于李清照的批評遠離了批評家的風度,已接近于謾罵了。
著名詞論家沈義父,則是周邦彥的堅定擁戴者。其《樂府指迷》論詞崇“協律”“雅正”,惟推周邦彥。論及周邦彥則以為“冠絕”“作詞當以清真為主”;論及其他詞人則以為“各有得失”,唯為指瑕;或有不便指責處,則極力往“知音”周邦彥身上靠,努力維護“周邦彥標準”。他論及周邦彥時,推揚其“冠絕”,只有好話,沒有意見。當論及其他詞人的時候,則都只是論其“得失”,論其得者則說深得清真之妙,論其失者則多半是與清真不一樣之處:
康伯可、柳耆卿音律甚協,句法亦多有好處。然未免有鄙俗語。(《樂府指迷》“康柳詞得失”條)
姜白石清勁知音,亦未免有生硬處。(《樂府指迷》“姜詞得失”條)
夢窗深得清真之妙。其失在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可曉。(《樂府指迷》“夢窗得失”條)
施梅川音律有源流,故其聲無舛誤。讀唐詩多,故語雅淡。間有些俗氣。蓋亦漸染教坊之習故也。亦有起句不緊切處。(《樂府指迷》“梅川得失”條)
孫花翁有好詞,亦善運意。但雅正中忽有一兩句市井句,可惜。(《樂府指迷》“花翁得失”條)[4]200
對于與周邦彥方向不一樣的豪放風氣,雖不敢直接批評蘇軾和辛棄疾,卻筆鋒一轉,將蘇辛之外的其他豪放詞風來了個一網打盡:
近世作詞者不曉音律,乃故為豪放不羈之語,遂借東坡、稼軒諸賢自諉。諸賢之詞,固豪放矣,不豪放處,未嘗不葉律也。如東坡之《哨遍》、楊花《水龍吟》,稼軒之《摸魚兒》之類,則知諸賢非不能也。(《樂府指迷》“豪放與葉律”條)[4]203
后人所謂“《詞源》論詞,獨尊白石。《指迷》論詞,專主清真”(蔡嵩云《樂府指迷箋釋》引言)[4]207的批評,是很有見地的。
(二)單向“粉”行為
當然,“粉絲”所行,也不盡如上述張炎、周密、王灼、沈義父等走向兩個極端。也有一些只是單方面的欣賞和喜愛。這些喜愛表現在一系列具有區別意義的“粉絲性”行為上,如點評、感嘆、追憶、為之張目、推介等,這些“粉絲性”行為無一不具有極好的傳播效應。
如蘇軾愛秦觀“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就化身成為秦觀的最大推銷者:
《冷齋夜話》云:“少游到郴州,作長短句云:‘霧失樓臺……’東坡絕愛其尾兩句,自書于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苕溪漁隱詞話》卷三)[4]92
黃庭堅推崇賀鑄《青玉案》詞,則用以詩論詩的方式進行了獨特表達,如:
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時時度曲。周美成與有瓜葛,每得一解,即為制詞,故周集中多新聲。賀方回初在錢塘,作《青玉案》,魯直喜之,賦絕句云:“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賀集中,如《青玉案》者甚眾。大抵二公卓然自立,不肯浪下筆,予故謂語意精新,用心甚苦。(王灼《碧雞漫志》“周賀詞語意精新”條)[4]111
賀方回為《青玉案》詞,山谷尤愛之,故作小詩以紀其事。及謫宜州,山谷兄元明和以送之云:“千峰百嶂宜州路,天黯淡(原作但,據臨嘯書屋刊本改)、知人去。曉別吾家黃叔度。弟兄華發,遠山修水,異日同歸處。 長亭飲散尊罍暮,別語纏綿不成句。已斷離腸能幾許?水村山郭,夜闌無寐,聽盡空階雨。”山谷和云:“煙中一線來時路,極目送、幽人去。第四陽關云不度。山胡聲轉,子規言語,正是人愁處。 別恨朝朝連暮暮。憶我當年醉時句。渡水穿云心已許。晚年光景,小軒南浦,簾卷西山雨。”洪覺范亦嘗和云:“綠槐煙柳長亭路,恨取次、分離去。日永如年愁難度。高城回首,暮云遮盡,目斷人何處。 解鞍旅舍天將暮,暗憶丁寧千萬句。一寸危腸情幾許。薄衾孤枕,夢回人靜,徹曉瀟瀟雨。”(吳曾《能改齋詞話》“山谷愛賀方回《青玉案》詞”條)[4]47-48
秦少游《千秋歲》詞為晁補之、黃庭堅極力推稱,晁、黃二人的“粉絲性”表現耐人尋味:
秦少游《千秋歲》,世尤推稱。秦既沒滕州,晁無咎嘗和其韻以吊之云:“江頭苑外,嘗記同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謳云繞扇,趙舞風回帶。嚴鼓斷,杯盤狼藉猶相對。 灑涕誰能會。醉臥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宴悄,虎觀英游改。重感慨。驚濤自卷珠沉海。”中云“醉臥藤陰蓋”者,少游臨終作詞所謂“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故無咎用之。……一日,過山谷論文,山谷傳少游《千秋歲》詞,嘆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父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而未有以卻之者。次日,又過山谷問焉,山谷答曰:“昨晚偶得一海字韻。”功父問其所以,山谷云:“羞殺人也爺娘海。”(吳曾《能改齋詞話》“世推重少游醉臥古藤之句”條 )[4]48
張侃《揀詞詞話》推崇秦觀,則直接采取了評論的方式,謂其“古今絕唱”:
秦淮海詞古今絕唱,如《八六子》前數句云:“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刬盡還生。”讀之愈有味。又李漢老《洞仙歌》云:“一團嬌軟,是將春揉做,撩亂隨風到何處。”此有腔調散語,非工于詞者不能到。毛友達可詩“草色如愁滾滾來”,用秦語。(張侃《揀詞詞話》)[4]149
周密愛吳文英胞弟翁元龍詞,則直接采取了“點評”與“摘句”方式為之張目,謂其詞可與吳文英并肩[4]184:
翁元龍,字時可,號處靜,與君特為親伯仲,作詞各有所長。世多知君特詩,而知時可者甚少。予嘗得一編,類多佳語,已刊于集矣。今復摭數小闋于此。《江城子》云:“一年簫鼓又疏鐘。愛東風,恨東風。吹落燈花,移在杏梢紅。玉靨翠鈿無半點,空濕透,繡羅弓。 燕魂鶯夢漸惺松。月簾櫳,影迷蒙。催趁年華,都在艷歌中。明日柳邊春意思,便不與,夜來同。”《李春·西江月》云:“畫閣換粘春帖,寶箏拋學銀鉤。東風輕滑玉釵流,纖就燕紋鶯繡。 隔帳燈花微笑,倚窗云葉低收。雙鴛刺罷底尖頭,剔雪閑尋豆蔻。”《賦茉利·朝中措》云:“花情偏與夜相投,心事鬢邊羞。熏醒半床涼夢,能消幾個開頭。 風輪慢卷,冰壺低架,香霧颼颼。更著月華相惱,木犀淡了中秋。”《巧夕·鵲橋仙》云:“天長地久,風流云散,惟有離情無算。從分金鏡不成圓,到此夜、年年一半。 輕羅暗網,蛛絲得意,多似妝樓針線。曉看玉砌淡無痕,但吹落、梧桐幾片。”又如:“奧蓮牽藕線,藕斷絲難斷。彈水沒鴛鴦,教尋波底香。”真《花間》語也。(周密《浩然齋詞話》)[4]184
詞人之間的互粉,在士大夫階層刮起了一股旋風,并在文化領域形成了強有力的輿論引導,成為宋詞流行最深層的推手。
四、 最高統治者化身“粉絲”成為強力傳播者
除了文人互粉之外,杰出的詞人們還能夠吸引當朝者的注意,將當朝統治者變成他們的粉絲。宋神宗對柳永、蘇軾詞的欣賞就是很好的例子:
《后山詩話》云:“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宋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后宮,且求其助。后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此詞矣。會改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后改名永,仕致屯田員外郎。” 苕溪漁隱曰:“先君嘗云:柳詞‘鰲山彩構蓬萊島’當云‘彩締’。坡詞‘低綺戶’,當云‘窺綺戶’,二字既改,其詞益隹。”(《苕溪漁隱詞話》卷一)[4]74
神宗問內侍外面新行小詞,內侍錄此進呈。讀至“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上曰:蘇軾終是愛君,乃命量移汝州。(《歲時廣記》三十一。)(鲖陽居士撰、趙萬里輯《復雅歌詞》)[4]43
南宋·周密《浩然齋詞話》載宋徽宗因李師師歌周詞而對周邦彥的“知遇之恩”也可以算作其中的例子。
宣和中,李師師以能歌舞稱。時周邦彥為太學生,每游其家。一夕,值祐陵臨幸,倉卒隱去。既而賦小詞,所謂“并刀如水、吳鹽勝雪”者,蓋紀此夕事也。未幾,李被宣喚,遂歌于上前。問誰所為,則以邦彥對。于是遂與解褐,自此通顯。既而朝廷賜酺,師師又歌《大酺》《六丑》二解,上顧教坊使袁绹問,绹曰“此起居舍人新知潞州周邦彥作也。”問《六丑》之義,莫能對,急召邦彥問之。對曰“此犯六調,皆聲之美者,然絕難歌。昔高陽氏有子六人,才而丑,故以比。”上喜,意將留行。且以近者祥瑞沓至,將使播之樂府,命蔡元長微叩之。(周密《浩然齋詞話》)[4]186-187
所謂“上有所好,下必從焉”,統治者上層的激賞和評價,為宋詞的流行構建了最廣闊的輿論場,最終從某種意義上將宋詞從民間文化提升到了國家文化的高度。
當然,由于宋神宗、徽宗等的獨特身份,使得他們的“粉絲化”身份極為復雜,“粉絲性”在他們身上表現得并不徹底。但是,無論如何,宋詞文化的流行,這些統治者“粉絲”們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
結 語
宋詞作家通過各種途徑“親身參與自身作品傳播過程”[6]有能力將國家各個階層的人物都變成宋詞的熱愛者和傳唱著,宋詞的讀者“粉絲化”涉及上自天子下至普通市民各個層次,而每一個層次的粉絲反過來又成為宋詞文化最好的宣傳傳播者,吸引更多的“粉絲”參與進來,為宋詞文化的繁榮帶來更多的幫助,整個過程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終形成了浩浩蕩蕩宋詞流行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