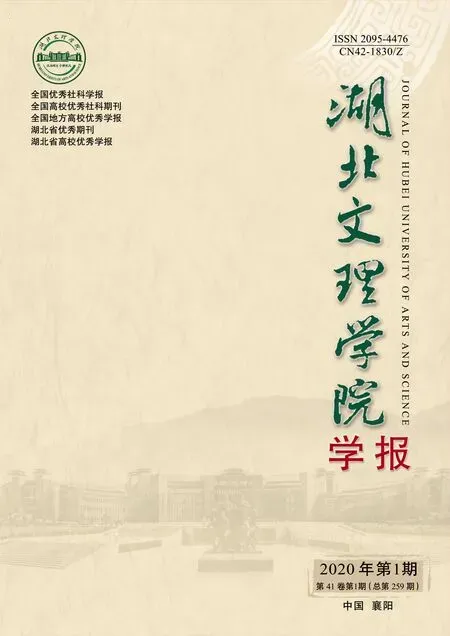明代戲曲理論從“畫工”到“化工”的演變
王玲玲
(溫州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溫州 325035)
明代戲曲批評史上《西廂記》《拜月亭》《琵琶記》地位之爭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探究論爭中諸位戲曲理論家提出的“本色”“當行”論(1)如一峰《當行論──戲曲編劇藝術漫筆》(《民族藝術》,1995年第2期),從臧懋循的“當行”引出,展開明代諸位戲曲理論家對《西廂記》《拜月亭》《琵琶記》及其他名劇的評價,探究“當行”的戲曲意義;王漢民《“本色論”在明代的兩次論爭》(《戲劇》,1997年第4期)其第一次論爭則是對這場戲曲作品地位論爭中何良俊、王世貞等人就“本色”展開的問題進行探究;劉于鋒《曲學史上一次戲曲本體特征的論爭》(《戲劇文學》,2009年第10期)認為“在論爭中,明代曲家在本色觀上,認為本色與填塞學問無關,而在雅俗、深淺、濃淡之間”;敬曉慶《明代戲曲本色說考論》(西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通過明代的名劇之爭與意法之爭來論述明代戲曲“本色”論的發展。趙春寧《明代<西廂記>與<琵琶記><拜月亭>的高下之爭》(《中華戲曲》,2006年第2期)除了“以本色、當行為標準”之外,還提出“以音律為標準”“以戲為標準”對這場論爭進行分析。;二是依托于論爭重點研究其中單部劇作的戲曲意義(2)如劉小梅《南戲<拜月亭記>及其歷史影響》(《戲曲藝術》,2004年第3期),著重探討《拜月亭》在這場戲曲作品地位的論爭的獨特地位和戲曲風格;馮俊杰《明代士子眼中的<琵琶記>》(《中華戲曲》,2008年第1期)依托于論爭中諸位戲曲理論家的觀點來重點研究《琵琶記》的戲曲地位。;三是將戲曲作品地位論爭與元曲四大家的成員及其對他們評價的論爭、湯沈之爭等放在一起考量,研究“論爭”這一獨特的理論批評形態(3)如敬曉慶在其碩論基礎上寫就博論《明代戲曲理論批評論爭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對明代名家之爭、行戾之辨、名劇之爭、意法之爭等做全面地分析;祁志祥《明代的戲曲美學論爭》(《藝術百家》,2017年第4期)從戲曲美學視角,從明代諸多論爭中總結出“本色論、情趣論、折中論”等三方面。。本文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借用晚明戲曲理論家李卓吾在論爭中所提出的“化工”與“畫工”說來探究明代戲曲理論的演變。李卓吾《焚書·雜說》謂:“《拜月》《西廂》,化工也;《琵琶》畫工也。夫所謂畫工者,以其能奪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無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百卉具在,人見而愛之矣,至覓其工,了不可得,豈其智固不能得之歟!要知造化無工,雖有神圣,亦不能識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誰能得之?由此觀之,畫工雖巧,已落二義矣。”[1]96這幾句話以“化工”與“畫工”之高下確立了《西廂記》《拜月亭》高于《琵琶記》的戲曲地位。“化工”之作以《西廂記》《拜月亭》為代表,劇作者以自然為美,推崇真情。“畫工”之作以《琵琶記》為代表,劇作者以宣揚倫理道德為創作宗旨,為達到這一目的而“窮巧極工”,導致劇作品感人不深。
一、明正德以前戲曲理論之重教化:“畫工”階段
明正德以前統治者內部矛盾沖突嚴重,為鞏固統治而過度強調封建倫理道德,如朱元璋稱:“天下甫定,朕愿與諸儒講明治道。”[2]這一階段社會思潮為“程朱理學”,它以“存天理,滅人欲”為基本指導思想,把“人欲”與“天理”對立起來。“程朱理學”從客觀條件出發,依據外在的條條框框來規范百姓的行為,強制百姓遵守社會準則,故對百姓思想的禁錮十分嚴重。這一思潮的影響下,戲曲為統治者所利用,成了為封建專制服務的工具。明初法律規定,民間演劇不準妝扮“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賢”,但“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者不在禁限”[3],故戲曲創作內容受到限制。同時,參與戲曲創作的文人也在漸少。明初科舉恢復,與元代長期廢止科舉致使大批文人轉而從事雜劇創作的局面相反,明人得以參加科舉考試,故不再熱衷于戲曲。何良俊《曲論》謂:“祖宗開國,尊崇儒術,士大夫恥留心辭曲,雜劇與舊戲文本皆不傳”[4]6。基于以上原因,明初戲曲理論的發展由元代的活躍局面轉向沉寂。相較于元代一大批的戲曲理論專著如《錄鬼簿》《青樓集》《唱論》《中原音韻》等,明初戲曲理論著作甚少,只有一部《太和正音譜》,其他皆散見于序、跋之中,不成體系。
朱權《太和正音譜》,其名“太和”即是天下太平、政通人和之意,是將戲曲定性為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工具,他言:
猗歟盛哉,天下之治也久矣。禮樂之盛,聲教之美,薄海內外,莫不咸被仁風于帝澤也,于今三十有余載矣。近而侯甸郡邑,遠而山林荒服,老幼瞆盲,謳歌鼓舞,皆樂我皇明之治。夫禮樂雖出于人心,非人心之和,無以顯禮樂之和;禮樂之和,非自太和之盛,無以致人心之和也。故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5]29
(《太和正音譜·序》)
蓋雜劇者,天下之勝事,非太平則無以出。[5]57
(《太和正音譜·群英所編雜劇》)
朱權作為一位皇族戲曲家,其身份決定了他對戲曲藝術的認識具有“太和”之局限性,他把戲曲當作體現“太和之盛”同時又能促進“太和之盛”的工具。“太和之盛”方有“禮樂之和”,禮樂又可以教化人心,促使盛世的安穩。而能有這“太和之盛”皆因“皇明之治”。戲曲的政教功用自漢代司馬遷《史記·滑稽列傳》有之,其言“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6]3197“善為笑言,然合于大道”[6]3202。元代夏庭芝《青樓集志》也認為戲曲在君臣、母子、夫婦、兄弟、朋友等關系上“皆可以厚人論(倫)、美風化”[7]7,周德清《中原音韻序》也認為戲曲“曰忠,曰孝,有補于世”[8]。明初戲曲的政教功用發展至高峰,這有其積極意義,可為戲曲正名,將戲曲置于詩、文同等位置,但其負面效應遠大于此。戲曲作為一門藝術,過于強調其教化百姓的功用,戲曲就會成為歌功頌德的工具,而失去戲曲的藝術審美性。這一點體現在明初的戲曲創作中。
戲曲理論是戲曲創作的反映同時也指導著戲曲創作。這一時期的戲曲作品教化思想濃厚,甚至充斥著假道學的風氣,偏離了戲曲創作的正確軌道。高明所作《琵琶記》是明初戲曲創作重教化的典型代表,其第一出《副末開場》云:“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瑣碎不堪觀。正是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9],他以有“關風化體”為創作宗旨,講述了一個“子孝共妻賢”[9]的故事,故塑造了“全忠全孝蔡伯喈”[9]的形象。故該劇得到了朱元璋的褒獎,“高明《琵琶記》,如山珍、海錯,富貴家不可無。”[5]483由于統治者對《琵琶記》的稱贊,一大批宣揚倫理道德的戲曲作品產生。
成華年間文淵閣大學士邱濬所作傳奇《五倫全備記》,繼《琵琶記》之忠孝,提出忠、孝、節、義、信等“五倫全備”。他在該劇凡例中指出:
此記非他戲文可比,凡有搬演者,務要循禮法,不得分外有所增減,作為淫邪不道之語及作淫蕩不正之態。[5]210
并在卷首開場白中曰:
若于倫理無關緊,縱是新奇不足傳。風日好,物華鮮,萬方人樂太平年。今宵搬演新編記,要使人心總惕然。[5]210
每見世人搬雜劇,無端誣賴前賢。伯喈負屈十朋冤。九原如可作,怒氣定沖天。這本《五倫全備記》,分明假托名傳。一場戲里五倫全,借他時世曲,寓我圣賢言。[5]211
邱濬以圣人之是非為是非,作“圣賢言”,而非“吾心之言”。李卓吾《藏書·儒臣傳》中就“圣人之言”與“吾心之言”謂:“夫所謂‘作’者,謂其興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詞不可緩之謂也。若必其是非盡合于圣人,則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為是非,則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詞非由于不可遏,則無味矣。”[10]戲曲以圣人之是非為是非,充斥著假道學的氣息,則缺乏戲曲的藝術性。諸多戲曲理論家對此作出批判,如呂天成《曲品》謂:“大老鉅筆,稍近腐”[11]228。祁彪佳《遠山堂曲品》亦言“一記中盡述伍倫,非酸則腐矣”[11]46。邱濬作《五倫全備記》后不久,邵燦創作了《香囊記》。其第一出《家門》謂“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觀省名行。有缺綱常。那勢利謀謨。屠沽事業。薄俗偷風更可傷。怎如那歲寒松柏。耐歷冰霜。閑披汗簡蕓牕。謾把前修發否臧。有伯奇孝行。左儒死友。愛兄王覽。罵賊睢陽。孟母賢慈。共姜節義。萬古名垂有耿光。因續取《五倫》新傳。標記《紫香囊》。”[12]。從《琵琶記》到《五倫全備記》再到《香囊記》,戲曲創作均代“圣人言”,而缺乏“吾心”之作。明初還有很多諸如此類的作品,如成化年間姚茂良作有傳奇《金丸記》《岳武穆精忠記》《雙忠記》,弘治年間周禮作傳奇《東窗記》,正德年間沈齡應楊一清之邀,撰寫《四喜傳奇》獻給武宗并受到賞識,等等。可以說,這些劇作以《琵琶記》為首皆為“畫工”之作,宣揚教化思想,感人不深。
二、明嘉、隆間戲曲作品地位論爭開啟:從“畫工”向“化工”過渡階段
明嘉靖、隆慶時期人們意識到“程朱理學”對百姓身心的束縛,下層老百姓意欲擺脫這些條條框框,社會興起了“王陽明心學”。它強調人性本善,不需要依據外在力量去強制百姓,只需要稍微提醒以喚起百姓內心的良知,百姓就會自覺遵守規則從而達到統治者的意愿。此時統治者對戲曲的態度也趨于和緩,明代戲曲理論得以向前發展。戲曲理論重教化的風氣從明初持續至明中葉,走過了百余年漫長的低潮期,戲曲理論家開始對戲曲理論作精細化探索。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開啟了一場聚焦于戲曲作品《西廂記》《拜月亭》《琵琶記》地位高低的論爭。
論爭自何良俊始,他認為《拜月亭》居于《琵琶記》《西廂記》之上。而在此前,《琵琶記》作為“南戲之祖”得到統治者的稱贊,《西廂記》作為元雜劇的經典有“天下奪魁”[7]173之美譽,以此二劇為南北曲之首為諸多戲曲理論家所認可。何良俊高呼《拜月亭》居于二者之上,引起了諸多戲曲理論家的注意。王世貞首先發出反對之聲,何王二人的觀點逐漸形成論爭的熱點。何良俊《曲論》曰:
《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所撰……余謂其高出于《琵琶記》遠甚。蓋其才藻雖不及高,然終是當行。其《拜新月》二折,乃檃括關漢卿雜劇語。他如《走雨》《錯認》《上路》館驛中相逢數折,彼此問答,皆不須賓白,而敘說情事,宛轉詳盡,全不費詞,可謂妙絕。《拜月亭·賞春·惜奴嬌》如“香閨掩珠簾鎮垂,不肯放燕雙飛”,《走雨》內“繡鞋兒分不得幫底,一步步提,百忙里褪了根”,正詞家所謂“本色語”。[4]12
近代人雜劇以王實甫之《西廂記》,戲文以高則誠之《琵琶記》為絕唱,大不然。……祖宗開國,獨尊儒術,士大夫恥留心辭曲,雜劇與舊戲文本皆不傳,世人不得盡見,雖教坊有能搬演者,然古調既不諧于俗耳,南人又不知北音,聽者即不喜,則習者亦漸少,而《西廂》《琵琶記》傳刻偶多,世皆快睹,故其所知者,獨此二家。余所藏雜劇本幾三百種,舊戲本雖無刻本,然每見于詞家之書,乃知今元人之詞,往往有出于二家之上者。蓋《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其本色語少。蓋填詞須用本色語,方是作家。[4]6
何良俊言《拜月亭》“才藻雖不及高,然終是當行”“正詞家所謂‘本色語’”,故比之《西廂記》《琵琶記》更高一籌。他的評判標準主要是“當行”“本色語”。對于“當行”,他舉出《拜新月》二折、《走雨》《錯認》《上路》館驛中相逢數折等例子,具體講了“彼此問答”“敘說情事”兩方面。“當行”,也就是彼此問答不需賓白;敘說情事宛轉詳盡、全不費詞,如此“可謂妙絕”。他對“敘說情事”的內涵,并舉了《王粲登樓》與《西廂記》正反兩例加以闡釋:
大抵情辭易工。蓋人生于情,所謂“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者”。觀十五國《風》,大半皆發于情,可以知矣。是以作者既易工,聞者亦易動聽。即《西廂記》與今所唱時曲,大率皆情詞也。至如《王粲登樓》第二折,摹寫羈懷壯志,語多慷慨,而氣亦爽烈,至后《堯民歌》《十二月》,托物寓意,尤為妙絕,豈作調脂弄粉語者可得窺豈堂廡哉![4]7
從中可看出,何良俊作為文人士大夫,其審美標準明顯有別于普通百姓。他認為,對于情詞,劇作者容易描摹,普通百姓也喜歡聽。而作為文人,他以詩歌的意境來審視戲曲,推崇“羈懷壯志”“托物寓意”,故言《西廂記》為“調脂弄粉語”。對于其“本色語”,誠如俞為民先生言“理論家們在運用這一術語來評論作家和作品時,卻都根據自己的文學主張和批評標準”,何良俊“在運用‘本色’這一術語時,也有著自己特定的內容與標準”[13]。從他所舉《拜月亭·賞春·惜奴嬌》和《走雨》中的兩句話來看,他之所謂“本色語”似指戲曲語言的俚俗,曲白雜以鄉語、口語。從其反例“蓋《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來看,“全帶脂粉”指的是兒女之情兼語言不夠質樸,“專弄學問”也就是言語富麗,用典頻繁。何良俊對“本色”的理解似有所偏頗,“偏”在“全”和“專”上,依照當時的審美,《西廂》是略帶些“脂粉”,《琵琶》也有些“弄學問”,但何元朗如此用詞,顯然是不合適的。[14]從何良俊的戲曲理論來看,他對“當行”的闡釋,以及看到《琵琶記》“弄學問”的特點,有其獨到之處。但他以士大夫的審美,對“情詞”加以否定,對《西廂記》之真情視而不見,可謂是其局限性。故可以說,何良俊的戲曲理論具有從“畫工”向“化工”過渡的傾向。
何良俊推崇《拜月亭》,引起了王世貞的批駁。王世貞認為《西廂記》高于《琵琶記》高于《拜月亭》。其《藝苑卮言》認為《拜月亭》有“三短”:
《琵琶記》之下,《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撰,亦佳。元朗謂勝《琵琶》,則大謬也。中間雖有一二佳曲,然無詞家大學問,一短也;既無風情,又無禆風教,二短也;歌演終場,不能使人墮淚,三短也。[5]519
北曲以《西廂》壓卷:
北曲故當以《西廂》壓卷,如曲中語:“雪浪拍長空,天際秋云卷,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淺淡櫻桃顆。”是駢麗中情語。……“昨夜個熱臉兒對面搶白,今日個冷句兒將人廝侵。”“半推半就,又驚又愛。”是駢麗中諢語。“落紅滿地胭脂冷,夢里成雙覺后單。”是單語中佳語。只此數條,他傳奇不能及。[5]513-514
而高明《琵琶記》“冠絕諸劇”:
則成所以冠絕諸劇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仿佛如生;問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至于腔調微有未諧,譬如見鐘、王跡,不得其合處,當精思以求詣,不當執末以議本也。[5]518
王世貞的《拜月》“三短”是參照《琵琶記》來講的,其有“詞家大學問”、有“風情”且有“裨風教”“使人墮淚”正是《琵琶記》的特點。相較于何元朗批判《琵琶記》“專尚學問”,王世貞對“詞家大學問”予以稱贊。他充分意識到《琵琶記》作者“琢句之工、使事之美”,卻以此為戲曲之美,對《琵琶記》“作者之工”贊曰:
偶見歌伯喈者云:“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詔赴春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舍親闈。”頗疑兩句句意各重,而不知其故。又曰“詔”,曰“書”,都無輕重。后得一善本,其下句乃“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難舍春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赴親闈。”意既不重,而“期逼”與上“欲化魚”字應,“難赴”與“空有”字應,益見作者之工。[5]518
這充分體現出王世貞“工美”的戲曲思想,即以“畫工”為戲曲審美標準。有“風情”且有“裨風教”更是承襲明初戲曲為封建專制而服務的特點。可以說,王世貞對何良俊觀點的反駁透露出他仍以明初“畫工”為美。相校而言,何良俊的戲曲理論則稍有進步意義,有向“化工”過渡的趨勢。至此,戲曲理論家就何王二位的觀點進行再探討,形成兩派。明中葉后期,何良俊的觀點居上風,支持他的戲曲理論家有沈德符、徐復祚等人。這些戲曲理論家對何良俊的觀點加以發展并對王世貞言《拜月》有“三短”加以辯駁。
沈德符對何良俊的戲曲理論加以繼承和發展,他在《顧曲雜言·拜月亭》中謂:
何元朗謂《拜月亭》勝《琵琶記》,而王弇州力爭,以為不然,此是王識見未到處。《琵琶》無論襲舊太多,與《西廂》同病,且其曲無一句可入弦索者;《拜月》則字字穩帖,與彈搊膠漆,蓋南詞全本可上弦索者惟此耳。至于《走雨》《錯認》《拜月》諸折,俱問答往來,不用賓白,固為高手;即旦兒“髻云堆”小曲,模擬閨秀憨情態,活托逼真,《琵琶·咽糠》《描真》亦佳,終不及也。向曾與王房仲談此曲,渠亦謂乃翁持論未確,且云:“不持特別詞之佳,即如聶古、陀滿爭遷都,俱是兩人胸臆見解,絕無奏疏套子,亦非今人所解。”余深服其言。若《西廂》,才華富瞻,北詞大本未有能繼之者,終是肉勝于骨,所以,讓《拜月》一頭也。元人以鄭、馬、關、白為四大家而不及王實甫,有以也。《拜月亭》后小半,已為俗工刪改,非復舊本矣,今細閱“拜新月”以后,無一詞可入選者,便知此語非謬。[4]210-211
沈德符對何良俊觀點的繼承表現在他認同何良俊所言《拜月亭》問答往來不用賓白之妙,《琵琶記》雖有可取之處,但不及《拜月亭》。將《拜月亭》與《琵琶記》相比,認可《琵琶·咽糠》《描真》“亦佳”,但較之《拜月亭》即旦兒“髻云堆”小曲,則不及也,并對《拜月亭》模擬情態之形象逼真大加稱贊;將《拜月亭》與《西廂記》相比,認可《西廂記》“才華富瞻”,但較之《拜月亭》,稍遜一籌。他將“才華”比作“肉”,從其沿襲何良俊的觀點來看,似將質樸自然的語言風格視為“骨”。并且,他認為《琵琶記》與《西廂記》有共同的不足“襲舊太多”。沈德符較之何元朗的觀點,其發展表現在從語言擴展到曲律方面,認為《拜月亭》為南詞全本中唯一可上弦索者。因此,沈德符不單是從案頭之曲來看待這三本戲曲著作,同時注重戲曲的演唱功能。
徐復祚對何良俊、沈德符的觀點是批判性地繼承。其《曲論》曰:
何元朗謂施君美《拜月亭》勝于《琵琶》,未為無見。《拜月亭》宮調極明,平仄極葉,自始至終,無一板一折非當行本色語,此非深于是道者不能解也,弇州乃以“無大學問”為一短,不知聲律家正不取于弘詞博學也;又以“無風情、無裨風教”為二短,不知《拜月》風情本自不乏,而風教當就道學先生講求,不當責之騷人墨士也。用修之錦心繡腸,果不如白沙鳶飛魚躍乎?又以“歌演終場不能使人墮淚”為三短,不知酒以合歡,歌演以佐酒,必墮淚以為佳,將《薤歌》《蒿里》盡侑觴具乎?[4]235-236
王弇州取《西廂》“雪浪排長空”諸語,亦直取其華艷耳,神髓不在是也。語其神,則字字當行,言言本色,可謂南北之冠。[4]242
由上看來,徐復祚對三本著作的戲曲地位排序是《西廂記》高于《拜月亭》高于《琵琶記》。一方面,他從“宮調”“平仄”方面稱贊《拜月亭》,認為何元朗“未為無見”;另一方面,他肯定了王弇州對《西廂記》的褒獎,注意到《西廂記》之“神”,贊其為“當行”“本色”之作,是“南北之冠”。同時,對王弇州之《拜月亭》有“三短”予以批駁。他指出“弘詞博學”不為聲律家之事,也就是不以文章的標準來論戲曲。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認為“風教”乃是“道學家”所為,而非聲律家之事,一改明初戲曲理論道學化現象。總體來講,徐復祚從明初戲曲重教化的理論中脫離出來,意識到戲曲的審美特質。故其戲曲理論符合從“畫工”向“化工”的過渡。
三、明萬歷以后戲曲作品地位論爭的進一步發展:“化工”階段
明代社會思潮從“程朱理學”到“王陽明心學”,其特點都是企圖讓百姓被動或主動遵守社會規則,以維護君主對整個社會的統治。而到了晚明時期,市民階級興起,資產階級的萌芽產生,出現了“王學左派”。相較于“王陽明心學”,有其進步之處,它更注重百姓的需求,強調順從民性。其中,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他不再以圣人或者君主的準則為“道”,而是以百姓的合理需求為“道”。李卓吾也是“王學左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張關注百姓穿衣吃飯這一類的實際生活需求。其《焚書·答鄧石陽》謂:
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飯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者也。[1]4
李卓吾認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百姓最關注的無非是吃飽穿暖,其他的事情都與穿衣吃飯相類似。也就是說,統治者應該順從民性,以民為本。從“程朱理學”到“王學左派”,明代的思想完成了從理學到心學的轉變。這一時期統治階層對百姓思想的禁錮開始瓦解,戲曲作品地位高低的論爭在心學思潮的影響下有了新的發展。呂天成、王驥德等戲曲理論家對何元朗陣營的觀點進行針對性地批駁,認為《琵琶記》《西廂記》高于《拜月亭》。但其評判標準則不同于王世貞,這一階段的戲曲理論家更加注重戲曲所傳達的“真情”以及戲曲的傳神境界。除此之外,李卓吾對以上兩派的觀點進行辯證地吸收,提出“化工”與“畫工”說,認為《西廂記》《拜月亭》的戲曲地位高于《琵琶記》,在這場論爭中具有總結性的意義。
呂天成《曲品》上下兩卷,上卷品作舊傳奇者及作新傳奇者,下卷品各傳奇。其上卷將高則誠列為“右神品”:
永嘉高則誠,能作為圣,莫知乃神。特創調名,功同倉頡之造字;細編曲拍,才如后夔之典音。志在筆先,片言宛然代舌;情從境轉,一段真堪斷腸。化工之肖物無心,大冶之鑄金有式。關風教特其粗耳,諷友人夫豈信然?勿亞于北劇之《西廂》,且壓乎南聲之《拜月》。[11]210
與之對應,下卷將《琵琶記》列為“神品一”:
《琵琶》蔡邕之托名無論矣,其詞之高絕處,在布景寫情,真有運斤成風之妙。串插甚合局段,苦樂相錯,具見體裁。可師,可法,而不可及也。詞隱先生嘗謂予曰:“東嘉妙處全在調中平、上、去聲字用得變化,唱來和協。至于調之不倫,韻之太雜,則彼已自言,不必尋數矣。”萬物共褒,允宜首列。[11]224
呂天成對高則誠及《琵琶記》給予很高評價,稱其“勿亞于北劇之《西廂》”。所謂“勿亞于”,也就是“大于等于”,他認為《琵琶記》的戲曲地位要高于《西廂記》,至少二者也應雙峰并峙。值得注意的是,他開始注重戲曲所蘊含的“情”,但戲曲理論家們對戲曲作品的評論標準往往不統一,其間蘊含著他個人獨特的閱讀感受。他認為《琵琶記》乃是“情從境轉,一段真堪斷腸”“其詞之高絕處,布景寫情”。同時,呂天成認為《琵琶記》“且壓乎南聲之《拜月》”,將《拜月亭》列為“神品二”:
云此記出施君美筆,亦無的據。元人詞手,制為南詞,天然本色之句,往往見質,遂開臨川玉茗之派。何元朗絕賞之,以為勝《琵琶》,而談詞定論則謂次之而已。[11]224
(《曲品》下)
呂天成看到了《拜月亭》之“天然本色”,開“玉茗派”創作風氣。但與《琵琶記》相比,則“次之”。總體來講,呂天成認為《琵琶記》高于《西廂記》高于《拜月亭》的戲曲地位。
王驥德認為《西廂記》高于《琵琶記》高于《拜月亭》。他針對何元朗所謂的“本色語”“蓋《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等問題進行有力批駁,認為《西廂記》《琵琶記》正是“本色”之作:
古戲必以《西廂》《琵琶》稱首,遞為桓文。然《琵琶》終以法讓《西廂》,故當離為雙美,不得合為聯璧。《琵琶》遣意嘔心,造語刺骨,似非以漫得之者。顧多蕪語、累字,何耶?《西廂》組艷,《琵琶》修質,其體故然。何元朗并訾之,以為“《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殊寡本色”。夫本色尚有勝二氏者哉?過矣!《拜月》語似草草,然時露機趣;以望《琵琶》,尚隔兩塵。元朗以為勝之,亦非公論。[15]109
王驥德認為《西廂記》“全帶脂粉”也就是“組艷”,《琵琶記》“專弄學問”即“修質”,由其“體”所決定,二者皆為本色之作。其《曲律·雜論第三十九上》對“本色”作出闡釋:
當行本色之說,非始于元,亦非始于曲,蓋本宋嚴滄浪之說詩。滄浪以禪喻詩,其言:“禪道在妙悟,詩道亦然。唯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有透徹之悟,有一知半解之悟。”又云:“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騖愈遠。”又云:“須以大乘正法眼為宗,不可令墮入聲聞辟支之果。”知此說者,可與語詞道矣。[15]112
這里的“詞道”即是指戲曲創作的規律性。王驥德以他所理解的“本色”,評判這三本著作,認為《西廂記》《琵琶記》是“本色”之作。上述諸多戲曲理論家認為《拜月亭》為本色之作,無可爭議。而對《西廂記》《琵琶記》之本色,則爭議較大。事實上,《拜月亭》作為早期南戲,起于民間,可謂民間化的本色,而《西廂記》等是被雅化了之后,堪稱典雅化的本色。戲曲產生之初,雜有鄉間俚語口語,發展至后來有了文人的參與,經過提煉、修飾,這時的“本色”則體現出人文精神與自然律則的統一性。王驥德認為“本色”一詞源自嚴羽:
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16]
嚴羽之“本色”被引入戲曲則見于徐渭《南詞敘錄》:
填詞如作唐詩,文既不可,俗又不可。自有一種妙處,要在人領解妙悟,未可言傳。[5]487
并且,徐渭就“本色”作進一步闡釋:
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猶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書評中婢作夫人終覺羞澀之謂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帶,反掩其素之謂也。故余于此本中賤相色,貴本色,眾人嘖嘖我呴呴也。[17]
徐渭以婢女扮作夫人為喻,辨析“本色”與“相色”。婢女的特點是“素”,涂脂抹粉、插帶裝扮成夫人,只覺羞澀,而無夫人的氣質,反而遮掩其“素”。換言之,“本色”就是要與劇中人物特定身份相符。這番話道出了徐渭“賤相色,貴本色”的原因。據此,徐渭認為南戲有一高處,即“句句是本色語”:
南曲固是末技,然作者未易臻其妙。《琵琶》尚矣,其次則《玩江樓》《江流兒》《鶯燕爭春》《荊釵》《拜月》數種,稍有可觀,其余皆俚俗語也;然有一高處,句句是本色語,無今人時文氣。[5]486
從中可以進一步看出,徐渭之“本色語”,指沒有時人文氣。“以時文為南曲”自《香囊記》始有。但同時也體現出,“本色語”并不等同于“俚俗語”。可見,王驥德作為徐渭的弟子,就“本色”與“妙悟”的關系充分地借鑒了徐渭的觀點。并且,王驥德認為《琵琶記》“本色”之作,但也看到其“遣意嘔心,造語刺骨,似非以漫得之者”,這正是李卓吾所謂“彼高生者,固已殫其力之所能工”。對《琵琶記》之“工”,王驥德作進一步地闡述:
《琵琶》工處甚多,然時有語病,如第二折引“風云太平日”,第三折引“春事已無有”,三十一折引“也只為我門楣”,皆不成語。又蔡別后,趙氏寂寥可想矣,而曰“翠減祥鸞羅幌,香消寶鴨金爐,楚館云閑,秦樓月冷”,后又曰“寶瑟塵埋,錦被羞鋪,寂寞瓊牕,蕭條朱戶”等語,皆過富貴,非趙所宜。[15]110
王驥德從語言和劇中人物形象上指出《琵琶記》工處之不妥。故綜合來講,王驥德認為“《琵琶》終以法讓《西廂》,故當離為雙美,不得合為聯璧”。對《拜月亭》,王驥德予以一定的肯定,稱其“語似草草,然時露機趣”,但與《琵琶記》相比則遠不如。他對王世貞、何元朗的觀點綜合評定:
弇州謂“《琵琶》‘長空萬里’完麗而多蹈襲”,似誠有之。元朗謂其“無蒜酪氣,如王公大人之席,駝峰、熊掌,肥腯盈前,而無蔬、筍、蜆、蛤,遂欠風味”。余謂:使盡廢駝峰、熊掌,抑可以羞王公大人耶?此亦一偏之說也。[15]110
從王驥德所設例子來看,他肯定了王世貞的觀點,而認為何良俊的觀點是“一偏之說”。晚明另一位戲曲理論家李卓吾與呂天成、王驥德的戲曲觀點稍有不同。
李卓吾認為《西廂記》《拜月亭》高于《琵琶記》。李卓吾的“化工”與“畫工”說對這場戲曲作品地位之爭具有總結性,他對何、王兩派觀點中較為中肯的部分有所吸收和融合,而非一味地肯定或否定。以上兩派戲曲理論家具體所論爭的點有:《琵琶記》“詞家大學問”,《西廂記》“才華富瞻”,有無裨風教、是否感人,“本色”與否。對這些論爭點進行分析,實則是以“自然”為美還是以“工”為美,尚“風情”還是尚“風教”。李卓吾推崇“化工”是以“自然”為美、尚“風情”的表現。
從論爭過程中諸位戲曲理論家的觀點來看,以“自然”為美的戲曲理論家除了李卓吾,還有何良俊、沈德符、徐復祚、王驥德等,以“工”為美的戲曲理論家以王世貞為典型代表。李卓吾在《琵琶記卷末評》曰:“《琵琶》短處有二:一是賣弄學問,強生枝節;二是正中帶謔,光景不真。此文章大家之病也,《琵琶》兩有之。”[5]548李卓吾認為“二短”是“文章大家之病”,也是“畫工”之病。尚“風情”的戲曲理論家有李卓吾、何良俊、沈德符、徐復祚,尚“風教”的戲曲理論家有王世貞、呂天成。而王驥德雖盛贊《西廂記》之“風情”,同時也對“風教”之作《琵琶記》予以很高評價。無論是“風情”還是“風教”,能否動人,始終是戲曲藝術的至高標準。王世貞認為《琵琶記》“歌演終場”能“使人墮淚”,呂天成認為其“情從境轉,一段真堪斷腸”。李卓吾對這個問題作出自己的見解:“彼高生者,固已殫其力之所能工,而極吾才于既竭。惟作者窮巧極工,不遺余力,是故語盡而意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以竭。吾嘗攬《琵琶》而彈之矣:一彈而嘆,再彈而怨,三彈而向之怨嘆無復存者。此其故何耶?豈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蓋雖工巧之極,其氣力限量只可達于皮膚骨血之間,則其感人僅僅如是,何足怪哉!《西廂》《拜月》,乃不如是。”[1]97李卓吾初讀《琵琶記》也如王世貞、呂天成一樣,“一字一哭”“一字千哭”“一字萬哭”[9],認為《琵琶記》是感人之作。但其反復閱讀之后,發現《琵琶記》之感人是浮于表面的,入人心者不深。李卓吾對“真情”的關注和闡述要高于諸位戲曲理論家。綜合以上兩方面,李卓吾將《西廂記》《拜月亭》歸為“化工”之作,較之“畫工”之作《琵琶記》,更勝一籌。
綜上來講,明代戲曲理論經過了從“畫工”向“化工”的演變。明初戲曲理論以朱權《太和正音譜》為指導思想,出現了一大批為封建專制服務的“畫工”之作,假道學風氣盛行。明中葉何、王二人對戲曲作品《西廂記》《拜月亭》《琵琶記》地位高低的討論形成熱點。何良俊、沈德符、徐復祚等人對天然本色的《拜月亭》的推崇體現出戲曲理論從“畫工”向“化工”的過渡。晚明呂天成、王驥德對何良俊陣營的觀點進行了“否定之否定”的批駁,李卓吾對以上諸位戲曲理論家的觀點進行總結和進一步發展。戲曲創作的藝術性得到關注,“真情”突顯出來,戲曲理論發展為“化工”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