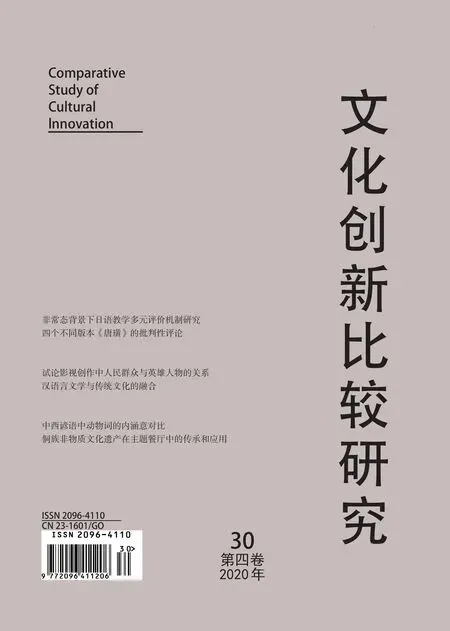重慶大學生不文明語言使用狀況調查研究
仵兆琪 陳 婷
(重慶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重慶 404100)
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在人類文明和個體智慧的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而高校則是傳播人類文化的圣地,構建高校和諧語言環境對人類文明和個體發展極為重要。但針對高校大學生這一群體的語言文明狀況的研究非常缺乏,大學生不文明用語使用的教育問題也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本文聚焦重慶大學生不文明用語使用現狀,全面調查分析臟話等詞語的使用的頻率、原因和影響制約因素,以期為高校語言環境的凈化提供一些參考。
1 調查方法
本文采用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相結合的方式,以重慶在校大學生為調查對象,首先通過問卷星向學生發放網絡問卷,從大學生對不文明用語的認知與態度、使用原因、使用頻率、使用后的補救與反思等角度來分析大學生使用不文明用語的具體情境;其次隨機抽取重慶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及三峽學院的10名大學生進行面對面的深入談話,以深入剖析重慶大學生不文明用語的使用真實心理,及不文明用語使用的限制和影響。
2 調查內容及分析
本次網絡調查共收回467份問卷,其中11份問卷因答題不合規范視為無效,故實際分析456份,主城大學生112名,區縣344名,包括大一至大四452人,研究生4名,男生卷64份,女生卷392份。在深度訪談中,10名大學生專科8名、本科2名,男女生各5名。
2.1 大學生對不文明用語的認知及態度
2.1.1 不文明用語認知較全面,傾向于使用方言臟話
陳原認為“臟話(不文明用語)”就是一種關于人的身體、器官生理現象以義及性行為的禁忌詞語,而這些詞語無法被社會傳統習慣接受而成為一種語言忌諱。[1]問卷第6題“您認為不文明用語是什么樣的語言?”的調查結果顯示,83%以上的學生認為臟話“涉及祖宗親戚的語言、將對方比擬為污穢物的語言”。大學生普遍認為此類詞語侮辱性強,這一數據特點顯示了中國人看重“輩分”、“血緣”的文化傳統。而“您通常說的臟話指哪些內容?”這一題票數最高的前三項依次是:語氣詞、名詞,、方言詞。可見,大學生使用不文明語的內容不僅涉及到“血緣”,還多延伸至色情、隱私、貶損。而重慶方言語調變化多樣,詞語生動,部分臟話表面“不臟”如“串串,棒槌”等,便于說話者充分宣泄感情,所以大學生有不少人使用方言臟話。數據顯示,63.6%的大學生認為“使用重慶方言比使用普通話更容易說臟話”。而深入訪談中有2位同學覺得“普通話就趕腳罵不來的”“要用重慶話才帶勁。”這一“渝罵”與“京罵”一樣,都是由地域性的文化語境滋生出的特殊臟話。
2.1.2 對臟話多持否定態度
問卷中共有3道題測試了重慶大學生接受不文明語言、使用臟話等不文明詞語的態度:其中78.95%的人認為說不文明用語會對形象造成破壞,因為“這是衡量一個人素質的重要標準”;73.68%的學生覺得自己使用臟話時很低俗。人們對于臟話的抵制和反感來源于臟話自身的“冒犯性”,語言學家露絲·韋津利在《臟話文化史》中將這一特點視為“臟話”的六個核心條件之首。[2]因此,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使用不文明話語的人都會觸犯對方的禁忌,造成聽者不自在、震怒。正所謂“言為心聲”,語言作為人際溝通的重要方式還反映了說話者的思想和內心情感,進一步展示其道德素質。 約翰·洛克指出:“一切德行與美善的原則在于,當欲望得不到理性認同時,我們需要具有克制自身欲望得到滿足的能力。”[3]所以51.75%的大學生對說臟話者“反感,覺得素質低下”。盡管大多數人都認為說臟話不僅會冒犯到他人、降低自身品質,但現實生活中臟話缺普遍存在。問卷中“當別人對你說臟話時候,你是怎么做的?”一題,有35.53%的學生選擇了“置之不理”,33.33%的學生選擇“言語回擊”,甚至“動手回擊”(占2.19%)。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選項“您會介意跟一個說臟話的人做朋友嗎?”的統計中,竟然有50%的人選擇了“不一定”,25%的人選擇了“不介意”。 通過深入訪談,我們發現大學生對臟話等不文明話語的容忍度依情況而定,重慶方言中諧趣、幽默的臟話雖然不文明,但使用者大都并非惡意和下作。
2.2 大學生不文明用語使用情境
不文明用語這種禁忌性的語言雖然遭人排斥,但卻有它產生的原因和必要性。數據顯示,只有25.44%的大學生選擇了“從來不說臟話”,且22.37%的人認為“周圍極少有人說臟話”。這兩組數據對照基本可以確定重慶大學生使用不文明話語的比例。語言學家Thomas與Wareing(1999:6-10)認為,人們使用語言表情達意、溝通信息,主要體現了語言的指示功能、情感功能、美學功能和社交功能。[4]我們結合語言的四大功能就能更好地分析大學生不文明話語的使用原因和背景。
2.2.1 以“臟話”回擊“臟行為”
上文已說有不少大學生選擇不文明話是被迫“回擊”,面對骯臟的某些行為或環境,人們會以“臟話”指稱這些對象。如大學生使用的部分臟話詞語,就是用粗俗的男女性行為指示某些令人不安的行為或事件。所謂“君子動口不動手”,雖然罵人不對,但無可否認有時候適當的臟話發泄也減少了暴力沖突。
2.2.2 發泄不滿,釋放壓力
情感功能是臟話最顯著的功能。63.16%的大學生表示使用不文明話語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表達自己的強烈情感。在“您通常在什么情況下說臟話?”這一問題中,排列前三的選項分別是:事態不受控制時(吃驚……)、發生沖突時(行為、認知沖突等)、打游戲時。一般來說,臟話的情感表達功能多數是宣泄負面情緒,但有時也可用來表達喜悅等情緒。訪談中的一名男生表示在打游戲獲勝時喜歡說臟話。問卷顯示,有28.95%的大學生說臟話只是出于“個人習慣”,當臟話被頻繁使用進而變成口頭禪時,壞習慣就更難以改變。
2.2.3 顯示個性,化“丑”為“美”
從數據中我們發現,16.67%的大學生認為“周圍說臟話的很多”,自己因跟風說臟話的占4.39%。此外,大學生說臟話受到周圍其他人影響的有47.37%,受同學或朋友影響的有36.84%,而家庭只影響3.95%。大學生跟風說臟話有時候只是故意想看對方生氣、暴怒的樣子,他們想用詞語操縱他人的“魔力”證明自身的獨特和個性。特別是當下流行的“嘻哈”說唱文化以丑為美,歌詞用對偶、押韻的方式夾雜了大量的臟話。大眾傳媒不當的宣傳,使不少青少年迷戀說臟話的“暢快”。訪談中有位男生表示自己的音樂偶像就擅長說唱歌曲,而他最喜歡的幾句歌詞也少不了臟字臟詞,“感覺說那幾句話的時候特舒暢!”以不文明話語入詞的形式其實體現了語言的美學功能,部分臟話適于頻繁的押韻和變化形式,展示了說唱者的語言才能。而這些臟話本意并非準確傳達信息,更多是宣泄強烈感情并將此種情緒強加到聽者的身上。
2.2.4 人際互動,融入圈子
有13.16%的大學生在“與朋友交往時”使用臟話,16.67%的人認為臟話“用于社交能加深友誼”。持這種觀點的人數雖然不多,但是訪談中兩名男生的表述為我們呈現了臟話在當下大學生圈中是如何發揮交際功能的。“能用臟話互相罵,那是好朋友,我們都不介意這種方式來溝通。”“男生都習慣說臟話。”他們還提到了用方言臟話會更好地融入本地圈子,正所謂“入鄉隨俗”。如重慶方言中“崽兒”、“幺兒”的稱呼語已經成為相當多人的口頭禪,相熟的朋友之間也會用此稱呼來拉近關系。加拿大社會學家戈夫曼的研究表明:當人們相遇時,面對面互動的基本處境便會具有極大的宣示性,即互動雙方會透露出彼此的外表、階層、關系……等信息,并藉由社會儀式化的過程將這些信息標準化后傳達給對方[5]。臟話打招呼也符合戈夫曼所提出的“互動儀式理論”,“崽兒”等臟話的本意帶有凌辱的意味,通常使用這類稱呼的人比對方地位(如金錢、年齡、權勢)高,且雙方應該關系非常密切,否則會引發誤會和爭斗。
2.3 大學生使用臟話的限制因素
2.3.1 文明環境的約束
社會認知理論認為,人與環境互相影響,人的行為既受環境的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著環境。66.23%的大學生非常注意說不文明話語的場景;在嚴肅、正式的場合中72.81%的大學生都覺得“要表現得文明一些”;而67.11%的人則在“您認為一段時間經常聽到臟話,說臟話的頻率會上升嗎?”這一題中選擇了“是”。可見,無論是網絡還是現實環境都會對大學生使用臟話產生一定的影響,反之,個人也會對現實環境和集體環境產生推動作用。正如數據所證,72.37%的人覺得自己說臟話是受到家人、同學的影響。但因為高校所教育對象大多已成年,故對語言文明這塊的監管不夠重視,調研數據表示只有35.09%的高校“明令禁止說臟話”,36.84%的高校“不允許說臟話,但不怎么管”;36.84%的教師會對說臟話的學生“批評教育、嚴格監管”,44.3%教師“批評教育,之后不怎么管”。
2.3.2 自我認知的警醒
陳汝東先生說:“污言穢語不僅影響人際交往與合作,給社會、他人造成危害,而且也降低了一個人的品格,為社會輿論和道德所不容。”[6]針對大學生說臟話的態度和認知分析也得出大部分學生對臟話所造成的惡果有較為清醒的認識,有51.75%的人覺得說臟話者“惡心,令人反感”;在“您認為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臟話使用頻率會降低嗎?”這一題中75%的大學生都覺得“會”。可見他們普遍認為臟話使用頻率與學識成反比,正因為有如此認知,高教育水平、高觀感度的大學生們才會謹慎對待臟話。張煥香等人針對北京高校大學生語言文明狀況的調查研究發現,文明用語的使用與性別有關。她認為,女性學生說話更注意禮貌性,文明用語的使用具有明顯的優勢。[7]而經過深入訪談,本次調研也發現女性大學生的語言文明自覺度高于男生,她們更在意語言給他人帶來的影響和對自身形象的作用。除此之外,在校成績好、擔任學生會等職務也減少了臟話的使用頻率,可見若大學生始終對自我保持清醒、嚴肅的認識,就不會頻繁觸及臟話這一“紅線”。
2.4 大學生使用臟話后的反思和補救
此次調研中,有19.74%的大學生在說完不文明的詞語后“非常后悔”, 82.89%的大學生“正在改正”說臟話行為。雖然有部分學生被迫用臟話反擊、宣泄不平,但數據說明大學生對于臟話有著“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無奈和愧疚。更有21.05%的大學生選擇使用攻擊力較小的網絡流行臟話(翔、我去年買了表)如諧音字或英文對應語(TMD、NMB)以降低臟話的侮辱性。而對“如果你的臟話傷害了,你如何挽救?”一題的回答中,66.23%的同學會“直接道歉”,28.07%則選擇“開玩笑岔開話題”,只有5.7%的人選擇“無所謂,順其自然”。受訪一個女同學說“無傷大雅的話,那么就此打住,但會提醒自己不再重說(臟話)。”還有一位男生表示:“如果真損了他面子,就會以開玩笑的方式道歉。”
3 調研結論
愛德華·薩丕爾在《語言論》中指出:“語言不脫離文化而存在,就是說,不脫離社會流傳下來的、決定我們生活面貌的風俗和信仰的總體。”[8]臟語是人們對社會認知的反映和個人內心情感的表達形式,突出體現了語言的情感、交際功能。從上文可知,要杜絕重慶大學生使用不文明話語是非常困難的,但我們不能消極放任。在研究中,不論是受訪者還是問卷調查,都顯示朋友圈和網絡是大學生不文明語言現象的重災區,這提示我們可以通過下面兩種途徑減少不文明話語的發生:
3.1 正視大學生使用不文明話語的現狀,不能“談臟色變”
大學生一方面抵制、鄙視不文明話語的使用者,另一方面又將臟話等視為宣泄情緒、另類表達的方式之一。部分臟話新詞,如“屌絲”、“我去年買了個表”等,已經隨著社會的發展由粗俗語變為戲謔性質的自我調侃。因此,我們對大學生言語失范不能搞“一刀切”,而應區分臟話在具體情境中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如果是彰顯個性、單純施暴,那么必須及時制止并施以懲罰;如果是以網絡流行語和省略語等諷刺時弊,那么我們也應該尊重這種頗具個性的表達方式,并引導其向正面衍生,而非暫時性泄憤。錢理群曾經表示:“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時間,這是我的兩個基本信念。”如果大學生僅僅是為了好玩、彰顯個性而去罵人,生活會教育他如何使用“文明用語”;如果為了宣泄不滿,教師和管理者則切忌站在力量和道德的制高點上對這樣的學生橫加指責。如此,只能是反襯出我們濫用權利的“無能”,因為只有順勢利導、凈化生存的環境,臟話才能“疏而不堵”。
3.2 營造更為健康、文明的語言環境
問卷數據顯示,大學生所用不文明話語很多存在于重慶方言中。從方言臟話詞語的語言構成來看,“錘子”等詞一般都比較簡短,多由一個字、兩個字的名詞、動詞或者兩個詞的動賓結構出現。其讀音短促而有力,聲調曲折可變,隨使用者的心情和說話語境而變化。因此,高校一方面要大力推廣普通話,減少方言使用頻率;另一方面,可以制作方言使用宣傳片,呼吁大學生正面使用方言。此外,還要加強網絡環境的凈化,多在學校公眾號平臺推薦如《弟子規》中 “刻薄語,穢污詞,市井氣,切戒之”等經典之語,注意QQ群、朋友圈的監管。總之,大學生年輕氣盛,對臟話一味的堵截可能會適得其反,而善意的提醒、別出心裁的宣傳提示,并輔以人際間的相互監督,將比嚴厲制裁更為有效。相信只要采取適當措施,拋棄社會偏見,高校語言文明建設會取得更多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