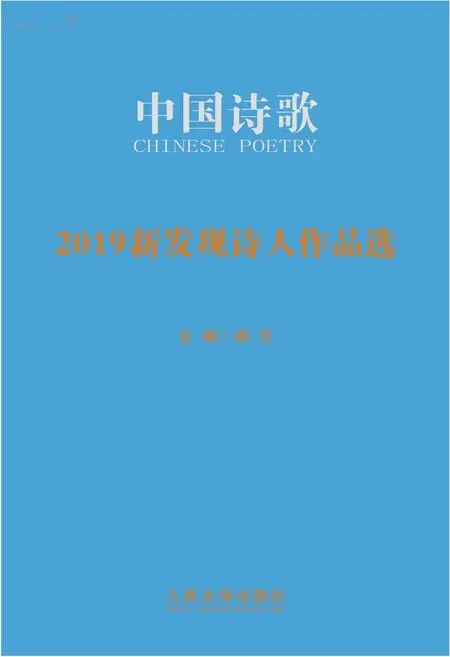陌鄰的詩
黃金面具
不提 今夜不提月光末了臨陣脫逃
而舊年的雪 將在新歲繼續流淚
不提煤火撲騰幾下 旋即深陷灰燼
多年生死成兄弟 老弟 走一個
不提眾兄弟已老 像圈老倔的橘皮
有人手指僵硬 握不緊一只酒杯
不提徹夜大風中滿坡翻滾的茅草
并不如一頭花白蒼茫 來 敬老哥
不提百八十米腳手架 人就是螞蟻
螞蟻們吭哧吭哧 把人間抬往天堂
每一塊鋼鐵 其實都比脊骨堅硬
其實黃金遠比頭顱昂貴 你們不提
其實一只螞蟻翻落 輕過一粒陽光
酒杯相碰 漸成今夜唯一回音
不提 不提火車更像一把孤獨的刀
終點不過是碗大個疤 統統不提
要說 就來說春晚光鮮年賽一年
說桃符換新說春聯燙金說燈籠大紅
說窗外的煙花 繁花再生繁花
若天空里 眾亡靈鍛造黃金的面具
親人
夜色初涼 已有人群接連趕來
于身體睡眠之際 和我相逢
他們三三兩兩 手提月光
——月光是盞心疼塵世的馬燈
白晝之后 徹夜流淌的皎潔
一遍一遍 反復浣洗人間陰晴
被稀釋的親疏 不再那么有別
我們交談 扎堆 相擁取暖
有人端出酒杯 勾兌流年
許多生活的堅硬 我們一碰而盡
同生前一樣 他們依舊酒量窄淺
三杯下肚 尥開一輩子輸贏
竟也輸贏相當 出進兩訖
依舊懷揣吝嗇 新瓶倒出舊酒
無酒可倒 我們也會頻頻舉杯
舉起多年來的自斟自飲
舉起陰陽兩隔 生死殊途
舉起彼世今生 唯一一盞馬燈
人群之中 我也曾遇見自己
滿一杯酒 我們就是至親的親人
寒夜記
北風一夜緊 捎帶緊了緊王家莊
巷里巷外 一扇扇鑄鐵大門
不約而同板起臉來 一本正經
你也不再想望 邂逅烏有的愛情
你卻邂逅所有愛情 你邂逅過
緊抱夜晚 把所有來世借給今生
所有感情 逐一考據為愛情
你把所有姐妹 暗地里喚作戀人
你定和妹妹中的她 結為夫婦
清晨小販手里 她接過新鮮蔬菜
黃昏大風臨門 你燒紅爐火
你們生有可愛寶貝 一定是女兒
你會給她們說千里萬里的路和云
但將省略此刻 此刻燈火閃滅
夜色如鋒刃 一寸寸逼退星辰
你瞪大雙眼 聽見黑暗一劍封喉
嘉陵釣事
還在一個人揮竿 一鉤一鉤揮出
江濤拍岸 一掌一掌拍向他的腳底
靜極 如遲疑的往事扇動翅膀
而對岸 江水是掙脫韁索的烈馬
永不回頭 頭頭撞命崖壁 千堆雪
之上群峰莽莽 是兀立天空的鐵
秋風里 銹出漫山紅葉 銹出創口
他身后 有浪頭擱淺 卻自成河流
水望著水 像望著過去 像窺視
大雨漫過季節 終歸留住些什么
譬如裸石 譬如一個人的泥沙俱下
愿者上鉤 或許真會有誰孤注一生
似一尾魚 縱身吻向冰冷的釣鉤
他頻頻起鉤 頻頻釣起草屑 葦根
弧線再次凌空之際 一頭黃昏躍出
像放下屠刀 有人終于揮竿而出
用盡畢生氣力 釣起一串嘟嘟忙音
能飲一杯無
寒露一過 月光似乎變得熙攘
似有新的人群 人群之中左右奔走
你識得他們 你枝枝蔓蔓的親人
然又砍枝斫蔓 深藏自己的親人們
你們碰面 還會匆忙塞你把月光
多么像那些年 女人們塞你把葵花
而男人們 則訥訥然不多言語
煙鍋一暗一明 是風把星辰擦亮
他們說 須得在大雪封山前趕回
須得再次深藏 方可躲得冰凍三尺
話音未落 已有雪花大片飄落
一群群白衣小人 赤腳天地間奔跑
你看著親人們 轉身 倏爾上路
看他們淺一腳深一腳 看他們跌撞
大雪覆壓枝蔓 白茫茫得發黑
你得承認 他們實際自你體內出走
能飲一杯無 你急忙立身大喝
雪們陡然消失 你也剝不開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