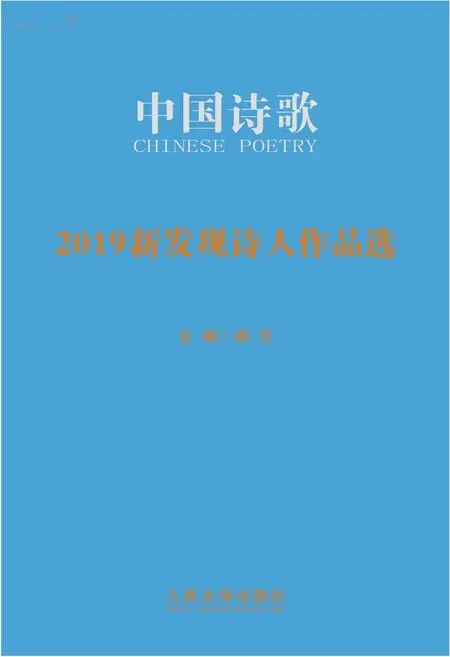陳凱啦的詩
春
我不屑于討論這世間關于春天的命題
猶如飛蛾投入火 月亮投入海水
我盡力維持著與這世界微妙的平衡
懷抱擁擠 然后把自己掙開
剛剛好的桃花溪里浮著一只鴨或者一尾魚
哪有那么多“春江水暖鴨先知”
尋個潮濕的地方一頭扎下去
春天 就來了
孤寂的孩子啊 能夠仰望天空是一件幸事
女人的胸脯上 必然浮著一枚彎月
如果這春天的罪惡能夠饒恕我
我也必將伏在這廣闊的大地上
棄筆從耕
行星
今日七點,大雪
我沒有起身
雨下了一天,雪下了七天
我總在夢里夢見一切崩塌之物,包括自己
可惜的是時間太長,我又腐朽迅速
而吶喊,仿佛是一件
遙遠而又不可追究的往事
如果有一粒灰塵和我的軌跡相同
哪怕是暫時,我也欣喜若狂
今日十點,新聞正好響起。播放
“一顆行星正經歷一場雪崩。”
酒
喝酒的動作,像在捕捉一尾魚
她說。是靈活的,所以需要使用誘餌
把胃里的火把一一釣出
火燃燒得旺了,就升起來
成為太陽,月亮
成為別的東西,使黑夜從山坡上滾下來
讓一朵花成為一個男人的春天
像千百個人搖晃同一個破碎的我
姑娘。她這么呼喚
可我不是。
羅賓·威廉姆斯
我的身體里有三個人
兩個女人,一個男人
女人對另一個女人扣動扳機的時候,我在場
加特林機槍,圓筒,1962 型
子彈以一分鐘一百碼的速度擊穿心臟
子彈射出去,彈回來
男人女人反反復復起身,坐下
此刻,不適宜兒童奔跑
任何一根針都可以成為一把刀
奶奶
她把身體蜷縮成干癟的圓
把憤怒、愉悅,以及每夜打開門的目光
小心地藏進褶皺
偶爾拿出來,就已經變成泛黃的老照片
或者,是喃喃時語氣里的感慨
牽著她的手時,我仿佛牽一個孩童
重復走路,重復學習使用手機
重復禿了牙床的大笑
隱疾
午夜,無話可談。
我與疾病耳鬢廝磨,它總是強迫我起身
看時間如何撕碎一百個月亮
拼成白晝
而今夜,月是圓的
我開始放棄睡眠,寫斷斷續續的詩
固執地不說——早安,晚安
在另一邊,或許有個和我一樣的人
因為對溫熱需求得不夠
便被長久的疼痛敲門算賬
今夜,月是圓的
而我的隱疾正把我豁開一道口子
把我二十年的嚎叫
一股腦地塞進身體里去
人間
人間是鮮奶與粥共煮的濃稠
裝進罐子里,售價三分
昨夜,雨水還未淹過我的一半
午夜時分,天空正好陰沉
仿佛子宮所包裹的顏色
我把月光聽了十八遍
然而沒有揚州
把月亮吞下,吐出嬰兒
遠方,流淌的河是女人
詩人說,在桂林購得大衣一件
五公斤,恰好是人間的重量
然而蘭波說,光陰短暫
陽光終究會踏碎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