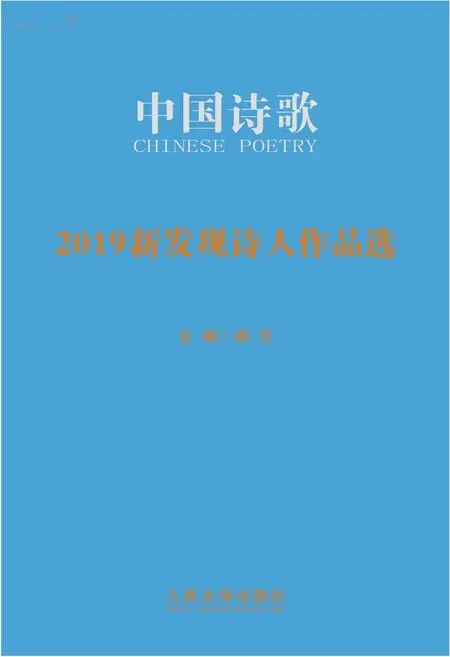醒洱的詩
風景之末
1
已然忘記,何時置身此地
天空低矮,秩序簡明
但仍需步入事物內部
一個草草寫就的廢園
是否能帶來新奇的觸覺?
沿著這條路,依舊是荷塘
碩大而肥厚,歡快的脈絡重復
朝各個向度增殖的綠
潔凈的細梗將其遞向湖岸
彎折或低垂之態
暗銀色葉腹,懸臨幽深的波瀾
湖水青綠,而天灰暗
鸛掠過水面,翅羽執掌氣流的力矩
低空滑翔,負荷疾行
我們驚嘆于這精微藝術的賦形之美
逗留于頑石,揚起黑色的喙
和失眠的細腿
“我們不走回頭路。”
熟稔的東西從不能使人充盈
進入叢林深處
一些灌木枝杈挑釁著我們
而蕨類的暗綠給予安慰
橫向生長,極低而寬闊
頂端漸變血紅,它內陷的風暴
涌出,但不能舒展
沿葉脈折疊自我,以封藏柔嫩的屈辱
它與生俱來的債務。哦,女性!
總在夜晚變得陌生
依盛夏之權威
存活,蔓延
此地:一個幽閉空間的宗教
2
步入此地的純粹智力
月之領土的干冷氣候
灌木尖銳而猩紅,封藏在小巧的籬笆中
精微結構的拉力控制
使柱蕊竭力伸長,它驚呼的喉舌增殖
花瓣避讓,反向折疊
白頭鵯停留,凝視復飛離
鱗塊裹挾的樹體,灰至深褐色
警戒斷面的明黃,仿擬光之牙齒
使新綠磨損
松果墜飾呈卵形,規律性崩裂
圓瓣遞進填補空隙
重復,變奏的綠交響,和柱狀新枝上幽微的刺
它的羽翼平展,斜向上式蔓延
被旋切成平頂,低矮近于荒草
遠處飛蓬,在疏于管理的湖岸
是由于攝取了水的狂暴和凜冽,
所以變得高挑而筆直?
葉脈上季節搏動
腳下的血管糾纏
是蒺藜深埋的叛亂
此地,無主的歷史
荒蕪鋪排的秩序
為新的廣延統攝
3
向前,是凌亂的松樹
積塵使脖頸微垂
并壓彎軀干和頎長的脊柱
松針緊鎖濃綠,向內的刺
聚成疼痛的骨節,它的新綠生成
這敏銳者的生產,灼熱中不斷磨損
月季開始衰敗,豐盈渡至褶皺
褪作枯朽的黃
黑心菊微笑,高舉中心的巨眼
我步入一股甜膩的腐味兒
既非月季也非黑心菊
是梧桐花無數癌變的喇叭
堆積在發黑的枝干
柔軟的淡紫花瓣上
稠密的霉斑,向內排布
而狹長的花柱向外探出,呼叫
被柔軟的絨毛裹挾
墜入潮濕的沉默中
而樹依舊高聳
太陽為石壁刻入影子,漆黑而堅硬的割線
其強力,其持久
將悲傷埋入律法
橫亙于此地的空氣
與歷史
夏日妝臺
把所有遲來的觸摸相加便得到你的形狀。
你低著頭,拼貼罪業的發票。
把所有遲來的觸摸砍除便露出無你的星空。
空空的藍,你的粉盤。
鏡中升起的雙眼,被黑色的時針劃分。
私語與紅燭,收納在底部抽屜。
眾光容納平凡的形體,歡愛如廣泛的性,
浮動裙裾般的樹冠。
你的耳飾一長串兒,翡翠的位序
種植,種植在耳垂,美的領域
須以迷途釋義。不忍但我折返,
那些陌生的干冷的反光。
一些尖叫的樹葉被重新組織。
雙手裁剪的路徑,跟隨花枝,針線拼接著鄰域。
天空晴朗地收縮著,有限的事物,
正在開發持續的冰冷。
鐘表微笑,證件在鐵盒里,周轉黎明。
事件還沒有新的主人。
晚風將樹葉擊散,
聲音介入了秩序。
瘋馬
瘋馬逐月,月不予應答
月于荒野,瘋馬不止
一些喃喃細語聲吹過灌木
那些懷望的眼睛瘋馬拒絕
瘋馬逐月 月于荒野
月搖晃,它罪惡的金黃
搖落夏日,那未經測量的盛大陰影
或陰影的陰影,筑世界于洪水的暴怒與滯留
瘋馬逐月 月于荒野
于時代的罪業諸峰
它的夢魘已被寬恕:
每一事件都源自內部閃電的碎裂
瘋馬領會月之意念,但無以承載
勻了三分殺意予我
季節
終究,我們失敗了。
是因為你的懶惰和自私
還是因為我的冷漠和多疑?
這質詢激蕩冬日的晴空,
澄澈、遼遠,如你的注視。
在這個以呼吸取暖的寒冷村落,
我們誕于貧窮等待瘋狂信仰宿命
如果訴說?我們拒絕訴說。
如果哭泣?我們拒絕哭泣。
為了焦渴的良心。
懼怕,譏笑和私語,我們小心地藏起。
看冰風中欒樹枯萎的果莢如風鈴觸碰,
大山雀機警的橢圓形眼睛旋即沒入叢林。
我們也是,如此機警,
如此努力地,小心地,不陷入孤絕。
面對笨拙和矯飾,
一貫致以嘲諷和鄙棄。
恰如它對我們的鄙視,滑溜如體制:
失敗者,
曾渴求藝術,
一頭栽入痛苦的經驗。
低音的震顫,在我們的手心共鳴。
還有什么能從苦痛中涌出使得一切得到報償?
又為什么自此一切叩問都得不到回答?
仿佛苦痛就是世界的極限之極限?
以致語言只能成為其描述?
我們也再不能借此擁抱?
而夜空的細語帶來安慰,
積云的身體教導柔軟
傳授遲鈍和化妝術,
使我們具備陰影之美以便與世界和解
并獲得有形的,緊實的歡悅,
以對抗血液中古老的敵意
飛機劃過,留下逃逸的痕跡。
它的白色滯留。
它的時間正涌來。
因為遲鈍,疼痛并未使我們馴順。
因為記憶,仍舊堅信愛之創造。
或許一切早已注定,我們的歷史也早已寫就。
我能看到它的重現:
欒樹的黃花散落成泥,
溫熱的雨水流過身體,
就像靈魂的柔軟滑過,就像溫柔的欺騙,
孔雀在叫喊,激越的經驗
在生命中溢出。
捕獲裝置
陰天,她習慣在傍晚觀望天空
以圖書大廈的避雷針參照
它灰冷、渺遠、真實
適于回應一個虔誠者的敬畏之心
真正的知識是悲傷
而她已足夠勇敢,以疼痛來體驗
她的習慣:以各種角度
注視自己最恐懼的事物
觸摸它的肌理,深深潛入它——
來習得生存的規則,計算它的出口
(多數時候幽深得令人迷失)
不斷忍耐著,又質疑它的真實
是否能磨礪出澄澈、堅硬的靈魂?
每一次哭泣的疲憊,失控后的灰冷
為何會化為一種怯懦和馴順?
難道這不會激化施虐者的惡行,
因為他們博學的恫嚇?
而此刻她已足夠冷靜和隱忍
拒斥流淚的安適和快慰
真正的知識乃是悲傷
她仍需注視,馴順者的敏銳和溫柔
如一位遙遠的母親
在夜晚用衛生紙折出玫瑰
藏匿于未流出的淚水
而他們熟稔施虐的藝術
樂于享受哭喊
是因為真正的思考只能以身體完成。
天空從不展示它深邃的認知
直到目不能視,恐懼之物不能再被解析
她會一直深入,因為
一個修行者要勇于面對恐懼
并展示破碎的自我
是因為他們的血并不淌在自己身上
一如她的眼淚并非為自己而流
喜鵲
和他走著,跟在后面
陽光透過拱廊的寬縫曬著我們
并透過我的塑料水瓶留下藍色的影子
我在說著,幸運和不幸,是否可以互相填補
這樣就可以為個人的際遇附上合乎邏輯的注腳
而你說,當我這樣想的時候,就證明我是
不幸的人因為幸福的人從不會想這件事情
我很失落,還是不愿意相信
然而是與不是,只能帶來一點兒縹緲的傲慢
孩子們從冰淇淋店走出來,吸溜著口水,發出嘿哈的笑聲
這個疑問更加使人惱怒了
“你才二十二歲,根本不該考慮這些。
雖然這是唯一能做的,但它并不能告訴你該做什么。”
然后你便沉默了
一輛輛卡車開過,揚起大片塵土
石灰味兒和土味兒
緊隨其后的三輪摩托載著三個漂亮的女孩兒
和她們鮮艷的嘴,映在積灰的玻璃中
想想吧,那些錘煉的詞句
是不是使生活更加逼仄了,但詞卻更加豐盈
可到底該如何自處
滾燙的高壓線上,暗含閃電的激流
它黑色的翅羽上幽藍的浮光
彰顯陌生的財富
和渾圓的白色的腹部
整潔,修長的尾羽
使我訝異,想把它趕走
大叫著,揮著手
太高了,它聽不見
依舊站在那里
專注地,深沉地,注視著
在閃電上
在死沉的熱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