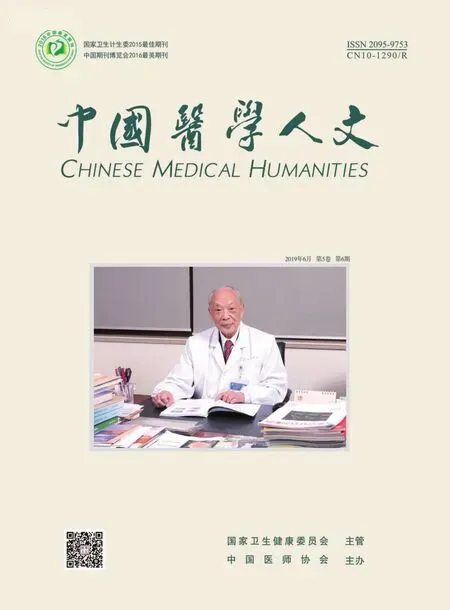守 望
文/周瑾容
給母親洗澡
母親因為肩關節手術,右肩功能還未恢復,康復期需要往返醫院,才住到了我家里。這是長大成年之后,與母親住回同一個屋檐下最長的日子了。
母親與我,一直不如其他母女那般親密無間。母親養育我,卻不曾知悉過女兒的內心。而面對平實沉默的母親,我也常常不會和她有過多交流。
對于常年習慣了照顧家人的母親,突然轉變到被人照顧,顯然是不習慣的,她不安且局促。平時洗漱進餐,她都盡量使用左手自理。只有洗澡,她不得不求助于我。
將塑料小凳放在衛生間,讓母親坐下,為她褪去衣服。最初,母親是羞澀的。我取下淋浴頭,打開試水溫。溫熱的水流先從脖頸處流下,母親不看我,也不言語。母親的右臂無力地在靠在胸前,她用她的左手擦拭自己能夠到的所有地方。我知道母親即使生病,也是不愿意麻煩別人的。
母親已經開始有些發胖,她的背部、腹部有脂肪一圈圈堆積,四肢卻仍然瘦弱。我記得母親年輕時有兩條烏黑光亮的大辮子,現在已經剪成短發,頭頂和額角有一簇一簇的白發。常年的操勞,她的手掌有粗糙的繭。為她擦拭的時候,感覺母親的肌肉松軟,失去彈性和光澤。等水流過全身,“好了!”母親急急地一聲輕呼,便扶著墻緩緩站起身,等著我用毛巾擦干水跡,為她穿上衣服。
母親既操持家務,也為我們縫衣梳頭,像個陀螺一般不停歇地轉,中心是丈夫孩子。在家里她從沒抱怨,也最不張揚,但卻是最重要的一個人。家里人累了,都可以有理由去休息。只有母親,頭痛了,腦熱了,腿酸了,她都挺著堅持著不能休息。
半生歸來,母親老了,而我已中年。母親像個孩子,她坐在我面前,巴巴地等著我為她洗一個熱水澡。
我為你洗去塵埃,你就還是我健碩的母親,可好?衛生間有水汽蒸騰,像薄薄的霧,掩蓋了我的淚眼。
擂茶里的鄉愁
入秋的傍晚,迎面吹來的風已有些微涼。路上的人,依然行色匆匆。回到家里,母親輕輕說,晚上吃擂茶吧?
大米浸泡到鼓脹,顆顆飽滿,放到擂缽里,一米多長的擂棍一圈一圈碾壓過擂缽內面的豎形紋路,米粒變成白色的米漿。將米漿導入滾水,攪拌。再將花生、茶葉、山胡椒放入擂缽,花生一定要是生熟各半,茶葉一定要是新采摘的,山胡椒就在屋旁的樹上摘下幾顆即可,擂碎,有花生帶著油脂的香味,有茶葉清新的氣息,有山胡椒透鼻的清涼,香氣四溢。就著熱氣倒入鍋中,加入適量食鹽,調料的香味便牢牢鎖在了濃稠的米漿中。
家鄉人對擂茶,常常用“吃”,而不用“喝”。擂茶既充饑,又解渴。一日三餐之外,要是少了一頓擂茶,鄉人便覺這一天還差了點什么。年少時,我常常可以一次吃掉三四碗擂茶。之后來到城市,嘗過各種琳瑯美食,卻還是忘不了家鄉的擂茶。而每次回家,親戚鄰里都會熱情的喊我的小名:來啊,等哈來吃擂茶!這便是鄉間最高的禮遇了。

作者和父母
母親此次因病呆在長沙已近半年,我疏于家務,每天只馬虎打發一日三餐。隔一段時間,母親就會去小妹那里停留一兩天,然后用密封玻璃瓶帶回來一罐擂茶。母親說,很久不吃,就想著這口兒。
擂茶倒進碗里,鄉愁就從心里涌出來。母親說,該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