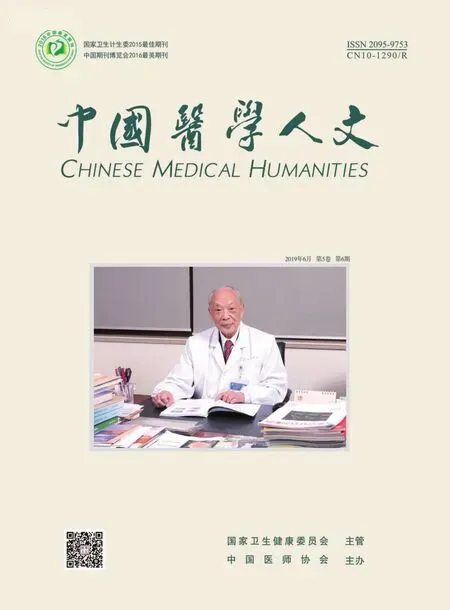白求恩的弟子
文/李悅敏 高洪文 孫平麗

醫(yī)院,這個見證了無數生死的地方,注定與我們每一個人相關。而醫(yī)院里的醫(yī)生們,是一群有著人的喜怒哀樂,卻扮演著神的角色的血肉之軀。
1997年,3歲的我得了一場大病,縣級醫(yī)院束手無策,心急如焚的父母連夜帶我趕到省級醫(yī)院。當年的兒科老專家顫顫巍巍地來到病房為我看病,父母總說那是位極好的老人。聽說,我是那個病房最愛笑的寶寶,科室的大夫們和護士姐姐都很喜歡我,就在這群白衣天使的幫助下,我痊愈出院了。回憶起當年那群可愛善良的人,父母總說要我好好學習,也成為那樣的人。
9歲那年我學了一篇《手術臺就是陣地》的課文,第一次知道了有位諾爾曼·白求恩大夫在中國做了很偉大的事情。課文里那張白求恩大夫在戰(zhàn)場為傷員做手術的插圖,深深刻在了我的腦海。
2013年,我正式成為了一名醫(yī)學生。我還記得第一次穿上白衣時,全宿舍的人都很興奮,仿佛看到自己當了醫(yī)生的模樣。事實上我們都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為一名優(yōu)秀的醫(yī)生。電視劇里說,這是一個成就英雄的行業(yè),生命就是我們所承載的天降大任。選擇讀醫(yī)科的那一剎那,我們就要明白自己所踏上的是怎樣一個征途。
2017年,我來到醫(yī)院實習。在產科,我吃到了家屬們送來的各種水果,見證了一個又一個家庭的喜悅;在消化科,我看到帶教老師為了一點點疑難翻查了大量的圖書和資料,希望能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精益求精。在新生兒科病房里,我見到了一名腦癱患兒,母親難產去世,父親不知所蹤。他的年齡已經超過了繼續(xù)住在新生兒科的年紀,也不需要保溫箱了,但是科室老師們要他繼續(xù)留在新生兒科,并自發(fā)捐錢為他購買嬰兒用品。我看著小床上的他,睡得踏實祥和,感受到了醫(yī)者的仁心仁愛。
2018年,我23歲,已經學了五年的醫(yī)學課,有幸來到白求恩醫(yī)學部深造。入學的時候,老師說我們成為了白求恩的弟子,要將白求恩精神傳承下去。我想起小學課本上的插圖,坐在寬敞明亮的會議廳聽著那些似乎很遙遠的往事,我終于明白了在那個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堅持在硝煙中的手術臺意味著什么。我仿佛聽到了白求恩去世前的話:“我在這里十分快樂,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多做貢獻……最近兩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義的日子。”
我想,無論身處烽煙滾滾的戰(zhàn)爭年代,還是飛速發(fā)展的科技時代,面對傷痛,面對生命,一名“快樂的醫(yī)生”,就是把多做貢獻作為自己的希望。醫(yī)學,是一個事關重大卻在很多時候無能為力的科學,是一個最應該追求完美卻一直有很多遺憾的科學。可是我們依舊懷揣希望,在科學的領域一點點探索著前進,同時盡自己的努力解決他們的病痛并安慰那些受了傷的人。
科室主任曾問我,開始學習病理的感受是什么,我答病理診斷很難,但是病理診斷疾病,指導臨床治療是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主任微笑著點頭說:“你慢慢會有更深的體會,這是一件能實現你人生價值的事情。”他不曾解釋這其中人生價值的含義。漸漸的,我明白了其中的內涵,知道了白求恩的弟子應有的樣子。我想,那便是盡自己所能,讓患者心里踏實。或許病理的工作是默默無聞的,背后的辛苦也鮮為人知,但它關系到患者的診斷結果與治療方案,這份沉甸甸的責任,便是每個病理工作者的價值。
從白求恩時代到今天,幾十年的時間過去了,醫(yī)學作為一門關系生命的科學,發(fā)展得飛快,早已不是當初那個青霉素都沒有的年代。“互聯(lián)網+醫(yī)療”“三醫(yī)聯(lián)動”“分級診療”,我看到越來越多的醫(yī)療改革方案出臺,一份份文件,一次次會議,我感受到一股想要使一切越來越好的力量,在努力改善人們看病難、看病貴的境地,在努力提升人們的幸福感。一代又一代醫(yī)者走入醫(yī)學之門,習治病救人之法,經歷了嚴苛的訓練與考試,也許見慣了生死,也許面對過質疑,但他們仍然不忘初心,用自己的一生追隨著醫(yī)學不斷前進的腳步、引領著醫(yī)療事業(yè)的發(fā)展,歷代人才輩出而燦若星辰,生生不息。
懸壺濟世大愛流淌,厚德妙術神州傳揚。從抗擊非典到地震救援,從援疆援藏到基層義診,從門診樓坐診到住院部查房,從外科手術臺到病理取材室,白求恩弟子的身影出現在每一個需要他的地方。四面云山都入眼,萬家憂樂總關心。不管經歷什么艱難困苦,只要將患者疾苦記在心上,人自高遠,心自廣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