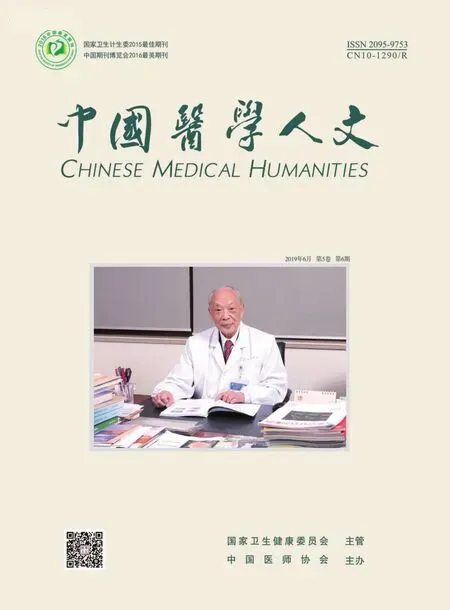醫德本身就是醫學的一部分
文/白巖松
最近在網上關于醫生最熱的是一張照片,照片中餐盒里滿滿的飯菜還在,餐盒下的餐巾紙上留言:“別動,插管去了。”大家看了都為醫生點贊。
但我們現在面對的局面是,公眾經常被醫生感動,同時也一直在施壓。但作為醫生也要理解病人的一些施壓和負面情緒是因為他們的確離不開醫生。那么如何理解重癥?如何理解ICU?中國古人總結的“生老病死”概括了人的一輩子,請問哪個階段離得開醫生?對于重癥來說,恰恰在“生老病死”的最后這一個字,它可能是鬼門關,它也可能是一條陽關道。因此人生中最極端的沖突和懸念就是圍繞著ICU展開的。這也正是這個行當不僅叫“重癥”,而且還很“重要”的關鍵所在。
“醫生與醫德”,坦白說我不太同意這個題目,就像我也不太認同現在很多醫院內經常開展“醫學與人文”的講座一樣。為什么?回到剛才那句“別動,插管去了”,這就是一位醫生正要吃飯卻剛好接到醫院的電話,病人手術需要切開氣管插管,對醫生來說這就是日常的工作,他自己不會被這個舉動輕易感動。但社會把它解讀為辛苦和醫德,我認為醫生與醫德不可以分開談,是醫生就一定有醫德,醫德就是醫術的一部分,不能分離。
我們有時候會說醫學與人文、醫生與醫德,剛開始的時候我覺得一切很正常,但是時間一長,隨著對醫生和醫療了解得越多,越覺得不正常。因為醫德和人文當成了外化的東西,不是充分條件、必要條件,而是選修項目——高興了可以有,不高興沒有亦可。你對醫學越了解越會感覺醫術加上醫德才是醫療,科學加上人文才是醫學。醫德也好人文也好,不是外化的東西,而是內在的東西,所謂大醫一定是醫術和醫德的結合體,從某種角度來說在診療過程中醫德也是重要的一味藥或一種重要的治療手段,因為帶著醫德的醫術結合起來才能起到最好的醫療效果。其實各位醫生都清楚,人文和醫德能跟醫學與醫生分開嗎?分不開!它不是增量部分,它是醫學和醫生天然的一部分。
在做《感動中國》節目的時候看到過一個讓我現場流淚的片子。有一位大夫,不是因為他做了多么高深的手術、有多么精湛的水平,而是一個很小的細節感動了我:他當醫生以來每天查房的時候一定把聽診器放在身子上捂熱再進病房,從來沒有讓任何一個患者接觸過冰涼的聽診器。我人生中第一次看病的經歷永遠也忘不了,就是因為與那個“鐵家伙”冰涼地放在我肚子上有關。這是不是醫德?當然是。
再比如林巧稚大夫,在紀念她的文章中有一個細節讓我感動“剛剛還愁苦滿天、哀怨四起的病房,她一走進去說會兒話,病人們的心情就因她的聲調和語氣慢慢平復下來,重新變得陽光燦爛,大家就開始都覺得有希望。”
再有鐘南山院士的例子,在SARS那年2月份我們欄目最早采訪了他。鐘南山院士不僅僅因為在醫學方面去推動如何面對SARS,更重要的是從頭到尾、即便在最緊張的關頭他依然是從容的。從容就是一種對社會的治療,是他骨子里的一部分。所有好醫生都是擁有精湛的技術與高尚醫德的結合體,因為醫德本身也是一種治療方式,甚至是必不可少一種的醫療。
我認為醫德就是醫生的一部分,人文就是醫學的一部分,而不是分開的,不是蛋糕上的那一個櫻桃。
說到重癥與撫慰,只要到了生老病死,涉及到“死”這樣一個關頭,撫慰就必不可少,就是醫學的一部分,就是一種治療。而且重癥這種治療更復雜,不僅是治療病人,還要治療家屬,因為家屬面臨著心情的急劇起伏和忐忑不安。ICU不僅涉及到死亡的問題,還有關于人生的無常。在ICU不分老少,什么樣的年齡都可能走進ICU的門口,這時撫慰本身就是一劑藥方,在人們最絕望、面臨無常、手足無措、腦海一片茫然的時候他需要來自醫生的堅定和背后所蘊藏的撫慰。我一直認為醫生最重要的藥方是給予希望、給予可能,即便到了ICU,即便是生命的最后一刻,希望的藥方還是要開。
圍繞撫慰涉及很多關鍵點,比如重癥醫生如何告知家屬,這本身就是一個學問。我不止一次地舉一個例子:一個孩子遇到突發傷害送到急診室,在搶救的時候醫生已經知道這個孩子沒了,但是門口跪著六個人,爺爺、奶奶、姥姥、姥爺、爸爸、媽媽,醫生又進行了兩個小時的急救。他知道沒有希望,但他一定要再多做一下,去爭取哪怕一點希望——但其實一點都沒有。更重要的是這個醫生告訴我,我要給門口跪著的六個人一個緩沖時間,讓他們慢慢能夠接受,否則他們中間的一些老人是接受不了的。請問這是不是一種更大的治療?
另外,大家知道這幾十年來全世界醫學界發生的一個相當大的變化,就是患者賦權。過去所有的決定都出自于醫生,如果最后沒治好都會覺得是命不好,不會埋怨醫生。現在任何一個決策都是醫生和患者共同去做。問題是患者學會了參與決策嗎?更重要的是,醫生是否可以在共同決策的過程中了解患者的心理?
告知是一門藝術。據我了解,中國所有的醫學院沒有一所開患者心理的課程,但是在患者賦權的情況下對患者心理的研究是現代醫學面臨的極大挑戰,醫患關系與這點緊密相關,尤其在重癥領域。美國醫生寫的書中舉了一個案例:他確診一個患者是癌癥中晚期,就約見了患者,告知病情。結果他發現這個患者很從容,然后就接著告訴他治療方案,詢問患者是否同意、會如何選擇等等,患者都給予了他回應,并且都記錄了下來。一個禮拜后患者來了,結果跟患者一聊,發現他那天跟患者定下來的所有治療方案患者全不知情。他問為什么?原來那天當他告訴患者你是癌癥之后,那個患者的腦子就“嗡”一下,剩下的話基本沒聽進去,全是機械式的點頭和搖頭,這就是患者心理。
加拿大醫生特魯多曾經講過一句話:“偶爾去治愈,時常去幫助,總是去撫慰。”即便醫學又發展了100多年走到今天已經是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句話的根基改變了嗎?我們依然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但撫慰作為醫生醫術當中相當大比例的一個職能,我覺得在重癥領域里頭格外重要。撫慰是醫術的一部分,是患者的潛在需求。所以必須建立在對患者心理更充分了解的基礎之上才能把這件事情做得更好。
香港是全世界人均預期壽命排第一的地區。我專門關注了一下香港老人為什么能這么長壽,其中除了“活到老、干到老”之外還有一條,就是香港的急救車到達時間必須是12分鐘之內,12分鐘之內全島幾乎沒死角,就能搶出重要時間。咱們很多地方的平均時間是遠遠超過12分鐘的。應急創傷學會的會長跟我說:“我們每年車禍死亡近20萬人,如果院外急救時間能縮短到現在的一半,可能能多活好幾萬人。”有一句話讓我深深觸動,“早來10分鐘做完手術,一個月的休整后他就能活蹦亂跳回到生活中,晚來10分鐘的話我就要給他蓋上白布了。”所以真正的無奈往往與社會的進步欠缺緊密相關。不是所有的疾病到醫院來都能治好,因此首先需要社會在整個院外急救領域盡快縮短時間。
令人高興的是去年上海進口博覽會賣出的第一個大商品是直升飛機——上海郊區買走了這個直升飛機用作緊急醫療救助。現在北京已經有一些醫院的大樓上方有停機坪,但由于各種航空管制等原因應用率很低。沒有社會進步,最后就全部都推到醫院、推進ICU,然后相當大比率“蓋白布”。相反,如果院外急救時間夠短,一個月之后就又是活蹦亂跳的鮮活的生命。
第二需要進步的是全社會要了解醫學的邊界。現在醫患關系相當大的問題在于大家把醫學當神學,不當科學,覺得我花了錢了、送到醫院了,你就要全部解決。可能嗎?醫學在進步,病毒也在不斷變異。因此,想要醫患關系和諧,需要大家對醫學有更充分的了解;想要讓醫生更從容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全社會必須明白醫學的邊界。
十幾年前,我因為咽炎找到中國這個領域最棒的醫生。我一進去就問我:“巖松,哪兒不舒服?”我說我咽炎,“我也是。”我倆聊了點別的就分別了。因為我充分了解醫學的邊界、醫療的邊界。到了重癥更是如此,我們應該對生老病死有更充分的了解。是不是送到醫院、花了錢就沒問題?不可能!醫學有邊界,我們現在依然有相當多的疾病和應急創傷是沒法治愈的,是不可逆的,甚至還有相當多的疾病需要50%、60%的冒險。如果醫患關系依然惡化,大家“偶爾被感動、經常去責難”,醫生就不會再有勇氣選擇冒險,最后倒霉的是患者。

傲骨 攝影/王鳳新 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所以探討醫學的邊界,并且讓整個社會公眾了解醫學的邊界已經成為現在醫學向前進和解決醫患關系中的重中之重,這不是醫德能解決的問題。大家習慣將責任推給醫生,我認為需要全社會去應對,尤其當患者賦權以后擁有很多決策權利的時候更要明白醫學的邊界。
有時候我們經常需要悲劇和意外幫助我們進步。汶川地震誰都不愿意看到,但是2008卻成為了中國急救醫學的元年、災難醫學的元年,我們現在已經擁有3支接近國際水平的應急救援隊,還有很多政府和民間的醫療救援隊伍。
前不久北京東單體育場有個鍛煉的人突然倒地,旁邊有四五個協和醫院的大夫正在打羽毛球,各個科室都有,加上體育館有除顫儀,幾百米開外就是醫院,所以得“病”選對了地方,搶救及時,患者啥事沒有。幸運的是中國很多公共場所增加了除顫儀。如果沒有這些東西,我們的ICU忙得過來嗎?我希望ICU只是越小比例越好,更多在科普和社會救助、社會進步方面。請問中國有幾個人能有這樣的運氣?倒地上了,旁邊站著的正好是醫生,這個概率極低。所以我們不能將自己的生命建立在幸運的基礎上,而是要建立在社會進步的基礎上。
我們早就應該改變這樣一種觀念和行為,就是常常買得起棺材不買藥,在買棺材的時候下得了手,買藥的時候總在心疼。科普與預防、與公共衛生的進步就是“多買點藥少買點棺材”,所以在重癥領域一定要呼吁社會快速進步。
我一直認為醫生是介于佛和普通職業之間的一種職業,最大的成就感不是來自于我們的鼓掌,而是來自于當一個不可能變成可能,當一個絕望變成希望,當一個消失的曲線重新成為有生命力的曲線時,千金不換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