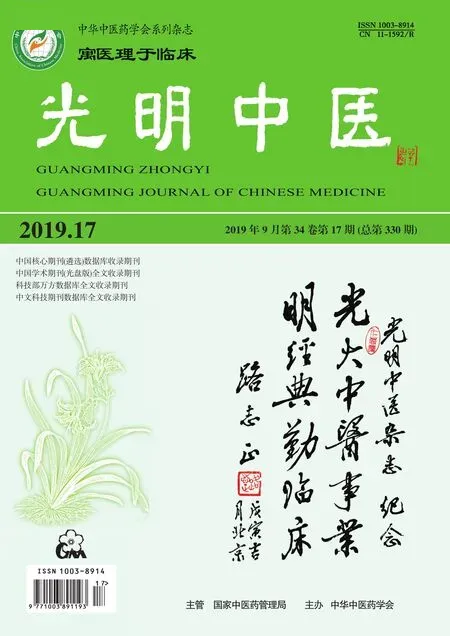也談中藥“毒性”(上)
張 良 尹亞東
中藥的“毒性”問題,其實是個很大的話題。以我們的學識修養,其實很難說清楚、說透徹。但因為這些年國家對中醫藥的重視程度加強,尤其隨著電視劇《老中醫》的熱播,出于種種原因,在有些別有用心者帶動之下,社會上對中藥“毒性”的議論又突然熱絡,所以我們覺得有必要也談一談這方面的認識。畢竟,筆者中醫藥大學畢業歷從事中醫藥行業已20多年,而且作者之一還是祖傳7代[1]的中醫藥世家子弟。
1 中醫學對中藥毒性的傳統認識
中、西醫學因為理論體系不同、思維方法不同、研究方法不同[2,3]會導致對藥物尤其中藥的“毒性”認識大相徑庭。
在中醫的發展史上,甚至把一切藥物都看為“毒藥”,《周禮·天官冢宰》曰:“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素問·湯液醪醴》曰:“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镵石、針艾治其外也”,《素問·異法方宜論》曰:“其病生于內,其治宜毒藥”,《素問·脹氣法時論》曰:“毒藥攻毒”,以上論述都是這種認識。一直到明代,仍然有醫學家謂“毒即藥”,如張介賓在《類經》中就說:“毒藥者,總括藥餌而言,凡能除病者,皆可稱之為毒藥”。
簡而論之,目前中醫業界公認,中藥的“毒性”認識可分廣義、狹義2種。狹義之毒,指藥物本身確有毒性,使用常用劑量或比較低的劑量,也可能對人體以及機能產生特定的損害作用,甚至中毒、死亡,如砒霜之類。廣義之毒則是指中藥的寒熱溫涼偏性、補瀉清潤作用。如黃連大寒、附子大熱,這個大寒、大熱就是藥物的“毒性”。所以張介賓就說:“藥以治病,因毒為能,所謂毒者,是以氣味之有偏也”。《神農本草經》說:“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應該就是這種認識。我們常說的“是藥三分毒”也基本上是從這個道理講的。
客觀上講,歷代藥物經典對中藥毒性的認識受制于歷史條件,相對是比較粗糙的。傳統對于中藥毒性的認識和分級均來源于臨床,基本上是以臨床實踐中觀察到的服用藥物后的身體反應來作為藥物毒性的認識依據,除中藥本身的毒性反應外,往往還包括了中藥的偏性等。這種研究方法明顯具有不確定性和隨意性,缺乏準確的、量化的、統一的標準[4]。如《神農本草經》將中藥分為有毒與無毒兩類;《吳普本草》把藥物二分為大毒、有毒,《本草經集注》(陶弘景著)把中藥分為大毒、有毒、小毒三類,《本草拾遺》(陳藏器著)則把中藥分為大毒、有毒、小毒和微毒四類。《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5]和高等中醫院校教材《中藥學》[6]對中藥毒性和分級標準也一致分為“大毒”“有毒”“小毒”三級標準。所以后世以及當代醫家一般都認為:“大毒”中藥,是使用劑量比較小即會引發中毒癥狀,中毒反應發生較快且比較嚴重,更容易造成死亡。“有毒”中藥,則是使用大劑量或較大劑量才會出現中毒,中毒反應發生比較緩慢,但后果仍然可能非常嚴重,甚至會造成死亡。歸類于“小毒”的中藥,則是在標準劑量下不易或不會中毒,超大量使用才會發生中毒反應,而且癥狀比較輕微,不會造成死亡[7]。但是這種“小劑量”“較大劑量”和“超大劑量”并沒有什么量化標準,從而缺乏實際上的準確性和可操作性。
2 中藥毒性的現代醫藥學認識
現代醫藥學對于中藥“毒性”的研究路徑和認識方法與中醫藥學幾乎全部來源于臨床實踐不一樣。西醫毒性試驗的一般方法,是先用一組動物,如小白鼠,給同樣的藥物和用量,使用相當一段時間后,觀察某些理化指標或者解剖觀察某些指標,來確定毒性的有無及大小,然后再運用于臨床觀察。應該說,這種方法是西醫藥規范化、標準化的特色體現之一,和工業化的要求一脈相承,也就是目前“科學”的研究方法[2,3]。
現代醫藥學和中醫藥學對藥物“毒性”的認識有很大區別。認識方法、研究方法不同,結果、結論肯定不同。但這種研究方法也未必就是絕對正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唯一可行的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方法從中醫思維看來,在追求標準化、規范化的同時,實質上會忽略用藥的個體差異以及中醫最注重的“辨證論治、對證下藥”[2,3]。當然,西醫的理論體系關注量化的理化指標,而中醫從氣血、陰陽、虛實、寒熱出發,認識到的個體差異以及基于“辨證”得出的結論,因為無法規范所以西醫基本是不認可的。
我們可以舉個直觀的例子。假如要研究白酒是否“有毒”,西醫的研究方法可能是每人每天喝半斤,連續喝幾個月,然后觀察肝功能指標。而中醫則會區別各人情況,酒量大者喝半斤,酒量小者可能喝一兩,且喝一兩的還有可能配合一些醒脾解酒的藥物,如果有濕熱表現者就直接排除不讓喝酒,過一段時間后看各人舌脈神氣、談個人感受。這樣不同的試驗方法必然會出現截然不同的結果、結論。西醫試驗結束后可能是50%受試者出現了肝功能異常。中醫試驗結束,即便也使用肝功能指標來佐證,異常者恐怕也微乎其微。姑且不談這樣截然不同的試驗方法孰優孰劣,僅就試驗結論而言,西醫恐怕會得出每日飲酒半斤有害健康的結論。事實上,這個結果對另外50%的人可能沒有多大意義,因為酒量的大小其實是因人而異而且差別很大。而在中醫,因為這樣喝酒其實并沒有誰感覺不舒服,而且有些人還會感覺很舒服,所以結論就是酒不但無毒還能入藥。所以就有了“藿香正氣水”和各種治療風濕的藥酒。
客觀上講,中西醫理論體系各有所長,也肯定各有所短。筆者不反對、不攻擊西醫藥的理論體系、研究方法。當然,中醫藥可以借鑒西醫藥的研究方法,但完全照搬移植西醫藥的方法來研究中醫藥,恐怕是不合適的。這并不是門戶之見、義氣之爭。主要是中西醫學是不同的醫學體系。認識方法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得出的結果、結論自然會不同。如以下這些研究:長期大劑量服用細辛會導致血清TBIL水平明顯升高,病理檢查可見肝細胞明顯損傷[8];中小劑量的大黃有瀉下、利膽、退黃作用,但如果療程過長、劑量使用過大會引起膽紅素代謝異常[9]。細辛在《神農本草經》雖列為上品,但后世公認其“辛溫有小毒”,并有“細辛不過錢”的說法,所以真正的中醫醫家臨床上大概率不會長期頻繁使用。而“大黃”藥性峻猛,屬于“中病即止”的用法和品種,療程不大可能過大、用量也不大可能過長。所以這種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對于指導中醫臨床,沒有太大的實際作用。就此而談中藥的毒性,意義也不是太大。而林小琪等[10]通過對144味“肝毒性中藥”(未查到認定標準)分析研究,歸類統計以后,認為肝毒性中藥和普通中藥在性味以及歸經方面,沒有明顯的分布趨勢差異,結論認為中藥肝毒性與中藥的藥性理論無相關性。尚秋羽等[11]研究也認為肝毒性中藥與一般中藥在性味歸經方面分布差異不明顯,說明中藥肝毒性與中藥藥性沒有相關性。這些研究的臨床意義不大,但至少也說明了完全西化的中藥毒性研究方法,可能是值得商榷的。
3 “馬兜鈴酸事件”對中藥“毒性”認識的影響
我們可以看看前些年國際上突然發難、國內公知精英推波助瀾,熱炒中藥毒性的“馬兜鈴酸事件”。自此而后,中藥的“毒性”問題,每隔一段時間,總會被別有用心的人拿出來熱炒。
“馬兜鈴”這味中藥國人應該都不陌生,電視劇《西游記》里用馬尿為朱紫國王治病,豬八戒失口說出一個“馬”字,孫悟空趕緊以“馬兜鈴”打了圓場。馬兜鈴就含有馬兜鈴酸成分。另外,含有馬兜鈴酸的中藥,還包括關木通、漢防己等數十個中藥品種。
國內六十年代就報道過因大量使用關木通造成腎損害。但沒有多少人關注,因為是“大劑量”。1990年至1992年,比利時有很多人服用減肥藥“苗條丸”,服用時間均在1年以上,有的長達3年。其中150名女性服用者中70人被查出腎臟受到損害。一家比利時研究機構認為是“馬兜鈴酸”中毒所致,比利時及一些西方媒體便開始以“馬兜鈴酸腎病”為名進行報道。英國在1998年發現了2例“服用過”含有馬兜鈴酸的中藥治療濕疹而“引起”的腎衰,隨即便稱其為“中草藥腎病”,1999年7月29日英國政府宣布:全面禁止使用、銷售所有含馬兜鈴屬植物的全部藥物以及補充劑。2000年初,美國媒體直接使用“中藥腎病”字眼大肆炒作。2000年6月9日,美國藥品與食品管理局(FDA)在“未收到類似不良事件報告”的前提下,命令全面停止含有或疑似含有馬兜鈴酸的藥品和原材料的進口、制造和銷售,70余種中藥材被列入黑名單。搞笑的是,有些被禁中藥品種僅僅因為英文翻譯名稱和“馬兜鈴”有關系就受到株連,而其實根本不含馬兜鈴酸成分。美國無端發難之后,西班牙、奧地利、埃及、馬來西亞、菲律賓、日本等國紛紛效仿跟進,最終釀成了世界范圍的“馬兜鈴酸事件”。而國內的某些公知、精英也上躥下跳、推波助瀾,弄得中藥都快和“毒藥”畫上等號了。
4 “馬兜鈴酸事件”完全歸過于中醫藥是不公平的
首先看“苗條丸”的主要成分:芬氟拉明、安菲拉酮、波希鼠李皮、顛茄浸膏、乙酰唑胺、防已、厚樸等。首先這樣的處方就很不嚴肅,純粹是不中不西的怪胎!馬兜鈴酸可能真的有腎毒性(下文論及),但處方西藥中就含有西醫明確認定有腎毒性的藥物。如芬氟拉明,在2009年1月已被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明確宣布停止生產、銷售和使用。且不論配方里中藥飲片炮制以及制劑制備過程、中藥品種配伍選擇是不是合適,僅僅從組方上來說,中醫就要從理、法、方、藥理論出發,講究君、臣、佐、使的配伍,治療原則是“中病即止”。《黃帝內經·素問·五常政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另外,處方還要靈活機變,“病萬變藥亦萬變”。《呂氏春秋·察今》中“是故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向為壽民,今為殤子矣”,說的就是“機變”這個方面。
再有,即便使用中藥養生,需要久服長養的話,也必會選取平和中正的藥品,絕不可能使用“漢防己”“關木通”之類不適合養生的藥物而大量久服數年。以上對中藥的“使用”方法顯然全部都未遵循中醫藥指導原則。既然如此,即便是服用這些中藥造成了傷害,究竟是中醫藥之過還是運用者無知,這一板子恐怕不應該不分青紅皂白結結實實直接打在中醫藥屁股上。
另外,因為馬兜鈴酸有問題,就要求禁用所有含馬兜鈴酸成分的中藥,恐怕也是過度反應的雙重標準。
從事臨床專業的同仁可以想想,西藥哪些品種沒有毒副作用。20世紀90年代我們讀大學時,西藥第十三版《藥物學》序言明確指出,收錄的藥物除了葉酸和葡萄糖沒有毒副作用外,其他所有藥物都有毒副作用。其實即如所謂無毒的葡萄糖,臨床實踐中某些胃病病人服用以后胃里也會不舒服。所以,有毒副作用也未必就要禁用。舞蹈“千手觀音”美輪美奐的表演者們,以及她們之外很多人,失聰的明確原因就是因為使用了鏈霉素類藥物,青霉素因為過敏反應也可能一針斃命,抗腫瘤類藥物的肝腎毒性等造成全身的嚴重毒副反應,從其問世到現在幾十年期間,無論從數量上還是程度上,可能遠超中醫藥幾千年毒副作用的總和,但是這類西藥也一直在臨床上大量普遍應用,沒有誰呼吁禁用、停用過。所以可見體系差別導致的認知差異有多大,足見雙重標準的運用者有多無恥!足見西方體系對中國、對中醫的文化傲慢、文化壓榨有多厲害[12]!
5 渲染中藥“毒性”有非專業因素
事實上,除了文化、體系的原因導致的認知差異,對于中醫藥的壓榨攻擊,恐怕還有深層次的世界醫療市場話語權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巨大的經濟利益問題。
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必然需要文化軟實力的輸出以彰顯民族個性,也必須取得世界級話語權、規則制定權以贏得自己應得的利益,中醫藥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領域。加上中醫藥因為毒副作用微弱、療效確切,這些年來在歐美得到了極其快速的發展,國外前些年都在謀劃制定中醫藥法律法規。受到馬兜鈴事件的倒逼,最近這幾年中國中央政府密集出臺中醫藥發展新政,以避免中醫藥話語權旁落。中醫藥讓歐美日制定標準才真的是中華民族最大的笑柄!但話語權的爭奪必然是激烈的。大家可能不太在意一個事情,西非“埃博拉病毒”肆虐的時候,中國在大量援非的同時,提出要捐贈中成藥“片仔癀”用于試驗治療,但最終被以法國為首的歐美國家以“片仔癀”不良作用不確定而全力阻擊,最終未能成功。屠呦呦教授研發的“青蒿素”獲諾貝爾獎以后,中國的宣傳口徑與西方的巨大差異,其實都源于此。雖然筆者也并不贊同把青蒿素看作是單純的中醫藥發展成果而最多只能算中西醫結合研究的結果[13,14]。“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那么中醫藥客觀上不可避免要擋某些醫藥利益集團甚至是某些國家的財路,不被黑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