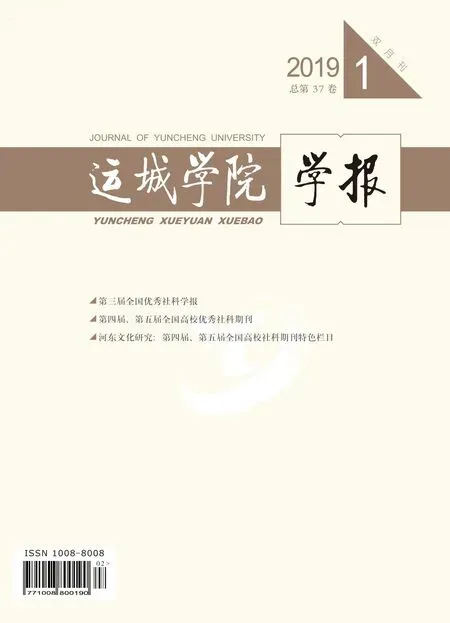社會變遷視角下的公民權利觀演變研究
——基于典型案例與事件的分析
王 從 容
(江西師范大學 財政金融學院,南昌 330022)
社會變遷是社會學經久不衰的話題。一般而言社會變遷即社會所發生的變化,既包括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宏觀因素的變化,也包括社會成員心理特征的變化[1]。如果把人類歷史比作一條長河,由于個體生命的短暫,大部分時候人們感覺不到這條長河的緩慢流動,但在特定年代,由于經濟發展、政治改革以及文化裂變,以至于影響這條長河中的每一個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矚目。隨之而來急劇的社會變遷表現為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及社會結構的變化,從而影響到社會中的每一生命個體。作為社會制度重要元素之一的法律也發生著重大變化,其既體現為法律因經濟發展、社會結構及民眾意識變化而發生變化,也可解釋為民眾的法律意識推動著司法變革,正如托克維爾所言“民眾的思想、愿望、痛苦、利益與激情,通常遲早會暴露在政府的面前”[2],而民意的變化應足以引起政府及司法機關的注意與重視。
本文的構思源起于筆者2017年7月至2018年7月在美國密蘇里大學堪薩斯分校法學院訪學期間與導師Lynch教授和Thomson教授就中美法律文化比較與差異進行的多次討論。他們認為從制度變革、社會結構與價值觀念角度來看,近40年美國似乎是靜止的社會,主要表現為宏觀上社會秩序平穩,政治經濟制度沒有大的變革;于微觀個體看,普通民眾兩代人乃至祖孫輩之間在價值觀的選擇上趨同。反觀中國改革開放后40年尤其是近20年社會結構、經濟制度等發生重大變化,在家庭關系中代際間沖突尤其是在價值觀上的沖突與矛盾凸顯。本文以近20年中國發展為背景,以法律中的權利觀為關鍵詞,以普通公民在婚姻關系、親屬關系以及勞資關系等社會關系的利益沖突為切入點,并從社會變遷的視角選取相關典型案例及事件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探尋公民權利觀的演變及其軌跡,并展望這一演變對將來中國法治建設所產生的影響。
一、道德與法律:公序良俗與自由意志
案例1:
黃某生前立有一份公證遺囑,將財產遺贈給與其同居生活并對其多有照料的張某。黃去逝后,張要求黃妻交付遺贈財產遭拒絕,張便訴至法院。一審法院認定,遺贈雖是黃本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且形式合法,但其遺贈行為“違反公共秩序和社會道德,違反婚姻法關于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規定,是一種違法行為,應屬無效民事行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張上訴。二審法院援引《民法通則》第七條“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規定,亦認定本案的遺贈遺囑是一種違反公序良俗和法律的無效行為,維持原判[3]。
1. 20年前基層社會的民意
這起發生在2000年首例“二奶”狀告原配案件曾轟動全國并引發熱議,之所以引發爭議是人們圍繞繼承法中的遺囑自由權與“包二奶”產生的違反公序良俗之間的沖突,從另一角度也即反映的法律(合法的遺囑)與道德(“包二奶”行為)的沖突。筆者無意就當時法官所做的判案作任何評判,從社會學及法治文化發展角度來看,任何案件的審理都不應離開當時的社會環境,從案件判決的細節“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也表明當時的基層社會民意。
2. 近年來理論界與實務界的檢討
耐人尋味的是,事發后20年期間,對此案的檢討仍不斷出現。筆者在中國知網以“瀘州二奶遺贈案”為關鍵詞進行文獻檢索,從2006年至2018年有40余篇文章并另有6篇碩士論文以此案為主題加以探討,在一些知名社交平臺如“豆丁網”“知乎”網上等對此案討論的參與者眾多。從文獻檢索中及相關討論中可以看出人們對此案判決中因立遺囑人的“真實意思表示”與“公序良俗”相違背而得出遺囑無效的判斷是有爭議的。甚至此案審判結束后十幾年,法官界也有不同的聲音,有人認為首先當依照法律確定黃某的遺囑合法有效,尊重并維護其出于真實意愿對屬于自己財產所作的處分;而不因黃某與其情人不道德的婚外情關系影響。法官不應該“變通明確的法律標準以求贏得當事人所在的社會或社區的好評,他負有維護法律尊嚴和民眾法律信仰的神圣職責和使命”[4]。
客戶第一次到一個新的汽車維修企業,總是懷著忐忑不安戒備心理、試探性心理,或者在不得已情況下所做的選擇,這和我們選擇一個陌生醫院、麥當勞、肯德基不同,他們品質、價格、服務相差無幾,而維修企業除了一些硬件大同小異,其他都會出乎你的意料之外。 所以我們太缺乏轉變經營理念、規范經營行為、實施標準工藝流程、統一服務價格等措施。而可靠性檢測與監測,實施的數據監控、實時跟蹤檢測功能是有可能真正解決企業與客戶問題的起始,是企業與客戶之間的粘合劑,是實現真正網絡服務的基礎。
3. 新生代的觀點
在近十幾年的教學中筆者就此案例讓大學生們討論,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從80后到95后普遍認為此案應尊重當事人的遺囑自由,他們認為:基于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受憲法和法律保護這樣的一個基本前提,公民有處分屬于自己財產的權利。既是當然的憲法權利,也是依意思自治處分個人財產的民事權利,是自由意志的體現,因此這一處分行為自然也就有道德上的正當性,而這種法律與道德上的正當性不因死者的婚外情關系而被否定。新生代們認為雖然法律與道德關系密切,但法律應與道德有一定的界限,法律之手不可伸到道德邊界,否則是對個人私權的侵犯。暫且不論新生代們的觀點是否正確,但從80后到95后的普遍觀點也足以說明在近20年因經濟發展和社會制度的變遷,人們的權利觀念在發生變化,即表現為個人權利意識的普遍增強,也體現在新生代們對道德與法律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有更理性多元化的思考。
此外,筆者就此案與律師們交流,他們認為假設此類案件再次發生,其審判結果在可能與當初不同,原因有二:其一是社會寬容度的增加,不會再有如此大的轟動影響;其二基于前一因素,在沒有社會輿論壓力下,法官們對類似案件也會因其對法律與道德關系的認知差異作出不同的判決。
二、集體主義到個人權利:人才流動中的權利意識
案例2:
2018年9月27日,一篇名為《離職能直接影響中國登月的人才,只配待在國企底層?》的文章引發網友關注。文章中稱,西安航天動力研究所一名科研人員張小平被一家民營企業挖走。據悉,張小平跳槽前的待遇是年薪為12萬元,跳槽后加入了北京藍箭空間科技有限公司,年薪達百萬。
1. 以公平為基礎的勞動者權利觀
20世紀60年代,美國行為科學家亞當斯J.S.Adams提出了公平理論。其基本觀點是:員工的工作態度既受絕對收益的影響,也受相對收益的影響[5]。相對收益即自己所獲得的收益(包括金錢、地位與認可及獲得賞識等)與付出(教育、努力及職務上所消耗的時間等)的比值。從法律角度來看,亞當斯J.S.Adams的公平理論也可解釋權利與義務是否對等,即付出的(因雇傭關系雇員對雇主所承擔的義務)和獲得的(雇員因履行職責所產生的由雇主支付的報酬)是否匹配。自2000年以來,因產業結的調整、科學技術發展、專業更新等因素,我國人才流動也變得越來越頻繁。一方面可以理解為因社會變革,人才流動的機制與保障措施較以前更趨向完善,另一方面也可解釋為因社會變革勞動者對人力資源作為生產要素這一價值的認識更為理性,更重視個人自身的價值是否能夠得到公平對待。
2. 勞動者權利觀變遷:從忠誠義務到契約關系
同時智聯招聘發布的白領跳槽指數調研報告還顯示:80、90后職場中,有跳槽想法(含正在辦理入職/離職、更新簡歷和有意向)的比例逐年升高,相比80后,90后的跳槽率更高。對此,智聯招聘人力資源專家分析,在90后群體心目中,“企業不再是我家,崗位不感興趣、薪酬沒有達到預期我就跳”。工作對他們而言不僅是一個收入的來源,更是實現自我價值的重要部分,他們更注重在職場上能被公平對待。
3. 高校教師流動中的“理性經濟人”現象
近些年來自高校教師的人才流動乃至校際間對高級人才的激烈爭奪也說明同樣的問題[6]。有學者在對1990年至2012年這20年的人才流動進行分析基礎上,并預測未來仍將呈現人才需求與供給的雙向增長,人才流動率將進一步提高[7]。正如人民網的評論“我們理解損失一個張小平的焦慮,但更認可人才的自由流動,崇尚人才管理在制度框架之內進行”。因此,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原有社會結構變動,人才的發展大趨勢由以前的忠誠于單位的“倫理人角色”向“理性經濟人”轉換。
三、國事與家事:法理與情理交織中的生命權
案例3:
2018年8月5日中午,四川省南部縣火峰鄉,明明(化名)父母帶著他開車出去辦事。回家途中,一直將他忘記在車內,等到最終發現他時,孩子橫躺在后排座上,手指甲、嘴唇發青,經120搶救無效死亡。明明的父親告訴成都商報記者,自己把孩子忘在了車里,找到時悲劇已經發生[8]。
1. 過失侵害兒童生命權法律后果中美之比較
作為“車輪上的國家”的美國,熱死兒童案例也時有發生,據該國非營利組織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afety Council)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美國于1998年至2017年間已有742名兒童死于交通工具內中暑,年平均死亡人數為37人。報告同時也顯示,全美已有21個州出臺相應法律,其中有8個州會對那些故意放任孩子,讓其獨處的父母施加重罪懲罰。例如2014年,美國堪薩斯州威奇托市的男子賽斯·杰克遜(Seth Jackson)因將10個月大的孩子遺忘在車內致其被熱死,面臨一級謀殺罪的指控;2016年10月,美國馬里蘭州一名母親因將嬰兒單獨留在車里,最終警察以危險行為和無人看護兒童的罪行將其逮捕。筆者訪學所在的密蘇里州立法明文規定禁止將10歲以下的兒童單獨留在家中。
隨著汽車及家庭轎車在中國普及,每年都有因疏忽導致兒童在汽車內熱死的悲劇發生。據媒體公開報道,2006年到2015年,至少發生20起兒童被忘在車內事件,造成15人死亡。引人深思的是近5年來,在被報道的事件中,兒童因教師、校車司機將其遺忘而被困車內的現象已經越來越少,究其原因是法律在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中發揮了懲戒作用并產生了預防功能。與此相反,近年媒體報道的信息卻顯示越來越多的情形是兒童被父母遺忘在車內,僅2015年已經發生5起,其中4人死亡,1人因及時發現獲救。筆者在相關檢索中,并未發現父母因過失導致兒童死亡案件被追究責任的此類案件。原因有二:一是因為我國刑法上僅有虐待罪和遺棄罪,這兩者都要求行為人存在主觀故意,而家長因疏忽導致孩子在車內死亡的情況,顯然無法證明其主觀故意,所以不能以虐待罪和遺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二是即便根據刑法要件規定,理論上可認定父母因疏忽置兒童于車內窒息死亡行為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但目前司法機關并未追究肇事父母的法律責任。究其原因,與中國固有的“家文化”相關,因為在中國,未成年人監護一直被認為是“家事”而非“國事”,對于家庭內部一些造成“嚴重后果”的傷害事件,法律體現著“和為貴”的初衷,并未主動介入。
2. 父母子女間的權利義務觀之演變
在互聯網媒體平臺騰訊上的一篇名為《幼兒悶死車內,父母內疚了事?》文章所附“你認為兒童悶死車內,疏忽的父母是否需要嚴懲?”的民意調查中,十萬以上的網民意見顯示:有91177人認為需要嚴懲,其比例達83%,僅有不到兩成的網民認為不需要(18890人,占比17%)。“父母本是孩子的第一監護人,本應該好好照看孩子的,只要孩子和父母在一起,不管在什么場合如因父母疏忽發生意外都應當追究父母的責任;因為是父母沒有盡到責任才導致幼小的孩子發生意外。”這一留言代表了大多數支持追究父母法律責任的民眾觀點,此類看法于20年前應是難以想象的。根據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悲劇發生后還去責難父母,甚至主張把他們送上法庭,顯得不近“情理”。但時至今日,通過這一調查結果可窺見人們的觀念已經發生變化:即應把曾經是家庭內部事務父母子女關系置于法律框架之下,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屬,而是獨立的生命個體,在情理與法理交織的關系中,絕大部分人選擇在法律框架下厘清父母子女之間的權責關系。
四、小我世界與廣大社會:現代公民意識的增強
1. 社會變遷中的“倫理人“角色演變
縱觀中國古代史及近代史,長期以來因原始耕作技術而形成的農業社會以及由此孕育出只限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加之中國過早“發育成熟”的中央集權政治制度,這三者有機結合而無法形成以交易為特征的商業社會,自然就無法產生契約社會的基礎條件。農業社會需要家族成員的內部合作,由此形成以宗族或家族為基礎單位的社會結構模式,這種以地緣和血緣為特點的差序格局[9]的熟人社會,自然也就無法過渡到以契約為基礎的陌生人社會。
但改革開放后尤其是近20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一方面原有的社會結構模式發生了改變,社會形態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過渡;另一方面由傳統的地緣、血緣的熟人社會逐步向契約型社會過度,尤其是隨著工業文明的發展,社會成員的心理也發生了變化,人們的價值觀也由以前崇尚的“集團本位”向“個人本位”價值取向演變,換而言之是從“倫理人”向“經濟人”過渡,從法律層面體現為公民權利觀的變化:個人權利意識的增強,即人們越來越注重個人權利,并愿意為贏得自己應有的權利而抗爭,正如耶林所言“世上一切法權是經由斗爭而獲得的……是一場經常延綿整個世紀以上的斗爭”[10]。
2. 由“經濟人”到“社會人”角色的演變
互聯網的發展,社交媒體的豐富,民眾獲取資訊的途徑越來越豐富,獲得的成本也越來越低,同時這些資訊的豐富,一定程度上也是除了學校教育之外民眾智識教育的重要途徑,另外互聯網的發展也為民眾參與社會治理,成為“社會人”提供了便捷的渠道。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民眾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與參與度逐步提高。從發生在21世紀初的孫志剛案、藥家鑫案、2009年鄧玉嬌案、2012年的“小悅悅事件”到2016年的“辱母案”乃至2018年的“昆山龍哥事件”等,正是民眾的高度參與所引發社會的討論,也成為另一種意義上的司法監督,產生了積極影響和令人滿意的結果。前者如取締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后者如“辱母案”在社會力量的推動下引發了法律界以及普通民眾關于適用“正當防衛”的大討論,而這一討論也直接對2018年的“昆山龍哥事件”產生影響,昆山公安部門公安機關經過縝密偵查,并商請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直接認定當事人于海龍行為屬正當防衛并撤銷案件。正如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所言,“辱母案”以后,關于正當防衛的適用,已經逐漸開始與民眾的情感和判斷基本接近一致。這樣的結論一方面說明近20年來,民眾不僅在維護自己的權利觀念上發生了變化,另一方面也顯示民眾逐漸開始積極參與社會治理,體現了新時期的公民素質。
五、結論與展望
縱觀改革開放40年中國社會的變遷,梳理公民權利觀的發展演變軌跡,不難得出這一結論:在最親密的婚姻家庭關系中,現代人珍視自己的自由意志和財產權利,在道德與法律的糾葛中,體現了普遍的理性,哪怕是父母子女關系,他們也能厘清父母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和本屬于子女的權利,即父母子女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亦有清晰“界線”,在勞資關系中追求個人的勞動價值時也更多滲入了現代契約精神。總之,近40年的社會巨變,出現了由最初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倫理人”角色向“經濟人”過渡,追求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契約關系。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現代人不局限于“小我世界”,積極參與社會治理,體現了現代社會的公民意識與公民素質,實現了由單一的“倫理人”向“經濟人”與“社會人”多重社會角色的轉變,充分體現現代人的權利意識的增強和權利內容的豐富。
作為執法機構與立法機構在立法如何對待這一巨變,是超前立法還是順應民意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法律根植于社會,法律生長于社會,法律的真實效力不是源于主權者,而是源于社會的承認[11]25。法律和制度必須在相當程度符合這一代中國人對自己、他人、社會和國家想象、情感[12]。1990年婚姻法修訂及近1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3次婚姻法司法解釋也代表了官方對民意的正面回應。[13]從婚姻法的司法解釋到正當防衛的適用,反映了司法機關與民意的良性互動。“辱母案”與“昆山龍哥事件”等案件的處理也體現了司法機關基于民意基礎上的實用態度。總而言之,基于社會變遷下民眾權利觀的演變也將是司法機關今后司法活動的重要考量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