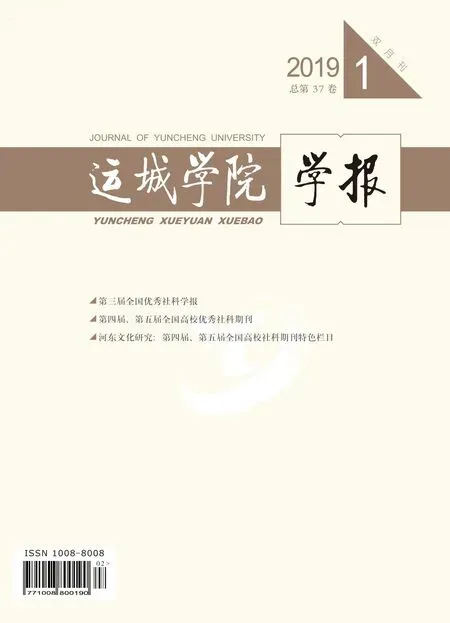《倚天屠龍記》中的“奔女情結”
姜 漢 西
(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金庸在他的武俠世界中,塑造了一系列成長中的英雄與俠客,這種以男性為主導的創作模式,固然符合了一定的俠義審美規范,卻也在某種程度上使得小說的思想內涵存在著缺陷。正像嚴家炎先生所說的那樣:“金庸小說積淀著千百年來以男子為中心、女性處于依附地位的文化心理意識,雖然作者自己也許并沒有明確地意識到。”[1]在金庸的諸多作品當中,都可以較為清晰地看到“‘第二性’即女性,是相對于男性而存在和定義的他者”[2],盡管金庸已是飽受現代文明熏陶的作家,但作品中女性人物始終沒有突破傳統武俠小說中女性形象作為陪襯角色的桎梏,女性依然是服務于男性的成長,在男性中心的外圍打轉,無法占據敘述的核心,成為被言說的主體。然而我們卻看到在這樣一個氛圍下的女性并沒有因此失去自身的光彩,她們的存在被人們深深記住,成為了小說金庸武俠小說中不可或缺的亮點。
西方已有一套相對完整的話語體系來闡釋男性和女性之間的沖突與調和,然而其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普適性卻值得懷疑,尤其是對于具有極大差異的東西方而言。于是在當下的時代環境里,江曉原先生在《云雨:性張力下的中國人》中提出了“奔女情結”這一概念,即“女子因愛慕男子而主動‘奔’就,這在中國古代久已有之,《禮記·內則》說‘聘則為妻,奔則為妾’也承認‘本’所成就的婚姻為有效”,而且“有美女愛慕來奔,是古代中國文士一直心馳神往的大快事之一”。當然在相對開明的社會制度下,這種奔女故事也許會出現,一旦社會道德和禮教規范日益嚴格起來,奔女故事出現和被敘述的機會也就相對減少。“然而此時這種故事又轉而成為深受禮教拘束的士大夫文人聊以自慰的白日夢(day dream),當禮教把上層社會中的許多女性改造得日益古板乏味時,文士們在這類故事中呼喚著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這類故事在他們意識深處積淀成一種“奔女情結”:希望有美麗多情的勇敢女子替他們沖破禮教的羅網,主動送愛傳情,投懷送抱”。[3]
正如徐岱所說:“金庸小說的獨特在于其較一般武俠作品更為熱鬧,擁有一種生命的熱烈”[4],極強的生命觀照意識是金庸小說中不變的價值標桿,也是其思想性得以維系的保障。在金庸的筆下,圍繞著張無忌這個男性創造了四個性格各異的年輕女性,她們蔑視禮法,敢于表達自己的愛恨,在她們身上,有著“五四”時期的女性身上才有的精神氣質和人格意識。在男權化的想象下,她們是自我婚戀的理想對象,然而他們性格中的復雜性卻容易為人所忽視,作為一位追求思想性的作家金庸,故事中有沒有自己的影子,在這些女子身上又賦予了什么樣的社會內涵?寄托了哪些理想化的追求?結合“奔女情結”對金庸筆下的女性進行分析,不僅是對作家本人思想的一次有益探索,也是深刻理解小說內涵的一次積極嘗試。
一、殷離:封建倫理束縛下的理想主義者
男權中心話語是在社會歷史的發展中不斷累積的結果,正是在社會環境的基礎上才得以建構起來的,封建社會中傳統的綱常倫理無時無刻不在塑造著其中生活于其中女性,也正是有了這樣一個依托,男權主義才得以生根發芽。因此反對封建社會中的綱常倫理,其實也是對男權社會的積極抗爭。小說中的四位女性中,殷離的成長道路最為坎坷,也是金庸小說中最具幻想特色的另類女子,她鐘情于那個少年張無忌,并一直在尋覓著心愛的人的足跡,條件上已具有奔女的雛形。
殷離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也可以說她是一個女權主義者。如果從環境對于人的塑造角度來看,殷離心智發生轉變的關鍵點正是從她媽媽的遭遇中她看到了女性在婚戀中完全的被動地位,真心的付出反而換來了男性的背叛和拋棄。對于一個涉世未深的小女孩來說,她是無法接受的,故而才敢于起來反抗替母親打抱不平“爹爹,你……你別殺媽媽,別殺媽媽!二娘是我殺的,你只管殺我好了,跟媽媽毫不相干……”。殷離的母親可以說就是一個男權社會下的犧牲品,她默認了男性中心主義這個社會現實并盡自己的力量去維護,試圖以此擺脫作為“他者”的地位,可卻在這個男權的泥淖里越陷越深。正是有了殷離的母親這一活生生的例子,在她的心目中才有了對男女關系的深刻認知,在她的理解中,男女之愛應該是專一的,從確定關系開始,兩個人就應該是遵守著這個契約,彼此都不能違背,當然更容不得第三者的存在,而她的父親在有了自己的母親后,又和其他的女人想好并娶進了家門,無疑是不能原諒的,而當殷離喊出“你不是我爹爹,你是負心男兒,是大惡人”的時候,其實已經在表明了一種反叛和分裂的態度,要徹底地與父權抗爭,表達出自己所代表的女兒身與作為男性的父親之間的勢不兩立的姿態,而當她因不忿母親受欺,殺死了父親的愛妾時,這種決裂和分庭抗禮的激情與熱血被推向了一個極點,而她也無法再回頭,殷野王的追殺也正式拉開了這場男權和女權斗爭的序幕。
殷離的反叛是在血和淚的融匯中激發出的抗爭,然而身單力薄的她,根本無法應對來自父權社會的壓力,更無法協調自己內心的掙扎與矛盾。她的反叛是一種生命的應激本能,充滿著理想化的特征,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下,她在努力追求著自己心中的那個既定對象,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擾,在精神自由的引導下呵護那份純潔的愛,孤獨而勇敢。
二、趙敏:官民殊途下的獨立人格捍衛者
趙敏本是異族的女子,遠離漢文化的影響區間,然而在這部小說中,金庸卻把這樣一個外邦女子塑造得有血有肉,可親可感。然而我們如果只是關注其郡主的身份和她的任性調皮等外在的表現,無疑會忽視掉這個女性身上許多的光輝,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趙敏和殷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這種相似表現在兩者對張無忌深深的愛戀,也就是在“奔女情結”上達到了統一。然而趙敏和殷離在一定程度上又有著差異,這種差異表現在對愛情的態度上,殷離在家庭悲劇的影響下,其心中的愛戀觀可以說是已經有了異化的色彩,呈現出的是心靈扭曲后的獨占和自私,為了達到自己的愛的目的,她可以選擇默默承受忍氣受屈。而趙敏對愛的理解則有著相對開明的態度,并且對男人尤其是自己喜歡的男人有著玩弄于股掌的野心,有著看在眼里明在心里的聰慧,故而她可以在張無忌面前侃侃而談,在男人的江湖世界中自由游走,不受世俗的羈絆與負累。
其實趙敏自在綠柳山莊對張無忌一見傾心后,便開始了她的“奔女”生涯。她以一種旁觀者的姿態追隨著這個男人,卻并沒有委曲求全,趙敏身上散發出的人格獨立的光輝,是殷離和小昭都無法比擬的,盡管她的內心愛戀著張無忌,然而她不是一味地宣稱要服侍張無忌一輩子,并表示永遠不離開這個男人,而總是在恰當的時間和地點出現在張無忌的面前,當然這種恰當有時候是她自己精心設計的結果。最為直接的體現便是給張無忌黑玉斷續膏,明明是她的人傷了張無忌的三師伯和六師叔,最后還要張無忌感謝她的給藥之恩,并答應替她做三件事。一定程度上來講,自張無忌答應了這三件事開始,男女雙方的主從關系已經發生了逆轉,可以說從此以后基本上都是趙敏在左右著兩個人的情感發展。于是才有了張無忌拜堂成親之時她的出現,并以此為要挾逼迫張無忌就范,從而阻止了張無忌和周芷若的結合。
趙敏的人格獨立不僅僅體現在對愛的方式上,還體現在她追求自己的愛時的那種超越民族和世俗的態度上。在張無忌看來,漢蒙兩族是處于對立的雙方,沒有任何緩和的余地,所以明教才會在各地起義反抗元朝的統治,而趙敏卻以一種愛的深厚性超越了種族的界限,打通了男女之愛的種族壁壘。然而作為女兒的她,盡管可以置國家和民族于不顧,卻無法擺脫來自父兄的鉗制,父兄所代表的其實正是男權話語。后來在爹爹面前,她以匕首抵在自己的胸口并說出:“你不依我,女兒今日死在你的面前”時,她的決然態度達到了頂點,而汝陽王的那句“從此不能再是我女兒了”則是宣告了父權的失敗。
趙敏思想的開放性使其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在愛戀的意義上實現了統一。而她在實現自己愛戀的圓滿的過程中,獨立和勇氣無疑是不容忽視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氣質,同時她也在以自己的實踐詮釋父權社會中女性的壓抑,但是父權的根系之廣已經滲透在了腳下的土地,只有徹底地決裂,才能找到自己獨立生存的空間,而她的決絕和毅力也為她爭取了屬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三、周芷若:師徒話語下性格裂變的孤獨者
周芷若與其他三個女性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也是最富爭議和引人深思的女性形象。在她身上有著一種極強的割裂感,從最開始的單純善良到后來的不露聲色,深諳韜光養晦之道再到最后原形畢露,她的性情在不斷變化,她的愛戀也在不斷地發生扭曲和變質。漁家貧女出身的她,在江湖中和派系內又有著怎樣的遭遇?何以會埋葬自己的善良,讓自己一步步變得兇狠和殘忍,終以悲劇收場?在自己的真情實意和師父的違背自己初衷的遺命中,她的自我意識被一步步消減,情感的內核逐漸被剝落,生命的存在成為了一具空殼,這種對于靈魂的蠶蝕的書寫成為了周芷若人生最為悲情的部分。
正如有人評論的那樣“周芷若身上有金庸小說中女性的許多的共性,但更引人入勝的是她在金迷認可背景下的性格裂變”[5],周芷若的人生以萬安寺臨危受命為轉折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但每個階段她身上都有著揮之不去的孤獨感,她的孤獨來源于缺乏依靠的漂泊生活和社會立足的急切渴望,這種孤獨的根源和她的無父有著緊密的聯系,其實孤獨感就是從她父親的離開為開端的。母親亡故之后,她就和父親在一起生活,后來父親也死了,她賴以生存的最后一根支撐也倒下了,還是小女孩的她只能是對這個世界以及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迷惘無措,茫然和恐懼。后來滅絕師太再次成為這世界上唯一喜歡她看重她的人,也是她唯一的依靠。正是因為如此,她不能離開峨眉派,否則就會流離失所,她不能叛離師父,否則她就是背信棄義。于是她惟有對師父言聽計從,與此同時也就內心中慢慢疏遠了漢水之湄的那個純真善良的漁家女孩,并且在光明頂上將倚天劍刺向了自己愛著的那個男人。
縱觀周芷若生命軌跡中情感線的發展,這個在成長中缺失了父親這一角色的女孩,一直在自卑的情緒中無法解脫,無論是在對張無忌的追求上,還是在成為了峨眉派的掌門人之后,她對自己都是充滿了懷疑的,這從一個方面也說明了父權固然在女性的解放上有著無法克服的桎梏,然而女性在徹底失去了父權的庇護后,同樣在社會中會迷惘和無助,找不到未來的方向,甚至誤入歧途。周芷若對于張無忌苦苦追求,并且以和他結合為最終的勝利作為自己的期許和希冀,其中就蘊含著男性中心的論調,當然她的目的并不純粹,然而僅憑一己之力,她終究是無法有所作為。作為男性的張無忌是她理想實現和遺命完成必不可缺的重要一環,師父的臨終囑托確實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我們從中正好發現了在這個冷漠的滅絕師太的內心其實也是有著男權化傾向的,只是她的聰明之處在于會利用這樣一個社會規范。然而她的遺言卻將崇尚善良和自然天性的徒弟一步步逼近屈服于男權話語的深淵,并使得其在分裂中獨自品嘗著孤獨的滋味。
四、小昭:種族矛盾中異國他鄉的漂泊者
小昭和趙敏相比,從思維到言行要收斂很多,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像一個接受了傳統文化熏陶的漢族姑娘,溫良恭儉讓是她身上抹不去的光輝。她有著貴族的身份,然而在光明頂和張無忌身邊卻一直自居奴婢之位,她明明愛著張無忌,卻不敢有太多的奢望與幻想,只是默默地守護在這個男人的身邊,不張揚不放肆,這種女子對男子的仰望姿態,強調的是女人的在自己愛人面前的謙卑,突出的是對男性的崇拜和依賴。而為了愛情,她又可以背叛身上肩負的重任,在張無忌遇到危險無法化解的關鍵時刻,她懷著一種極強的犧牲精神挺身而出,從此注定了孤獨的一生。
小昭身上的“奔女情結”和其他三位女性有著異曲同工之處,都表現在對于張無忌這個男人的愛慕,并且愿意常伴其左右,不同的是每個人受制于自身的家庭和身份背景與成長環境的影響,從而表現出一定的具體行為上的差異性和程度上的深淺的不同。而聯系小昭話語中所流露出的對于張無忌的尊崇和在行動上的犧牲來看,小昭在內心中是無法克制自己對眼前這個男人的迷戀的,這種發乎情止乎禮的內心沖動左右著她的一言一行,所以她才會在各個方面才會表現出一種心甘情愿的“臣服”。小昭為皆為答應前去波斯,臨行之前那句:“我決不愿做波斯明教的教主,我只盼做你的小丫頭,一生一世服侍你,永遠不離開你”則是將這種女性對于男性的極度順從與崇拜推向了極致,這種乖順與懂事,多少有點匪夷所思。
小昭對女性身份的懷疑和對男權世界的認可與維護在意義上具有一致性,她的溫順與賢淑,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傳統社會中,尤其是宋明理學興盛以來對女性束縛的結果,而這正是男權的體現。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發現小昭在服膺于這個男性中心的世界時,不只是從女性自身做出回應,還對自己的民族身份表達出背離意愿,在她和張無忌二人終于從密道中逃出后,張無忌說:“你是本地西域人,是不是?比之我們中原女子,另外有一份好看。”小昭秀眉微蹙,道:“我寧可像你們中原的姑娘。”而這種對于中原姑娘身份的渴望,很明顯是對自己民族文化不自信的表現,同時也是一種主動他者化的方式,正如王安憶在《我愛比爾》中所表達的如出一轍,這也可以看作是中國小說藝術中常用的敘事模式之一,只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具體的內涵發生了改變,正如陳平原所言,“金庸繼承了傳統的敘事模式,同時,以自己淵博的學識和高超的藝術技巧,使陳腐的敘事模式表現出新的內涵”[6]。
五、結語
《倚天屠龍記》以張無忌為中心展開了女性群像的男性化想象,從殷離、趙敏、周芷若到小昭,她們在各自不同的環境中成長,形成各自獨具魅力的性格特征,然而在情感的路上卻無一例外地遇到了阻力,凸顯出一種社會生活中女性集體的受壓制和被禁錮狀態,而這個幕后黑手正是傳統社會中沿襲下來的男性中心話語。當然這也并不意味著女性就徹底失去了有所作為的空間與動機,小說探討的正是面對這一強權話語,不同性格特征的女性如何處之的問題:殷離一心追求屬于自己的純愛想象,迷戀著那個曾經年少的張無忌無法自拔;趙敏能夠視富貴如糞土,棄尊榮猶如敝屣,并在家國沖突下,毅然選擇了愛情,在男人面前也不卑不亢,表現出了女性的勇毅與灑脫;周芷若從心地善良的漁家女郎到逐漸黑化的轉變,是情感的無法滿足后報復和嫉妒;小昭則是迷失在男權世界里。從以上人物分析來看,金庸筆下小說世界盡管是一種男權化的想象,但并不是一味地宣揚和維護,而是在對男權世界下的女性命運給予了無限的關注與同情,并通過對她們各自選擇道路的分析,進而強調出女性個性解放的重要意義。
而以上從這個基本固定的創作模式出發,進而去考察其中作者的文化心理以及在小說中人物身上所賦予的情感態度,我們會發現女性在傳統的男性話語下大多處于一個被遮蔽的狀態,但她們并不是完全屈服于時代所確立的禁錮之中,她們敢于為愛舍棄裝飾性的光環,也勇于為愛獻身,發出屬于女性自己的聲音和呼喊,由此可以看出,金庸以及他的武俠小說還有更多值得挖掘的精神特質和深層次的文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