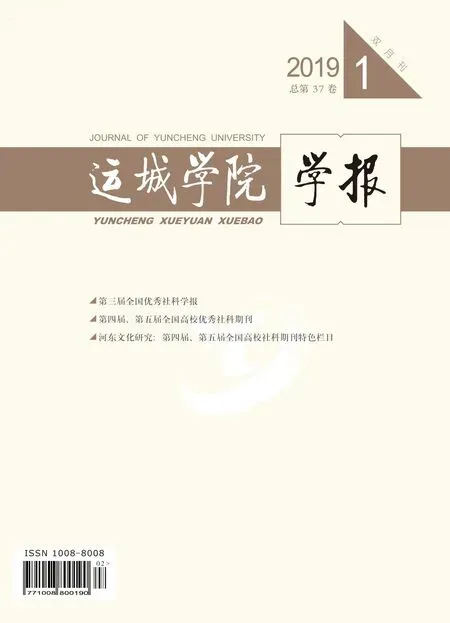李漁《巧團圓》的“玉尺”巧用
2019-03-05 13:22:00劉川楠
運城學院學報
2019年1期
關鍵詞:愛情
劉 川 楠
(福建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州 350007)
宋金時期的雜劇中有許多小件砌末,也就是舞臺演出所用的道具,如木杖、扇子等,一般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伴隨著古代戲曲演出程式的不斷完善,舞臺道具的種類也日漸豐富。及至明清時期甚至出現了許多以物品命名的劇目,其中又以定情信物作題目的居多,比如湯顯祖的《紫釵記》、孔尚任的《桃花扇》。在這類戲劇作品中,定情信物不但是舞臺的重要道具,它作為整部劇的關鍵,也是男女主人公對美好愛情希冀的象征,寄托著作者的寫作訴求。
目前對定情信物的研究已經有了一定的學術積累,一方面是對元明清時期一些作家如喬吉、洪昇等作品的個案研究,如金曉雪《定情信物在<鴛鴦被><金錢記>中的作用》[1]、徐龍飛《小議“金釵鈿盒”在<長生殿>中的作用》[2]。對某一時期作品中定情信物作用的分析,如王慶芳《古代愛情劇中信物的作用及文化意蘊解析》[3]、張青《明傳奇中的定情信物》[4]。另一方面,是關于定情信物作為審美意象的理論分析,如任暢《戲曲意象淺論》[5]、方李珍《戲曲意象初探》[6]、施旭升《象外與環中——戲曲藝術的原型特質分析》[7]等。《巧團圓》是李漁《笠翁十種曲》中完成較晚的一部傳奇,李漁在劇中也為男女主人公設置了一件定情信物——玉尺。“玉尺”同《玉簪記》中的“玉簪鴛墜”、《長生殿》中的“金釵鈿盒”、《桃花扇》中的“桃花扇”等信物在劇中的作用相似。鑒于此,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以李漁《巧團圓》為文本,具體分析玉尺作為劇中的道具,對故事情節的連接和推動作用,并承載姚克承和曹小姐對于自由美好愛情的渴求,體現作者對于自由、美好愛情的歌頌,亦作為一種審美意象,成為衡量男女主人公行事規范的抽象尺度。……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散文詩(青年版)(2022年4期)2022-04-25 23:52:34
都市(2022年1期)2022-03-08 02:23:30
戀愛婚姻家庭(2021年17期)2021-07-16 07:19:34
海峽姐妹(2019年9期)2019-10-08 07:49:14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8期)2019-09-23 02:12:26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6期)2019-07-24 08:13:46
文苑(2018年23期)2018-12-14 01:06:28
金橋(2018年9期)2018-09-25 02:53:32
小說月刊(2014年1期)2014-04-23 09:00:03
延河(下半月)(2014年3期)2014-02-28 21:0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