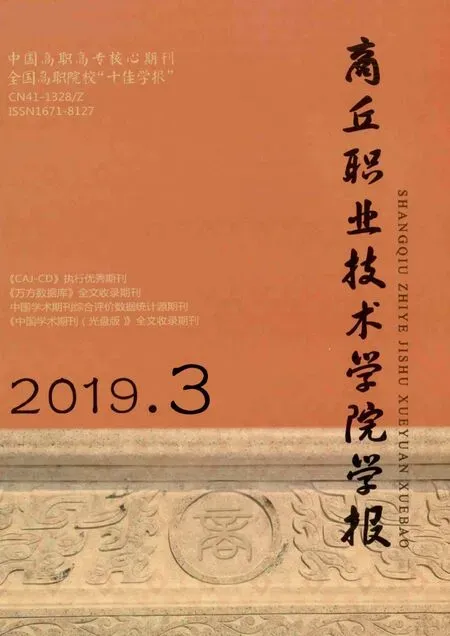《看不見的人》中間接的女性力量和艾里森的矛盾女性觀
衛佳睿
(云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拉爾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 1913-1994)是20世紀最有影響的美國小說家之一,《看不見的人》(Invisible Man, 1952)是其代表作。小說講述一個不被看見的黑人男青年“我”在不斷尋找被看見的過程,小說的開頭與結尾相互照應,都是“我”回到一個封閉的空間。主人公“我”是歷史這座巨型機器上毫不起眼的齒輪,齒輪離開了機器無法生活,而機器卻可以有源源不斷的齒輪來替代某個齒輪。在“我”尋找被看見的過程中,5位女性對“我”產生了不容忽視的作用。針對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國內外的關注點較少。最早關注《看不見的人》中兩性區別的是西爾萬德,她指出:“《看不見的人》中的黑人和白人女性都反映了美國白人男性所建立的被扭曲的刻板人物形象,”[1]并以艾里森本人在其論文集《影子與行動》中提到的“刻板人物”的定義,說明《看不見的人》是反對美國白人社會對黑人進行的“刻板”描繪,而女性的存在卻是非人性化的和刻板的。斯坦福延續了西爾萬德“刻板女性人物”的觀點,并對這些人物進行了更詳細的分類: “小說中黑人和白人女性都復制了描寫女性的傳統兩分法——婦人或妓女,母親或誘惑者。”[2]但她只是詳細分析了瑪麗這位人物的特征。劉曉潔沿用斯坦福的二分法,對5位女性人物進行了分類和解讀[3]。許麗萍在其碩士畢業論文中從女性主義視角探討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4]。與這些研究不同,本文擬在分析小說中的女性形象的基礎上,著重探討這些女性在宗教、心靈和身份三方面所蘊含的力量對“我”的巨大的影響,并與艾里森對女性形象的描述做對比,進而分析艾里森的矛盾女性觀。
一、間接的女性力量
“我”把自己定義為看不見的人,一方面出于對自己身份的懷疑;另一方面為揭示黑人在美國白人文化中的地位。但“我”還是踏上了尋找身份的旅程,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最終是如何被看不見的。“我”經歷過3次身份轉變,這3次改變促使“我”不斷向上爬,爬向別人能看見“我”的山頂。其間有5位女性在“我”3次身份轉變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女性本身所隱藏的力量把“我”推向了尋找的高峰,轉變了“我”尋找的方向,但最終卻走向了深不見底的深淵。這5位女性角色影響了“我”的宗教觀、心靈歸屬問題和身份建構與轉變。
(一)“我”的宗教觀
《看不見的人》創作歷時5年,1952年完成,其間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納粹覆滅后人們心靈、信仰和道德的崩潰與重建。1947年美國私刑迫害事件、種族問題愈演愈烈。一個致力于建立自由、平等、博愛的國家對黑人卻從沒兌現過他們的諾言,黑人一直被排除在平等和博愛之外。美國內戰結束后,“南方社會最大的變化是黑人奴隸身份地位的改變,奴隸制的廢除使得將近400萬的黑人奴隸獲得了自由。自由的來臨使許多的黑人相信上帝對黑人的拯救,認為這是上帝的仁愛與福音”[5]。解放后的黑人以極大的熱情投身于宗教生活中,學習和閱讀《圣經》,參與教會組織的各種活動。基督教已經融入美國黑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里,給予美國黑人希望和勇氣,為無助的他們重燃生活的希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人們精神造成的重創和美國私刑對黑人身體與心靈的毀滅動搖了他們對基督教的信仰,并懷疑上帝是否真的可以拯救他們。
小說通過一個老年婦女唱圣歌,反映出主人公矛盾的宗教觀,即對上帝的懷疑。小說前言里“一個老年婦女在唱黑人圣歌”[6]9,這部分的字體是斜體字,從前后文的語境來看,該部分產生于“我”的想象。“我”通過聽而超越現有的空間,進入一個想象的空間。在另一層空間的“我”與這位唱圣歌的黑人老婦女進行了實質性的交流。交談內容涉及上帝:“‘孩子,我滿心愛戴我的主人’她說道。‘你該恨他’我說。‘他給了我一個兒子,我愛這幫兒子,所以我雖然恨他,可我總得愛孩子的爹。’‘對這種既愛又恨的矛盾心理我也有體會,’我說。‘我此刻之所以在這兒出現,也就是因為這種矛盾的感情。’”[6]10-11。這段對話揭示出“我”精神上的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對上帝的矛盾心理。 “我急忙離開,聽見老婦人還在低吟:‘詛咒你的上帝,孩子,然后就死去吧。’”[6]9。上帝本應拯救黑人兄弟于水深火熱之中,但現實并沒有。所以“我”代表黑人兄弟對上帝的存在和力量持懷疑態度。然而為了生存,“我”一直隱藏自己的不滿情緒,這種情緒只能通過和老婦人的對話表現出來。一個是懷疑,一個是堅信,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部分人仍然堅信上帝對黑人種群的拯救,但另一部分人質疑上帝的存在能否解救他們于水深火熱之中。
此外,“我”對上帝的懷疑并未到此結束,與老婦人的對話喚起了一種類似答案的答案,指引了“我”對未來的尋找方向。在對話的后半段老婦人提到了“自由”,她用女性獨有的細膩在“自由”和上帝之間形成一種比較,并表明他們兩人都更愛“自由”,為后文奠定了尋求自由的基調。這位老婦人用自己獨特的方式,把上帝比喻成兒子,把“我”精神中對上帝的矛盾心理和對自由的向往表達出來,把“我”從一個看不見的影子慢慢具化成一個實體。
(二)“我”的心靈回歸
“我”是一個看不見的人,一直尋找不到自己的路。在大學里,遵紀守法,想要仿照布萊索博士,爬到高處,能夠被人看見。布萊索博士是一名典型的黑人功利主義者,即通過攀附和奉承白人獲取自己的利益。而“我”也照著布萊索博士的做法,巴結來參觀學校的白人贊助者,以此作為爬高的階梯。但“我”并沒有做好,反而弄巧成拙。當“我”要被布萊索博士開除時,“我”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迷茫到不知往哪里走,心不知飄到了哪里,好像一切都是一場夢。“我”就要離開自己用命奮斗出來的上學機會。直到遇見唱詩班“瘦削的棕色姑娘”[6]116,她的聲音和身體讓“我”回歸到出發的地方。這位女性是在布萊索博士找“我”談話之前出現的,當時的“我”正在觀察和敘述布萊索博士是如何走到現在的地位。敘述者只用了兩個段落描寫這位姑娘蘊含的力量。她的身體和歌聲聚積著無法言說的悲傷。埃萊娜·西蘇在《美杜莎的笑聲》中提到,在以菲勒斯語言為中心的父權社會,女性沒有自己的語言,她們只有用自己的身體作為語言:“它的肉體在講真話,她在表達自己的內心。事實上,她通過身體將自己的想法物質化了;她用自己的肉體表達自己的思想。”[7]所以,這位姑娘用自己的身體表達了內心深處的情感,盡管她還沒有自己寫作的機會。但是她的歌聲讓別人聽到了,刺激了“我”的心靈。同時,歌聲也給予“我”力量,讓“我”想到曾經、父母和家鄉。“我聽不懂歌詞的含意,但卻能領略演唱時的那種凄楚、渺茫和超凡入圣的情緒。”[6]116姑娘的這種力量讓“我”想到種種可怕的后果,包括父母的責備和不確定的未來。“這歌聲,雖是眼前情景的一個有機部分,似乎有一種力量,比這情景更加咄咄逼人,于是我一下子被拉回到現實之中。”[6]117想到祖父的囑咐,“我”決定直接面對未知的后果,盡自己努力繼續往前走。
(三)“我”的身份轉變
身份是“我”尋找的目標,目的是成為被看見的人。“我”從拳擊場的受辱,大學時期的努力與奉承,到大城市紐約的奮斗,全部是為了能出人頭地。但剛開始到紐約的“我”并沒有什么機會,直到遇到了3位女性。她們用自己的女性力量為“我”的身份轉變聚積了力量,點燃了導火索,最后找到了真正的意義,即自由。
瑪麗·藍博的關懷與言語為“我”的身份轉變積聚了能量。正如斯坦福所言,瑪麗是一種母親式的形象。她不僅給“我”提供了安居之所,并且還能讓“我”每天吃到熱乎乎的飯菜。在“我”最落魄和無所事事的時候,瑪麗給予“我”生活的希望。“我也不把瑪麗當作‘朋友’看待;她不僅僅是朋友——她是一種力量,一種堅定的、熟悉的力量,這力量像來自我的過去的某些東西,使我不致卷進我不敢正視的某種未知的境地中去。”[6]259瑪麗對“我”的影響不只在這段特殊時期,她的力量和影響貫穿“我”今后的生活,讓“我”能勇敢地去尋找一種改變。在紐約的這幾個月,打破了“我”對現實與想象的界限。在以前,“我”盡量遵循別人的話,尤其是布萊索博士,但還是被他欺騙,被他所寫的推薦信蒙蔽。在遇到瑪麗之前,“我”在一個油漆工廠找到工作,卻由于身體原因,無法勝任。我一直處于碌碌無為的狀態。在靠著賠償金度過艱難的日子時,瑪麗時常提醒“我”,并且不斷地督促“我”去做些事情以取得有新聞價值的成就。在瑪麗的關懷和鼓勵下, “我”開始重新認識自己,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而這些一定程度上歸因于瑪麗身上具有的女性力量,她不僅在生活上對“我”體貼入微,還在思想上激勵“我”做一些事情。瑪麗對“我”的影響是深遠長久的,在“我”迷茫的時刻,瑪麗的愛和力量充滿“我”的內心,即使走投無路時,也是想著去瑪麗家。“上瑪麗家去,我只有這個念頭,上瑪麗家去。”[6]572
被白人趕出自己家的老太太是點燃“我”憤懣和身份發生質變轉化的導火索。“我看見一群人面有慍色地朝一座房子看著,那兒有兩個白人男子正在往外搬一張單人扶手椅,椅子里坐著一位老太太,她正在用無力的拳頭打他們。”[6]267事件開始時,這位老太太有兩次直接面對“我”說:“只要看一看他們是怎樣對待我們的就夠了。看一看就夠了。”[6]268老太太的直視刺激了“我”。接著白人搶走了老太太的圣經,而且不允許她進房間內祈禱。白人的這些做法讓圍觀群眾奮起反抗,而當“我”在撿起抽屜里的東西,看到一張“自由身份證”[6]273時,想起了黑人的現實處境。這促使“我”在白人拔槍的時候走到黑人們面前,并說服他們用守法的方式與其進行對抗。這一行動標志著“我”被看見和被發現,為以后加入兄弟會埋下了伏筆。“而在整個過程中,那位年老的女性一直發出刺心的叫喊。”[6]271老太太的女性力量在無形之中刺激著“我”心底里潛藏的憤怒和不滿,點燃“我”內心不斷翻騰的火焰,從而使“我”在人群之中脫穎而出,尋找到新的發展方向。
西比爾,一位白人已婚婦女,小說中她作為自由的化身觸動了“我”的反叛和對自由的尋找。劉曉潔借用Stanford的兩分法,把西比爾定義為誘惑者。但筆者認為西比爾對“我”來說是最后的醒悟和解脫。她其實是自由的化身,肆無忌憚地釋放自己,用酒精和性愛麻痹自己以逃避現實。“我”接觸西比爾是想學習賴因哈特,試圖通過女性來獲得兄弟會的內部情報。當“我”戴上墨鏡時,人們把“我”認成賴因哈特,而“我”借此想象賴因哈特是怎樣的人,并且把自己化身為賴因哈特,為獲得情報而接近西比爾。但西比爾刺激了“我”對女性的同情和憐憫以及對自由的意義的尋找。尤其是在“我”送她走后,她又出現了。“她等在一座街燈下向我招手。我絲毫不感到奇怪;我相信這是命中注定的。我慢慢走近時聽到她在笑。她在我前面跑了起來,光著雙腳,悠悠然地仿佛在夢中一般跑。東倒西歪,但是很敏捷。”[6]539-540這時的西比爾與第一位老年婦女所向往的“自由”形成了呼應,把“我”對女性的印象混雜在一起。西比爾給予“我”的力量不同于前幾位女性,她讓“我”把對女性的鄙視、厭惡、愧疚和同情等各種情感交織在一起,帶給“我”一種沉重感,使得“我”對兄弟會和整個社會徹底失望。她讓“我”更加確定自己是看不見的人,一位無名的黑人而已。
這5位女性所賦予“我”的女性力量,讓“我”想起了家人的囑咐和初心,刺激了“我”一次次的身份轉變。正如有學者說:“黑人女性形象在必要時可以為了黑人男性做出犧牲,為整個黑人所謂的黑人民族性付出全部的努力,而同時隱藏她們的自我和個體需求。”[8]142這5位女性就是這樣的形象,為黑人而埋藏了自己。所以,這些女性所隱藏的特有的女性特質帶給“我”力量,在“我”尋找身份的路上起到關鍵的作用。
二、艾里森的矛盾女性觀
5位女性自身的力量無法直接改變黑人的現狀,而是以“我”為中間者,或者說通過男性本身的性別優勢,為黑人種群性運動發揮自己的微薄之力。但艾麗森對這些女性的片面描述又夸大了她們的缺點和劣勢,揭示了作者的矛盾女性觀。
文中所描述的女性力量并不能直接對外界產生任何作用,而是通過“我”的改變來顯示,即這些力量是在“我”身上發揮作用。因為父權社會的壓制,女性的地位低于男性,而黑人女性又受到白人女性的抵制,其地位更是處于社會階層的最底層。她們是男性的附屬品,只能通過男性尋求自身在社會上的位置。例如,瑪麗經常對“我”說:“只有靠你們這些年輕人去改變這個世道了,你們得帶頭,得斗爭,使我們大家多少提高一點。”[6]255-256從中可以看出,瑪麗作為女性的無能為力,她們只能在年輕男性的帶領下,為自身和自己的種群爭取平等的權利。而且無論是黑人老婦女還是跳舞的棕色女孩,她們都無法直接表達出自己的不滿和憤怒,她們的聲音和動作只能選擇性地被男性聽見和體會。所以,在男權社會里,女性所起的作用永遠是被動的,并受到種種限制,特別是黑人女性。而“我”在小說中發揮了橋梁作用,女性的力量成為“我”的行動動力,刺激“我”不斷尋求新身份,為改變黑人的現實境遇做出一些努力。
然而,這些女性形象在“我”心中卻是不完整的。文中所論述的5位女性,只有瑪麗和西比爾擁有自己的姓名,前面3位卻無名無姓,只是“我”根據她們的特征給她們貼上相應的標簽。第一位是“我”想象中唱黑人圣歌的老婦人,所以對她的描述僅僅停留在聲音上面,一是她唱的歌,二是與“我”的對話。缺少對其具體面貌和表情的描述。第二位是唱詩班的棕色姑娘,她也是通過歌聲和身體帶給“我”無窮的力量,對她的長相和經歷亦無從得知。第三位是被趕出家的老太太,她的叫喊、眼神和行為點燃“我”心中的火焰,但“我”并沒有去描述其悲傷和憤懣的心理狀態。瑪麗和西比爾雖然有姓名,但是對她們的描述卻仍然是片面的。瑪麗第一次出現的形象是“那個大塊頭黑女人用沙啞的女低音”[6]253,還有“看著她那粗糙的褐色的手指拿著那只亮晶晶的玻璃杯”[6]253,而且其言行始終體現其對男性的依賴。西比爾對“我”的印象類似于色情狂,即使現在美貌依舊,但“她馬上就會身材粗壯,有一個小小的雙下巴,腰腹部得勒上三層緊身褟。……但是我同時越來越發覺她身上有一種女性美,暖洋洋的”[6]527。可以看出,文中的女性盡管各自擁有其獨特的力量,但艾里森卻沒有全面完整地刻畫任何一個女性形象。黑人女性主義批評家認為,“男作家文本中的黑人婦女老套形象的刻畫是文學上‘厭女癥’的表現,這些文本并沒有抓住黑人婦女的真實形象……盡管有些形象似乎是正面的,但黑人婦女不論以怎樣的面貌出現,民族主義文學都沒能刻畫出黑人婦女的多重性格特點”[8]141。所以,艾里森雖然致力于跳出黑人的圈子,融合美國的價值觀和文學價值,但是對于女性在美國社會中的作用,艾里森的觀點依然是按照傳統男作家對女性的刻板認識,女性是男作家們烘托男性優勢的背景材料。但同時,艾里森也認識到這些女性所擁有的獨特的女性力量。艾里森的矛盾女性觀,表明了黑人男作家在逐漸打破性別的界限,并試圖為黑人同胞尋找出路的努力與嘗試。
三、結語
“我”在自我身份追尋的過程中離不開女性無形之中的力量,小說中的5位女性以女性獨有的魅力和優勢支持“我”在跌倒之后爬起來繼續尋找自己的出路。而男性作家對女性的刻板印象和片面描述反映其矛盾女性觀。這既體現了艾里森對女性價值的認同及對女性現實遭遇的同情,又打破了黑人男作家固有的偏見,表明黑人男作家也在努力超越性別差異,為黑人種群的共同利益所做的有益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