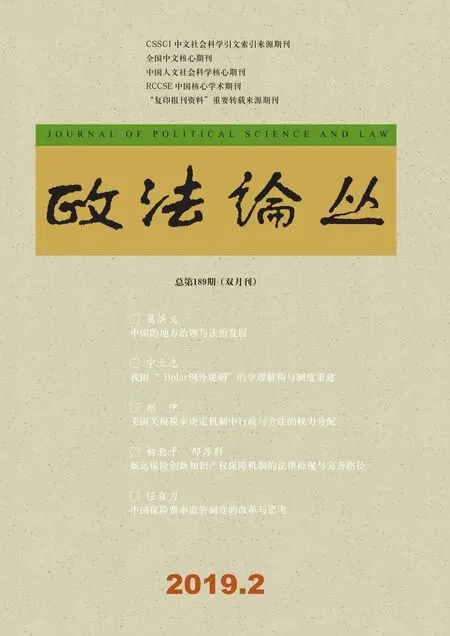法律現實主義思想再檢視*
王德玲
(山東大學法學院,山東 青島 266237)
法律現實主義緣起于十九世紀后期壟斷資本主義導致的經濟危機,吸智于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等社科新成果,借力于破除陳舊規則,增強政府控制的羅斯福新政,盛行于二十世紀20-30年代的美國,被認為是美國法哲學的開端,霍姆斯是法律現實主義的奠基人,盧埃林與弗蘭克是其主要代表人物。①法律現實主義的核心理論是“規則懷疑論”與“事實懷疑論”。我國學界對法律現實主義的研究不溫不火,原因主要在于:其一,在西方各法學流派群星璀璨的背景下,法律現實主義的光芒并不那么耀眼,尤其在它的先驅者霍姆斯思想,并行者龐德社會法學,后來者經濟分析法學光芒的映襯下,現實主義的主體地位很容易被忽略,常常作為上述思想的“伴童”被提及。其二,我國學界早些年對法律現實主義刻上了“極端、淺薄”的烙印,也消減了學者的研究熱情。其三,我國學界對待司法的態度傾向于形式主義,普遍認為“我國必須要經歷一個相當于自治法階段的嚴格規則主義階段,暫時犧牲實事求是原則,完全按法律規則辦事。”[1]P71-72研究面向上的冷淡并沒有阻止法律現實主義在司法實踐中被運用這一事實,也無法抹殺我國司法對現實主義的客觀需求。近些年來,我國司法注重法律的社會控制功能,主張“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有效解決糾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主張“司法為民”“能動司法”“案結事了”,這一系列司法倡議中蘊含著現實主義思想。從許霆案到趙春華案,近些年來曾引發社會廣泛討論的公共案件的最終裁判也都折射著現實主義的影像。當然,我國司法中的“現實主義”帶有典型的中國特色:一方面,這些案件或多或少都與民意的浸潤有關,裁判大都是在民意的裹挾下被動性作出的;另一方面,這種“現實主義”的裁判大都是在法律形式主義框架下隱蔽、含蓄存在的,它被或巧妙或生硬地裝在了法律形式主義的袋子里。被動性與含蓄性體現了我國司法對現實主義的矛盾態度。轉型時期的中國與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有類似之處,面臨著新與舊的躍遷,面臨著重要思想的革新,面臨著開啟一個法學新時代的歷史使命。對法律現實主義的再認識,厘清其價值與風險,有利于正本清源,也有助于我們思考當下的中國問題。
一、從“形式主義”到“現實主義”的嬗遞
法律現實主義以“反叛者”著稱,它大張旗鼓地向法律形式主義(嚴格來講是蘭代爾形式主義)宣戰。法律形式主義指涉相對模糊具有多重意涵,總體來講,法律形式主義是一種司法方法論,如布萊恩·萊特言,“是關于法官實際怎樣裁判案件和(或)關于他們應當怎樣裁判案件的理論。”②法律形式主義認為法律是先驗存在的,是永恒不變的;法律具有整體性和自洽性;司法者是發現法律,而不是創造法律。法律形式主義是人類法制發展到相對成熟階段的產物,可以追溯到古羅馬。羅馬帝國時期,立法日趨精細,法律的觸角延伸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形成了較完備的法律體系,人們開始認為,只要法律足夠理性完善,任何社會糾紛都能夠通過法律得出唯一正確的結論,司法活動開始表現出嚴密的系統性和邏輯性。這種法律形式主義攀附著羅馬法復興、歐陸法典運動、分析法學的發展和運用以及布萊克斯通的《英國法釋義》傳入美國,在美國落地生根。到十九世紀后期,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蘭代爾提出了“法律是一門科學”的論斷,將法律形式主義推向了巔峰。
蘭代爾形式主義認為,任何領域的知識都可以構建成由相互關聯的、邏輯上可證明的基礎原則所支配的科學,法律就是一門科學。[2]蘭代爾法律科學以類似幾何學的面貌步入科學殿堂:第一,法律自足性。認為人類通過理性可以制定出在制度上一以貫之,在邏輯上無懈可擊,在實踐中無所不包的自足完滿的法律體系。第二,法律推理形式性。認為法官的裁判是一個科學的邏輯運算過程,“法律推理應該僅僅依據客觀事實、明確的規則以及邏輯去決定一切為法律所要求的具體行為”,[3]P3每一個司法裁判都出自于可展示的三段論推理。第三,裁判結論的確定性。不管案件如何紛繁復雜,只要通過適當的邏輯推演,都能從現存的法律體系中得出唯一正確的判決。蘭代爾形式主義統治了美國法律界長達半個世紀,成為美國法學史上影響深遠的正統思想。蘭代爾形式主義正統地位的獲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種邏輯的方法和形式迎合了每個人心中對于確定和安寧的渴望”。[4]P24蘭代爾形式主義作出的司法確定性的承諾帶給了人們安全與安定感,這種安定感對于任何社會都是有價值的,對于當時變動不居的美國社會更是彌足珍貴。
但是蘭代爾形式主義只是一種美好的愿景,它最終無法通過實踐的檢驗與理性的剝離。就像學者評價的那樣,蘭代爾形式主義“以回避現實的方式來回應現實”,追求無法實現的確定性,“在基因里就藏著隱患”,它根據規則裁剪案件事實,以“犧牲現實的多樣性來獲得理論的統一性”,必將造成法律僵化。[5]事實上,從法律形式主義產生的那刻起,對形式主義的懷疑情愫就暗流涌動——法律真是一門精準科學嗎?到二十世紀初,經歷了歷史法學、社會法學的沉淀與積累,通過霍姆斯的振臂一呼,反形式主義思潮開始取得受關注的地位。“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一個時代為人們感受到的需求、主流道德和政治理論、對公共政策的直覺——無論是公開宣布的還是下意識的,甚至是法官與其同胞們共有的偏見,在決定賴以治理人們的規則方面的作用都比三段論推理大得多。”[6]P1霍姆斯的經驗論推翻了“已成為美國法律內在生命的形式主義和空洞傳統主義的圍墻。”③二十世紀20-30年代,盧埃林、弗蘭克等現實主義法學家以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為智識來源,以霍姆斯的經驗論、預測論為理論基礎,舉起了法律現實主義的大旗,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法律現實主義運動,把反形式主義推向了高潮。
法律現實主義的核心命題是“規則懷疑論”。現實主義認為:其一,規則不能決定裁判結果,法律規則為大前提,案件事實為小前提,并不能推導出唯一確定的結論。盧埃林區分了“紙上規則”與“真實規則”,認為“紙上規則”對法官的行動無法提供充分的指引,也無法施加足夠的限制,解構了形式主義的“紙上規則決定裁判結果”的論斷。盧埃林認為“關鍵在于觀察法律官員做什么,他們如何處理糾紛或者其他任何事務,以及觀察他們的所作所為,從中尋找某種獨特的規律性——這種規律性使人們有可能對法律官員及其他官員今后的所作所為作出預測。”[7]P7他提出了“法律是官員處理糾紛的行為”這一現實主義的核心論斷。其二,規則并不是裁判的思維重心。盧埃林說,“對于多數思想家來說,規則就是法律的核心,在連貫有序的體系內編制規則是法律學者的事務,而依據規則的主張從一個規則中找出一種適用于處理手頭案件的簡單方法——這屬于法官和律師的事務。但是,在我看來,所有的這一切具有極為悲哀的誤導性。”[7]P6他主張關注“法律官員的行為”,關注行為中的“真實規則”。弗蘭克則主張將目光從法律規則轉向事實認定,認為法官的裁判是基于事實的直覺判斷,法官的思維是“預想在先,合理化在后”的結論先行的后果取向思維,而不是傳統的三段論思維。其三,“確定性”是法律形式主義編織和維護的現代法律神話。因為不確定性容易引起人類的恐懼,就像原始初民用神明裁判來戰勝恐懼一樣,現代人也不自覺地采用了現代法律神話——法院判決的基本組成部分是法律規則,法律規則是剛性明確的,法官是明智理性的,判決是確定的——來戰勝這種恐懼。現代法律神話是所有人都愿意相信的“高貴謊言”,法官出于對民主立法原則的維護自然而然地隱藏起了“法官造法”的舉動,普通人出于兒童的“戀父情結”也樂于相信司法裁判的確定性。“紙上規則”主要充當了使裁判結果“合法化”的手段,滿足了人們對“法律神話”的信仰。④對法律確定性的追求是在追求一種超過實際可能性的東西,從“法律確定性”的幻想中解脫出來是法律現實主義的第一步。
法律現實主義的另一命題是“事實懷疑論”。以弗蘭克為代表的事實懷疑論者認為,抽象的規則并不能保證司法正義的實現,案件的事實如何判斷和認定才是重要的。“事實懷疑論”具體懷疑什么呢?其一,案件事實是客觀確定的嗎?現實主義認為“事實即猜測”,當案件出現在法庭的時候,“事實”已經成為過去,法官不是案件的親歷者,與歷史學家一樣,他們雖然總是試圖去發現客觀真相,但是卻只能依賴缺乏可靠性保障的二、三、四手證據,而證據所證明的事實也不過是客觀真相中的幾個點,點與點的聯系還要通過合理的“想象”、通過“猜測的藝術”加以構建。案件事實不是客觀事實,而是法官認為它們是什么,傳統理論中的“真相大白原則”是不現實的。其二,法官是天使嗎?現實主義認為法官是凡人,他們有著人類通常的優缺點,法官的主觀性對裁判的影響至關重要,特定法官的特殊性格與偏見常常在他的裁判過程中起重要影響。
從法律現實主義思潮興起的那刻起,關于它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不管是支持者的支持還是批判者的批判,客觀上都成為體現現實主義深遠影響的一個棱面,成為對現實主義進行全面梳理、客觀評價的“凸透鏡”。綜合來看,學界對法律現實主義的評價,正像現實主義的主張一樣,具有時空性、流動性,隨著社會發展大體呈現出“肯定-否定-肯定”的認識軌跡。當法律形式主義阻礙法律與社會發展時,具有強烈批判意識的法律現實主義就像一股狂風驅散了僵化的傳統思想的陰霾,在這一時空下,人們更多感受到的是實用主義的清新之風、現實之魅,現實主義因社會的接納與認可最終成為了一種思潮。法律現實主義為抨擊形式主義而生,當形式主義的大廈轟然倒塌后,現實主義繼之成為新的審視對象,塵埃落定再回眸之時,人們已經少了往日的心潮澎湃,多了些許理智甚至挑剔的審視,尤其二戰以后,對極權主義的警惕使得現實主義成為了許多學者批判的對象,稱其為學術界的狂風驟雨、任性且淺薄。時間前行至今,經過了歲月沉淀與學術洗禮后,人們繼而發現,現實主義所謂的“批判有余而構建不足”“極端”“淺薄”等缺陷很大程度上是時代賦予它的,透過極端、淺薄的面紗,我們會發現彌足珍貴的批判精神及對司法的深度思考,會看到面向現實引領未來的創新與深刻。整體而言,法律現實主義是顯形的毀滅者,隱形的創造者,激進與保守、淺薄與深刻并存,在法律思想的起承轉合中起到了重要的紐帶作用。
二、法律現實主義的破壞與構建
在法律思想史中,去發現法律現實主義所反對的東西遠比去描述它所追求的東西來的容易與清晰,法律現實主義具有濃郁的“破壞”氣質與“批判”色彩。規則懷疑論、事實懷疑論是它的基本命題,而對于“破”舊后的“立”新,法律現實主義則沒有那么系統與明確。批評者認為盧埃林對“真實規則”的討論僅僅是對“紙上規則”與“真實規則”的區分,并沒有抽象出關于“真實規則”的理論模型,其提出的裁判思維的宏大風格也是模糊的;弗蘭克提出了司法裁判是法官基于事實的直覺判斷后,就沒有了下文;弗蘭克法律不確定性理論的核心是懷疑與批判,但他并沒有在此基礎上提出科學完整的建設性理論。[8]“現實主義者沒有給我們任何的可以安放在被他們摧毀的地方的東西……他們技藝嫻熟地帶領我們進入了這片沼澤,他們的錯誤在于確信,他們知道走出沼澤的路,但是他們不知道,至少我們現在還在那里……法律現實主義是一個破壞性的運動,我們處于一個不能被重建的法理學的殘骸中間。”[9]薩默斯也指出,“工具主義者最重要的貢獻可能就是對形式主義法律方法的批判。但有意思的是,具有科學和技術頭腦的工具主義者并沒有為基本的創設和實施法律工作發展出有體系的決策理論,這仍然是項未完成的重要工作。”[10]P233
法律現實主義到底有沒有構建性貢獻呢?客觀來講,現實主義的確以批判為己任,但“破”與“立”往往是融合的,“破”的過程中往往呈現著“立”的影像。而且現實主義者在后期也或被動或主動地著手了替代性理論的構建,進行了嘗試性的探索。盧埃林在“規則懷疑論”之后提出了法律是“官員處理糾紛的行為”的論斷。在1951年《荊棘叢》修訂版的后記中,盧埃林提及了“真實規則”的理論模型:法院所持續追求的這種規則是滿足了普通法的傳統——宏大風格需求的規則。每一項規則都有一個在表面上能夠輕易獲取的理由,規則的理由指引規則的方向,理由缺失則規則無效,每一個支配著規則的理由指導甚至控制著這條規則的適用。[7]P241盧埃林在后期著作《普通法傳統》中論述了裁判的宏大風格與裁判的可估量性理論。弗蘭克在反“法律的確定性”之后提出了“結果的可估量性”理論(另一種意義上的確定性)。弗蘭克在《初審法院》中構建了一種后果取向裁判模式,并提出了陪審制度改革、判例制度改革、法學教學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方案。這些勉強可以看作是現實主義的替代性理論,這些理論是在工具主義指引下構建的,把法作為實現社會目標的工具,核心強調法官行為、法官經驗及法官的主觀能動性。但同時這些理論又是粗略的有缺憾的:一是現實主義的理論構建大都是個人的、零散的,現實主義群體之間缺少共識;二是現實主義的理論構建大都著眼于司法實踐與具體司法技能,是形而下的,并非對“法的本體”“法與道德的關系”等法學基本問題的構建;三是現實主義的理論構建大都“本質上是一種態度和起點,而不是一種結論和意識形態,”[11]其中的一些主張并沒有給予充分的論證,也沒有給予充分的闡述。現實主義成功地破除了形式主義所構建的封閉的規則系統,成功地把政策分析、利益平衡、目的性解釋引入司法,但如何把這些模糊立場變成規范性論證方法,他們卻鮮有論及。現實主義主張“法律是實現目標的工具”,但法律所要服務的社會目標是什么?現實主義雖然從實用主義的立場上進行了論述,但并沒有指出明確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目標,這對法律工具論來講也是不完整的。
法律現實主義的目標是要構建一種更具說服力的替代理論,但此目標是否實現,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實現,則見仁見智。整體而言,現實主義精于批判而疏于建構,在理論建構方面力不從心、遺憾甚多、未能周全,沒有構建一種完全取代形式主義的新范式。但是,理論建構是浩大工程,不是任何一個學派在某一個歷史時期就能完成,現實主義理論建構中出于忽視、出于失誤的空白是可以逐步豐富的。事實上,法律思想史的發展大致延續了這一軌跡,后來的批判法學、經濟分析法學直至新法律現實主義都深受法律現實主義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實現著對法律現實主義的豐富與完善。法律現實主義思想在學界的一再追問、不斷發展中得以傳承,觀念普及日趨廣泛,理論內涵日趨豐富,法律現實主義的故事愈釀愈醇。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拘泥于法律規則而開始關注法律運作的實際動態。當然,這種完善本身也并不完善,法律現實主義在今天依然需要面對諸多核心問題:法律在多大程度上是實現社會目標的工具?法律的目標體系中包含著怎樣的復雜性?“紙上規則”與“真實規則”如何相互影響?在司法實踐中,擁有現實主義精神的法官如何具體適用法律?如何判斷法的實效?這些問題在今天仍有理論探討的必要與空間。法律現實主義的理論大廈遠未完工,未竟事業可謂任重而道遠。
三、法律現實主義的激進與保守
關于法律現實主義的核心理論——規則懷疑論,批評者認為法律現實主義否定了法律規則,激進且淺薄。現實主義者澄清道,法律現實主義并不是否定法律規則的價值,只是反對從法律規則出發的法學研究,反對從法律規則出發的裁判思維,反對法律規則的中心地位。盧埃林辯護稱,“倡導關注法官行為,并不是說法律規則對法官行為沒有影響,也并不否認法律規則有時會對法官行為做出非常準確的描述……只是它需要進行客觀的檢驗: 規則與裁判實踐何時符合,何時偏離? 多少符合,多少偏離? 如何發生符合,如何形成偏離?從規則出發無法進行這樣的檢驗,只有觀察法官行為,才能真正把握法律運作的復雜現實。”[12]弗蘭克說:“否認母牛是由牧草構成的,并沒有否認牧草的實在性或母牛吃了牧草。所以,當我們說規則不是構成判決的唯一因素時,這并不等于說規則不存在。水不是氫,玉米穗不是耙犁,獨唱不是由聲帶構成的,一趟旅行不是旅客列車。然而,氫是水的一種構成元素,耙犁有助于玉米的生長,聲帶是獨唱必不可少的條件,旅行列車可能是這趟旅行的交通工具,而且,氫、耙犁、聲帶、旅客列車都是實在的。法律規則也沒什么不同。”[13]P196關于法律規則的作用,盧埃林有一段精彩描述:“當我把關注點轉移到法官行為時,也強烈地感覺到拋棄對規則、概念的強調同樣是不明智的……新觀念對舊觀點的反叛,只能表明舊有觀點的不充分,并不意味著舊有觀點沒有堅固基礎。如果我們能夠檢視舊觀點的基礎并將這種檢視帶入新觀念中,將十分有助于減少極左極右的鐘擺式發展。”[14]P37“這種反對非此即彼、贊成兼而有之的觀點體現了明智的適當態度”,弗蘭克進一步澄清道“盧埃林經常正式地通知追隨者們,要保護、修復而不是破壞那些古老的關于法律思想的態度和傳統的法律思維工具。”⑤上述論述表明了現實主義者的理性立場而非激進立場,也進一步表明了他們的規則觀:并不否定法律規則的作用,最多是否定了規則的核心地位。而大多數學者認為,否定了規則的核心地位就等于否定了法律、否定了法治,而且現實主義未對司法行為的制約給予關注,它依然是激進的。
批評者還認為,規則懷疑論過分強調了法律的不確定性,使法治走向了虛無。人類在諸多社會調控手段中核心選擇了法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法律具有確定性,如果失卻了確定性,法律的權威就蕩然無存,法治也就無從談起。[8]批評者指出,現實主義試圖使人們從確定性的幻想中解放出來,事實上人類也確實走出了現實主義的第一步,但是“法律必須被信仰”,世俗化對于法律來說不見得是什么好事情,它使得人們對法律的遵守由信仰轉為功利,司法審判由對真理的宣告變成了解決問題的試驗,這樣的法律是長短腿的,必將走不遠。現實主義針鋒相對,認為對司法真相刻意隱瞞的“高貴的謊言”是無用的、非民主的,而且司法的自我欺騙助長了不負責任的司法。“我不認為,在公布那些措辭冷靜的判決意見時掩蓋其偏見的人,會借此使這些偏見的影響變得無蹤跡。”[13]P171法院是屬于公民的,公民有權知道司法審判中存在的缺陷,有權知道哪些缺陷是固有的,哪些缺陷是可以消除的以及如何消除。只有正視問題、坦承問題才能解決問題,如果一味沉浸在法律的謊言里,法律的缺陷就得不到重視,法律的完善就無從談起。弗蘭克反復要求人們從“恰如其分的謊言”中清醒過來,丟掉幻想,去適應現實世界,這才是“現代心智”。客觀上講,過于“神話”與過于“世俗”都不是法律適當的方式,過分贊譽與過分詆毀都是有害的,現實主義與批評者的上述爭論似乎很難做出擇一舍一的選擇,法治的發展一直在致力于謀求兩者的平衡,試圖在兩者之間尋求最大的交換值。
事實懷疑論被許多學者視為“奇談怪論”。批評者認為,事實懷疑論過分夸大了法官個性對裁判的影響。批評者對弗蘭克的“法官是人嗎?”的提問,提出了三項反問:“法官是動物嗎?”“法官是普通人嗎?”“法官只是個別的人,而不是一類人嗎?”批評者認為,如此強調法官個性,是將法官認定事實的過程等同于動物性的刺激反應了;如此強調法官個性,是將法官完全等同于普通人了,忽視了法官有別于外行人的價值觀念、知識結構、思維方式與實踐經驗;如此強調法官個性,是僅僅關注了法官作為個體的獨特性,而忽視了法官是法律職業共同體中的一員,忽略了法官的共性。弗蘭克對此進一步反駁說:法官當然不是動物,不是僅憑感性進行裁判,但他的理性更多在“合理化”過程中發揮作用;法官當然不是普通人,但他的法律思維只能與日常經驗和常識一道形成判斷;法官當然是職業共同體中的一員,但他改變不了事實乃是被建構的這一客觀規律。⑥弗蘭克與批評者的分歧在于一方強調法官是普通人,另一方則強調法官是職業人;一方強調法官個性,另一方則強調法官共性。而我們的現實情境一定是兩者的統一,因此,上述兩種觀點都算不上完滿但也都不能歸結為謬誤。實際上,廣受詬病的事實懷疑論使法學研究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使法學研究跳出了在法律規則的圈圈里打轉的現狀,把研究聚焦于司法實踐,聚焦于案件事實,聚焦于規范與事實的復雜互動。它提出的法官個性問題客觀上也有利于推動法治的完善與發展。但是,事實懷疑論確有極端之實,它似乎走向了主觀意識決定論,司法裁判必然會滲透法官的意志,但法治就是試圖盡可能減少這種影響,法官個性必然會對判決產生影響,但個性并非任性與任意,更不起決定性影響。
“叛逆者”往往需要一點點矯枉過正,我們不妨將“激進”作為法律現實主義的理論魅力與另類理性。梳理現實主義的論斷,我們會發現現實主義沒有傳說中的那么極端,尤其是其代表人物盧埃林,與其說他是一個“懷疑論者”,不如說他是一個“偽裝在懷疑論者外衣下的傳統主義者”,[15]“他的現實主義很明顯具有中間道路的性質”。[16]可能由于現實主義的理論匆忙與激進文風,由于現實主義沒有提出系統理論來調和形式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矛盾,所以現實主義在表象上似乎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顯得過于“經驗”與“社會”了。雖然主觀上無意識,但現實主義者客觀上使用了與現實主義藝術家一樣的表現手法。現實主義藝術家往往把丑惡的東西用加倍的丑惡來表現,而法律現實主義則把司法中的非理性、非邏輯的部分強調到了“無可附加”的地位。可能正是這種“極端”使得現實主義思想成為一種高效清醒劑,把美國社會從法律夢境中喚醒了起來。可能正是這種“極端”招致了諸多追捧與批判,在追捧與批判聲中,“法律是一門精確科學”的觀念被人們拋擲腦后,現實主義反形式主義的目的達成,一度僵化的法律思想開啟了新的航道。
同時,透過法律現實主義“極端”“激進”的面紗,我們也能發現現實主義對法律、法治的一片溫情。弗蘭克是現實主義的激進代表,但弗蘭克表示,是霍姆斯大法官的榜樣使他對缺乏現實基礎、華而不實的法律觀念的批判信心百倍。霍姆斯說,“我相信沒有人會因為我對法律的批評是如此的自由而認為我是帶著對法律的蔑視在說話,我對法律,特別是我們的法律體系,當作是人類精神最偉大的成就加以崇敬……但是一個人也可以批評他所崇敬的東西。法律是我所獻身的事業,而且除了獻身于它,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致力于使他更為完善。”[13]P3完滿的司法是人類所不及的,但它不能成為放棄對司法進行實質性改革的借口,“司法過程的許多缺陷是能夠被消除的,司法行為的實質性提高是可能的”,承認缺陷并對其加以公開有助于這些缺陷被明智地處理,這也是完善司法過程的前提。[13]P2“我揭示法律神話背后的司法機關的實際運作情況是為了喚起建設性的懷疑主義,激發大家關注司法機關的活動,司法機關的活動之所以沒有像它們能夠的那樣充分地發揮作用,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很少被公開討論。”[13]P2弗蘭克在《初審法院》中提出了一系列司法改革建議,這是他對法律的溫情。我們有理由相信,不管是以盧埃林為代表的法律現實主義溫和派還是以弗蘭克為代表的激進派,大家均秉持著弗蘭克式的動機。現實主義至少提醒了我們,應認真地研究審判過程,研究法律的適用,研究司法心理學,建立有效的法官裁判約束機制以實現司法公正。
四、法律現實主義的淺薄與深刻
批評者認為法律現實主義繞過法律規則把法律界定為“官員處理糾紛的行為”,這一論斷扭曲了普通人的法律常識,冒犯了法律職業者的專業認知,淺薄且荒謬。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書中批評道,“規則懷疑論”的荒謬在于它繞開了白紙黑字的規則,錯誤地定義了法律。哈特用“兩個推論”“解構”了這一“定義”,并幾乎全面“解構”了法律現實主義。⑦還有批評者認為,盧埃林把法律的關注點放在了司法行為上,放在上訴審階段,把法律的功能限定在解決爭端的范圍內,極少涉及其他法律領域,這樣得出的定義豈能涵蓋“法律”這一概念?在《荊棘叢》1951年修訂版的致謝中,盧埃林承認“法律是官員處理糾紛的行為”這個短句在沒有被充分的闡釋、拓展與修正之前,確實是不恰當的。但他同時申辯道“在那些批評者中,沒有人——準確地講,沒有任何人——在圍攻這個短句時能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他們曾經真正讀過了《荊棘叢》的其余部分”,批評者們斷章取義地理解了這個短句,掀起一場“茶壺里的風暴”。[7]P6-9盧埃林稱自己從未“定義”過法律,更沒有把法律定義成“官員處理糾紛的行為”。他認為“法律”這一概念包含了太多的內容,尋找這些內容的共同點都很困難,何況加以定義了……每個定義都劃定一片領域,有些內容包含在內,有些內容排除其外,任何排除都是專斷的,不準備從法律事務中排除任何東西……既然定義的缺陷根源于試圖描述事物的“邊際”,那么能夠取而代之的應該是找尋事物的“中心”,所有法律事務都有一個繞不開的中心——“官員處理糾紛的行為”。[12]P431-465弗蘭克也聲稱,“何為法律? 完整的定義不可能存在,甚至一個有效的定義也將耗盡讀者的耐心。”[17]P47他甚至聲稱要避免使用“法律”這個詞。取代“法律”的將是“法院實際上所做的;法院應該做的;法院是否做了他們應當做的;法院是否應當做他們應該做的。”[13]P3法律現實主義的研究者布萊恩·萊特說:“現實主義者們都不是哲學家,更不是分析哲學家,他們在法律的概念方面沒有明晰的東西。”[18]英國法學家推寧說,法律現實主義者幾乎不關注“法律是什么”等傳統法理學的主要問題。[19]法律現實主義的支持者也表示,現實主義者不會如此幼稚,“法律即規則”的常識不是他們要推翻的,任何一種反叛都不是脫韁的野馬,都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間接地強調限度與規制,沒有人能忽視這一點。貌似淺薄的論斷可能蘊含著深刻的洞見,毋容置疑,法律現實主義強調政治因素、法官行為在判決中的作用,引領了人們去關注司法行為及司法活力,去研究司法制度及其運作環境,增加了法學研究的實際分量。法律現實主義揭示了司法既要對規則進行入乎其內的真誠解讀,又要讓規則滲透進現實的聲音,極大地加深了社會對法律制度的理解,迅速推動了“自動售貨機理論”走向了式微。
批評者還認為現實主義把法官的裁判認定為是基于事實的“直覺判斷”,輕率地把理性與合法性丟到了一邊,是一種淺薄。現實主義辯護稱,“直覺判斷”絕非是一種純粹的感性,法官在案件審理中的“直覺”包含了他們在專業學習及職業生涯中積累起來的智識努力與職業素養,它不同于普通人的日常直覺,“就好像武林高手無招勝有招的絕頂修為不同于莊稼漢胡輪草叉的瞎把式,作曲家的神來之筆不同于音盲對歌曲的隨意篡改一樣。”[20]在“直覺判斷”中,法律規則不是無用的而是內化為法官的職業經驗并對判斷過程進行了限制。更重要的是,法官“直覺判斷”后的規范性論證過程會進一步對“直覺”加以驗證與修正,使“直覺判斷”獲得理性與合法性的支持。現實主義認為司法過程是一個理性與非理性交織的過程。弗蘭克因為強調判決過程的“非理性”因素而被指責為“反理性”,他辯護稱,事實恰恰相反,理性的范圍不會因虛假的偽裝而得到擴展,而現在虛偽的理性已經超過了理性的實際范圍。虛偽的理性可能是“反理性”的最佳偽裝。他引用了帕斯卡爾的格言:“兩個極端,一端是排除理性,一端是只承認理性。”事實上,某些理性和某些非理性都是人性自然的和令人欣慰的組成部分,而且只有承認了非理性才能正確地處理非理性并盡可能地減少非理性,而逃避非理性,對那些可能帶來問題的丑惡事物保持某種無知狀態的愿望實乃是一種“近視”策略。⑧現實主義的上述辯護還是很有說服力的。當然,至于現實主義主張的類似法官早餐吃了什么都會影響裁判等觀點,的確是過于強調主觀的作用,過于片面了,法官不可能無節制地根據自己的主觀意志來裁判案件。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它并非毫無道理,放眼整個司法領域,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一定不是主要的更不是決定性的,但如果放眼于某一具體個案,某一具體環節答案就不那么確定了。
以今天的視角來看,法律現實主義的“極端”與“淺薄”是時代賦予它的,“理性”與“深刻”也是放在當時的背景下對它的評價。現實主義打破了形式主義的銅墻鐵壁,它提出了“法律是官員處理糾紛的行為”,“法官的裁判是基于事實的直覺判斷”等現實主義論斷。在“破”與“立”的過程中,它的激進與極端是顯性的,在表面上走向了形式主義的反面,形成了另一種“形式主義”。激進與極端之下必然附帶著淺薄,也必然招致更激烈的批判,正是在這種批判聲中,現實主義從鼎盛迅速走向了衰落。但是,離經叛道的背后蘊含著對法律、司法的深度思考,現實視角與世俗眼光甚至主觀立場亦屬于一種理性,它提醒法官“永遠不要讓法律忘記觸摸普通人的需要,”⑨提醒人們“司法永遠不是自動售貨機”。時至今日,在法律現實主義的影響下,人們對法律形式主義的態度日趨理性,法律現實主義的許多論題也被人們所熟知甚至成為了陳詞濫調,法律與現實的互動成為受歡迎的研究課題。在法律思想的長河中,法律現實主義完成了一種思想的重要轉折。如果說,法律現實主義“沒有栽下大樹,但至少清除了許多灌木,它標志了一種態度,一種導向,同時也標志著一種方向的改變。這就是它所提供的,并且,也許還相當多”。[21]P464麥考利說“在我們看來,那個年代學術界的一些事情充其量像是一些奇聞軼事。然而無論如何,當回顧法律現實主義的歷史時,必須意識到,我們的曾祖父輩和祖父輩所懂得的東西實際上比我們歸功于他們的更多。”[22]弗里德曼也認為“在一個重要的意義上,法律現實主義在終結時幾乎打敗了其所有的敵人。”[23]P493
五、法律現實主義在轉型中國的司法運用
我國司法整體上是法律形式主義的,裁判必須嚴格依照“法律”作出,運用嚴謹的演繹推理得出結論。它在制度層面的典型體現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制要求。雖然近些年來我們開始強調“公正司法”等法治新要求,但司法的基本面向并未改變。出于對司法環境及職業安全的考量,法官在案件審理中習慣于也樂于作法條的“服從者”,而不愿做法條的“創造者”,即使對“據法裁判”的結果感到不適,服從法律也是大概率選擇,這種選擇既省卻了規則重構成本,又獲得了“法律”保障。我國學界的基本傾向也是法律形式主義的,賀衛方教授的觀點具有代表意義:“依據我們現行體制,法官果真能夠成為法律條文的奴隸,那豈非國之大幸……法官嚴格適用法律作出判決,即便這結果與民眾的情感相背離,引起輿論不滿,該指責也不應該是法官,而是立法者。我們不允許法官僅僅依賴于自己對立法是否公平的判斷而決定是否適用它們。相反,在司法中,法官必須抑制自己的情感,泥滅自己的個性,對了,就像自動售貨機那樣。”[24]
與此同時,我國社會對法律現實主義有著強烈需求,這種需求根源于社會轉型、法律移植、實質正義的追求等社會因素。第一,社會變革期的新舊躍遷。規則治理是建立在社會關系同質預設基礎上的。如果社會處于穩定期,今天像極了昨天,抽象涵蓋了具體,規則與社會相適應,形式主義司法必然是最法治、最高效、最明智的選擇。如果社會處在變革期,新與舊的轉折與躍遷使得法律正義與社會正義張力凸顯,異質化案件頻發。面對異質化案件,司法需要對急劇變化了的因素予以考量,需要在法律與社會之間尋求互動,法律現實主義往往是必須、必要的。我國正在經歷一場全面而深刻的社會轉型,結構性矛盾復雜多變,在許多新型案件面前,形式主義司法不僅表現出司法能力不足,而且在化解矛盾的過程中還易引發新的矛盾,這正是我國倡導“能動司法”的重要原因。第二,法律移植的本土化調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立法領域走的是“速度型”立法之路,法律體系在“法制建設”目標下得到迅速發展與完善,在短時間內經歷了由不全面到較全面再到相對完善的過程。在立法高速路上,法律移植為我國法律體系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促進了我國法治的迅速發展。但是,移植的法律必然存在與本土文化的融合問題,而這種融合是一個系統工程,移植的法律與本土社會的民情民意是否兼容、是否沖突、如何調和等問題不僅在法律移植之前、之中需要考量,在法律移植之后,在司法過程中仍然需要作進一步的調適。“借”的東西只有在“鑒”的基礎上反復調試才能成為真正適合自己的東西,移植的法律只有通過多次實踐才能實現制度的自主性。在我國傳統社會的較遠處,在國家法與民間法沖突頻繁的司法領域,移植法律的內涵常常被司法者“通過各種非正式的司法運作方式重新建構,以滿足本土的政治、社會和組織秩序的多元的合法性要求。”[25]這種重構并非可有可無,而是十分必要。第三,實質正義的追求。我國有“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在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社會正義與法律正義之間,我國公眾始終都偏向于前者。雖然近些年來“程序乃實體之母”等理念引入我國,但由于傳統的根深蒂固,理念難以在短時期內發生質的改變。而且,在任何時空下,體現美好與幸福的實質正義將永遠是人們欣然向往的目標。在傳統文化的影響及社會現實的客觀需求下,我國司法要求法官在審理案件時除了“定分”還要“止爭”,要“有效解決糾紛”,案件審理追求“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讓人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司法服務于和諧社會的職責使得司法裁判不得不對公共政策給予考量,對實質正義的追求亦是對法律現實主義的需求。概言之,轉型中國對法律現實主義有著特殊的需求,法律現實主義對轉型中國有著獨特的價值。
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法律現實主義是有跡可循的,早些年許霆案的重審判決,瀘州繼承案的一、二審判決,近年的劉大蔚網購仿真槍案的再審決定、天津趙春華案的二審判決,這些在社會上曾經引起廣泛討論的公共案件的最終結果幾乎都是現實主義的。當然,它們最多只是一種“現實主義的面向”而非一種真正的法律現實主義。由于上述矛盾——司法的形式主義要求與社會的現實主義需求的矛盾——的存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的“法律現實主義”判決呈現以下樣態:其一,被動性。“法律現實主義”的判決大多是在二審、重審中出現的,大多是在民意的裹挾下被動性作出的。這些案件的一審判決往往受到人們廣泛的質疑甚至批判(理由不是因為判決沒有嚴格適用法律,而是因為判決結果與人們的認知相差太遠),在質疑與批判聲中,一般案件演變為公共案件,在民意的支持或者圍攻下,法院在二審或重審中做出現實主義的判決。許霆案的重審判決、天津趙春華案的二審判決是其典型代表。其二,隱蔽性。這種“法律現實主義”的裁判大都是在法律形式主義框架下隱蔽、含蓄存在的,它被或巧妙或生硬地裝進了法律形式主義的袋子里,以“嚴謹”的三段論形式呈現,其動機是實現“依法裁判”,瀘州繼承案是其典型代表。⑩這種被動性與隱蔽性隱含著副作用。被動性有對民意“被動屈從”的意味,判決雖然實現了公眾要求的正義,卻因一審、二審、重審結果的“反復無常”而不利于法律權威的樹立,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建立。隱蔽性以維護法律權威,維護法治為動機,但它的說理往往牽強機械,往往“有懈可擊”,致使案件長期被學界爭論。當法律形式主義綁架了法官思維,現實主義判決匹配上形式主義說理時,機械甚至牽強是必然的。此外,隱蔽性也不利于判決的說理在司法實踐中發揮指導作用,不利于同案同判,不利于維護法律確定性。簡言之,被動與隱蔽的“法律現實主義”既不利于對現實主義的解讀,也不利于對形式主義的維護。
被動與隱蔽體現了我國司法對法律現實主義“需要+排斥”的矛盾態度。追本溯源,我國學界和實務界對法律現實主義保持戒備與排斥的原因,應該與擔心非法律性因素搶占法律地盤、法律現實主義沒有貢獻可操作的司法規則、法律現實主義存在濫用風險等因素有關。理論的排斥改變不了社會的需求,深入研究、規范適用、有效制約應該是對法律現實主義的必要態度。法律不是純粹科學,“而是法律人在法治社會中必須捍衛的治理術”。[20]這種治理術既不單一,也不是那么清晰明確。法律現實主義不是毒蛇猛獸,更不是反法治的,它具有合法性基礎 ,它所進行的權衡“也是一種論證形式,既需要有內部證成的結構,也需要有外部證成的實質論據。”[26]法律現實主義與法律形式主義一樣,都是司法應有的色彩,他們優勢互補,共同構建起多元的司法樣態。整體來講,規則是司法安身立命之本,即使在轉型社會,一般案件也應該遵循形式主義的思維方式,而且大多數案件依賴規則和邏輯能夠找到理想的答案,在合法性中實現合理性。但是,我們也必須關照到社會的急劇變遷,關照到那些疑難、復雜、新型的案件,關照到規則和邏輯之外的廣闊空間。在各類疑難案件面前,法官應該從法律形式主義那里大膽地掙脫出來,用真正的法律現實主義思維去權衡“法與社會”,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在疑難案件占比高的當下(社會轉型、法律移植、實質正義追求等原因導致),我們的司法制度除了積極倡導之外,應該秉持一種更積極、更開放的態度,通過可操作的制度設計為法官審理疑難案件提供規范、有效的現實主義審判機制,為法律現實主義的司法運用提供具體指導。
注釋:
① 在法律思想史上,“法律現實主義”更多被表述為“現實主義法學”,本文主要從方法論的角度、在司法領域探討之,為與法律形式主義相對應,故使用“法律現實主義”這一表述。法律現實主義分為兩支:美國法律現實主義與斯堪的納維亞法律現實主義,兩者既有共性又有差異,相較而言,美國法律現實主義波及面更廣,影響更深遠,本文所稱法律現實主義僅指美國法律現實主義。美國法律現實主義所指的學術范圍,法學界的界定并不明朗更不統一,有廣義說與狹義說。尊重學界的普遍觀點,并從文章主旨出發,本文對“法律現實主義”的學術范圍做“中心明確、邊緣模糊”的界定:法律現實主義是一種以實用主義哲學為基礎的法學思潮,是與法律形式主義相對立的一種司法方法論,盧埃林、弗蘭克是其主要代表人物,同時本文注重法律現實主義與霍姆斯實用主義法學、龐德社會學法學的共性與相承性。
② 參見柯嵐:《法律方法中的形式主義與反形式主義》,載《法律科學》2007年第2期。
③ See Biddle,Mr.Justice Holmes 61(1986 Ed.);轉引自[美]伯納德·施瓦茨:《美國最高法院史》,畢洪海、柯翀、石明磊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④ See Jerome Frank,Law and the Modern Mind,Gloucester,Mass: Peter Smith,1970,p14-23,29;轉引自陸宇峰:《“規則懷疑論”究竟懷疑什么?》,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
⑤ See Jerome Frank,Book Review,40Yale Law Journal,1120 (1931).(reviewing Karl Llewellyn,The Bramble Bush(1930));轉引自劉劍:《“規則懷疑論”者的規則觀——評卡爾·盧埃林的<荊棘叢>》,載《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第2期。
⑥ See Jerome Frank,Are Judge Huma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931,(80),pp.18-19,pp.28-29;轉引自陸宇峰:《“事實懷疑論”的淺薄與深刻——弗蘭克法律現實主義再解讀》,載《江漢論壇》2014年第10期。
⑦ 哈特的兩個推論是:其一,如果“法律不過是官員的行動”,那么不僅不能說:按照法律,某法院的某判決是錯誤的;而且連“上級法院根據法律否決下級法院的判決”這樣的說法也是胡言亂語。其二,如果“法律不過是官員的行動”,那么當一名法官找尋可適用于某一個案的法律時,他只能不合情理地自問“我將會如何判決?”。
⑧ 當一個近視的人第一次戴上眼鏡時,他通常會抱怨:“我難以忍受這副眼鏡。它使我所有的朋友看起來是那么丑陋,他們的臉上都有斑點。而所有的房子又是如此的臟亂和陳舊。我不喜歡這副眼鏡,我也不想看清所有的細節。”參見[美]杰羅姆·弗蘭克:《初審法院——美國司法中的神話與現實》,趙承壽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71頁。
⑨ 參見武宏志:《論霍姆斯的“邏輯”和“經驗”》,載《政法論叢》 2016年第6期。
⑩ 瀘州繼承案一、二審法院均依據《民法通則》第七條“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排除了《繼承法》在本案中的適用,認為遺囑無效。表面看,法院的判決是法律形式主義的,完全是基于法律而做出的。細致分析,本案的理由有待于進一步的追問,本案中還有一些能推出相反結論的理由。本案的審理法院——納溪區人民法院副院長劉波說:“如果我們按照《繼承法》的規定,支持了原告張學英的訴訟主張,那么也就滋長了‘第三者’、‘包二奶’等不良社會風氣,而違背了法律要體現公平、公正的精神。”(參見“社會公德”首成判案依據,“第三者”為何不能繼承遺產,北方網,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1/11/02/000181618.shtmll,2018-8-2)其實,這才是本案判決的真正理由。因為這一理由不是一個法律的理由,所以法院沒有公開聲明它,法院的判決找到了另一個“法律上”的理由——《民法通則》第七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