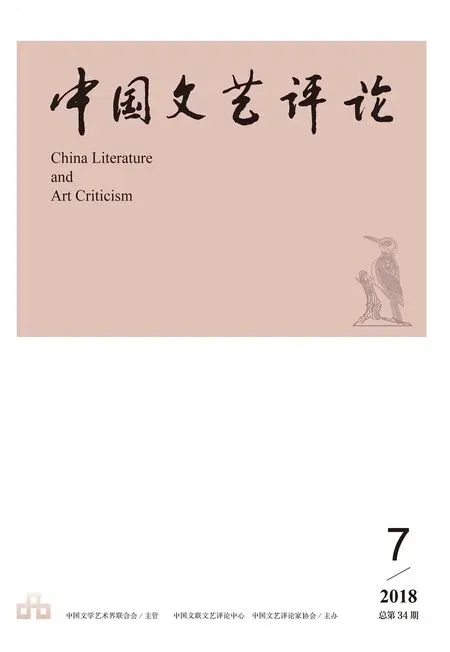論中日當代文學作品對“記憶”的藝術(shù)表達
2018-11-12 19:24:50張文穎
中國文藝評論
2018年7期
張文穎
一
自從有了文學,文學與記憶便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既是人類記憶的產(chǎn)物,也是人類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洪治綱曾說:“寫作作為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特殊形式,永遠也無法剝離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的雙重制約。”中日近現(xiàn)代作家們集體表現(xiàn)出關(guān)注記憶的傾向就是一個明證。夏目漱石在作品《心》中借主人公“先生”留下了這樣一句話,現(xiàn)在品味起來仍覺得十分沉重。「記憶してください、私はこのように生きてきたのです」(請記住,我是這樣活過來的)。《心》是一部關(guān)于記憶的作品,記憶當中有美好的記憶,也有不敢觸碰的記憶,不敢觸碰的記憶就像一枚定時炸彈時刻發(fā)出危險的信號。主人公“先生”就是被記憶壓垮了,還好他有敢于說出讓他萬分痛苦的記憶的勇氣,以負責任的態(tài)度走完自己的一生。魯迅作品《故鄉(xiāng)》里讓我們印象最深的是主人公對兒時的玩伴閏土的記憶,讓我們感受到了記憶與現(xiàn)實的殘酷。魯迅作品中的經(jīng)典人物都值得我們?nèi)ビ洃洠斞杆茉爝@些人物就是希望他們永遠被記住,借此來拯救中國人的靈魂。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更是以記憶為核心,通過邊緣記憶來對抗中心記憶;莫言的作品幾乎都是對于過去記憶的復雜呈現(xiàn),《紅高粱》是對祖先的追憶,也是對當下不爭氣的自我的追認。《豐乳肥臀》是對母親波瀾萬丈的人生的追憶,同時也是對永遠無法斷奶的中國人的深刻剖析。村上春樹的文學從處女作《且聽風吟》開始基本上都是帶著淡淡的感傷和自我調(diào)侃來講述記憶,近年來其作品中關(guān)注歷史記憶的文學作品越來越多。……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小哥白尼(神奇星球)(2020年7期)2021-01-18 05:07:16
學苑創(chuàng)造·A版(2020年10期)2020-11-06 05:21:26
娃娃樂園·綜合智能(2019年7期)2019-08-26 09:38:48
作文周刊·小學一年級版(2016年27期)2017-06-03 23:21:17
快樂語文(2016年15期)2016-11-07 09:46:39
中國現(xiàn)當代社會文化訪談錄(2016年0期)2016-09-26 08:46:32
小學生導刊(低年級)(2016年8期)2016-09-24 07:43:42
絲綢之路(2016年9期)2016-05-14 14:36:33
新湘評論·下半月(2016年4期)2016-05-05 22:12:41
新湘評論·下半月(2016年4期)2016-05-05 22:1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