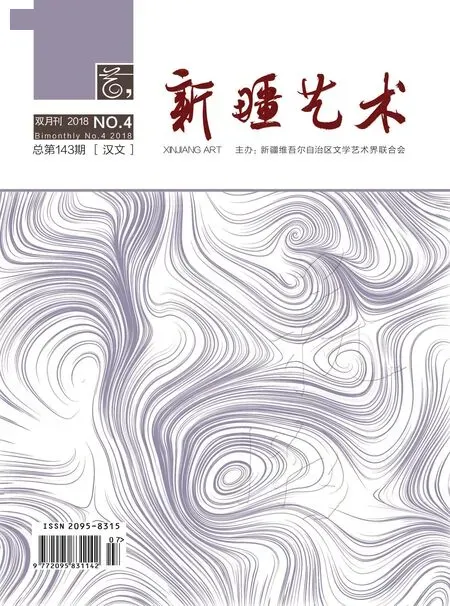走近詩(shī)人雷霆
□ 王翠屏

詩(shī)人雷霆
一
夏日的午后,一場(chǎng)雨驟然而至。
走進(jìn)雷霆家,迎面85歲的老者正是兵團(tuán)著名作家、當(dāng)代有影響的西部詩(shī)人雷霆。房間光線有些暗,沙發(fā)旁的茶幾上摞著十幾本已經(jīng)翻舊而發(fā)黃的相冊(cè)。老者身材頎長(zhǎng),濃眉大眼,銀發(fā)稀疏,背已彎駝,臉上有一絲歲月沉積的青灰暗淡與孤傲,開口間,卻有溫潤(rùn)的火花從眼神中掠過(guò),思維清晰、表達(dá)準(zhǔn)確,時(shí)而談興甚濃,時(shí)而又靜默如鐘,伴隨著生動(dòng)的手勢(shì),蒼白修長(zhǎng)的手指顯得格外醒目。
“你上午來(lái)電要約個(gè)時(shí)間采訪我,下午就來(lái)了,我心里一有事就會(huì)失眠,事了了,我才可以睡得好些。”他喃喃道。聽了他的話,我很慶幸自己的決定。我是第一次見到他,我急需他的照片和生活藝術(shù)簡(jiǎn)歷。兵團(tuán)老作家在兵團(tuán)文藝發(fā)展中功不可沒(méi),鑒于他們大多年逾古稀,我們一定要趕在他們有生之年,記錄下他們生活和藝術(shù)的足跡,傾聽他們的心聲,給老藝術(shù)家們一個(gè)安慰……也給歷史一個(gè)交待!
雷霆老師步履艱難地去取他多年來(lái)收集整理的作品剪報(bào),厚厚的三大本。據(jù)他說(shuō),文革期間,因?yàn)閾?dān)心被銷毀,他曾將這些剪報(bào)寄回西安才得以保存。“不知怎么了,我會(huì)接受你的采訪。”他繼續(xù)說(shuō)道,之前他拒絕過(guò)幾次訪談。他又遞給我兩本書,一本散文集《伊犁紀(jì)事》,一本詩(shī)歌集《伊犁河的漣漪》。我有一點(diǎn)猶豫,也有幾分莫名的感動(dòng),外面雨聲正濃,這些剪報(bào)提起來(lái)沉甸甸的。我需要用到這么多的資料嗎?我對(duì)他的了解尚在初級(jí)階段,一個(gè)被無(wú)情的歲月之手推入“垂垂老矣”晚境的老者,落寞、敏感、孤傲、卻很真摯。我猶豫的心理逃不過(guò)他的眼神,空氣瞬間變得靜默而凝滯。
我還是把雷霆老師視作珍寶的文字帶回了家。翻開《伊犁紀(jì)事》,書本很薄,內(nèi)有30多篇散文,每一篇的篇幅不長(zhǎng),開篇《風(fēng)雪旅程》吸引了我:大卡車載著作家一家老少四口,三代人同行在去往伊犁的風(fēng)雪旅途,“暮色漸漸逝去,夜色降臨,車燈射出兩道耀眼的光柱,雪花兒紛紛揚(yáng)揚(yáng),粉蝶般在燈光中旋舞。他們的心緒,像粉蝶般飛騰……”“在風(fēng)雪彌漫的冬夜里,我向往著明天,向往著風(fēng)停雪霽的春天,向往著旅途的前方……”廖廖數(shù)語(yǔ),回味無(wú)窮,這樣的風(fēng)雪之夜,這般蕭索凄涼,懷揣著對(duì)主人公命運(yùn)的猜想和擔(dān)憂,一篇篇讀下去,文字精巧,構(gòu)思奇妙,故事有料,作品很有質(zhì)感。心緒在文字中沉浮,情感在敘述中升騰,感動(dòng)、感嘆、感慨,怎一個(gè)“感”字了得。上世紀(jì)八十年代的作品,二十年后讀來(lái)沒(méi)有陳舊感,沒(méi)有陌生感,這是讓人驚奇的感覺(jué),對(duì)這位老者,油然而生敬意,對(duì)他本人以及他的作品有了進(jìn)一步了解的迫切和沖動(dòng)。
二
雷霆,1930年出生于陜西省西安市,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中國(guó)音樂(lè)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曾任兵團(tuán)文聯(lián)《綠洲》雜志社副主編,副編審。
雷霆一生命運(yùn)多舛。
1949年參加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時(shí),不滿20歲的他對(duì)新生活充滿了熱愛。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之日,在解放軍西進(jìn)途中,雷霆擔(dān)任百人秧歌隊(duì)的領(lǐng)隊(duì),在酒泉街頭演出秧歌劇《兄妹開荒》。后隨軍進(jìn)駐新疆哈密墾區(qū),參加大生產(chǎn)運(yùn)動(dòng),從事文藝工作和新聞工作。當(dāng)時(shí)火熱的生活激勵(lì)著他,也感染著他,這期間,他才情迸發(fā),寫了大量的通訊、報(bào)道、人物專訪和詩(shī)歌,熱情謳歌戰(zhàn)斗在一線的戰(zhàn)士、建設(shè)農(nóng)場(chǎng)的職工、各行各業(yè)的英雄人物,像《鐵工排的成長(zhǎng)》《烏什塔拉水庫(kù)工地上的鐵道兵》等,發(fā)表在《新疆解放軍》《生產(chǎn)戰(zhàn)線》《新疆日?qǐng)?bào)》等報(bào)刊。深入農(nóng)場(chǎng)、牧場(chǎng)、水利建設(shè)工地的采訪生活,為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
1951年,他開始在全國(guó)及各地報(bào)刊發(fā)表大量文學(xué)作品。1952年,他的敘事詩(shī)《因?yàn)橛辛斯伯a(chǎn)黨》在全國(guó)詩(shī)歌刊物《說(shuō)說(shuō)唱唱》8月號(hào)“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詩(shī)歌題欄”中發(fā)表,他的藝術(shù)才華在全國(guó)嶄露頭角。1954年,他被調(diào)入兵團(tuán)主辦的《生產(chǎn)戰(zhàn)線》報(bào)做副刊編輯,有了充分施展才華的平臺(tái)。1957年,他創(chuàng)作的組詩(shī)《尤魯都斯牧歌》在《解放軍文藝》上發(fā)表,引起詩(shī)壇矚目。
可惜好景不長(zhǎng),渾然不覺(jué)間,正冉冉升起的文學(xué)新星就被打入另冊(cè),步入命運(yùn)的另一端。
1957年反右運(yùn)動(dòng)開始,在整風(fēng)反右的風(fēng)浪中,雷霆由于編采了一篇兵團(tuán)文藝工作者鳴放座談會(huì)的專題報(bào)道,給自己惹下了禍端。在當(dāng)時(shí)的歷史節(jié)點(diǎn)和政治背景下,他蒙受不白之冤,被調(diào)離編輯工作崗位,下放到伊犁邊遠(yuǎn)偏僻的農(nóng)場(chǎng)連隊(duì)勞動(dòng)改造,即將付梓出版的《天山南北散歌》也半途夭折。命運(yùn)對(duì)他來(lái)說(shuō)是多么殘酷:“農(nóng)場(chǎng)的第一夜,像秋風(fēng)中的落葉,枕巾上落下一層密密麻麻的頭發(fā)。”也是從那時(shí)起,他開始經(jīng)常失眠。
在勞改農(nóng)場(chǎng)、在牧區(qū)、在礦山生活的二十年里,他經(jīng)受著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經(jīng)歷了常人無(wú)法想象的苦難生活:“氣溫在零下三十度以下,在葦湖里挖排水渠,整天泡在刺骨的冷水里,沉浸在寒冷勞累苦悶孤寂的泥沼中,好在我下來(lái)時(shí)有充分的思想準(zhǔn)備,準(zhǔn)備吃大苦耐大勞受大罪,所以雖苦雖累雖孤雖寂,但已置榮辱于度外,視厄運(yùn)為常。”文革后期,他又被當(dāng)作“垃圾”和那些“牛鬼蛇神、三教九流”一齊下放到一個(gè)叫卡山奇的荒山禿嶺、邊遠(yuǎn)偏僻的小山溝,在土法水泥車間從事高強(qiáng)度的勞動(dòng)。“土法生產(chǎn)水泥,勞動(dòng)條件極差,……每天下工,人便成了整個(gè)兒一個(gè)土人兒。”風(fēng)驟雨狂,崎嶇坎坷,苦痛掙扎,漫漫二十多年啊!
從云空跌入谷底的凄慘處境,被命運(yùn)之手拋棄的無(wú)奈心境,對(duì)文學(xué)追求始終不滅的希冀和夢(mèng)想,二十年來(lái)一直伴隨著他,困擾著他:“無(wú)言是犀利的對(duì)抗,地心蘊(yùn)藏著熾熱的巖火。縱然在厄運(yùn)中苦斗終身,決不在愚昧中蹉跎歲月。”(雷霆詩(shī)《選擇》)。
逆風(fēng)的方向,更適合飛翔。面對(duì)困境,一個(gè)詩(shī)人堅(jiān)強(qiáng)而高傲的靈魂躍然紙上。
此間,他拿起手中的筆,將不滅的希望訴諸筆端,化名石爾萱、萬(wàn)鈞,寫了大量反映農(nóng)場(chǎng)日新月異的變化、反映各族人民情誼的通訊及詩(shī)歌,像《建設(shè)山區(qū)的人們》《英雄的業(yè)績(jī)》《魚水之憶》《養(yǎng)鹿行家》《十月抒情》等,發(fā)表在《生產(chǎn)戰(zhàn)線》《新疆日?qǐng)?bào)》副刊上。1963年,他發(fā)表的通訊被《生產(chǎn)戰(zhàn)線報(bào)社》評(píng)為一等獎(jiǎng)。這些記錄農(nóng)場(chǎng)真實(shí)生活的通訊,喚醒人們對(duì)兵團(tuán)史詩(shī)般生活的敬意和熱愛。這些作品,無(wú)論是歡樂(lè)還是悲憫,都成為他生命的烙印和一個(gè)時(shí)代的見證。

青年時(shí)代的雷霆意氣風(fēng)發(fā)
歷經(jīng)坎坷,備嘗艱辛,終于等來(lái)云開霧散時(shí)。
八十年代初,平反后的雷霆回到闊別已久的文壇,49歲的他已滿頭銀絲。正逢改革開放的大好時(shí)期,也是文學(xué)的興旺期。他先后編輯《群眾文化》和《綠洲》文學(xué)刊物,一干又是十年。社會(huì)進(jìn)步,政通人和,這是他編輯生涯中最舒心、最美好、最快樂(lè)的時(shí)光,猶如巖漿下噴礡而出的火山,他將全部的生活體驗(yàn)和感悟,凝聚在《伊犁河的漣漪》(詩(shī)集)中。1986年,組詩(shī)《西部抒情》獲烏魯木齊天山文學(xué)獎(jiǎng);1989年,散文《伊犁趣憶》獲兵團(tuán)新時(shí)期優(yōu)秀文學(xué)藝術(shù)成果獎(jiǎng);2000年5月,他的散文集《伊犁紀(jì)事》出版后,好評(píng)如潮,獲得了兵團(tuán)“五個(gè)一工程”獎(jiǎng)。《伊犁紀(jì)事》和詩(shī)集《伊犁河的漣漪》一并收藏于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館。
雖遭厄運(yùn),仍孜孜以求;懷揣夢(mèng)想,去等待希望。
這首《犁鏵》,正是作者人生的寫照。
三
雷霆的作品不算多,但以質(zhì)取勝。作者有著厚重的生活積累,被風(fēng)霜雪雨鍛造的人生經(jīng)歷,他的筆鋒觸及生活內(nèi)核,挖掘出原生態(tài)的社會(huì)形態(tài)。真誠(chéng)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真摯的情感表達(dá),精巧、準(zhǔn)確、冼練的文字,幽默風(fēng)趣的語(yǔ)言風(fēng)格,加之更多思考力的支撐,對(duì)生活認(rèn)識(shí)的重組,對(duì)文學(xué)審美的提煉。打磨出的作品,耐人尋味,經(jīng)得起時(shí)間的考驗(yàn)。
就他的詩(shī)歌而言,總體還屬于新邊塞詩(shī)的范疇,有著新邊塞詩(shī)的風(fēng)骨和氣質(zhì)。早期詩(shī)歌手法還比較傳統(tǒng),但風(fēng)格婉轉(zhuǎn)、細(xì)膩、熱烈、明朗,《炊煙》《小河》《云朵》《細(xì)雨》《夜霧》等詩(shī)作,大多洋溢著草原芬芳的氣息,充盈著生活的甜美和快樂(lè)。“像一根透明的圓柱,從草坪上伸到彩色的云里,牧人的帳篷上升起炊煙,勸酒的歌聲飄蕩在天際……尤魯都斯的黃昏,從來(lái)就這樣使人著迷”讀起來(lái)清新潔凈,明快自如。既詩(shī)情畫意,又悠然自得。
他后期的詩(shī)歌風(fēng)格凝重、質(zhì)樸、深沉,平實(shí)中激蕩著灼熱的愛,簡(jiǎn)單中蘊(yùn)含著哲理性的思考。“大地凝凍的歲月,冰湖是我的倩影,我是冰湖知音,大地回春的季節(jié),冰湖迎春風(fēng)消融,我沐春雨重生。”(《冰湖》)“大漠和綠洲,都可以棲息,天堂和地獄,同時(shí)是歸宿,選擇只是徒勞,高山平地,風(fēng)里雨里,還不如唱著歌兒,一路走去。”(《歌者》)。作者從命運(yùn)的籬笆中掙脫出的歌聲,那是世上最美的歌聲。
雷霆詩(shī)大多直抒胸臆,意境幽遠(yuǎn),富有神韻。有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理性冷靜,更有浪漫主義的夢(mèng)想情懷。“冬季漫長(zhǎng),孕期漫長(zhǎng),潔白無(wú)垠的產(chǎn)床上,春天臨盆,不會(huì)久遠(yuǎn),雪落雪融只是瞬間”“不知是生活的輪子,把轍印碾得太深,還是記憶的橄欖果,嚼久了才品出滋味,即使在無(wú)風(fēng)的夜里,心湖仍蕩起波紋”。細(xì)細(xì)咀嚼,淡而有味。
從早期浪漫主義風(fēng)格,轉(zhuǎn)換到后期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和他的人生經(jīng)歷分不開。詩(shī)人天生的浪漫主義情懷在他現(xiàn)實(shí)的作品中也時(shí)有體現(xiàn),這在他后期的詩(shī)作中尤為明顯,只是側(cè)重點(diǎn)有所不同而已。
相比他的詩(shī)歌,他的散文更加有“味”,有生活的味,有情感的料,有藝術(shù)的美,這是以苦難歲月為基底熬出的汁。比起只有皮毛之癢、蜻蜓點(diǎn)水浮光掠影式地玩弄文字技巧的作品,雷霆的散文有著靈魂之痛點(diǎn),刻錄著他切身經(jīng)歷和情感體驗(yàn)的印記,濃縮著他洞知世象人生的智慧。
實(shí)驗(yàn)組患者接受鼻內(nèi)鏡電凝止血治療,具體方法為:對(duì)患者予以全身麻醉插管,采用0.1% 腎上腺素面紗對(duì)患者患側(cè)鼻腔血管行收縮處理,通過(guò)鼻內(nèi)鏡找到患者出血部位,通過(guò)雙極電凝止血或高頻電刀止血,術(shù)后無(wú)需對(duì)患者接受鼻腔填塞。
散文集《伊犁紀(jì)事》取材于他在農(nóng)場(chǎng)、牧區(qū)、礦山時(shí)的生活,都是原湯原汁凡夫常人和逸聞趣事。幽默中流淌著詩(shī)意,苦痛掙扎中滿含美好的憧憬,讀來(lái)五味雜陳,感觸萬(wàn)千。語(yǔ)言除承繼詩(shī)歌的精美和冼練外,更豐富了詩(shī)歌的語(yǔ)言技巧,拓展了詩(shī)歌的意境表達(dá),生動(dòng)風(fēng)趣,準(zhǔn)確到位,人物形象撲面而來(lái)。像《“不得勁”主編》中裝模作樣、讓人啼笑皆非的主編;《頂頭上司》中“渾身線條,均朝下行,加上一付下垂的肚皮和短而彎曲的腿,如海豚一般”喜好整人的“頂頭上司”;《上海灘》中丑陋卻不甘寂寞,把生活當(dāng)舞臺(tái)的阿美:“每逢集會(huì)游行,她總是臺(tái)上臺(tái)下地晃來(lái)晃去,拋頭露面,洋洋自得,三分神氣,七分滑稽”;這些時(shí)代的產(chǎn)物和怪胎,筆之所及,讓人覺(jué)得可笑可憐又可恨。
拜倫曾說(shuō):這個(gè)世界有兩種寫作者,一種人寫自己的生活,一種人寫自己的幻想。我想雷霆老師是屬于前者的。

新疆胡楊 劉元 攝影
二十年壓抑屈辱的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一個(gè)劫難,也帶給他生命中一筆財(cái)富,那些沉積在他心中的人和事,喚起他無(wú)盡的回憶,那是他取之不盡的文學(xué)富礦:用愛溫暖他,將他內(nèi)心創(chuàng)痛緩緩撫平的正直爽朗的“開明政委”;八面玲瓏卻又重情重誼的“維持會(huì)長(zhǎng)”;在艱難困苦中,帶給他希望的八位老兵:“那個(gè)寒冷的冬天,我就是依靠劉‘班長(zhǎng)’的酒和酒一般溫馨的熱情度過(guò)的……他意味深長(zhǎng)地對(duì)我說(shuō):天再冷,地再凍,只要根不死,心不僵,來(lái)年春天就會(huì)發(fā)芽長(zhǎng)葉”。(《元老兵》)
還有《鹿苑趣聞》《婚事三則》《災(zāi)年鼠患》等原汁原味的生活,在他的筆下都非常出彩。
雷霆是一個(gè)文學(xué)藝術(shù)多面手,他在音樂(lè)領(lǐng)域也頗有造詣。除了詩(shī)歌、散文,他還發(fā)表過(guò)歌詞、曲藝、電影文學(xué)劇本、獨(dú)幕劇等。曾創(chuàng)作《奎孜》《哈密風(fēng)云》電影文學(xué)劇本,被西影和長(zhǎng)影導(dǎo)演看中,雖最終未能出爐,但卻傾注了他很多的心血,展示出他多面的藝術(shù)才華。五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由他作詞的歌曲有許多,像《絲綢之路上有座古城》《各族人民團(tuán)結(jié)緊》《我愛邊疆山河美》《阿麗亞的眼睛會(huì)說(shuō)話》《我的故鄉(xiāng)》《請(qǐng)到阿吾勒來(lái)做客》《心中的歌兒獻(xiàn)給黨》《將軍的腳印》《我登上天山頂峰》《藍(lán)色的賽里木湖》等,發(fā)表在《新疆藝術(shù)》《新疆日?qǐng)?bào)》《天山音樂(lè)》等雜志上。獲獎(jiǎng)作品《雪蓮花為誰(shuí)開》《我愛邊疆山河美》發(fā)表在《歌曲》雜志上,并分別在新疆電臺(tái)和烏魯木齊市電臺(tái)播放;《我愛邊疆山河美》上了中央臺(tái)春節(jié)音樂(lè)會(huì)。
四
雷霆把文學(xué)當(dāng)事業(yè)來(lái)做。以他的文學(xué)天賦、生活積累和創(chuàng)作的勤奮,是可以創(chuàng)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的。五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他斷斷續(xù)續(xù)做了四十年的報(bào)刊編輯,終年跋涉于文山墨海,天天在文字堆里“摸爬滾打”,把一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傾注于報(bào)刊的編輯工作中。可謂照亮了別人,燃燒了自己;熬白了頭發(fā),耗盡了心智。
他先后編輯《戰(zhàn)旗報(bào)》《生產(chǎn)戰(zhàn)線報(bào)》《紅星報(bào)》《軍墾戰(zhàn)報(bào)》《群眾文化》《綠洲》等報(bào)刊;編輯過(guò)文學(xué)叢書《天山戰(zhàn)歌》《從中原到邊疆》《艱苦奮斗十六年》《民族團(tuán)結(jié)之歌》;主編《獨(dú)幕劇選》。
1984年,《綠洲》復(fù)刊后,他任《綠洲》編輯部副主編、副編審。在沒(méi)有主編的情況下,主持《綠洲》工作。他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辦刊上,把心血傾注在培養(yǎng)作者身上,甘愿當(dāng)一名默默的耕耘者。“我在大漠上留下一行正直的腳印,即使冰雪掩蓋了我的足跡,大漠也不會(huì)忘卻我的深情,待到春天冰雪消融,芳草將在我的腳印上叢生。”
他談到,《綠洲》作為新疆二百多萬(wàn)軍墾大軍的文學(xué)領(lǐng)地,是中國(guó)西部的文學(xué)殿堂,是培育作家詩(shī)人的搖籃。他在辦刊中提出,“觀眾是電影的上帝,讀者則是刊物的上帝,一本刊物的興衰成敗,命運(yùn)掌握在它的讀者手中”“編輯如廚師,應(yīng)盡力把它辦得營(yíng)養(yǎng)豐富,又味道鮮美。”他認(rèn)為,“封閉沒(méi)有出路,停滯必然走向絕境”,一個(gè)雜志沒(méi)有特色和個(gè)性是沒(méi)有希望的,“真實(shí)地反映西部生活,真摯地扶持青年作者,熱情地鼓勵(lì)創(chuàng)新,忠誠(chéng)地服務(wù)讀者,這就是綠洲的特色,這就是綠洲的個(gè)性。”
他繁榮中國(guó)西部文學(xué)、扶植青年作家為已任,《綠洲》文學(xué)社成立后,把發(fā)展、扶植、培養(yǎng)年青作者作為編輯工作的神圣職責(zé)。他說(shuō):“在看稿中我會(huì)沉浸到作者構(gòu)思的奇妙藝術(shù)境界中去,那些出自青年作者之手的作品,會(huì)使我變得精神煥發(fā)而年輕起來(lái)。通過(guò)作品,我看到了一個(gè)五彩斑斕的人生世界。”他經(jīng)常抽查青年編輯處理的稿件,從廢品堆中挽救可刊發(fā)稿件,并常常叮囑青年編輯要重視下邊作者來(lái)稿,下邊作者寫點(diǎn)東西不容易,要對(duì)他們多加溫,少冷水。他經(jīng)常強(qiáng)調(diào),做編輯最可貴的是嚴(yán)謹(jǐn)、認(rèn)真、負(fù)責(zé),我從不主張刊物之間唱“拍手歌”,把作品當(dāng)作商品交換,這關(guān)系到編輯的職業(yè)道德問(wèn)題。為了堅(jiān)持《綠洲》的辦刊宗旨,他甚至得罪了名作家、老戰(zhàn)友、好朋友,退回了他們不符合發(fā)表要求的稿件。他提出,對(duì)青年作者要培養(yǎng)幫助,對(duì)有影響的作者的作品,應(yīng)予以重視。他在一位青年作者來(lái)稿的稿簽上寫道:“此篇出自一個(gè)青年之手,反映的是青年生活,運(yùn)用的又是青年人喜愛的手法,應(yīng)予提倡,不要把刊物辦成老頭刊物了。”在《綠洲》卷首語(yǔ)中,他寫道:中國(guó)西部詩(shī)歌,不應(yīng)拘泥于某一形式,不應(yīng)囿限于少數(shù)詩(shī)人,作品應(yīng)多色彩,作者應(yīng)多層次;在多聲部的交響中,青年應(yīng)是主旋律。”
在“西部新綠詩(shī)歌聯(lián)誼會(huì)”上,雷霆充滿激情的話語(yǔ),激蕩著許多文學(xué)青年的心:“中國(guó)西部文學(xué)希望之所在,屬于青年;中國(guó)西部詩(shī)歌希望之所在,屬于青年;希望、未來(lái)、詩(shī)歌,是屬于青年的。雛鳳清于老鳳聲,青年詩(shī)人一定會(huì)比老中年詩(shī)人唱得更好更美,更動(dòng)聽”。
一批文學(xué)新人從《綠洲》脫穎而出,王剛、王遐、韓天航、王伶、郁笛、段海曉等都得到過(guò)他的扶持和幫助,像王遐和段海曉的處女作,都是在綠洲發(fā)表的。雷霆慧眼識(shí)珠,不但發(fā)她們的作品,還配發(fā)作者簡(jiǎn)介、照片,積極推出新人。這些人目前已經(jīng)成為兵團(tuán)文學(xué)隊(duì)伍中有影響的作者。雷霆獲得過(guò)歌曲、演藝、文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作等近20種榮譽(yù)證書。但他也曾經(jīng)多次放棄各種“名錄”“辭典”的錄入及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館大瓷瓶上的留名。
心靈的高度決定了人生的高度,無(wú)論是為文還是做人,雷霆都彰顯了一個(gè)老文藝工作者的境界與格局,責(zé)任與擔(dān)當(dāng)。“雪的貞潔,冰的堅(jiān)毅,冷宮里深蘊(yùn)的火熱情誼”使他的作品呈現(xiàn)出藝術(shù)的持久性和生命力。
2014年,兵團(tuán)成立60周年之際,雷霆榮獲兵團(tuán)文藝界最高獎(jiǎng)“綠洲文藝獎(jiǎng)”貢獻(xiàn)獎(jiǎng)。
始于痛苦,達(dá)于壯美,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生活對(duì)他是公平的。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