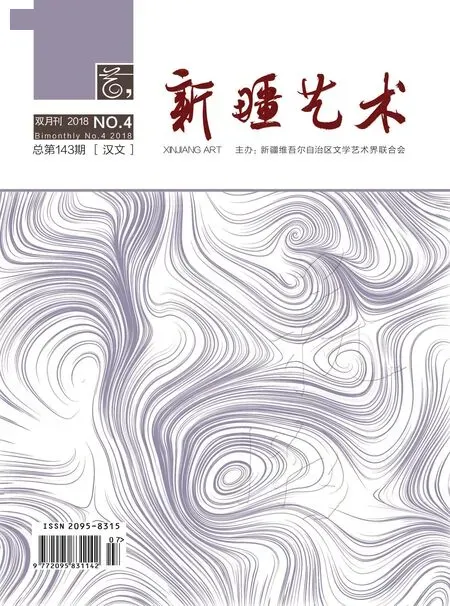藝術行者:柴新春
□ 馮國偉
人生,就是從原點出發的行走。而藝術家,則背負著繆斯之夢,在腳步丈量大地的同時,用他的眼睛去觀察,用他的手去描繪,用他的心去訴說,從而以肉體和靈魂的方式完成人生的修行,以求抵達理想的圣殿。柴新春,無疑就是這樣的一位藝術行者。
對于生于新疆,在新疆生活、工作的柴新春而言,藝術是他的理想,而行走就是他的宿命。從十五歲開始習畫,他就不停地在新疆這片熱土上行走著。從那拉提到塔什庫爾千,從哈密到和田,從雪山到沙漠,從牧場到戈壁,而四十余年的沉淀,呈現給世人的不僅有一條橫貫天山南北的地理之路,還有傾注在油畫布上,蘸有色彩、構圖、筆觸、光線諸要素構成的靈魂之路。從激蕩多變的風景,到樸拙生動的人物,光油畫寫生他就創作了一千余幅,通過這些畫,讓我們觸摸到了一個人面對藝術的虔誠和執著,面對天地人心的肅穆和敬畏,面對自我成長的坦率與堅持。這已經不是簡單的腳步的丈量,而是一個人的心靈成長史和藝術歷程記。
從他大量的不間斷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階段柴新春油畫作品中所具有的時代烙印,看到不同時期他的藝術思考和探索,也能看到不同心境下他的個人趣味與狀態。所有這些變化都是在行進中完成的,是在一個人的藝術苦旅中沉淀的,是在新疆這樣一片廣闊遼遠的大地上成就的。這種獨具個人標簽式的風格演化,與書齋式的經典臨摹和學院化的觀念嬗變有了不同的演化軌跡,也有了不一樣的參考和對照價值。

《童年的記憶》(油畫)

《大學生之六》(油畫)
柴新春的藝術功力非常扎實。他畢業于中央民族大學美術學院,學院的系統教育和他個人的勤奮苦學,使他的藝術探索并不仰仗于新疆題材的優勢和地域特色的加持,反而能從一種藝術自身變化的軌跡看出他的努力和拓展。他早期的創作,留有學院教育的痕跡,顯然受了前蘇聯厚重扎實畫風的影響,比如上世紀九十年代創作的《老倆口》《進城》《夕陽》《生息熱土》這些作品,底蘊深厚氣息濃郁,是偏重歷史敘事的,與那個時代的整體風向也有關聯。這一類作品更多關注的是題材和色彩,社會道德和大眾的價值觀往往左右著大眾的集體審美,也自然間接影響著畫家的創作。進入新世紀,柴新春的繪畫有了新的變化,抒情的意味大于敘事,筆觸干凈,構圖凝煉,比如《秋》《秋實》《看新娘》等作品,倫勃朗、席勒、柯羅及印象派大師的影響在他的作品中不時有所顯現,這種帶有古典主義的寫實風格使他從題材的形式感中跳出來,對技術的迷戀,對畫面語言的精心雕琢開始成為畫面的主體語言,這種表達是凝重而虔誠的,有種肅靜、莊重的沉郁之感。近十年的創作,尤其是他大量的風景寫生作品,能明顯看出柴新春新的變化和追求,作品的儀式感越來越弱化,筆觸越來越松脫,色彩更加克制和收斂,而涉及的題材則更加寬泛,來自于歷史和時代的宏大敘事被更多個人的感受和情緒所替代,身即山川的意象化和對人物形象的捕捉有了更深的感知和表現,繪畫語言的空靈使畫面有了更多的詩意,體現出了更多的中國畫意味。這些變化,可以看出柴新春的創作經歷了一個從側重社會到藝術乃至回歸個人心靈的演變。這種從大到小、由外向內、由眼及心的變化其實正暗合著當代藝術整體的時代演進,只不過,在新疆這片浩翰的大地上,一個人的藝術行旅中,總是顯得那么渺小,但一點不缺少完整和堅硬。

《鐵熱克提之秋》(油畫)

《北江雨后》(油畫)
正是這種漫長的旅途所具有的孤立和孤獨感,我們能看出柴新春的藝術初心,那就是對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在與風景的對話中,在與人物的交流中,在與內心的靠近中,柴新春筆下的風景慢慢褪去了形象和概念,呈現出了鄉野的本色和曠野的質樸感,而成為個人的獨自吟唱和抒情。就如他作品《家園》中那溢出畫面的野花,既能看出形態也能聞到花香;而他的人物也從莊重到質樸,突破了民族服飾、骨相、動作等元素所具有的鮮艷、明媚和約定俗成的表現,而成為了一個有溫度的人。這種觀察的角度是審慎的,帶有一定距離,但又不是冰冷的。這種保持適度距離的視角所帶來的客觀性,也許恰恰還原了真實和現實,成為個人的心境和狀態,也成就了個人的視角和表達。
在以眾多表現新疆題材的油畫作品中,柴新春的畫并不以熱烈的形式取勝,也不以獨特的視角見長,但他的氣質如同一株新疆云杉,不畏寒涼,挺拔自健,更因為帶著行走中的風和雨,帶著思考中的靜和動,帶著繪畫中的情與意,有了一種外冷內熱,蘊籍而悠長的詩意。那是需要靜下心來體味的。
那一刻,我們是否也能感受到畫外的柴新春在天地之間發出的一聲感慨:我來了,我在!
(本文圖片由柴新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