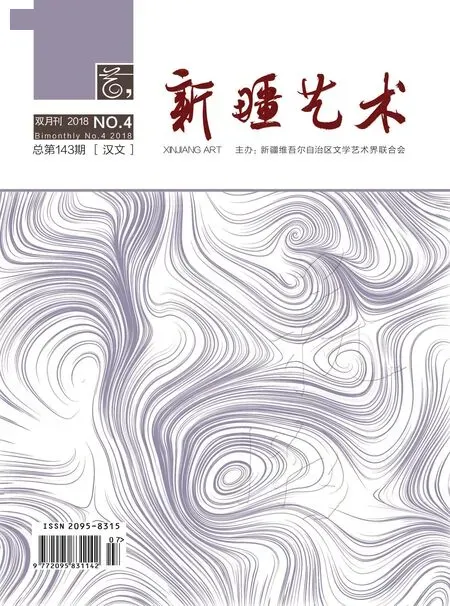二十世紀(jì)吉爾吉斯斯坦音樂發(fā)展的三種思潮
□崔斌

音樂思潮指的是在某歷史階段中對(duì)音樂實(shí)踐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思想潮流,它有三個(gè)要素:一是與音樂實(shí)踐密切相關(guān),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影響到該時(shí)段的音樂實(shí)踐活動(dòng);二是有思想的成分,即受到了某種社會(huì)思想的影響,是某種社會(huì)思想在音樂中的反映;三是具有潮流性,即產(chǎn)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音樂思潮的表現(xiàn)多種多樣,可以說某個(gè)特定歷史時(shí)期內(nèi)較為流行的音樂品種、樂曲風(fēng)格等皆可作為判定音樂思潮的指標(biāo)。但能夠從整體上、最為直接反映整個(gè)音樂學(xué)科發(fā)展脈絡(luò)的指標(biāo)當(dāng)屬由著名作曲家創(chuàng)作的音樂作品和學(xué)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當(dāng)一系列相同或相似的作品、成果集中出現(xiàn)于某個(gè)特定歷史時(shí)期時(shí),一定意味著受到了主流音樂思潮的影響。筆者擬通過梳理百年吉爾吉斯斯坦的代表性音樂作品和重要音樂研究成果,并結(jié)合筆者的學(xué)術(shù)調(diào)研來揭示影響吉爾吉斯斯坦百年音樂發(fā)展的三次重要思潮。
本文僅針對(duì)吉爾吉斯斯坦學(xué)者和與吉爾吉斯斯坦音樂學(xué)術(shù)密切相關(guān)的蘇聯(lián)學(xué)者的成果,試圖從該國(guó)音樂學(xué)科的內(nèi)部視角展開研究。
一、收集整理民間音樂的思潮
十月革命之后,吉爾吉斯斯坦成為蘇聯(lián)的一部分,大批優(yōu)秀的蘇聯(lián)音樂家開始走進(jìn)吉爾吉斯斯坦從事民間音樂的收集與整理工作。
最早收集吉爾吉斯斯坦民間音樂的是俄國(guó)學(xué)者А·扎塔耶維奇,他的工作開始于20世紀(jì)20年代,形成了多部具有重要資料價(jià)值和參考意義的作品集和研究著作:出版較早的是1934年在莫斯科出版的《250首吉爾吉斯器樂曲和歌曲》和《173首吉爾吉斯庫姆孜琴、科亞克琴、楚爾、鐵木爾庫姆孜曲譜》①;他的另外兩部作品出版于1971年,分別為包含428首器樂曲和歌曲的《吉爾吉斯器樂曲和民歌》(1971)與《蘇聯(lián)各民族民間歌曲》(1971),后者除了包含吉爾吉斯斯坦民間音樂,還涵蓋許多蘇聯(lián)境內(nèi)其他民族的民間音樂資料。
А·扎塔耶維奇還利用資料的便利率先對(duì)吉爾吉斯斯坦民間音樂展開了系統(tǒng)研究:一、確定吉爾吉斯斯坦民間音樂的分類體系,按題材劃分為勞動(dòng)歌曲、禮儀歌曲、抒情歌曲等;按樂種類型劃分為民歌、阿肯彈唱、器樂曲(奎依)等;二、明確了傳統(tǒng)民間音樂的調(diào)式,認(rèn)為混合利第亞大調(diào)是最為常見的,同時(shí)還有伊奧尼亞調(diào)式、愛奧利亞調(diào)式、多里亞調(diào)式和變化多端的交替調(diào)式;三、認(rèn)為吉爾吉斯斯坦民間音樂在整體上擁有建立在混合或單獨(dú)的七聲音階基礎(chǔ)之上的穩(wěn)定調(diào)式體系。由于А·扎塔耶維奇開展民間音樂收集與研究的時(shí)代較早,記錄設(shè)備較為簡(jiǎn)陋,很多辨音工作只能靠其出色的聽覺來完成,因此他收集的音樂資料難免有旋律標(biāo)記不清、歌詞紕漏等瑕疵,但這些問題不能掩蓋他篳路藍(lán)縷的開創(chuàng)之功和取得的卓越成就,著名學(xué)者В·維諾格拉多夫評(píng)價(jià)說:“他記錄的吉爾吉斯民歌和器樂曲具有典范意義,至今仍然是吉爾吉斯斯坦民族音樂發(fā)展的不竭動(dòng)力,而且無論國(guó)內(nèi)還是國(guó)外的音樂家、作曲家,都能從這些優(yōu)秀作品中獲得啟發(fā)和靈感。”②

采訪吉爾吉斯斯坦國(guó)立音樂學(xué)院院長(zhǎng)別格里耶夫·木拉提
蘇聯(lián)時(shí)期另一位收集民間音樂的巨匠是В·維諾格拉多夫。他的代表性成果有:《100首吉爾吉斯歌曲和器樂曲》(1958)、《托克托古勒的音樂遺產(chǎn)》(1961)、《托克托古勒和吉爾吉斯阿肯》(1952)、《吉爾吉斯民間樂人》(1952)。
《100首吉爾吉斯歌曲和器樂曲》收錄了民歌,《豐收歌》《牧歌》等與宗教信仰及薩滿遺存有深刻聯(lián)系的禮儀歌曲,史詩《瑪納斯》的精彩片段,以及1940至1952年間由作曲家或民間藝人創(chuàng)作的庫姆孜和科雅克器樂曲等作品,即這部曲集實(shí)際涵蓋了吉爾吉斯斯坦所有種類的傳統(tǒng)民間樂曲和自十月革命至上世紀(jì)60年代間改編或新作的各類民間樂曲。《托克托古勒的音樂遺產(chǎn)》和《托克托古勒與吉爾吉斯阿肯》是關(guān)于著名阿肯托克托古勒的研究著作。托克托古勒(1864—1933)是吉爾吉斯斯坦最為著名的民間樂人之一,也是一位堅(jiān)定的蘇維埃支持者,他掌握了包括牧民音樂在內(nèi)的幾乎全部的傳統(tǒng)曲目,為傳統(tǒng)民間音樂尤其是“哭喪歌”這種儀式音樂的傳承起到了關(guān)鍵作用,被認(rèn)為是吉爾吉斯斯坦社會(huì)轉(zhuǎn)型時(shí)期(十月革命社會(huì)主義轉(zhuǎn)型時(shí)期)最杰出的民間音樂家。《托克托古勒的音樂遺產(chǎn)》共有兩部分,第一部分(1-18號(hào))收錄了А·扎塔耶維奇《250首吉爾吉斯器樂曲和歌曲》中由托克托古勒在1928年表演的作品;第二部分為第19-101號(hào),由В·維諾格拉多夫親自記錄,是托克托古勒的學(xué)生們?cè)?940年5月至7月和1956年10月至12月間通過回憶表演的。《托克托古勒和吉爾吉斯阿肯》《吉爾吉斯民間樂人》是對(duì)包括托克托古勒和庫熱尼凱耶夫·穆熱塔勒③在內(nèi)的各類民間藝人的民族學(xué)、人類學(xué)研究,是考察吉爾吉斯斯坦民間藝人歷史、早年藝人生存狀況、民間音樂傳承方式和傳承體系的重要成果。
此外,В·維諾格拉多夫還記錄了多支由庫姆孜演奏的結(jié)尾曲,更為全面地展示了吉爾吉斯斯坦民間音樂的面貌。相對(duì)А·扎塔耶維奇收集的作品,В·維諾格拉多夫收錄的資料更為精確:具有準(zhǔn)確的節(jié)拍標(biāo)志和歌詞,更為符合現(xiàn)代民族音樂學(xué)的要求和規(guī)范。
對(duì)民間音樂作品的收集和整理還有一個(gè)重要的分支,即對(duì)史詩《瑪納斯》的記錄整理。《瑪納斯》無疑是中亞地區(qū)最重要、最典型的英雄史詩。對(duì)《瑪納斯》的系統(tǒng)記錄和研究亦始于上世紀(jì)20年代。④最早對(duì)《瑪納斯》進(jìn)行系統(tǒng)記錄的工作開展于1922到1926年間,是對(duì)薩恩拜·奧諾孜巴克夫⑤版本的記錄。他演唱的《瑪納斯》第一部版本長(zhǎng)達(dá)25000行,是迄今最為完整的一部。1947年,В·維諾格拉多夫在瑪納斯研究者依布拉音·阿布多熱合瑪諾夫(他曾為奧諾孜巴克夫的表演錄音)的幫助下,記錄下了這個(gè)版本的音樂。
蘇聯(lián)時(shí)期另一位著名瑪納斯奇是薩雅克拜·卡拉拉耶夫⑥,他在1935—1947年間,他完整地記錄了一套《瑪納斯》(400000行,包括英雄瑪納斯、瑪納斯兒子賽麥臺(tái)依、瑪納斯孫子賽依臺(tái)克三部分),以及一首關(guān)于葉兒·吐什托克⑦的史詩。薩雅克拜更為重要的貢獻(xiàn)是完整地表演了《瑪納斯》故事的續(xù)篇,即以賽依臺(tái)克的兒子凱耐尼木,以及凱耐尼木的兩個(gè)兒子阿勒穆薩熱克和庫蘭薩熱克為主人公的篇章。薩雅克拜是在無樂器伴奏的情況下表演的,其音樂由В·維諾格拉多夫記錄。筆者在吉爾吉斯斯坦調(diào)查時(shí)觀察到,比什凱克中央廣場(chǎng)、國(guó)家歌劇院門口、各地州的廣場(chǎng)、花園中都能看到薩雅克拜的雕像和畫像,彰顯著他崇高的文化地位,藝術(shù)作品中他那高昂的頭顱和向上翹起的胡須更成為當(dāng)代吉爾吉斯人文化自信的典范。
自十月革命至上世紀(jì)50年代,全面收集民間音樂的工作一直在有條不紊地進(jìn)行著,產(chǎn)出了一大批至今仍有重要影響的成果。對(duì)吉爾吉斯斯坦音樂學(xué)科建設(shè)產(chǎn)生了重要而深遠(yuǎn)的影響。全面收集民間音樂的主力軍是蘇聯(lián)學(xué)者,但這項(xiàng)工作在民間藝人中也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儼然成為十月革命后吉爾吉斯斯坦民族音樂發(fā)展的重要思潮:蘇聯(lián)學(xué)者遍訪國(guó)家的各個(gè)角落,幾乎收集了全部具有代表性的民間音樂作品;眾多具有重要影響的民間藝人則毫無保留地積極配合。在二者的通力合作下,吉爾吉斯斯坦的民間音樂得以較為全面地記錄,促使流傳于民間的口頭音樂成為書面化的曲譜,為其它音樂學(xué)科的發(fā)展奠定了扎實(shí)的資料基礎(chǔ);同時(shí),還對(duì)吉爾吉斯斯坦民間音樂進(jìn)行初步整理和研究。
二、蘇聯(lián)化思潮
十月革命之后,吉爾吉斯斯坦成為蘇聯(lián)的一部分。蘇聯(lián)政府迫切需要了解境內(nèi)各民族文化,因此派遣大量學(xué)者、藝術(shù)人才走入吉爾吉斯斯坦(二戰(zhàn)期間,蘇聯(lián)政府為了保護(hù)藝術(shù)人才,亦曾安排大量科學(xué)家、藝術(shù)家到伏龍芝避戰(zhàn)),學(xué)者和藝術(shù)家的到來將蘇聯(lián)的音樂制度、音樂教育體系完整地帶入吉爾吉斯斯坦;另一方面,通過加盟蘇聯(lián),吉爾吉斯斯坦跨越性地完成了從奴隸制社會(huì)到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的巨大轉(zhuǎn)變,極大地振奮了民族精神,從政府到群眾的各個(gè)階層都對(duì)蘇聯(lián)文化產(chǎn)生了膜拜之情,開始在熱切宣傳革命、謳歌新生活的過程中積極學(xué)習(xí)蘇聯(lián)音樂文化。在雙方的共同意愿下,蘇聯(lián)的音樂體系迅速完整地移植到吉爾吉斯斯坦,引領(lǐng)了吉爾吉斯斯坦音樂學(xué)科的近代化和現(xiàn)代化,最重要的表現(xiàn)有三個(gè)方面:
一是建立專業(yè)的音樂院校,將蘇聯(lián)的音樂教育模式完全復(fù)制到吉爾吉斯斯坦,培養(yǎng)專業(yè)音樂人才。二是在收集民間音樂和將民間音樂運(yùn)用到音樂教育、舞臺(tái)表演的過程中,完成了對(duì)吉爾吉斯傳統(tǒng)民間音樂的改造工作,以及對(duì)民族樂器的改良工作(即對(duì)樂器的材質(zhì)、形制、定弦標(biāo)準(zhǔn)、音域、演奏技巧等方面加以規(guī)范和統(tǒng)一,并按高、中、低聲部改造民族樂器,建立符合西方管弦樂編制的民樂團(tuán)等)。三是通過表演蘇聯(lián)著名作品,或創(chuàng)作以民族文化元素為靈魂的作品等方式,引入交響樂、歌劇、芭蕾舞劇等音樂品種,極大地豐富了音樂品種和傳統(tǒng)音樂的表現(xiàn)手法。在全面學(xué)習(xí)蘇聯(lián)的過程中,以上三方面工作促使吉爾吉斯斯坦音樂學(xué)科迅速完成了近、現(xiàn)代化,因此,本文將這一時(shí)期的發(fā)展思潮稱之為“蘇聯(lián)化思潮”。

采訪青年庫姆孜奇扎科爾別克·都沙別

與木卡沙·阿布都拉耶夫?qū)I(yè)音樂學(xué)校師生座談合影
蘇聯(lián)化思潮的迅猛進(jìn)展從一份年表中便可得知:十月革命期間,吉爾吉斯斯坦便出現(xiàn)了大量革命宣傳隊(duì),借助蘇聯(lián)的文藝宣傳手法發(fā)動(dòng)群眾,鼓舞革命。至1926年,在伏龍芝成立了第一所專業(yè)音樂學(xué)校——戲劇藝術(shù)學(xué)校。1928年比什凱克工人劇院建成。1936年,比什凱克音樂劇院建立。同年,交響樂團(tuán)和交響樂愛好者協(xié)會(huì)成立。1939年,作曲家協(xié)會(huì)和音樂家協(xié)會(huì)成立。1942年,音樂劇院擴(kuò)建成為吉爾吉斯斯坦歌劇院,成為各類音樂表演的中心。1955年,芭蕾舞劇院建成。在此期間,各州市的音樂機(jī)構(gòu)和民間團(tuán)體也相繼成立,至今已呈現(xiàn)遍地開花之勢(shì)。
(一)歌劇和芭蕾舞劇方面,在十月革命前后,便產(chǎn)生了一種特殊的音樂體裁——“音樂劇”,其本質(zhì)是對(duì)傳統(tǒng)民間作品進(jìn)行政治性加工,并用于政治宣傳。1939年,阿布都拉斯·瑪勒德巴耶夫、費(fèi)拉索夫·弗拉基米羅維奇·亞歷山大、弗拉基米爾·吉?dú)W吉維奇·費(fèi)雷共同創(chuàng)作了吉爾吉斯斯坦的第一部歌劇《美麗的月亮》,改編自一個(gè)吉爾吉斯斯坦廣為流傳的民間故事。1940年,費(fèi)拉索夫和費(fèi)雷又共同創(chuàng)作了吉爾吉斯斯坦第一部芭蕾劇《阿納爾》,以及歌劇《瑪納斯》。后者與《美麗的月亮》一起被視為吉爾吉斯劇作的瑰寶。
阿布都拉斯·瑪勒德巴耶夫⑧,吉爾吉斯斯坦著名劇作家,他的創(chuàng)作生涯始于1922年,一生創(chuàng)作了3300多首作品,其作品《斯都切得爾瑪多什》具有國(guó)歌地位,另外兒童歌曲《庫魯弄》《吉爾德日木》,合唱曲《艾穆蓋克瑪什》,民歌《古麗都爾穆什》《烏庫杰爾居孜》等亦非常著名。瑪勒德巴耶夫?qū)獱柤姑褡宓纳鐣?huì)歷史文化非常了解,他的作品往往觸及到民族精神的精髓,并且善于融合民族和西方音樂的特點(diǎn),創(chuàng)造了一種全新的藝術(shù)種類,具有很強(qiáng)的藝術(shù)感染力和沖擊力。學(xué)者先琴科曾將瑪勒德巴耶夫的創(chuàng)作與吉爾吉斯斯坦傳統(tǒng)音樂和蘇聯(lián)音樂進(jìn)行了綜合比較,并對(duì)瑪勒德巴耶夫進(jìn)行高度評(píng)價(jià)。⑨
該時(shí)期其它歌劇創(chuàng)作還有納斯?fàn)枴さ懒兴鞣虻摹稁鞝柭鼊e克》,穆卡什·阿卜德熱耶夫的《暴風(fēng)雨之前》《烏勒卓拜》《柯西木江》,阿合瑪特·阿曼巴耶夫的《阿依達(dá)爾和阿依夏》,薩特勒汗·烏斯莫諾夫的《賽依麗》;芭蕾舞劇有米哈伊爾·勞赫維杰的《喬麗盼》等。
(二)西洋音樂方面,不得不提到作曲家、音樂教育家舒賓(1894-1948),他畢業(yè)于圣彼得堡高級(jí)音樂學(xué)院,是第一批來到來吉爾吉斯斯坦的蘇聯(lián)音樂家之一,并于1928年定居伏龍芝。他知識(shí)淵博,富有熱情,還對(duì)東方文化有著強(qiáng)烈的好奇心。他組織建立了吉爾吉斯斯坦的第一個(gè)專業(yè)樂隊(duì),并借助樂隊(duì)向參與者傳播西方音樂知識(shí)和理論,對(duì)蘇聯(lián)音樂文化的傳入及吉爾吉斯斯坦音樂教育的發(fā)展做出了突出貢獻(xiàn),瑪勒德巴耶夫等第一批著名的吉爾吉斯斯坦音樂家皆曾參與他的樂隊(duì)活動(dòng),并從中受益無窮。20世紀(jì)50年代,一批從莫斯科專業(yè)院校畢業(yè)的人才進(jìn)一步擴(kuò)充了這一陣營(yíng),這便包括吉爾吉斯斯坦著名音樂家塔什坦·葉爾瑪托夫,穆凱·阿不德熱耶夫等。在蘇聯(lián)音樂家和吉爾吉斯斯坦民族音樂家的共同努力下,涌現(xiàn)出費(fèi)拉索夫創(chuàng)作的大量吉爾吉斯民族風(fēng)格的序曲,尼古拉夫·熱克夫和圖列耶夫創(chuàng)作的交響樂作品,朱瑪巴耶夫的史詩交響樂,V.居蘇耶夫的中提琴協(xié)奏曲,阿曼巴耶夫、葉兒瑪托夫、S·阿依提凱耶夫合作創(chuàng)作的弦樂四重奏,吉勒德孜·瑪勒德巴耶夫創(chuàng)作的二十四首鋼琴前奏曲等著名作品。
(三)20世紀(jì)50到70年代,吉爾吉斯斯坦還走出了卡里·莫勒多巴散耶夫⑩。別格里耶夫·木拉提[11]等著名音樂家,這些后起之秀進(jìn)一步延續(xù)了“蘇聯(lián)化思潮”。
卡里·莫勒多巴散耶夫是吉爾吉斯著名劇作家、作曲家,其最為著名的作品是1976年創(chuàng)作的戲劇《母親大地》,該作品曾被翻譯為多種語言在多國(guó)演出,堪稱開辟了吉爾吉斯斯坦藝術(shù)的新領(lǐng)域。憑借這首作品,莫勒多巴散耶夫在1976年獲得了蘇聯(lián)國(guó)家獎(jiǎng)項(xiàng),并在1979年獲得蘇聯(lián)人民藝術(shù)家稱號(hào)。他的其它作品還有《一瞬間》《神奇的即興表演》《在瑪納斯的陣營(yíng)中》《曼庫特的傳說》《我們是歡樂的兒童》、芭蕾舞劇《繼艾特瑪托夫之后》等。
著名作曲家別格里耶夫·木拉提現(xiàn)任吉爾吉斯斯坦音樂學(xué)院院長(zhǎng)。他在創(chuàng)作方面善于將各類藝術(shù)形式與本民族傳統(tǒng)元素進(jìn)行巧妙結(jié)合,其代表作有音樂劇《白色的帆船》、音樂童話劇《木板路》,交響樂《瑪納斯》《啟示錄》,弦樂四重奏《吉爾吉斯之歌》,鋼琴曲《老人的回憶》等。1993年,他參與建立吉爾吉斯國(guó)立音樂學(xué)院,并成為該校教授、校長(zhǎng)。2016—2017年間,筆者曾先后兩次赴吉爾吉斯斯坦國(guó)立音樂學(xué)院對(duì)其展開深入訪談。在筆者眼中,作為一名深受前蘇聯(lián)音樂模式影響的作曲家、教育家和國(guó)立音樂學(xué)院院長(zhǎng),別格里耶夫·木拉提具有國(guó)際化的眼光和寬廣的胸懷氣度,他既延續(xù)了前蘇聯(lián)的音樂教育體系,扎實(shí)推進(jìn)學(xué)生基礎(chǔ)素質(zhì)的培養(yǎng);又頻繁赴歐美、亞洲考察他國(guó)的音樂教育經(jīng)驗(yàn),將新的元素不斷融入到音樂教育中;同時(shí)注重振興吉爾吉斯民族音樂,結(jié)合自身善于挖掘吉爾吉斯傳統(tǒng)民族音樂特質(zhì)和精髓的特點(diǎn),在創(chuàng)作方面提倡本民族傳統(tǒng)音樂元素的創(chuàng)新化。
總之我們可以將上世紀(jì)20年代直至上世紀(jì)80年代稱為吉爾吉斯斯坦音樂的“蘇聯(lián)化”時(shí)期,學(xué)習(xí)蘇聯(lián)音樂和利用蘇聯(lián)音樂的經(jīng)驗(yàn)改造吉爾吉斯斯坦的傳統(tǒng)民間音樂是這一時(shí)期音樂發(fā)展的主要思潮。這一思潮是當(dāng)時(shí)蘇聯(lián)音樂家和吉爾吉斯斯坦音樂家的共同心聲,在雙方的合作與努力下,吉爾吉斯斯坦的音樂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系統(tǒng)地奠定吉爾吉斯音樂學(xué)科的基礎(chǔ)。
三、蘇聯(lián)化思潮對(duì)民間音樂發(fā)展的制約
雖然學(xué)習(xí)蘇聯(lián)的思潮在整體上促使吉爾吉斯斯坦音樂學(xué)科取得了飛躍性的發(fā)展,但也極大地改變了民間音樂的原生環(huán)境,使民間音樂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它在自然環(huán)境下的發(fā)展方向。這種改變的根源在于民間音樂傳承方式和表演環(huán)境的改變。
在蘇聯(lián)之前,民間音樂一直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承,其樣態(tài)具有一定的活性,即在傳授和表演的時(shí)候具有較強(qiáng)的即興成分,而即興成分是民間音樂在自然傳承過程中不斷發(fā)展出新的動(dòng)力和源泉。以庫姆孜曲為例,在口傳心授的自然狀態(tài)下,同一首庫姆孜曲被不同藝人表演時(shí),甚至同一藝人在不同場(chǎng)次的表演中,都會(huì)產(chǎn)生或多或少的變化。這便導(dǎo)致觀眾所聽與學(xué)習(xí)者所學(xué)的音樂并不固定。聽眾可以選擇切合自己內(nèi)心的表演作為心中判定表演高下的標(biāo)準(zhǔn),學(xué)習(xí)者也完全可以根據(jù)自己的喜好對(duì)音樂進(jìn)行適度的發(fā)展。流傳至今的傳統(tǒng)曲目正是在這種傳承方式中不斷得到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的。
蘇聯(lián)時(shí)期,民間音樂離開了原生的游牧環(huán)境,走入了專業(yè)化的音樂教育和劇場(chǎng)等各類舞臺(tái),原有的傳承方式和表演環(huán)境都發(fā)生了重要變化:民間音樂在自然環(huán)境中的即興性質(zhì)顯然無法滿足專業(yè)音樂教育的需要,因此它們被譜寫成了樂譜,具有了固定的形態(tài)。另一方面,為了適應(yīng)舞臺(tái)表演,庫姆孜奇不斷創(chuàng)新出花樣百出的新鮮手法,以翻飛的手式花樣吸引觀眾的眼球,制造了精彩的舞臺(tái)效果,比如當(dāng)今最為著名的青年庫姆孜奇扎科爾別克·都沙別,他曾連續(xù)5次獲得國(guó)家?guī)炷纷未螵?jiǎng)賽的冠軍,代表了當(dāng)今吉爾吉斯斯坦庫姆孜的最高水平。筆者曾在吉爾吉斯斯坦對(duì)其進(jìn)行過三次專訪,他自豪地介紹道,他的住房就是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guó)總統(tǒng)獎(jiǎng)勵(lì)的。他表演的《夜鶯》具有繁復(fù)而精彩的手法,翻飛的手指就像一個(gè)美麗舞者,具有超強(qiáng)的震撼力。他告知我們:《夜鶯》一曲已有百年歷史,為了增強(qiáng)舞臺(tái)效果,他在繼承傳統(tǒng)表演手法的同時(shí)不斷增加、美化原有的表演手法,使其更具觀賞性。有的吉爾吉斯學(xué)者并不贊同這種一味注重視覺效果、忽略聽覺效果的表演方式,認(rèn)為這種表演方式實(shí)際影響了傳統(tǒng)庫姆孜曲以音聲動(dòng)人的美感和對(duì)曲目感情的抒發(fā)。而筆者認(rèn)為,這些反對(duì)的聲音正反映出了舞臺(tái)化表演對(duì)傳統(tǒng)民間音樂造成的沖擊。
蘇聯(lián)時(shí)期還實(shí)行過某些抵制民族文化的政策,或者在宣傳層面有意貶低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價(jià)值,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約了民族音樂的發(fā)展,《瑪納斯》在蘇聯(lián)時(shí)期的境遇可謂典型:上世紀(jì)50年代,《瑪納斯》表演被定義為一項(xiàng)“業(yè)余愛好者”活動(dòng),蘇聯(lián)雖沒有明確禁止瑪納斯的表演,卻在意識(shí)形態(tài)上貶低其價(jià)值和內(nèi)涵。筆者在吉爾吉斯考察期間,曾采訪著名瑪納斯奇、《瑪納斯》研究博士、瑪納斯基金會(huì)秘書長(zhǎng)巴科齊耶夫·塔朗塔里,他為我們講述:“記得初中時(shí),老師讓我在節(jié)日晚會(huì)上演唱《瑪納斯》,我便演唱了瑪納斯的誕生部分,我覺得我唱的很好,但卻受到了大家嘲笑,他們認(rèn)為是過時(shí)的東西”。《瑪納斯》之所以會(huì)遭遇此命運(yùn),與其本身的“宗教”色彩及其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有關(guān)。[12]其實(shí)不唯《瑪納斯》,在蘇聯(lián)時(shí)期,許多中亞史詩都被壓制了,與此同時(shí),還產(chǎn)生了與時(shí)代相適應(yīng)的史詩作品,比如烏茲別克斯坦便產(chǎn)生了一種用大段詩歌贊頌列寧、斯大林和集體化的史詩作品。這些“新型”史詩仍舊使用傳統(tǒng)的表演方法,才使中亞史詩的表演傳統(tǒng)不至斷絕。
可以說,蘇聯(lián)時(shí)期引入的新型音樂發(fā)展模式和樂種在短時(shí)間內(nèi)極大地?cái)U(kuò)充了吉爾吉斯人民的視野,但也制約傳統(tǒng)民間音樂的發(fā)展,導(dǎo)致部分學(xué)者一度認(rèn)為只有蘇聯(lián)引入的音樂才是現(xiàn)代的、藝術(shù)的,本民族的傳統(tǒng)音樂則是“原始的”,這樣的心態(tài)集中反映在蘇聯(lián)時(shí)期的音樂史著作中:巴勒拜·阿拉古什夫的《吉爾吉斯音樂歷史》(1989)是一部較為普及的音樂史教科書,它將蘇聯(lián)時(shí)期的音樂歷史細(xì)致地劃分為幾個(gè)階段,但對(duì)蘇聯(lián)以前的傳統(tǒng)民間音樂卻僅有一段單薄的概述;薩利耶夫則在他的《吉爾吉斯藝術(shù)史》(1971)中提出:吉爾吉斯的音樂經(jīng)歷了一次跨越式、革命性的發(fā)展歷程,而這種變化是受外來文化、尤其受蘇聯(lián)音樂的影響而發(fā)生的。
四、民族意識(shí)復(fù)興背景下的民族化思潮
進(jìn)入上世紀(jì)80年代,蘇聯(lián)對(duì)吉爾吉斯斯坦的思想控制逐漸減弱,取而代之的是民族意識(shí)的復(fù)興。這種民族意識(shí)體現(xiàn)在當(dāng)今吉爾吉斯斯坦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比什凱克市為例:蘇聯(lián)功勛雕塑和油畫被瑪納斯、以及著名瑪納斯奇等歷史文化名人的雕像和畫像取代;許多原以蘇聯(lián)英雄命名的城市街道皆改用民族英雄的名字;不再使用盧布作為貨幣,改用索姆,且貨幣上的人物皆換作本民族的歷史名人等等。但若認(rèn)真思考不難發(fā)現(xiàn),雕塑和油畫是由蘇聯(lián)傳入的;城市的街道基本上是蘇聯(lián)幫助建造的,并且大多還保留著它們最初的樣子;即便貨幣,也是由蘇聯(lián)引入的。正因吉爾吉斯斯坦的近、現(xiàn)代化是在蘇聯(lián)時(shí)期下完成的,所以蘇聯(lián)文化已然植根于每一個(gè)現(xiàn)代吉爾吉斯人的血液中。音樂方面也是如此,當(dāng)今吉爾吉斯斯坦的音樂學(xué)科體系幾乎全是蘇聯(lián)模式的,因此當(dāng)復(fù)興的民族意識(shí)試圖尋找突破時(shí),必然會(huì)遭遇諸多困難。
走在比什凱克的大街小巷,探訪國(guó)立音樂學(xué)院、木卡沙·阿布都拉耶夫?qū)I(yè)音樂學(xué)校[13]等,皆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吉爾吉斯斯坦音樂仍延續(xù)著由蘇聯(lián)引入的體系:《喀秋莎》《山楂樹》《畢業(yè)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紅梅花兒開》等蘇聯(lián)歌曲仍在傳唱;蘇聯(lián)引入的手風(fēng)琴、鋼琴等西方樂器的表演非常盛行,庫姆孜、科雅克等民族樂器的表演則延續(xù)著被蘇聯(lián)改造、規(guī)范后的模式。音樂教育方面,以木卡沙·阿布都拉耶夫?qū)I(yè)音樂學(xué)校為例,該校開設(shè)有:(1)鋼琴(2)弦樂(3)管樂和打擊樂器(4)音樂理論(5)音樂教育(6)鋼琴伴奏及室內(nèi)音樂(7)吉爾吉斯民族音樂等專業(yè)。民族音樂專業(yè)所占比例非常小,且仍沿襲蘇聯(lián)傳入的教育模式。[14]

作者與《瑪納斯》研究博士、瑪納斯奇、瑪納斯基金會(huì)秘書長(zhǎng)巴科齊耶夫·塔朗塔里
然而自上世紀(jì)80年代開始,隨著民族意識(shí)的復(fù)興,一大批學(xué)者開始關(guān)注吉爾吉斯斯坦傳統(tǒng)音樂的民族特征和生成民族特征的文化土壤,試圖從學(xué)術(shù)角度證明吉爾吉斯的傳統(tǒng)民間音樂既不“原始”,也不“落后”,更非西方音樂的附屬品,它應(yīng)與其它國(guó)家、民族的音樂一樣,被視為世界音樂的一部分。
較早從事民族音樂工作的是康奇別克·都沙里耶夫院士,他在1982年出版的《吉爾吉斯民間歌曲》(1988)一書中,從調(diào)式體系、旋律結(jié)構(gòu)、曲式結(jié)構(gòu),以及民族歌曲與民間詩歌的關(guān)系方面詳細(xì)分析了吉爾吉斯傳統(tǒng)民間音樂的特點(diǎn);其《吉爾吉斯民歌的體裁和歷史》(1993)的研究對(duì)象則是民歌、儀式歌、庫姆孜彈唱、民間說唱等不同體裁作品的創(chuàng)作方法和歷史發(fā)展。
蘇巴納里耶夫《吉爾吉斯的民間樂器》(1986)對(duì)吉爾吉斯體鳴、膜鳴、管樂器等各類傳統(tǒng)樂器進(jìn)行了深入研究,作者一方面從語言學(xué)角度考證了“庫姆孜”“科雅克”等傳統(tǒng)樂器名稱的詞語來源;一方面從人類學(xué)角度闡釋了樂器起源的社會(huì)背景,以及樂器應(yīng)用、發(fā)展的社會(huì)環(huán)境。巴特瑪·克別闊瓦《吉爾吉斯—哈薩克民間歌手創(chuàng)作比較研究》(1985)將吉爾吉斯和哈薩克音樂放置于草原文化的背景下,并對(duì)二者的異同進(jìn)行了深入分析;他的另一部著作《吉爾吉斯民間歌手的歷史概況》(2009)詳細(xì)考證了吉爾吉斯民間歌手在不同歷史階段,包括蘇聯(lián)時(shí)期的生活狀態(tài)和行為方式;巴亞斯坦·伊薩·克夫《儀式歌的藝術(shù)特點(diǎn)》(2003)有機(jī)地將吉爾吉斯民族儀式與音樂聯(lián)系起來,著重考察音樂和儀式的關(guān)系、音樂在儀式中的作用及意義等問題。R·Z·克德爾巴耶娃《吉爾吉斯口頭文化的形成史》研究了包括說唱、彈唱在內(nèi)的民間口頭文化的歷史。此外,作為一個(gè)游牧民族,幾乎每一首吉爾吉斯器樂曲背后都有一個(gè)精彩的背景故事[15],阿散·卡依比勒達(dá)《吉爾吉斯民間歌曲的傳說》(2000)和布達(dá)依別克·薩布爾《講唱藝人與民間故事》(2008)便是對(duì)歌曲背景故事的收集和研究。舞蹈方面,羅別爾特·哈桑諾維奇《吉爾吉斯民間舞蹈》(1991)較為全面地研究了吉爾吉斯族傳統(tǒng)舞種的動(dòng)作、內(nèi)涵等。在2004年,吉爾吉斯斯坦還舉辦了旨在保護(hù)傳統(tǒng)音樂的學(xué)術(shù)會(huì)議,再次強(qiáng)調(diào)了民族音樂保護(hù)工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此次會(huì)議的論文集由阿曼諾娃整理出版。[16]
音樂史方面,切列德尼琴科·達(dá)吉雅娜·瓦斯列維娜的《古代音樂文化》(1996)將音樂納入了“民族文化”這個(gè)更大、更具底蘊(yùn)的范疇中,試圖用本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來闡釋本民族音樂的“獨(dú)特性”;巴拉巴依·阿拉古少夫的《吉爾吉斯百年弦樂》則研究了百年吉爾吉斯弦樂的演變,并較為客觀地分析了蘇聯(lián)思潮對(duì)吉爾吉斯弦樂帶來的影響。
史詩《瑪納斯》的演唱也具有音樂性質(zhì),因此關(guān)于《瑪納斯》的研究也往往與音樂有關(guān)。后蘇聯(lián)時(shí)期,吉爾吉斯斯坦政府為了填補(bǔ)意識(shí)形態(tài)的真空,大力弘揚(yáng)史詩《瑪納斯》和瑪納斯精神,《瑪納斯》研究也因此迎來了一個(gè)新高潮。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艾山吐爾·阿布都德力德耶夫《史詩<瑪納斯>的歷史層次》(1999),阿依聶克·加依納闊瓦《史詩<瑪納斯>的封建因素》(1997),薩馬爾·本薩耶夫《部落時(shí)期的史詩<瑪納斯>》(1999)等,這些研究皆部分涉及了音樂的內(nèi)容。莫勒多哈孜耶夫《卡尼凱的駿馬與托泰如一同奔馳——著名瑪納斯奇薩雅克拜·卡拉拉耶夫的表演藝術(shù)——附樂譜》(比什凱克,1995)和巴勒拜·阿拉古什夫《瑪納斯的音樂》(1995)是專門針對(duì)《瑪納斯》音樂的研究。而關(guān)于《瑪納斯》的兩次國(guó)際會(huì)議論文集《瑪納斯史詩一千年紀(jì)念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論文集》(阿斯卡爾歐夫編著,1995),《史詩<瑪納斯>的問題研究》(阿依聶克·加依納闊瓦編著,1999)也收錄有關(guān)于《瑪納斯》音樂的研究文章。
以上研究成果皆是民族意識(shí)復(fù)興思潮的產(chǎn)物,其中既有專門研究音樂的著作,也有關(guān)于文學(xué)、口頭傳統(tǒng)等其它民族文化方面的研究,說明民族意識(shí)復(fù)興的思潮并非僅出現(xiàn)于音樂學(xué)科,而是各個(gè)學(xué)科普遍存有的一種思想狀況。在該思潮的影響下,民族音樂研究領(lǐng)域的各個(gè)角度、各個(gè)方面都產(chǎn)生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主要特征是:往往回避蘇聯(lián)音樂的影響,注重強(qiáng)調(diào)吉爾吉斯斯坦傳統(tǒng)音樂的民族屬性。
另一方面,民族意識(shí)復(fù)興思潮主要得到了部分民族音樂家和民族音樂研究者的共鳴,并非所有音樂人都支持這一思潮;且這一思潮主要在學(xué)術(shù)研究層面發(fā)生影響,還未從根本上改變音樂表演和音樂教學(xué)實(shí)踐以蘇聯(lián)音樂模式為基礎(chǔ)的狀況。但隨著近年民族意識(shí)的升溫,從學(xué)者到普通民眾,從老師到學(xué)生,越來越多的吉爾吉斯人都逐漸受到了該思潮的影響,因此恢復(fù)民族傳統(tǒng)的嘗試會(huì)在學(xué)者的推動(dòng)下不斷上演。
注釋:
①庫姆孜琴是一種三弦彈撥樂器;科亞克琴是二弦拉弦樂器;楚兒(又譯作“潮爾”)是草本植物制作的吹奏樂器;鐵木爾·庫姆孜是口弦,有木制和金屬制兩種。
②B·維諾格拉多夫《A.扎塔耶維其和吉爾吉斯民間歌曲和器樂曲》,莫斯科,1971年,第30頁。
③ 庫熱尼凱耶夫(1860—1949),著名民間藝人。出生于一個(gè)民間藝人世家,其祖父別列克和他的父親庫熱尼凱(1826—1927)都是著名的民間藝人。他從小就學(xué)會(huì)了庫布孜、科雅克、潮爾等多種民族樂器,他的科雅克技藝尤其高超,可以模仿諸如動(dòng)物哭聲、雷電風(fēng)等自然音聲以及部分人類語言的聲音,民間流傳著“庫熱尼凱耶夫的科雅克琴聲可以說話”的諺語。庫熱尼凱耶夫幾乎傳承了所有類型的傳統(tǒng)民間音樂,尤其在傳承儀式音樂方面貢獻(xiàn)突出。
④19世紀(jì)50年代,哈薩克學(xué)者喬坎·瓦利汗諾夫和著名俄國(guó)德裔學(xué)者拉德洛夫便開始收集《瑪納斯》,兩人記錄了史詩片段《闊闊拖依汗的祭奠》,并對(duì)其展開學(xué)術(shù)研究。但《瑪納斯》更為集中、系統(tǒng)地記錄始于十月革命之后。
⑤奧諾孜巴克夫(1867—1930),著名瑪納斯奇,在年少時(shí)就曾聽過別勒穆拉提·庫勒瑪諾夫(1793-1873)等杰出瑪納斯奇的表演,這對(duì)他后期個(gè)人風(fēng)格的形成有重要幫助。與其他史詩表演者不同,奧諾孜巴克夫有深厚的文學(xué)功底,他在幼年便以即興詩歌創(chuàng)作而知名。他演唱的版本長(zhǎng)達(dá)25000行,是迄今最為完整的《瑪納斯》第一部的版本。
⑥薩雅克拜·卡拉拉耶夫(1894—1971),著名瑪納斯奇。他曾跟隨同鄉(xiāng)著名瑪納斯奇喬依凱·吾木爾歐夫(1863-1925)學(xué)習(xí),并在1924年成為一名瑪納斯奇。
⑦葉兒·吐什托克:吉爾吉斯古代民族英雄。至今流傳著以其為主人公的史詩《葉兒·吐什托克》。
⑧ 阿布都拉斯·瑪勒德巴耶夫(1907—1978),吉爾吉斯最為杰出的作曲家和歌唱家之一,被認(rèn)為是吉爾吉斯現(xiàn)代音樂的奠基人,1930年開始任伏龍芝音樂學(xué)院院長(zhǎng),1939—1967年間任吉爾吉斯作曲家協(xié)會(huì)主席,1953—1954年任吉爾吉斯音樂芭蕾舞學(xué)校校長(zhǎng),期間于1940—1947年在莫斯科音樂大學(xué)學(xué)習(xí)。他的女兒吉勒得孜(1946.6—)被認(rèn)為是吉爾吉斯斯坦第一位女性作曲家。
⑨先琴科《瑪勒德巴耶夫的歌曲創(chuàng)作》,伏龍芝:吉爾吉斯斯坦,1977年。
⑩卡里·莫勒多巴散耶夫,吉爾吉斯著名作曲家,1928.9.28生于納倫州鐵列克的一個(gè)著名阿肯家庭。在童年時(shí)期,他便可以演奏多種民族樂器。成年后,他進(jìn)入吉爾吉斯國(guó)立音樂與舞蹈學(xué)院學(xué)習(xí)指揮和編舞。之后他又在莫斯科音樂學(xué)院進(jìn)修,指導(dǎo)老師為金茲布爾克,并于1954年畢業(yè)。1966-1973年間,他成為吉爾吉斯國(guó)家歌劇院和芭蕾舞劇院的主要指揮和吉爾吉斯作曲家協(xié)會(huì)(1979-1997)的核心。
[11]別格里耶夫·木拉提,1955年出生于納倫州敏庫什村,他先后就讀于以M·阿伯德拉耶夫命名的音樂小學(xué)、伏龍芝市國(guó)家音樂專業(yè)學(xué)校、吉爾吉斯斯坦國(guó)家藝術(shù)學(xué)院等,自1977年開始,赴莫斯科音樂學(xué)院就讀本科和研究生,先后學(xué)習(xí)過單簧管、小號(hào)、鋼琴、音樂理論、作曲等專業(yè)。自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以來,他的音樂創(chuàng)作便在整個(gè)蘇聯(lián)中嶄露頭角,并曾先后榮獲以托克托古勒命名的國(guó)家音樂大獎(jiǎng)、“瑪納斯”獎(jiǎng)等國(guó)家級(jí)獎(jiǎng)項(xiàng),及俄羅斯、德國(guó)、瑞士等國(guó)頒發(fā)的國(guó)際獎(jiǎng)項(xiàng)。
[12]史詩《瑪納斯》表演的宗教性質(zhì)體現(xiàn)在多方面,比如瑪納斯奇往往是通過英雄托夢(mèng)的形式走向表演生涯的;在表演時(shí),他們的精神聯(lián)系于另外一個(gè)世界,并會(huì)進(jìn)入精神恍惚的狀態(tài);《瑪納斯》表演還會(huì)影響聽眾的情緒,將聽眾引向狂熱等。《瑪納斯》和瑪納斯奇對(duì)于吉爾吉斯族還有著特殊的意義:《瑪納斯》在民族中扮演族譜的角色,其歌詞中含有大量民族信息,有強(qiáng)烈的民族標(biāo)志性;瑪納斯奇往往具有高度的社會(huì)影響力和號(hào)召力,甚至充當(dāng)著部族的精神領(lǐng)袖,這些無疑都有悖蘇聯(lián)的政治需要。
[13]該校是目前吉爾吉斯斯坦最為著名的音樂學(xué)校,幾乎當(dāng)今吉爾吉斯斯坦著名的音樂表演和理論家均出自該校。
[14]目前吉爾吉斯斯坦從小學(xué)至研究生教育所用各等級(jí)教材均為“五線譜”教材,比如瑪?shù)戮S洛娃·麗瑪、安德列·吉?dú)W吉維奇·庫茲涅佐夫《吉爾吉斯鐵木耳庫姆孜教材》(是吉爾吉斯斯坦第一部鐵木兒·庫姆孜教材,伏龍芝,1988),努拉合·阿布都熱合曼《阿布都熱合曼·諾夫樂曲作品集》(比什凱克,2009),未署名《吉爾吉斯斯坦兒童音樂學(xué)校教程》(比什凱克,2003)等。
[15]游牧民族器樂曲既有單純的器樂演奏,又有彈唱曲目,前者往往有背景故事,后者往往有引言或序曲。
[16]阿曼諾娃等《傳統(tǒng)音樂的歷史、保護(hù)與發(fā)展國(guó)際會(huì)議論文集》,比什凱克:Kyrgyz National Conservatory,2004年。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