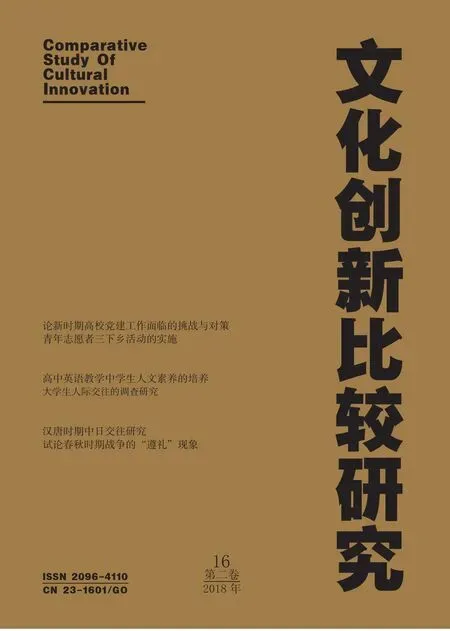淺談“太一辟兵”與刑罰的關系
朱榜燕
(上海大學,上海 200444)
馬王堆三號墓出土帛書《神祇圖》一出土就引發了學界熱烈的關注,李零先生和李家浩先生兩人的爭論也一直持續,認為此圖是“太一避兵圖”。此《神祇圖》為神出行時圖像。帛書長43.5厘米,寬45厘米,出土時帛畫與約12萬字帛書一起折疊放置在槨室中。
1 “太一”與“避兵”的關系
筆者認為首先需要先弄清楚太一與兵之間的關系,不能因為一個“避”字就斷定。饒宗頤先生提出質疑,認為在畫史上,曾有兩幅關于太一和兵的關系的畫,可以證明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據張彥遠《歷代書畫名記》載,用腳趾畫神獸的后漢張衡所畫《太一三宮用兵成圖》,另外就是南宋有“梁瘋子”之稱的梁楷的《太乙三宮用兵陣圖》,載于厲鄂的《南宋畫院錄》。兩者皆言用兵,而不言避兵。
筆者再添一例,即《隋志》錄有《太一三宮兵法立成圖》,置于兵陰陽書類下。筆者認為,不僅在畫史上,在兵書類的歷史記錄中,也是言“用兵”。《隋志》中:“《太公三宮兵法》一卷,梁有《太一三宮兵法立成圖》,二卷。《太公書禁忌立成集》,二卷。《太公枕中記》一。”其下還有“梁有《辟兵法》一卷,《黃帝太一兵歷》一卷”的記載,其下還有:“《太一兵書》一十一卷”一條,皆列于《隋志》兵書類,《隋志》總結右一百三十三部五百一十二卷的兵書時候說道:“兵者,所以禁暴靜亂者也。易曰: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周官大司馬掌九法、九伐以正邦國,是也。然皆動之以仁,行之以義,故能誅暴靜亂以濟百姓,下至三季,恣情逞欲,爭伐尋常,不撫其人,設變詐而滅仁義,至乃百姓離叛,以至于亂。”此言明上列的圖書都是用兵之書,太一與兵的關系是太一用兵。用兵目的是為了征伐,誅暴靜亂。筆者找到最初記載太一用兵的書籍,《漢志》兵陰陽家下列有《太壹兵法》一篇,《天一兵法》三十五篇。也確實都是用兵之書,不是避兵。
兵,“兵”本武器之義,《說文》:“兵,械也。 ”,所出土甲骨文與殷周之金文可見,確為兵器,戰爭之指稱在戰國才發生,中國古代語言中卓有引申借代之用法,故而后有以兵借代戰爭之用,如《孫子兵法》:“兵者,國之大事也。”戰國之際兵燹連綿,死于兵者多是死于戰爭,人們往往用“兵死”來指稱死于戰爭中的人,故而有戰爭的意義。后又因戰爭之義衍生出武力之義,如新郪虎符銘文:“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王符,乃敢行之。”兵到漢代,才通行為“戰爭”和“士兵”的意思。“辟兵”應當解釋為用兵,兵即武力,表代天行刑以討伐亂臣。而“辟”本身也表示刑罰。
李零先生所舉證的 《抱樸子·內篇》:“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樸子答曰:“吾聞昊大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書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為先登鋒陷陣,皆終身不傷。”這段描寫中很明顯地寫了“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為先登鋒陷陣”,意思是皇帝令左右的數十個人書寫了北斗字及日月字,能夠使沖鋒陷陣后沒有任何的傷害,是以這是需要沖鋒陷陣的人才書此字,登鋒陷陣者,就是需要戰斗的人,是現實的戰斗,如果書此符的目的是讓敵軍退卻,不敢進攻,那么沒有交刃,怎么能稱作登鋒陷陣呢?就更不需要強調“終身不傷”了,只需要說無兵敢犯即可。巫鴻先生提出人死后的靈魂有“二重”旅行,第一重是跟隨出殯的隊伍,第二重是靈魂死后升仙的旅行。根據此圖中有四名武弟子(據李零先生釋義,武弟子為四人總稱)的題記讓我們知道似乎人死之后靈魂出行會受到來自百兵的傷害。其右起第一人執戈,第二人執劍,第三人未執兵器,但是身披似甲胄之物,第四人執戟。尚且不論四武弟子身份到底為何人,亦不管太一神到底為誰,在僅存的可以確定的文字中,可以判斷,死人魂靈出行容易受到的傷害。武弟子像之三題記:“我虒裘,弓矢毋敢來。”“虒裘”者,按此當理解為某種甲胄,武弟子四題記已殘,難以看清,然可認為魂靈出行似乎會受到弓矢的傷害。
另據總題記:“……□承弓,禹先行,赤包白包,莫敢我鄉(向),百兵莫敢我[當]。□□狂謂不誠,北斗為正。即左右唾,徑行毋顧。太一祝曰:某今日且行,神(從之)……”根據這一條的文字,我們似乎也可以確定死人靈魂出行會受到百兵的進弓。“赤包白包”釋為“赤豹白虎”,“鄉”即“向”,“莫我敢□”此殘字,饒宗頤和李零皆釋為“當”。“北斗”為北斗七星。“左右唾”,古人認為唾液能去鬼禳兇,“徑行毋顧”即言徑直向前走莫要回頭看,古代的巫術實施的時候,通常會有被施法者不能回頭看的要求。“太一”者,具體為何,尚無定論。“某今日且行,神(從之)”為祝禱之詞,其“神”字若隱若現“社”字,原亦因此而稱“社神圖”。“百兵莫我敢當”一句更明確的交代了魂靈出行主要受到的傷害便是兵死者鬼魂的騷擾。另有武弟子題記:武弟子像之一題記:“武弟子,百刃毋敢起,獨行莫[理]”這條的記載也可以知道死人靈魂出行似乎會受到刀刃的傷害。
2 漢代巫術中的指罪壓勝
李零先生曾經舉例漢武帝伐南越的時候舉行的告禱太一的儀式目的就是避兵,確實,但是主要是利用了刑罰的威懾功能,令百鬼退卻。《漢書·郊祀志》:“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泰一鏠,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廼誅五利。”此條記載取自亡佚的《史記·武紀》,為元成年間褚先生補缺,因而采用《漢書·天文志》記載的內容。此處特意指明了以荊畫幡,牡荊原本是刑具,此儀式是漢武帝討伐南越而舉行的,討伐是“大刑用甲兵”的表現,中國古代的法律思維有著自然主義的傾向,認為刑自天出,拿到了上天的旨意的人就可以成為神使,代行上天懲罰對方的意旨。
葛洪在《抱樸子·內篇》中所列出的十二條避五兵之道中有八條都只是佩戴符,惟 “牡荊以作六陰神將符”這一條記載,后有“符指敵人”一句,亦就是說其他的符都只需要佩戴在身,即可辟兵,唯牡荊作之六陰神將符相異,多出了一道“符指敵人”這一程序,在巫術之中,儀式的程序是非常重要的,葛洪斷然不會無緣無故隨意添加程序,必然是前人經驗的累積。漢代有持北斗之柄,指有罪之人的做法,《漢書·兵書略》:“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以為助者也。”其中的“隨斗擊”,是指以北斗星的斗柄位置判斷戰爭的結果,斗柄所在者勝,所指者敗。也因此可以知道,太史手中所握著的牡荊相當于北斗之柄。而總題記中有一句“北斗為正”,其實就是以北斗為刑罰的主要依憑。手中有北斗之柄,而太史奉以指所伐國,就是在給南越做了一個定罪的審判程序。一旦這樣的程序完成,南越就成了罪人,而自己出師“假鬼神以為助”了。這樣的做法也被用于陰間的“壓勝”法術,《漢書·王莽傳下》:“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眾兵。”
這樣的靈魂出行反而更像是出行打仗,如果具象化一下這張圖背后應對的陰間圖像,似乎敵方都是手持兵器之鬼,但陰間的百鬼的傷害未必只是武器的傷害。死者靈魂從進入陰間之后的旅行就是從黃泉升入仙境而獲得永生。這樣的武弟子的存在,更應該是以壓制暴亂的形態出現。現今我們在觀看這張圖的時候,會自然的代入自己的角色,但是這張圖本身是放在墓中的,它面對的是那些潛在的傷害,所以這張圖是為百鬼而設的,不是給我們看的,也不是給死者的靈魂看的。從戲劇的角度,百鬼這些潛在的危害才是主要的觀看受眾。這張圖所起到的作用應該是恐嚇,令百鬼退下而不敢傷害。
“兵刑同源”,古之出兵討伐是取上天旨意,出師有名,這是“大刑用甲兵”的觀念遺存。其實這樣的做法不僅僅是在這張“太一辟兵圖”,同墓東邊廂一長方形漆奩中而這一組武弟子圖與曾侯乙內棺漆畫上的一組圖十分相似。畫有利于靈魂出行的門窗的曾侯乙墓內棺畫上,亦有四人執戈立于棺畫上,其上有四只大鳥。這樣執戈的人的存在就是為了保護出行的安全,其手中有的刑罰的權力能夠讓百鬼退后。之所以能起到這樣的作用,是因為刑罰本身對于觀看者的內心所起到的震懾作用,也因此在用兵討伐之前,必有檄文。
3 “避兵”可能與社前行刑有關
遠古行軍中會隨時攜帶“祖”“社”,是為了隨時對犯教之士兵行刑。此圖中間的神像標有“大一”(但又標“社”字,此“社”字還比較大),“某今日且行,神(從之)”為祝禱之詞,其“神”字若隱若現“社”字,原亦因此而稱“社神圖”。我們知道“社”為農業祭祀,而在四個武弟子之上的神人旁邊有“社”字。《虞夏書·甘誓》:“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書序》說這是啟和有扈氏戰于甘之野,作甘誓。文中的“王”即夏啟,他指責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所以他奉承天命對有扈氏降下刑罰,如果戰爭中有人犯教,則在社前殺害他。這段記載雖然在《墨子·明鬼》中被引為《夏書禹誓》,但是其中關于“戮于社”的記載并無二,筆者引用當沒有問題。《太平御覽》引《摯虞決疑要注》:“古者帝王出征伐,以齊車載遷廟之祖及社主以行。”在這里“社主”的功能更像是一個刑罰的見證者。“掌管懲罰的不是大社之神,而是君主的個人之神“王社”——處罰權實際上是集權的基本表現。”先秦時候的社有聽訟的功能,《周禮·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社主并不僅僅是表現了土地崇拜,社還有作為刑罰的見證者這樣一個角色,見證者有處罰違反任何契約的任何一方的權力,在刑場的四個重要角色中屬于判定的角色,也就是犯罪定義的認證。
古代出門前的“軷祭”,有一特殊的禮儀程序,就是將一犬置于道路上,以車輪磔之,即可起到保護出行的作用。而此圖中“弓矢勿敢來”、“百兵莫我敢鄉”以及“百刃毋敢起”這些語言更是處于一種絕對自信的命令,漢墓中還常見一種鑄有“辟兵莫當,除兇去央”銘文的銅辟兵符。 “除”即“消除”,“去”即“驅逐”,都是為了將災害在出行的周邊消失。1960年5月出土于湖北荊門一座戰國墓的“兵辟太歲戈”上所畫的就是一個頭帶四羽之冠,兩足踏日月,左右手各握一蛇,雙耳珥蛇,腰纏兩蛇,胯下還有一蛇的神人形象。此神人的形象中操蛇,李零先生用此戈證明馬王堆出土的《神祇圖》是“避兵圖”,但是筆者以為,這更像是畫太歲之形,使太歲降臨,或者招來太歲之神力的意圖,是“假鬼神以為助”的用法。在死人靈魂出行的時候,用這樣的圖像和語言來恐嚇鬼,是利用了這樣的權力壓制的思想。
對人鬼關系的思考是人們在現實世界中觀念的投射,古代人們認為鬼會害怕刑具,不是鬼害怕,鬼使不存在的,產生害怕心理的是人類。中國的刑場是戲劇性的刑場,中國古代的行刑是公開的。廖志敏先生認為,這樣一項刑罰的活動中涉及的角色就有四方,一是作為犯罪的定義者,即國家,一是犯罪的實施者,一是被害人,一是觀眾,也被稱為潛在犯罪者。刑場的存在是國家故意設定的,不但是為了懲罰犯罪的人,更是為了教育潛在犯罪者,令其產生恐懼的內心而不敢再次犯罪。陰間出行采用太一避兵也正是因為這樣,避即辟也,而辟也應當是解釋為刑罰才更為合適。而那些靠近的百鬼其實正是觀看者的角色。
4 結語
筆者以為,“太一辟兵”的內涵很可能是“太一”用刑,而社神很可能就是一個刑罰的見證者的角色,故而在太一神的旁邊會有一個較大的“社”字。這是古人對刑權的內涵的理解,認為刑權不僅僅是掌握了生殺大權,其懲罰的功能更能達到震懾的作用。
[1]班固,撰.漢書[M].顏師古,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
[2]魏徵.隋書·兵書志[M].北京:中華書局,1973.
[3]墨子,著.新編諸子集成:墨子校注[M].吳毓江,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
[4]李昉.太平御覽[M].北京:中華書局,1960.
[5]李零.中國方術續考[M].北京:中華書局,2006.
[6]廖志敏.刑場上的國家、民眾與犯罪人——一種關系犯罪心理學分析[J].四川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4):17-22.
[7]孫武,著.孫子兵法[M].陳曦,注譯.北京:中華書局,2011.
[8]巫鴻,著.黃泉下的美術:宏觀中國古代墓葬[M].施杰,譯.北京:三聯書店,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