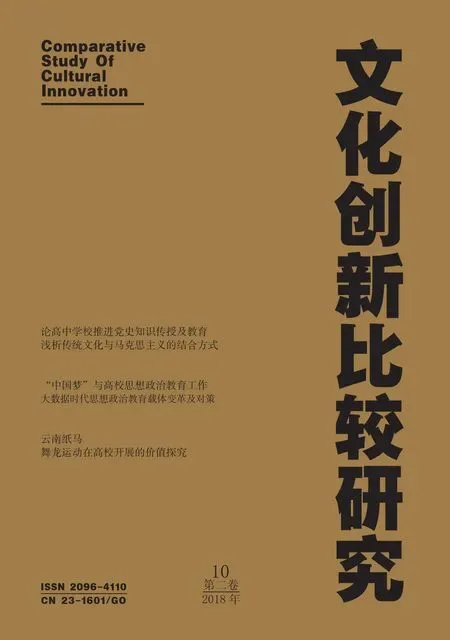女駕駛員身體形象中的政治話語與符號文化
——以梁軍為個案
米莉,曾巧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長沙 410083)
盡管精于“婦工”是傳統中國女性的四大理想品質之一,但大多限于織布、刺繡等與家庭相關的勞動,女性往往被排除在“技術”工作之外,長期處于社會分工的邊緣位置[1]。 近代以來,科技革命在帶來先進交通工具的同時,也促進了中國社會性別分工的發展。尤其是女性駕駛員的大量涌現,作為婦女運動和女權主義思想在近代中國發展的客觀產物,則在某種程度上縮小了性別分工的鴻溝,也體現了女性政治、經濟等社會地位的提高。
近代中國女性駕駛員的形成與發展深受國家權力建構的影響,亦隱含著社會文化的發展與推演,成為打破傳統性別分工、建構新的性別空間話語的有力武器。在這其中,自行車、汽車、火車、拖拉機、飛機等眾多交通領域女性從業群體數量日益攀升,也出現了許多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女性形象。本文將從新中國第一位女拖拉機手梁軍的案例出發,詳細闡述女性身體形象在這一時期的變化與發展,進而論述所展現出來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從整體上而言,梁軍作為新中國第一位女拖拉機駕駛員的出現,既是社會發展的自然結果,而其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大量出現在課本、報紙、電影、人民幣中,更隱秘蘊含著主流社會的文化建構。換言之,女駕駛員身體形象背后的符號文化,對于理解近現代中國思想觀念以及性別文化的變遷具有極其重要的管窺作用。
1 政治覺醒: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的雙重話語體系
將婦女解放納入民族解放的歷史進程,是中國婦女解放道路的重大特色[2]。近現代中國女駕駛員形成和發展,深受國家權力、階級、集體主義、現代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顯示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趨勢及其與民族解放之間潛在的邏輯關系,隱含著政治話語的某種建構與實踐。
對于婦女解放與勞動解放的關系,在中國共產黨建黨早期就已有所討論,如中共二大就曾指出:“婦女解放是要伴著勞動解放進行的”[1]。新中國成立之后,民族解放與婦女解放緊密聯系的特征,不僅使得婦女作為國家建設重要的一員,更是與勞動、生產、革命緊密結合起來,自上而下地嵌入了國家與民族解放的話語體系之中,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符號。
客觀而言,一方面,國家建設的需要使得女性就業領域不斷拓寬,另一方面,迅速恢復國民經濟的現實目標也要求婦女開始學習文化和農業技術,在此政治格局影響之下,城鄉婦女開始廣泛投入到國家建設中。而以交通部門為例,第一批女拖拉機手、女火車司機、女子包乘組、女火車調度員等不斷涌現[1],既是國家權力帶動、社會政治影響的結果,隱含著政治話語的主動建構,也是對于傳統性別分工的某種打破,跨越了性別空間秩序,體現了社會性別文化、思想觀念的變遷。
梁軍作為第一位女拖拉機手在北大荒的出現,正是這一時代的產物。作為當時耕地面積最大、機械化程度最高的墾區,北大荒是新中國最重要的商品糧基地,在保障糧食安全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1],因而開發建設北大荒也成為了新中國的一項重大發展戰略。梁軍作為北大荒第一位女拖拉機手,帶動了許多婦女加入農業生產的建設,不僅成為了北大荒開發建設的耕耘者之一,也推動了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為新中國建立初期國民經濟的迅速好轉發揮了積極作用[1]。
以梁軍為首的女拖拉機手和 “女子拖拉機隊”,肩負著婦女解放和國家建設的雙重歷史使命,并為新中國的機械化農業做出了極大貢獻。1952年,梁軍女隊所屬的4臺拖拉機,全年工作量為2700公頃,工作量比上年度增加91%,每臺拖拉機每公頃年均耗油量也比上年度降低2.1公斤。在北大荒的原野上,梁軍與女伴們經常唱著自編的 《開荒之歌》:“在這個花開的季節/開荒也很美/無數艱辛/無數阻礙/都阻止不了我們前進的步伐/開荒/讓我們共同開荒/開辟一片屬于我們北大荒的美好天地……”這首歌曾激勵著無數墾荒的婦女,也是她們對于自己所肩負的前所未有的社會工作和由之而來的自我滿足感的詮釋闡發。她們是民族解放與婦女解放共同作用的產物,她們是“女拖拉機手、拓荒者”的同時,也成為了無數“新婦女的典范”[3]。
2 個體自覺:以個人努力來承擔國家解放之宏大命題
以梁軍為代表的女駕駛員形成和發展的過程,無疑體現了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之間的潛在邏輯關系問題:一方面,婦女解放運動是民族解放運動的要素之一,婦女解放深受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推動,有利于民族解放的發展;另一方面,婦女解放雖然在很多時候被納入民族解放的歷程,但它也在沿著自身的軌跡向前發展。其中,個人、國家、社會,這三種因素在橫向空間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運作體系及文化網絡,在這個體系和文化網絡中,個人雖位于最底層,卻有著不可否認的主動地位;國家處于最高點,所有體系運作的最終落腳點是國家;而正是通過社會,國家和個人之間發生了最緊密的連接。
對于梁軍這一個案而言,除了國家建構的宏觀背景之外,她通過個人努力來戰勝種種困難,最終參與社會勞動進行國家建設的故事以及以生命歷程為主線所形成的符號文化背后,也映射出了女性在這一時代背景下追求自我發展的個體自覺。正是這種個體自覺,不但推動著個體的解放,而且也推動著國家解放的宏大歷程。
1930年3月,梁軍出生于黑龍江省明水縣的一個貧苦家庭,在同伴的眼中“高高的個子,一身灰衣服,戴一頂舊草帽;圓、胖而紅的臉常常在笑,大眼,兩道快要立起的眉毛顯出了她是個個性強、有毅力的女孩子[1]。”對于梁軍來說,成為女拖拉機駕駛員并非易事,這條道路漫長且充滿著反抗精神,尤其是她對裹小腳和童養媳身份的反抗,是她突破傳統社會對于女性空間的種種限制而成為女拖拉機駕駛員的轉折點。
梁軍幼時,裹腳之風在她家鄉還比較盛行。當她七歲時,父母也開始準備給她裹腳。梁軍的祖母是小腳,祖母的腳布壓在梁軍一生的記憶中:“祖母總是踮著小腳,……梁軍和她抬水,一次也只能抬半桶,一來是梁軍的力氣有限,二就取決于祖母可憐的小腳,走幾步就要歇一歇[4]。”于是在梁軍的堅決抵制下,她那被纏了一段時間的腳被解放了,相比之下,她的許多伙伴卻并沒有這個運氣。梁軍的反纏足行動已然開始體現出她崇尚自由、追求自我的個體意識初步覺醒。而她對于包辦婚姻的反對,則進一步顯示了其個體自覺的不斷成長與發展。
1941年,母親為了換取兒子娶媳婦的彩禮錢,不得已將梁軍送到曹家當童養媳。梁軍在反抗無效后堅決地對母親說:“媽媽,讓我訂婚可以,曹家有錢,對我印象好,必須得先讓我上學[5]!”最終,梁軍借著同意當童養媳所換來的機會,去鄉村學校開始了學習生涯,從而為日后成為女拖拉機駕駛員奠定了基礎。盡管梁軍對于童養媳身份的反抗并沒有取得即時的效果,表明了女性個體自覺依然受到社會經濟、思想文化、國家發展的現實制約(婚約直到1952年才最終解除),但也初步體現出了梁軍追求身心獨立的文化自覺和對于傳統處境的自我救贖[6]。
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深受蘇聯模式的影響,而蘇聯第一位女拖拉機駕駛員巴莎打破傳統性別制度的制約,擴寬女性職業范圍,也給了梁軍諸多啟發。在巴莎“10萬女性上拖拉機”的號召下,蘇聯總共出現了20萬名左右的女拖拉機手。1947年梁軍觀看了影片《巾幗英雄》,該片描述了主人公巴莎駕駛拖拉機開荒種地,為國家為集體農莊發展做出貢獻,駕駛坦克同德軍奮戰的英雄事跡。隨后,梁軍寫了一篇《像英雄巴莎學習》的心得,表明向她學習的堅定心意。在梁軍看來,第一,巴莎通過個人努力打破傳統性別制度成為女拖拉機駕駛員,體現了女性的個體自覺和自我意識的提高,推動了婦女解放的進程;第二,巴莎在成為女拖拉機駕駛員之后,也對國家經濟建設作出了貢獻,有助于國家和民族解放。
1948年,梁軍力排眾議,加入了黑龍江省委興辦的拖拉機訓練班,成為了其中唯一的女性學員。開課之前,她也曾遭遇歧視和偏見,因為培訓班不收女學生,她專門去找校長理論時,校長說到:“開拖拉機太臟、太累,生理上又不允許……[7]”當她堅持加入學習,到后面開始上課時,男學員們也都用異樣的眼光看著梁軍,質疑道:“女人也能開火梨?(拖拉機的別名)”但是培訓班里的指導員楊清海倡導婦女解放,認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主要任務是追求婦女在政治上的解放和平等。在他的支持下,梁軍頂住壓力,經過兩個多月的刻苦努力,終于成為了新中國第一名女拖拉機手[8]。
從某種意義上說,梁軍將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發展緊密聯系,以個體努力來承擔國家和民族解放的歷史重任,無疑體現了她個體意識與個體的不斷覺醒和日益提升。然而需要意識到的是,這種個體自覺也是建構在國家、民族的發展脈絡之中的,往往會因國家、民族的宏大敘事進程而被外界所忽略。因此,梁軍的個案也在向我們表明,提高對女性個人意識的關注和主動性的挖掘,對于整個國家的發展建構具有某種重要的意義,也將有利于女性政治話語權的不斷提升。
3 “獨立女性”:國家文化建構中的身體形象
在尼采看來,身體作為社會性的存在,是各種力量發生與開展的基本空間場域[10]。換言之,人們的身體形象是社會建構的產物,而近現代中國女性的身體形象與文化建構,也與民族國家的文化想象與社會建構具有不可分割的關系。新中國成立初期,不僅民族國家的解放與發展需要女性的參與,而且女性尋求自我解放的過程也需要得到民族國家的認可與支持。因此,在民族國家的文化建構之下,以梁軍為代表的女駕駛員的身體形象呈現出了獨立、自由、彰顯個體權利的基本特征。
1950年,梁軍所在的萌芽農場作為北大荒農墾事業中的典型農場,在農業方面取得了大豐收。在給毛主席的匯報中梁軍寫到:“開的荒地都種上了,又開了一千坰荒地……毛主席,我們現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家底也大了,現在我們親手開出來的土地有1500坰、房子100間、制粉場一個、油房一個、鐵工廠一個、馬80匹、大車12臺、汽車3臺、拖拉機10臺,……[11]”出于對梁軍的宣傳贊揚,《人民日報》關于這些事跡的報道在社會上、尤其是女性群體中引起了廣泛積極的回應。在她的影響下,女拖拉機手逐漸增多,越來越多的婦女開始成為“女拖拉機手”和“北大荒建設者”。1950年6月3日,德都萌芽鄉村師范學校宣布成立了新中國第一個女子拖拉機隊——“梁軍女子拖拉機隊”。而在北大荒,繼梁軍之后全國第二個女拖拉機隊——國營通北農場第二生產隊也櫛次出現。這些女性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國民經濟作出了貢獻,也由此而被譽為了“新婦女的典范”[10]。
女拖拉機手的不斷增多和若干女子拖拉機隊相繼成立的背后,反映了女駕駛員這份職業越來越受到婦女歡迎,也逐漸得到了社會、國家的認可。相比較傳統社會而言,女駕駛員的身份和角色,延伸了女性傳統的私人生活空間和公共活動空間,擴展了女性的職業范圍,促進了社會性別分工,也塑造出了一種自由、獨立的女性形象。而作為“新時代的獨立女性”所被塑造出來的積極形象,正是國家、社會所需要的正面人物,通過提倡新的獨立女性形象和貢獻,國家的經濟與文化得到了更大的支持和發展。與此同時,通過國家的正面肯定與積極呼吁,婦女也實現了個體空間的重要拓展。換言之,女駕駛員的身體形象與民族國家的文化建構之間展現出了不可分割的緊密關聯,女駕駛員不僅實現了身體與技術的交融,具有身體流動性,而且也縮小了性別分工的鴻溝,促使女性的政治、經濟權利得到提升。
梁軍一生獲得的榮譽無數,1949年10月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1950年以“梁軍”命名的女子拖拉機隊成立,梁軍擔任隊長,1954至1966年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多次獲得全國、省、市級勞動模范光榮稱號,2009年當選共和國成立六十年來最具影響力的勞動模范之一……除了獲得各種榮譽,梁軍還活躍在各個政治領域,曾訪問蘇聯、赴日本考察,后期的職業范圍也得到了大大拓展,如1960年10月擔任哈爾濱市香坊區農機局副局長,1988年成為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兼任市農機局總工程師[11]。通過獲得榮譽與參加活動,梁軍以一種不同于傳統婦女的角色而向社會展現出一種積極正面的獨立女性形象。成為文化標桿后的梁軍在代表著個人形象的同時,也代表著國家發展的積極努力,而這種嶄新的女性形象正是國家所努力塑造的國家形象的重要內容。通過國家建構,女性個人的身體形象得到了完善,女性權利在得到鞏固的同時地位也有所提高,并將進一步推動良性性別文化體系的建構。
4 符號文化:現代性別消費視野下的梁軍形象
在梁軍的典范性人物形象被確立之后,她開始以各種方式出現在課本、報紙、電影、人民幣、郵票中。1949—1953年,梁軍的故事被編進小學《國語課本》教材中;1950年,以她為原型的紀錄片“女拖拉機手”開始拍攝,梁軍親自參演,并以“新中國第一位女拖拉機手、北大荒建設者、女勞模、新婦女的典范”等形象出現。“女拖拉機手”在全國公映后,梁軍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1960年,一元券正面“女拖拉機手生產圖”將梁軍作為原型,并于1962年正式發行;1970年,以梁軍為原型設計的郵票發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梁軍所代表的這種特定的符號文化,在當代商業社會對于經濟利益的追求中,也開始遭遇過度消費的困境,并進而被利用為可以牟利的商業因素。如吳小英曾指出:“女性的身體、外貌和角色在消費文化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市場將傳統女性的角色定位推向極端[12]。”現代消費文化中極具特色的廣告,其重要策略便是將女性身體所展示出來的青春、美麗、性感、健康等形象與所推銷的產品緊密結合,從而使得這些形象成為消費社會中可供牟利的重要商業文化因素。梁軍作為早期“新婦女的典范”的積極正面女性形象,也開始受到許多廣告代言商的青睞,如沈陽的《晚晴報》,正是利用梁軍身上自由、獨立的新女性形象,未經本人同意而在其所刊登的“仲景視神明目貼”的廣告中盜用了梁軍的一張半身照,且該照片代言的藥品為假藥。為了維護權益,梁軍于2008年5月將晚晴報社起訴到法院,中央電視臺還對此進行了跟蹤報道,官司歷經一年半,梁軍的形象保衛戰最終獲得了勝利[13]。
毫無疑問,廣告并不僅僅是商品的推銷與展演,更隱含著社會的性別文化建構,進一步而言,這種建構在女性身體形象建構之上的性別化消費,已然由于其隱含的巨大商機而成為消費社會的重要特征之一。對于梁軍而言,其在當代商業社會的女性身體形象被過分渲染,無疑在某種意義上導致了其原本性別角色和性別定位的失真和扭曲,而這種建立在性別消費基礎之上的營銷也從側面體現了一種新的性別角色固化。這種性別角色固化不但沒有加深人們對女性的理解,反而由于將女性的身份和社會角色單一化而愈發引發了新的不平等,這種發展趨勢無疑值得受到進一步的反思。
5 結語
如前所述,以梁軍為代表的女性駕駛員的大量涌現并活躍在各個領域,表明了建國前后女性自由身份、獨立形象和政治話語權的提升,也展示了女性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的不斷擴展,從側面折射出了近代中國社會性別分工的發展脈絡。
從宏觀意義上而言,這種獨立的女性形象、自由的職業身份的出現,與整個國家對于民族解放、社會發展的追逐歷程和文化建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但仍然需要意識到的是,如果僅僅將這種身體形象與民族國家的想象和建構等同起來,將她們置于國家、民族的至高點而忘卻了作為獨立個體的積極努力和自我嘗試,無疑將會落入重視表面歷史現象而忽略其背后真實話語的思想窠臼。正如杜贊奇的復線歷史觀所表明的那樣:“看似清純或連續性的歷史語言背后,掩蓋著對不同意義的利用[14]。”從這個意義上說,女駕駛員的形成、發展與身體形象所體現的政治話語與符號文化,以及內在所蘊含的批判性、連續性、繼承性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謝瑞蓮.淺探女性被邊緣化的根源[J].大觀周刊,2011(31):20.
[2]韓賀南.中共將婦女解放納入民族解放的歷史必然性及理論支撐[J].中共黨史研究,2012(6):165.
[3]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史研究室.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鄧穎超.新中國婦女前進再前進[N].新中國婦女,1952-10-05.
[5]王晨力.試論中國共產黨對北大荒開發和建設的領導(1947—1978)[D].湘潭大學,2013.
[6]顧秀蓮.20世紀中國婦女運動史[M].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2013.
[7]顧雷.女拖拉機手梁軍[N].人民日報.1950-01-17.
[8]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東北籌委會編.模范青年團員故事[Z].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東北籌委會宣傳部,1950.
[9]王軍.梁軍傳[M].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12.
[10]張嶸.女性尊嚴在于個體自覺[N].東莞日報,2013-11-18.
[11]程亞麗.從晚清到五四:女性身體的現代想象、建構與敘事[D].山東師范大學,2007.
[12]1950年9月27日梁軍寫給毛主席的信[N].人民日報,1950-10-04.
[13]吳小英.市場化背景下性別話語的轉型[J].中國社會科學,2009(2):172.
[14]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