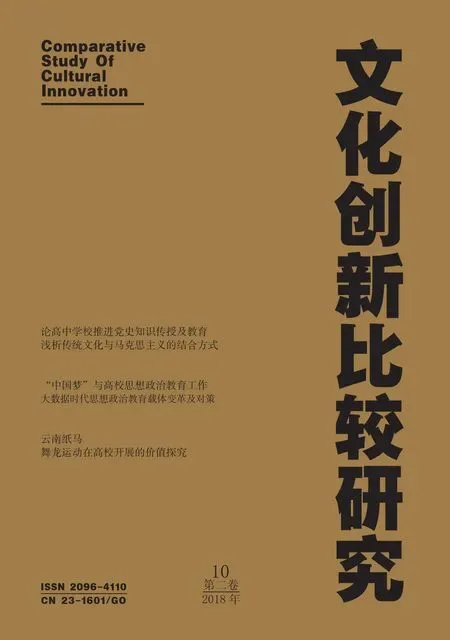從紅綠之爭到紅綠聯盟
——論戴維·佩珀的生態社會主義觀
祝玲玲,艾志強
(遼寧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遼寧錦州 121001)
佩珀作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第三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其《生態社會主義:從深生態學到社會正義》一書中,清晰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所蘊含的生態思想對于應對當代生態運動中環境議題的政治相關性的重要意義,并在此基礎上比較分析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與綠色分子的無政府主義社會,揭露了無政府主義社會的反人本主義和烏托邦色彩,從而建議綠色分子應該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實現與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即紅色分子的聯盟,最終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社會。
1 解決紅綠之爭的思想基礎
隨著傳統工業化與城市化生產生活模式的反生態本質和不可持續性特征的暴露,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生態運動已經成為西方新社會運動的主流,但是隨著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西方生態政治思潮出現了“紅綠之爭”。 “所謂的‘紅綠之爭’指的主要是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和生態主義者在關于實現生態社會方面的紛爭[1]。”在佩珀看來,“紅色的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充分利用了馬克思主義,而綠色的生態主義者則更多地受惠于無政府主義,以至變成了生態無政府主義者[2]。”并且佩珀認為,綠色分子主張建立的生態無政府主義社會是一種反人本主義,其將自然神秘化的論調與做法最終將導致生態無政府主義淪為無法實現的生態烏托邦社會。因此,佩珀主張實現 “紅綠聯盟”,即將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學思想作為紅綠聯盟的思想基礎,從而實現生態馬克思主義和綠色無政府主義積極因素的結合。
佩珀明確肯定馬克思主義蘊含了豐富的生態學思想,并著重分析了馬克思生態思想中兩個對紅綠聯盟具有啟示意義的理論視角。
第一個視角涉及到物質生產和集體斗爭對于實現社會變革的重要性。其一,社會變革依賴于生產力的狀態。馬克思反對僅僅作為觀念進步的歷史觀,他強調“物質生活中的生產方式決定著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生活進程的一般特征”[3]。因此物質生產是馬克思主義歷史概念的起點,物質生產構成了所有社會的基礎。佩珀認為這一理論對于生態運動是重要的,因為它表明生產方式構成了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方式。因此,我們若想改變目前人與自然異化的關系,不僅要尋求人們思想意識的改變,而且更加重要地是要看到思想意識的改變對于物質生產和經濟生活的依賴關系。只有如此,方能克服西方綠色分子的“意識決定論”,即人們在自然界中的實踐活動將隨著個人意識的變化而變化,把社會變革寄希望于個人價值觀變化的思想。其二,針對綠色分子將個人作用“神圣化”的做法,佩珀更加重視馬克思的社會變革集體觀。馬克思曾明確指出:“任何人想要變革社會,就必須清楚意識到社會變革如何與集體的政治斗爭相關[3]。”佩珀認同馬克思以階級觀點審視環境主義興起的思想理路,因此,他認為,如果我們想要改變資本主義社會人與自然異化的狀態,創建一個生態社會主義社會,應該“少關注個人態度和價值觀的變革,更多地關注全世界無產者的集體的政治斗爭”[2]。這有利于克服西方綠色分子主張的“個體決定論”,即“個體在社會變革中處于關鍵地位,相信個人的就是政治的,否認群體運動,認為工人階級作為一個群體,不能掌握資本生產的組織和勞動制度的觀點”[4]。
第二個視角涉及到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分析。在馬克思看來19世紀的環境問題主要是由城市化、資本主義工業化以及農業化相關的經濟剝削產生。因而,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遭受生態破壞的主要場所是工廠和產業工人的居住地,大規模農村和鄉村貧民窟[5]。”在論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環境的破壞性時,佩珀主要選取了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農業技術對環境的破壞這個視域。佩珀表示,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家出于對農業利潤的追逐,發動了通過技術來提高生產力的農業革命,然而在資本主義農業革命中,“所有的進步是在技藝上的進步,它不僅掠奪了勞動力,而且掠奪了土壤,所有在既定時間內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法,都是一種毀滅那種肥力的持久源泉的進步”[6]。由此佩珀認為,真正引起環境破壞的是資本主義這種生產方式,而并非綠色分子倡導的將自然系統的破壞歸咎于技術發展的技術原罪論。
2 構建紅綠聯盟的社會模式
在探索解決紅綠之爭思想的基礎上,佩珀又積極探究了實現“紅綠聯盟”的社會模式——生態社會主義社會。并且為了切實實現紅綠聯盟的社會形態,佩珀在比較分析紅綠雙方觀點差異的基礎上,又進一步論述了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具體特點。
首先,關于紅綠雙方主張的差異。佩珀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第一,在環境退化根本原因的斷定上。紅色分子主張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罪魁禍首,他們認為:“正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人類干預自然的方式造成了土地退化和生態掠奪”[7]。但是綠色分子則認為,引起生態問題的根本原因是人們之間的權力關系——等級制和支配關系,正如默里·布克金強調:“在人類社會等級制發展的同時,帶來了一種統治意識,這種統治意識主要表現為男人對女人的統治和人類對自然的統治,因此最終結局是生態危機”[8]。第二,在實現生態社會的戰略上。綠色分子主張非暴力運動,在政治中對個人的崇拜取代了集體的意識,并且鄙視“工人崇拜”。對此,綠色無政府主義者布金早在1936年就不再把無產階級說成一個革命的力量,而是把他們看成“不了解自身,缺少階級意識和才智,屈服于偏見的群體”。與之相反,紅色分子則支持暴力革命和有組織的革命先鋒隊。佩珀指出:“即使無產階級在奪取權力時不想發動暴力,資方將在試圖平息起義中使用暴力,因此工人階級必須準備斗爭來保衛他們的生命和事業[2]。”第三,在對待國家的態度上。綠色分子擁有簡單化的國家觀點,主張廢除國家。他們贊同巴枯寧的主張,即“資本家僅僅因為國家的恩惠擁有他的資本,因此國家是主要的罪惡,一旦國家廢除了,資本主義將會自行消亡”[9]。但是紅色分子奧康納則認為,應努力使國家民主化,而不是去嘗試取消國家的生態學計劃,他指出:“大多數經濟,社會和生態難題不可能在地方水平上得到恰當處理,區域的,國家的和國際的計劃是必要的”[11]。
其次,在比較紅綠雙方觀點差異的基礎上,佩珀又進一步描述了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具體特點。第一,針對綠色分子將自然神秘化以及由此產生的反人本主義性質,“自然是人類社會的一個模型,是人類的第一任倫理教師,人類必須完全順從自然”[11]。佩珀明確提出生態社會主義是人類中心論的,他強調:“自然的權力如果沒有人類的權力是沒有意義的”[2]。但與資本主義短期的人類中心主義相反,生態社會主義社會是一種長期集體的人類中心主義,它主張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通過勞動來合理地實現人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第二,針對綠色分子把生態社會的經濟模式設計成“自然社會”的模式,即亨特主張的“自然社會是獵人采集者的社會,是懶散的和‘經濟零增長’的社會”[12]。佩珀明確表示生態社會主義社會也需要生產,也需要發展經濟,但和追逐利潤和交換價值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同,生態社會主義的生產建立在以人為本和使用價值的基礎上,“這是一個在藝術上更加豐富的社會,人們享受更加巧妙精致的食物,接受更好的教育……[14]。”第三,對于綠色分子主張的生態社會中技術必須是小規模的觀點。佩珀堅決認為,這是一種技術上的非歷史主義,它忽視了技術難題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聯系。佩珀主張,“伴隨著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舊的機器將會被更快捷,更智能化的機器所取代,并且這是一種適應自然而非異化的技術[13]。”
3 實現紅綠聯盟的實踐策略
為了促成紅綠聯盟,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社會,佩珀認為紅色分子——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應該要選擇性地吸收綠色無政府主義者的積極因素。因此佩珀選取了綠色分子的一些環境行動模式,雖然這些行動沒有一個事例是完全讓人滿意的,但它們都值得紅色分子的支持和仿效。
第一,采用以工會為核心的政治經濟互動戰略。佩珀認為,工會和勞工運動在環境運動中發揮的積極作用是值得提倡的,正如英格蘭伯明翰老郵政大樓因為建筑工人和環境主義者的聯盟而最終免于破壞等事件一樣。但是針對工會運動在環境運動中的消極作用,正如20世紀70年代澳大利亞悉尼的綠色禁令由于工人團結一致的抵制而被迫取消的現象,佩珀又進一步強調,“工人”計劃必須采取集體的方式,生態社會主義的實踐不可能離開階級斗爭,因為“階級斗爭是將人性從資本主義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的核心,如果沒有一個意識成熟的多數社會主義者,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14]。”
第二,構建城市自治主義和國家扶持并重的治理模式。為了阻止資本主義控制國家,綠色分子曾經提出要把主要權利交給地方和基層組織,使地方共同體可以自我管理和改善他們的城市環境,比如城市自治社會主義。對此,佩珀指出:“雖然城市自治社會主義不是革命性的,但是它確實接受了一些重要的社會主義原則[15]。”例如它倡導用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的觀點來規范、控制、補充或消除市場的原則,以及對于環境的界定集中于人們的生活場所而并非原始自然的原則等。但是針對早期城市自治社會主義無法實現,以及改善城市自治社會主義的問題,佩珀強調國家扶持的重要性。在這里佩珀比較支持弗蘭克爾的國家觀,即“在社會主義發展中,一個有能力的國家對于計劃的實現是重要的,如果沒有復雜的管理和國家來確保民主參與,民權和經濟的協調是不可行的”[16]。
第三,實行地方貨幣制度。為了克服資本在權利意識的支配下只追逐利潤而無視生態危機的缺陷,綠色分子主張取消貨幣。但是佩珀認為,倡導一種無貨幣的經濟在現實性上注定是一種空想。為此,他提出可以通過貨幣制度改革來保留貨幣,從而彌補綠色分子的空想性缺陷。對此,佩珀指出:“在當今社會中,權利已經不存于任何一個階級之中,而是存在于以貨幣為媒介的制度本身,改革貨幣制度是使制度擺脫資本控制的關鍵[17]。”佩珀在此主要提倡的是地方貨幣,對于地方貨幣的特征,佩珀比較贊成巴頓的觀點,即“成員賬戶起于零點;沒有貨幣被存蓄或發行;……從沒有任何貿易的義務;一個成員知道另一個成員的余額和周轉;總的來說,沒有余額利息被索要或支付”[18]。從上述觀點可以看出,佩珀所謂的地方貨幣僅僅是一種勞動符號,通過此種符號可以避免資本主義憑借貨幣進行空間復制,預防在區域內的剝削和積累現象,規避剩余價值的區域間占有,而后者恰好是諸多環境問題的根基。在佩珀看來,具備了上述特征的地方貨幣一定是與生態社會主義相一致的。但是佩珀并沒有真實地領悟到馬克思對貨幣的批判,即“貨幣體現的是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經濟關系,貨幣的不同形式可能更好地適應不同階段的社會生產,但是只要他們依舊是貨幣形式,那么任何貨幣形式都不能根除貨幣關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這種或那種形式上代表這些矛盾”[19]。所以,佩珀所提倡的地方貨幣并不能真正解決資本的控制問題。
參考文獻
[1]王雨辰.論戴維·佩珀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J].漢江論壇,2008(12):27-32.
[2](英)戴維·佩珀,著.生態社會主義:從深生態學到社會正義[M].劉穎,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2:2,4,59,259.
[3]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M]//馬克思,恩格斯:基本著作.倫敦:封塔納出版社,1859:40, 50.
[4]羅斯扎克.創造一種反文化[M].倫敦:法伯出版社,1970.
[5]帕森斯·馬克思和恩格斯論生態學[M].倫敦:格林伍德出版社,1977.
[6]費爾·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著作[M].倫敦:封塔納出版社,1859.
[7]約翰斯頓.環境難題:自然、經濟和國家[M].倫敦:貝爾哈溫出版社,1989.
[8]默里·布克金.自由生態學:等級制的出現與消解[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
[9]巴枯寧,著.上帝和國家[M].樸英,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10]奧康納.生產的“外部自然的”條件、國家和生態運動的政治戰略[M].桑塔克魯茲生態社會主義研究中心,1991.
[11]塞爾.土地居住者:一個生物區域視角[M].圣弗蘭西斯科希拉俱樂部出版社,1985.
[12]亨特.自然的社會:綠色無政府主義的基礎[M].牛津EOA圖書出版社,1974.
[13]戴維.佩珀.生態社會主義:從深生態學到社會正義[M].劉穎,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
[14]詹姆斯·奧康納.社會主義和生態學[J].綠色政治思想,1991(1).
[15]戴維·佩珀.公社與綠色觀點:反文化、生活風格和新時代[M].巴辛托克綠色圖書出版社,1991.
[16]弗蘭克爾.后工業烏托邦[M].劍橋政體出版社,1987.
[17]李旦.綠色政治的紅色滲透-試論戴維.佩珀關于生態社會主義的政治構建[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3):24-27.
[18]巴頓.綠色思想詞典[M].倫敦:羅特里奇出版社,1988.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