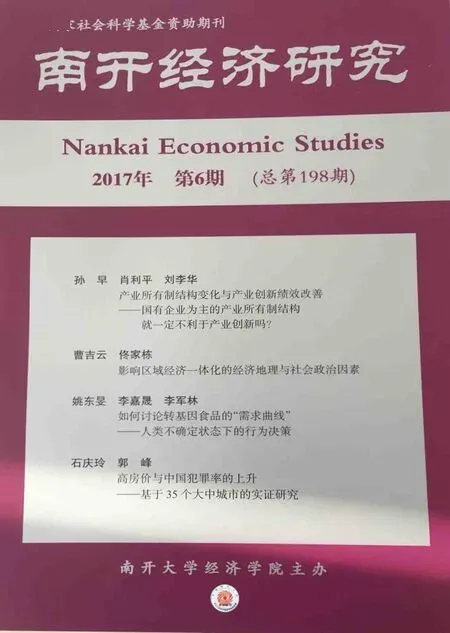外部沖擊對我國股市暴跌的影響研究
郝項超 李 政
一、引 言
2016年1月4日,我國股市正式實施了指數熔斷機制(index circuit breaker),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當天下午熔斷機制就被連續兩次觸發。兩天之后的 1月 7日,開盤后半個小時之內熔斷機制再次被連續觸發,幾乎全天停市。社會各界針對連續的股市暴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但大多集中于討論指數熔斷機制的影響,忽略了這次股市暴跌實際上是近期我國股市極端波動的再次體現。
是什么原因導致我國股市近期頻繁出現異常波動呢?遺憾的是,盡管這一問題非常重要,但目前除了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課題組(2015)之外,其他較系統的研究非常有限①證監會原副主席高西慶在 2016年兩會期間曾建議中央政府應當成立專門的調查組,查明股市異動等事件的原因。證監會原副主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李劍閣在最近的博鰲論壇上也強調 2015年的股市暴跌“需要一個系統的研究才能說清楚”。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87年10月美國股市發生閃崩(crash)之后,美國各界專家迅速對股市暴跌的前因后果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廣泛的討論,最終促成了以美國布拉迪報告(the Brady Report)所提出的熔斷機制為代表的監管措施。。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課題組(2015)在《完善制度設計,提升市場信心——建設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的資本市場》的研究報告中分析了 2015年發生的多次股市暴跌,認為宏觀層面原因是實際經濟表現差于市場對我國經濟轉型和改革的預期,微觀上的原因則是我國資本市場建設不完善等技術問題。該研究報告還指出不同的股市暴跌形成的原因也不盡相同,因此其結論是否適用于 2016年初的連續股市暴跌值得商榷。近期也有一些研究分析了融資融券制度以及股指期貨等資本市場制度安排對我國股市暴漲暴跌的影響,但這些研究不僅得到了相互矛盾的結論,也沒有清楚地回答融資融券對個股崩盤風險的影響如何演化成股市系統性風險②支持的研究認為,融資交易發揮了“助漲助跌”的作用,加劇了股市波動(李政等,2016),融券交易會增加股價波動(陳海強和范云菲,2015),融資融券制度的實施惡化了標的股票的股價崩盤風險(褚劍和方軍雄,2016)。但是也有研究提供了相反的證據,發現融資融券交易可以防止股票價格的暴漲暴跌和過度投機(李志生等,2015)。。Hao(2016)重點分析了熔斷機制磁吸效應在 2016年初股市暴跌中的作用,但沒有分析其他股市極端波動的原因。不僅如此,現有研究大多關注的是國內原因,忽略了國際因素的影響。然而,隨著我國股市國際一體化水平的明顯提升,國際金融市場風險對我國股市變動的影響可能已經不容忽視(李紅權等,2011;梁琪等,2015)。
與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側重通過股市暴跌事件的分析來研究國際股市風險和人民幣匯率風險對我國股市的影響,以及我國股市暴跌對國際股市和人民幣匯率的影響。為此,本文首先借鑒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課題組(2015)等研究并結合我國指數熔斷機制實施期間的情況,選擇滬深 300股指跌幅明顯大于其他交易日、暴跌后短期內未能恢復至原來水平、投資者損失慘重且對股市信心急劇下降的交易日作為股市暴跌事件。這樣的股市暴跌可以視為股災事件,具有明顯的研究價值。依據上述標準,本文發現過去一年中共有五個交易日符合股市暴跌的定義,分別為 2015年 6月 26日、8月24日和25日③本文沒有考慮將2015年8月18日的股市下跌作為股市暴跌,原因有兩個:第一,8月18日雖然也發生了千股跌停,但并不是持續下跌,且與后續的股市暴跌間隔太長;第二,就新興市場而言,8月 18日的跌幅也不是足夠大,且下跌不是持續的單邊下跌。這周突然出現的下跌很可能是部分知情交易者對負面信息的反應,是股市暴跌的前兆或者警示,因此這一交易日的股市下跌不太適合作為股災事件。以及2016年1月4日和7日。本文將臨近的暴跌進行合并,形成了2015年6月、8月和2016年1月三次股市暴跌事件。然后,本文引入了歷史分解方法(historical decomposition),分別測度了每次股市暴跌前后每個交易日國際股市風險和人民幣匯率風險對我國股市變動的動態影響。
二、國際股市風險、匯率風險與我國股市暴跌的關系分析
(一)國際股市風險與我國股市暴跌的關系分析
目前,有關股市暴跌的文獻大多出現在 1987年 10月美國股災之后。這些研究從不同的角度解釋了美國股災發生的原因和形成的過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Fama的有效市場觀和Shiller的行為金融觀。這些研究側重于討論美國國內因素,忽視了同時期全球其他主要股市也都出現了類似的股災現象。針對這種全球股災現象,Roll(1988)比較分析了23個國家股市在股災前后的表現,發現美國股市的暴跌是全球股市暴跌的源頭,做市商、自動報價、程序化交易、價格限制、保證金等制度安排與全球股市暴跌沒有關系,但各國股市與全球股市的關聯關系可能是全球股市普遍暴跌的原因。
在此基礎上,King和Wadhwani(1990)提出了一個理論模型,認為盡管各國的經濟差異很大,但 1987年 10月美股暴跌體現的特有信息仍然可以通過關聯信息渠道(correlated information channel)傳播到他國股市,并導致全球股市普遍暴跌。Calvo(2004)和 Yuan(2005)等提出了國際股市風險的流動性傳播渠道(correlated liquidity channel)。這種渠道比較適合解釋發達國家股市之間的情況,無法解釋東南亞金融危機、拉美金融危機等事件,因為發達國家的股市流動性更好,更容易成為清算的對象。Kodres和 Pritsker(2002)認為,跨市場的投資者對某一市場沖擊的最優策略是調整其他市場的組合,這就導致沖擊在不同的市場之間傳播,因此新興市場國家的股市風險傳染是通過跨市場平衡渠道(cross-market rebalancing channel)形成的。與上述研究不同,Yang和 Besslor(2008)采用歷史分解方法研究 1987年 10月全球股災期間國際股市變動傳染效應的每日動態變化。他們發現,全球股災的源頭確實是美國股市的暴跌,但股災之后日本股市的上漲幫助了美國股市的恢復。此外,Forbes和 Rigobon(2002)發現,如果考慮了各國股市的異質性,1987年10月全球股災、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以及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國際股市之間的共同變動并不是由信息傳染(contagion)導致,而是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導致。
綜上,國外主流文獻通過對重要金融危機事件的分析證實了國際股市風險會通過傳染效應導致他國股市出現極端波動。但是傳染效應的成立必須是建立在一國股市與國際股市存在密切關系的基礎上,即一國股市應當具有較高的國際化水平(Kodres和Pritsker,2002)。那么我國股市國際化水平如何?早期的研究發現我國股市與國際股市的聯動關系非常弱,基本不受國際股市的影響(洪永淼等,2004)。但近期研究發現在美國次貸危機之后我國股市與國際股市之間的聯動關系明顯加強(張兵等,2010;李紅權等,2011;趙進文等,2013;梁琪等,2015)。有的研究還發現,中國股市對國際股市的影響不斷擴大,但美國等重要國際股市對我國股市的影響更為明顯。因此,伴隨著我國股市國際一體化水平的大幅提升,國際股市風險很有可能傳染到我國股市并誘發股市暴跌。
比較滬深300指數與美國道瓊斯工業指數、英國富時100指數、日經225指數、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恒生指數以及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等主要國際股市的走勢可以發現,2015年 6月我國股市暴跌前后,除港股之外的其他國際股市都沒有出現明顯下跌,但在2015年8月以及2016年1月兩次股市暴跌前后,美、日股市和我國港股都出現了明顯下跌。因此,與2015年6月的股市暴跌相比,2015年8月和2016年1月的股市暴跌很可能受到了國際股市極端波動的影響。
(二)匯率風險與我國股市暴跌的關系分析
匯率風險如何影響股票市場的變動?現有研究提出了兩個主要理論來解釋這一問題。首先是現金流導向論(flow-oriented theory)。該理論認為,匯率變動會影響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減少或增加其未來現金流,進而影響到股票價格,但對不同企業而言,匯率變動對股票價格的影響存在差異。比如,匯率貶值可以提高出口型企業的競爭力,推動其股價上升;但匯率貶值會增加進口型企業的成本,降低利潤,從而導致其股價下跌。其次是資本流動理論(capital flow theory)。該理論認為,匯率變化會引起短期資本流動,從而影響到股票價格(Oreiro,2005)。比如一國匯率的迅速貶值會導致跨境投資者將資金轉移到安全貨幣資產上,結果導致該國股市出現嚴重拋售壓力,股市出現明顯下跌。但是基于組合平衡理論(portfolio balancing theory)的研究認為,不是匯率影響股市,而是股市影響匯率(Frankel,1983)。
大量實證研究采用不同國家的數據對上述理論進行了檢驗,得到了不一樣的結論。就發達國家而言,Ajayi和 Mougoue(1996)發現,資本流動理論在長短期都是成立的,而組合平衡理論只在長期是成立的;Kollias等(2012)則發現,匯率與股市的關系是隨時間動態變化的,即在正常情況下,匯率變動導致股價變化,但在危機期間,股價變化導致匯率變化。對于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結論差異更大。比如 Granger等(2000)、Yau和 Nieh(2009)發現現金流導向理論和資本流動理論在大多數東歐國家得到了支持。Tsai(2012)采用分位數回歸模型發現當匯率過高或過低時,股價與匯率的負相關關系更加明顯。Lin(2012)發現,危機期間股市和匯率的共同變動趨勢明顯增加,而且主要通過股價變動對匯率的影響實現。他還發現,共同變動在出口導向企業中并沒有更明顯,說明這種共同趨勢是由資本賬戶驅動,而不是貿易賬戶驅動。
就我國外匯市場和股市而言,有關研究主要針對 2005年人民幣匯改以后的情況進行了分析。張兵等(2008)依據匯改后兩年數據的實證研究發現,匯率和股價存在長期協整關系,人民幣匯率變動對股市有明顯的影響,但短期兩者之間的影響是相互的,而且匯率變動對股市變動的影響有時滯。趙進文等(2013)進一步將時間擴展到 2011年12月,發現外匯市場與股市之間存在動態關系,并且在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期間人民幣匯率對股票的影響更加明顯。吳麗華和傅廣敏(2014)發現,人民幣匯率升值會導致資本流入增加,推動股價上漲,且這種影響在2008年之后愈加明顯。
綜上分析,國內外文獻對匯率與股市的聯動關系并沒有得到完全一致的結論。兩者之間的聯動關系不僅在不同的國家表現不同,在危機和正常時期的表現也不一致。因此依據現有研究的結論,本文認為很難確定匯率風險一定會傳遞到股市并引起股市變動,尤其是在股市出現極端波動期間。就我國的情況而言,多數現有研究討論了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匯率對股市的影響,但沒有考慮近兩年人民幣匯率大幅貶值以及波動增加的影響。最后,即便是匯率與股市變動總體上存在聯動關系,但在股市極端波動事件中匯率風險對股市變動到底有多大影響并不是非常清楚。因此,人民幣匯率是否是觸發股市暴跌以及股市未能在短期內恢復的重要因素目前還沒有非常明確的答案和證據。
分析2005年6月到2016年3月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變化與股市走勢可以發現,2015年8月11日匯率改革之前人民幣匯率持續緩慢上升且波動較小,因此人民幣匯率風險對 2015年 6月股市暴跌影響有限。但是匯率改革之后人民幣匯率大幅下跌且波動加劇,人民幣匯率風險不斷凸顯并開始對股票市場產生重要影響,盡管這種影響有些滯后。在接下來的部分,本文將采用歷史分解方法進一步檢驗上述直觀判斷。
三、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分析國際股市風險和人民幣匯率風險在我國近期三次股市暴跌事件中的動態影響。要實現上述分析,本文必須將國際股市風險、匯率風險對股市變動的每日影響測度出來。為此,本文首先構建了包含我國股市、國際股市以及外匯市場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并在此基礎上借鑒 Burbidge 和 Harrison(1985)以及Yang和Bessler(2008)等研究,引入了歷史分解方法。歷史分解方法可以將時間序列的數值分解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未來沒有新息時的時間序列值,即基于歷史信息的預測結果,另一部分則是未來信息出現時導致的時間序列數值變化。因此,歷史分解方法能夠將特定時間點之后的變動分解到不同的影響因素,特別適合分析特定時間發生的重大異常事件,比如股市暴跌期間各影響因素所傳遞的新信息產生的影響。
借鑒Burbidge和 Harrison(1985)以及 Yang和 Bessler(2008)等研究,本文首先構建了如下VECM模型:

其中,Xt是我國股市、國際股市以及人民幣匯率等變量構成的向量。本文以滬深300指數(CN)衡量國內因素對股市暴跌的影響,以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①離岸人民幣的走勢與在岸基本一致,結果沒有明顯差異。(FX)衡量人民幣匯率風險影響,以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恒生指數(HK)、美國道瓊斯工業指數(USA)、日本日經 225指數(JP)、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SP)、英國富時 100指數(UK)5個主要國際股市指數來衡量國際股市風險的影響①國內外股市指數和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都采用其對數。。式(1)中長期關系矩陣αβ′Π= 的秩決定了協整向量的個數,α為調整系數,β為協整系數,Γj為短期動態系數矩陣,μ為截距列向量,εt為隨機擾動列向量,用來衡量隨機新息沖擊。
與 Yang和 Bessler(2008)、李政等(2016)、李政(2017)等研究一致,本文首先估計出式(1)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的參數,然后將其轉化為水平形式的 VAR模型。假定 T為要考察的股市暴跌事件的時間起點,那么對于 j=1,2,……,事件期間的XT+j可以表示為如下移動平均形式:

其中,c代表了確定性成分(deterministic component)。為依據截止到時間 T時的所有信息對XT+j作出的預測。是考慮了T+1到T+j事件期間每期加入的新息沖擊后XT+j的變化部分,即新息沖擊對XT+j的影響。就我國股市而言,是依據股市暴跌之前信息預測的滬深300股指走勢,而則是股市暴跌期間國際股市和匯率風險沖擊對滬深300股指變動的影響。
需要注意的是,鑒于新息εt通常存在同期相關性,以往研究通常使用 Cholesky方法或者 Bernanke(1986)的方法將非正交新息轉化為正交新息,然后再進行歷史分解。但是這些方法具有一定的主觀色彩②比如 Chelosky方法通常對變量施加一個遞歸的同期因果結構,這導致研究結果對變量的順序十分敏感,而結構因子方法需要先依據經濟理論、前期成果或者研究者的主觀判斷對同期關系矩陣施加約束條件,然后識別估計出同期關系矩陣。,可能會對結果產生重要的影響。為克服這一問題,本文借鑒 Diebold和 Yilmaz(2014)等研究,采用完全基于數據驅動的廣義因子來進行歷史分解。假定ε=Fη,其中F為廣義因子矩陣,則可以轉化為:

舉例來說,如果j等于2,X1,T+2就可以寫為歷史新息的線性組合:
借鑒以往文獻,本文分別選擇三次股市暴跌事件前后共計一年的日交易數據來估計上述VECM模型的系數。具體樣本期間分為2014年7月22日—2015年7月23日、2014年9月21日—2015年9月22日以及2015年1月28日—2016年1月29日。考慮到匯率風險對股市的影響存在時滯,因此本文選擇股市暴跌事件的時間起點T為每次暴跌前的第11天,終點是股市暴跌發生后的第19天。加上股市暴跌當天,整個事件的考察期間為30天,即預測期間j為30。股市和人民幣匯率日交易數據均來自湯森路透Datastream數據庫。
依據三次股市暴跌事件的數據,本文首先采用 AIC準則來確定 VAR模型的滯后階數,結果發現三個 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均為 2。然后,本文采用了跡檢驗來確定協整向量的個數,通過Johansen(1992)的序貫檢驗對 VECM的模型形式進行識別。檢驗的結果表明,VECM 模型不存在線性趨勢,μ應作為協整向量的截距項,而非原始序列的時間趨勢項。檢驗結果還表明,在 10%,的顯著性水平下,三次股市暴跌事件的VAR系統都僅存在1個協整關系。在此基礎上,本文使用三次股市暴跌事件的日頻交易數據估計了VECM模型的有關參數,并將其轉化為水平VAR模型的形式。
四、國際股市與匯率風險對我國股市暴跌的動態影響分析
在前述 T(即股市暴跌事件前第十一個交易日)和 j(股市暴跌前后共計 30個交易日)選擇的基礎上,本文對 7個變量進行了歷史分解。同時借鑒以往文獻,本文將歷史分解的結果轉換為圖形,更加直觀地展示三次股市暴跌期間各個變量對滬深 300股指變動的動態影響。圖 1~圖 3分別報告了三次股市暴跌期間國際股市和人民幣匯率風險對滬深300股指走勢的影響。圖1~圖3的每一個子圖表示的是對應因素對我國股市變動的動態影響,比如USA代表的是美國股市對我國股市變動的動態影響。圖中的實線為股指的實際走勢,點狀線為基于每次股市暴跌前信息預測的滬深 300指數值,斷線則表示的是滬深300預測值加上某一因素影響后的股市預測值。如果斷線預測值更加接近實際值,則說明該因素對暴跌期間我國股市變動的影響更為突出;反之,如果斷線預測值接近基于暴跌前信息的點線預測值,則該因素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其對股市變動的影響也就非常有限。另外,橫軸上0值代表前文所界定的股市暴跌交易日,負值代表股市暴跌之前的交易日,正值代表股市暴跌后的交易日。本文將分別就每次股市暴跌進行分析。
(一)內外部沖擊對2015年6月股市暴跌的動態影響分析
圖1報告了2015年6月股市暴跌前后30個交易日內國際股市風險、匯率風險與我國股市變動的動態關系。可以看到,如果依據股市暴跌之前的數據信息,滬深300指數的走勢是比較平穩的,但實際情況與預測值出現了巨大的偏離。這說明股市暴跌前后國內外因素確實出現了新的信息,并導致股市出現顯著下跌。從左上角 CN的結果來看,國內因素對滬深 300股指下跌的影響在股市暴跌之前的十個交易日內已經非常明顯,該影響一直持續到股市暴跌后第七個交易日,即政府宣布救市后的第一個交易日2015年7月6日。因此,政府救市政策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國內因素的不利影響。由于加入國內因素后的滬深 300指數預測值(即斷線)明顯低于其實際值(即實線),因此如果沒有其他因素的影響,滬深 300指數的下跌幅度會更大。本文進一步發現在2015年6月股市暴跌期間,美國、日本、新加坡和英國等股市對滬深300指數的變動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但是我國香港股市從股市暴跌前的第五個交易日開始到暴跌后的第六個交易日對滬深300指數的影響都是顯著的拉升作用。這說明港股傳遞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滬深300股指下跌的程度。因此,就圖1的結果而言,此時港股是阻止滬深 300股指下跌的反向影響力量。另外,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影響幾乎接近于零,這說明匯率風險對此次股市暴跌前后滬深 300指數沒有顯著影響。考慮到人民幣匯率在此之前一直維持了緩慢升值的穩定狀態,因此上述結果是比較符合實際的。綜上分析,2015年 6月份的股市暴跌主要是由境內因素導致的,而我國香港股市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滬深300股指的下跌,但人民幣匯率風險對滬深300股指變動沒有任何影響。
(二)內外部沖擊對2015年8月股市暴跌的動態影響分析
圖2報告了2015年8月股市暴跌前后國際因素影響的動態結果。本文發現圖2的結果與圖 1的結果表現出非常明顯的差異。CN的結果表明國內因素對股市暴跌當日的滬深 300股指下跌沒有影響,在股市暴跌后兩個交易日推動了滬深 300股指下跌,但在其他交易日國內因素則是推動滬深300股指上漲的力量。這就是說,如果股市暴跌期間只有國內因素的影響,那么滬深 300股指不應該出現如此明顯的下跌,而是相反。在國際股市風險的影響中,HK的結果表明,在股市暴跌發生前的第三個交易日到股市暴跌后的第十個交易日之內我國香港股指的走勢顯著推動了滬深 300股指下跌。USA的結果表明股市暴跌前的第三個交易日到事件期間結束,加入美股影響后的滬深300預測值非常接近滬深300股指實際值,因此美股大幅下跌是滬深300指數暴跌的最主要力量,也是股指暴跌后未能恢復的最主要力量。相比之下,日本、新加坡和英國股市的影響并不明顯。綜合以上結果,本文認為美股是2015年8月滬深300股指暴跌和未能恢復的最主要力量,其次是港股。

圖2 2015年8月股市暴跌中匯率風險與國際股市風險的動態影響
為什么美股的影響如此明顯?本文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解釋。第一,美股在我國股市暴跌之前出現了極端波動。以道瓊斯工業指數為例,美國時間 2015年 8月19日到24日,該指數分別下跌了162點、358點、530點和588點,累計下跌1640點,跌幅達到-9.69%,。盡管其跌幅無法與 1987年美國股災時相比,但在當前國際經濟與金融形勢波譎云詭的情況下,美股的異動還是引起了全球股市的恐慌,主要股市都出現了明顯下跌。第二,國際股市之間的聯動關系越來越強,國際股市風險的傳染效應更加明顯。2015年8月21日,全球股市跟隨美股暴跌。2015年8月24日,受國際股市暴跌影響,美國股市開盤之前標普 500股指期貨、納斯達克 100指數期貨以及道指期貨均出現暴跌并觸發熔斷機制①其中標普500股指期貨下跌了5.17%,納斯達克100指數期貨9月合約跌5%,道指期貨則暴跌700點。。美國監管部門不得不啟動 48號規則②48號規則允許在交易所內特定市場做市商在開盤前不公布價格指標。該規則是為了使得在當天市場波動可能非常巨大的情況下順利而快速地實現開盤,從而避免熔斷機制觸發后導致全天停市的不利影響。以避免全天停市,但當日道瓊斯工業指數仍然下跌588點,而后全球股市再次跟隨美股暴跌。美股極端波動透過傳染渠道在國際股市間不斷被放大,并導致國際股市普遍出現暴跌的情況。盡管近些年我國股市對國際股市的影響日益增加,但總體上美股對我國股市的影響要更大一些,尤其是在金融市場出現極端波動時(李紅權等,2011;梁琪等,2015)。因此,在上述兩個方面的共同影響下,美股的極端波動直接導致了我國股市 2015年 8月份連續出現暴跌。實際上,本文在后續的分析中進一步證實了美股的暴跌不僅是我國股市暴跌的主要力量,也是其他國際股市暴跌的最主要力量。
讓人意外的是,盡管2015年8月股災之前第八到第十個交易日(即2015年8月11日到8月13日)人民幣對美元出現了短期大幅貶值,波動明顯加劇,但人民幣匯率風險對滬深300股指下跌的影響并不是非常顯著。本文認為其可能的原因是2015年8月下旬國際股市的極端波動抵消了匯率波動的影響。因為人民幣貶值期間正好發生了全球股市暴跌,這可能導致國際投資者更多地關注國際股市的極端波動,從而減弱了人民幣快速貶值對我國股市的沖擊。另外,本文進一步統計了股市暴跌前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持有 A股流通股股票數量的變化,結果報告在表1中。本文發現從2014年第四季度開始,QFII持有 A股流通股數量開始減少,2015年前兩個季度出現明顯的大幅減持,但2015年三季度末QFII持有A股流通股票的數量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出現了大幅增加。表1的結果表明,QFII似乎并沒有因為 2015年 8月份人民幣匯率急劇貶值而贖回投資,反而增加了投資。因此,人民幣貶值風險在 2015年 8月份股市暴跌事件中的影響并不顯著。

表1 2014—2016年QFII重倉流通股數量季度統計情況
(三)內外部沖擊對2016年1月股市暴跌的動態影響分析

圖3 2016年1月股市暴跌中匯率風險與國際股市風險的動態影響
圖3報告了2016年1月我國股市暴跌期間國際因素對滬深300股指變動的動態影響。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雖然股市暴跌之后滬深300指數的預測值高于其實際值,而在暴跌前的十個交易日內卻低于其實際值。這一結果說明暴跌十日前的信息已經預測到了滬深 300股指的下跌趨勢,但股市和匯率等影響因素的新息延緩了股指下跌的趨勢。就股市暴跌之前的結果來看,國內因素、美股、新加坡和英國股市是導致滬深300股指實際值高于預期值的主要力量,港股是推動股指下降的力量,人民幣匯率風險的影響并不明顯。就股市暴跌當日來看,2016年1月4日股市暴跌的主要推動力量是國內因素,而美股和新加坡股市則是延緩股市下跌的力量;2016年1月7日股市暴跌的主要推動力量是港股的影響。就股市暴跌之后的情況來看,美股、港股以及新加坡股市都是滬深 300股指下跌的主要力量,國內因素反倒是股指恢復的主要力量,但相比之下,下跌的力量更加強大。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人民幣匯率持續貶值在股市暴跌前和暴跌當日對滬深 300股指的影響并不明顯,但在股市暴跌之后其影響變得越來越明顯。這一結果與張兵等(2008)是一致的,表明匯率風險對股市的影響有一定的時滯。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發現在2015年8月和2016年1月兩次股市暴跌中,國際股市風險都是滬深 300股指下跌的驅動力量,并且其影響明顯超過了國內因素的拉升作用,從而使得我國股市整體大幅下跌。人民幣突然大幅貶值并不是股市暴跌的主要因素,但持續的貶值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股市的下跌。
(四)我國股市暴跌對國際股市和人民幣匯率的動態影響分析
上述分析討論了國際風險對我國股市暴跌的影響,并得到了一定的支持證據。考慮到近期我國股市國際一體化水平的提升,這三次暴跌對國際股市和人民幣匯率有何影響?表2~表4分別報告了三次股市暴跌期間(即股市暴跌前后 30個交易日)國內外因素相互影響的均值統計結果。表中每一列表示的是該列因素對行因素影響的 30日平均值。比如表2第一列表示的是滬深 300股指對自身、5個國際股市以及人民幣匯率影響的30日平均值。
可以看到表2第一列的結果中,除了人民幣匯率之外,其他六個變量30日均值都為負值。這表明國內因素是2015年6月滬深300股指下跌的最重要力量,貢獻了所有下跌影響的 94.39%,;滬深 300股指的下跌也導致港股大幅下跌,貢獻了 76.25%,的下跌影響;同時,滬深 300股指下跌也推動了美股、日本股市、新加坡股市以及英國股市的下行,但相比之下其影響要弱于對港股的影響。圖4給出了2015年6月股市暴跌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動態影響,提供了進一步的支持證據。除此之外,圖4中FX的結果還表明在2015年6月份股市暴跌期間,滬深300股指的持續下跌給人民幣匯率帶來了明顯的貶值壓力。前述表1中數據表明 2015年二季度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流通股持股比例在一季度下降 13.17%,的基礎上,又進一步下降了 11.46%,,這意味著境外資本短期內有明顯流出我國股市的沖動。因此,本文的證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股市變動影響匯率變動的組合平衡理論。
表2的結果還表明,與我國滬深股市的影響相比,我國香港股市、美股以及日本股市對全球股市的影響都是正的,是維持股市上漲的力量,而新加坡股市和英國股市則是驅動國際股市下跌的力量。

表2 2015年6月我國股市暴跌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平均影響

表3 2015年8月我國股市暴跌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平均影響

表4 2016年1月我國股市暴跌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平均影響
表3的結果表明,2015年8月滬深300股指的極端波動對國際上其他股市的影響都不顯著,甚至比2015年6月的影響更弱。圖5的結果表明在整個股市暴跌期間,滬深 300股指的變動只對港股有一定影響,對其他國際股市的影響都不顯著。然而與我國股市的影響相比,美股暴跌和熔斷機制觸發的連續出現對全球股市造成了非常顯著的影響,導致全球股市普遍暴跌。本文同時發現美股之外的其他國際股市的影響則不是非常明顯。綜合上述結果,本文認為 2015年 8月份全球股市暴跌的來源是美股暴跌。實際上,上述結果也表明由于中國股市是跟隨美股暴跌,因此盡管出現了連續暴跌,但其影響比較有限。最后本文發現我國股市的變動并沒有對人民幣匯率的變化產生顯著影響。

圖4 2015年6月我國股市暴跌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動態影響
表4的結果表明總體上2016年1月滬深300指數的極端波動推動了港股之外其他國際股市的下跌,但其經濟影響仍然不是非常顯著。圖 6的動態影響結果進一步表明2016年1月4日的滬深300股指的暴跌推動了美國之外的四個國際股市下跌,但在其他交易日的影響并不顯著,包括2016年 1月 7日股市暴跌當日。這就是說2016年1月4日的股市暴跌對國際股市產生了影響,但2016年1月7日的暴跌則是受到了國際股市的影響。表4的結果還表明除了我國香港股市以外,其他國際股市的相互影響也明顯下降,說明港股是 2016年 1月國際股市風險的重要來源。此外,本文還發現股市暴跌之前滬深 300指數已經預測到人民幣匯率貶值的趨勢,但暴跌之后滬深 300股指變動對人民幣匯率并沒有顯著影響,這說明股市暴跌以及持續的下跌趨勢并不一定導致人民幣匯率的顯著貶值。
綜上分析,本文發現在三次股市暴跌期間,滬深 300指數暴跌事件以及暴跌后的持續下跌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國際股市的下跌,表明我國股市在國際股市中已經具有了一定的影響力,這與李紅權等(2011)、梁琪等(2015)等研究的結果是一致的。與之不同的是,本文還發現盡管我國股市國際一體化水平和影響力不斷提升,但其國際影響力目前還比較有限。相比之下,美股仍然是國際股市風險傳染效應的最重要來源,港股對滬深 300股指的影響已經不容忽視,但對其他股市的影響則比較有限。此外,本文還發現在人民幣貶值的背景下,僅有微弱的證據表明股市極端波動會影響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而且其經濟影響比較有限。因此,本文的結果與張兵等(2008)以及吳麗華和傅廣敏(2014)等基于人民幣升值背景下的結論并不完全一致。這意味著有必要區分人民幣升值和貶值對股市影響的差異,但這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不再贅述。

圖5 2015年8月我國股市暴跌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動態影響

圖6 2016年1月我國股市暴跌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動態影響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在過去幾年我國股市頻繁出現極端波動,尤其是2015年6月、8月和2016年1月的三次股市暴跌,嚴重打擊了投資者信心,影響到股市正常的融資功能,凸顯出股市系統性風險的特征。盡管少數已有研究考察了國內因素對三次股市暴跌的影響,卻忽視了股市暴跌期間國際風險因素的影響。隨著我國股市國際一體化水平的不斷提升以及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深化,國際股市以及人民幣匯率風險等國際風險對我國股市的影響可能會越來越突出。基于上述觀察,本文依據國內外股市和外匯市場的日頻數據,構建了向量誤差修正模型,采用歷史分解方法,實證分析了國際股市風險和人民幣匯率風險在我國近期三次股市暴跌中的動態影響。本文首先發現盡管國際股市以及人民幣匯率與股市存在總體的聯動關系,但其在不同股市暴跌中的影響存在明顯差異。具體而言,在股市暴跌當日,2015年 6月股市暴跌的主要因素是國內因素,國際金融市場風險影響不顯著;2015年8月股市暴跌的主要原因是美股和港股的暴跌;2016年1月 4日暴跌的推動力量是國內因素,而美國和新加坡股市則是延緩股市下跌的力量,但港股的下跌是2016年1月7日股市暴跌的最主要力量。在股市暴跌后的交易日中,港股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2015年6月股市下跌程度,美股和港股是2015年8月以及2016年1月股市暴跌后持續下跌的主要力量,而日本股市對2016年1月股市恢復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其次,本文發現人民幣匯率在三次股市暴跌中的影響并不是非常明顯,僅在2016年1月股市暴跌之后推動了滬深300股指的持續下跌。最后本文進一步分析了我國股市暴跌對國際股市的影響,結果發現盡管我國股市的下跌是國際股市下跌的驅動力量,但其經濟影響非常有限。相比之下,美國股市的極端波動仍然是全球股市暴跌的最重要來源。
本文結論的政策含義主要體現為兩點。第一,在我國股市國際一體化水平不斷提高的背景下,證券市場監管部門不能只關注國內因素對我國滬深股市極端波動的影響,還要密切關注國際股市極端波動的影響。鑒于目前我國股市與港股的高度關聯以及美股在全球股市的核心地位(梁琪等,2015),本文建議應當特別加強對美股和港股極端波動的關注。第二,在當前資本管制的背景下,人民幣匯率變化與我國股市的極端波動并沒有非常顯著的關系,因此股市的波動并不是目前我國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需要關注的重要因素。
[1]陳海強,范云菲. 融資融券交易制度對中國股市波動率的影響——基于面板數據政策評估方法的分析[J]. 金融研究,2015(6):159-172.
[2]褚 劍,方軍雄. 中國式融資融券制度安排與股價崩盤風險的惡化[J]. 經濟研究,2016(5):143-158.
[3]洪永淼,成思危,劉艷輝,汪壽陽. 中國股市與世界其他股市之間的大風險溢出效應[J]. 經濟學(季刊),2004(2):703-726.
[4]李紅權,洪永淼,汪壽陽. 我國 A股市場與美股、港股的互動關系研究:基于信息溢出視角[J]. 經濟研究,2011(8):15-25.
[5]李 政. “811匯改”提高了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市場基準地位嗎?[J]. 金融研究,2017(4):1-16.
[6]李 政,卜 林,郝 毅. 我國股指期貨價格發現功能的再探討——來自三個上市品種的經驗證據[J]. 財貿經濟,2016(7):79-93.
[7]李 政,梁 琪,涂曉楓. 融資交易、杠桿牛市與股災危機[J]. 統計研究,2016(11):42-48.
[8]李志生,杜 爽,林秉旋. 賣空交易與股票價格穩定性——來自中國融資融券市場的自然實驗[J]. 金融研究,2015(6):173-188.
[9]梁 琪,李 政,郝項超. 中國股票市場國際化研究:基于信息溢出的視角[J]. 經濟研究,2015(4):150-164.
[10]吳麗華,傅廣敏. 人民幣匯率、短期資本與股價互動[J]. 經濟研究,2014(11):72-86.
[11]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課題組,吳曉靈,李劍閣,王忠民. 完善制度設計,提升市場信心——建設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的資本市場[J]. 清華金融評論,2015(12):14-23.
[12]張 兵,范致鎮,李心丹. 中美股票市場的聯動性研究[J]. 經濟研究,2010(11):141-151.
[13]張 兵,封思賢,李心丹,汪慧建. 匯率與股價變動關系:基于匯改后數據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08(9):70-81.
[14]趙進文,蘇明政,邢天才. 未預期收益率、傳染性與金融危機——來自上海市場與世界市場的證據[J]. 經濟研究,2013(4):55-68.
[15]Ajayi R. A.,Mougou? M. On the Dynamic Relation between Stock Prices and Exchange Rat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1996,19(2):193-207.
[16]Bernanke B. S.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of the Money-Income Correlation[J].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1986,25:49-99.
[17]Burbidge J.,Harrison A. An Historical Decomposi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to Determine the Role of Money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5,16(1):45-54.
[18]Calvo G. A. Contagion in Emerging Markets:When Wall Street Is a Carrier[M]. London,UK:Palgrave Macmillan,2004:81-91.
[19]Diebold F. X.,Y?lmaz K. On the Network Topology of Variance Decompositions:Measuring the Connectedness of Financial Firm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2014,182(1):119-34.
[20]Forbes K. J.,Rigobon R. No Contagion,Only Interdependence:Measuring Stock Market Comovements [J]. Journal of Finance,2002,57(5):2223-61.
[21]Frankel J. A. Monetary and Portfolio-Balance Models of Exchange Rate Determination[M]. Cambridge,MA:MIT Press,1983:84-115.
[22]Granger C. W.,Huangb B.,Yang C. A Bivariate Causality between Stock Prices and Exchange Rates:Evidence from Recent Asia Flu [J].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0,40(3):337-54.
[23]Hao X. C. The Magnet Effect of Market-Wide Circuit Breaker: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EB/OL]. Available at SSRN:https://ssrn. com/abstract=2859540,2016.
[24]Johansen S. Determination of Cointegration Rank in the Presence of a Linear Trend [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2,54(3):383-97.
[25]King M. A.,Wadhwani S. Transmission of Volatility between Stock Markets [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1990,3(1):5-33.
[26]Kodres L. E.,Pritsker M. A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 of Financial Contagion [J]. Journal of Finance,2002,57(2):769-99.
[27]Kollias C.,Mylonidis N.,Paleologou S. The Nexus between Exchange Rates and Stock Markets:Evidence from the Euro-Dollar Rate and Composite European Stock Indices Using Rolling Analysis [J].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12,36(1):136-47.
[28]Lin C. The Comovement between Exchange Rates and Stock Prices in the Asian Emerging Market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2012,22(1):161-72.
[29]Oreiro J. L. Capital Mobility,Real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and Asset Price Bubbles in Emerging Economies:A Post Keynesian Macroeconomic Model for a Small Open Economy [J].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2005,28(2):317-44.
[30]Roll R. The International Crash of October 1987 [J].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1988,44(5):19-35.
[31]Tsai 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 Price Index and Exchange Rate in Asian Markets:A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Institutions and Money,2012,22(3):609-21.
[32]Yang J.,Bessler D. A. Contagion around the October 1987 Stock Market Crash [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8,184(1):291-310.
[33]Yau H.,Nieh C. Testing for Cointegration with Threshold Effect between Stock Prices and Exchange Rates in Japan and Taiwan [J].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2009,21(3):292-300.
[34]Yuan K. Asymmetric Price Movements and Borrowing Constraints:A Rational Expectations Equilibrium Model of Crises,Contagion,and Confusion [J]. Journal of Finance,2005,60(1):379-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