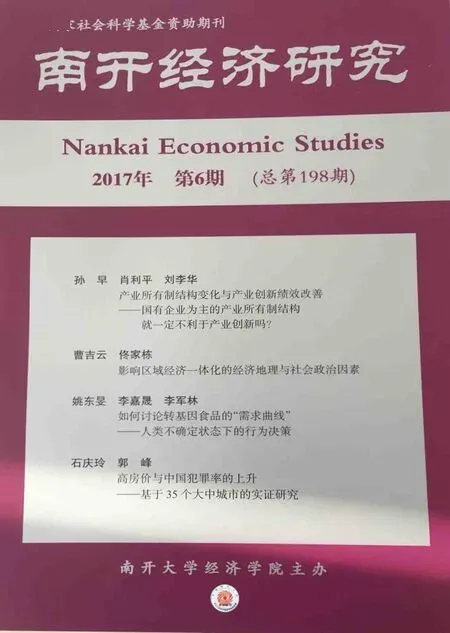我國環境財稅體系的優化配置研究
——兼論經濟增長和環境治理協調發展的實現途徑
童 健 武康平 薛 景
一、引 言
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環境的公共品屬性和經濟主體的“內化利益”會不可避免地帶來環境污染問題。政府的環境監管懲罰力度不嚴,環境法制法規不健全,直接導致了企業環保社會責任的匱乏。逯元堂等(2008)指出,在當前環境稅制體系下,企業的環境守法成本是違法成本的46倍,環境污染的稅費懲罰力度長期過低,促使企業愿意接受環境稅費懲罰以獲取合法排污權。現階段我國稅目、稅基、稅率的選擇均沒有考慮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與發達國家的環保型稅收體系相距甚遠。其實,目前我國并沒有環境稅,僅存在與環境保護有關的稅種,如資源稅、耕地占用稅和土地使用稅等。目前我國的資源稅只是為了調節資源開發型企業因資源品質和地理位置差異而獲得的極差收入,由于財稅分權體系下該收入歸地方政府,實際鼓勵了地方政府的資源開發行為。同時,我國現階段的環保財政支出以環境問題導向的應急式投資為主,缺乏持續性的制度保障。總之,作為政府激發企業參與環境治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經濟手段,環境稅的實施勢在必行。
關于環境財稅體系改革的文獻主要從稅制結構變遷和財政支出結構變遷兩個角度加以研究。從稅制結構變遷視角來看,Magat和Viscusi(1990)、Jorgenson和Wilcoxen(1993)指出增加碳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取決于消減何種稅收。Milliman和Prince(1989)、Laplante 和 Rilstone(1996)、Krutilla 等(1996)、Wolfram 等(2003)、Ulph (1996)、Panayoutou(1997)、Koskela和 Schob(1999)、Bayindir和 Raith(2003)指出,在扭曲的勞動市場中,用環境稅替代勞動稅會增加就業和產出,但最終不利于環境。Greenstone(2002)、Poyago-Theotoky(2007)等研究發現,用環境稅替代資本稅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量,激勵企業技術創新。Glomm 等(2008)指出,用汽油稅替代資本收益稅會從消費量和環境質量兩方面提升社會福利水平。Nemet和 Baker(2009)指出靜態環境稅不僅不能實現外部性內部化,還可能帶來企業為抵消環境規制成本而擴大生產的行為,即“環境困局”。Oueslati(2014)在增長經濟下研究不同類型環境稅制結構變遷的增長效應,發現用環境稅替代收入稅會一直促進經濟增長,但在短期不利于社會福利,而福利的長期效應取決于資本調整成本。武康平和童健(2015)指出,環境稅應以激發企業內生性環境治理動機為目標,并輔之以專項補貼來最大程度地實現環境稅的政策效果。
從財政支出結構變遷視角來看,Busom(1995)研究發現政府財政專項補貼會對企業 R&D投資起到激勵效應。Petrakis和 Poyago(2002)認為研發補貼在降低成本的同時可以消減污染排放。Lewis和 Wiser(2007)認為電價補貼能促進新能源產業發展。Greaker和Rosendahl(2008)比較了針對污染部門實施更嚴格的環境規制政策和研發補貼政策效果,發現嚴格的環境規制政策和研發補貼政策是互補的。 樑嚴成 和龔六堂(2009)研究發現,相對于生產性公共支出,政府對資本積累或研發進行補貼會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Nemet和 Baker(2009)認為,綠色價格補貼優于研發補貼,因為綠色價格補貼見效快,而研發補貼時間長且充滿不確定性。姚昕等(2011)認為,取消化石燃料補貼會損害經濟增長,但若將補貼用于發展清潔能源會促進經濟增長。魏瑋和何旭波(2012)認為,對生產部門實施適當的研發補貼有助于生產部門在節能減排的同時維持經濟增長,但若補貼率太高會損害經濟增長。何小鋼(2014)通過構建研發補貼與環境規制政策雙重互動的綠色技術創新誘發機制模型研究研發補貼政策與環境規制政策間存在明顯的互動效應,研發補貼能透過綠色創新降低減排成本。Fischer等(2014)研究發現,補貼上游企業要優于補貼下游企業,因為補貼上游企業不僅能降低減排技術的價格,還能減少污染排放。
不難發現,上述研究充分肯定了征收環境稅對污染治理的必要性,但同時指出環境稅在實施過程中存在“環境困局”。學者們指出環境財政補貼政策可以破除環境稅實施過程中存在的“環境困局”,但不同學者對環境稅的配套政策及環境財政支出方式的選擇存在較大差異。同時,中國綠色消費市場尚未建立,難以形成價格歧視。本文認為政府環境政策應以激勵企業內生性環境治理作為導向,實現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轉型。由于環境財稅體系的優化配置路徑是將環境政策由“經濟趕超”型向“功能”型轉變,而綠色專項補貼①政府的綠色專項補貼有:綠色政府采購、綠色技術研發補貼、生產者綠色價格補貼和消費者綠色價格補貼。又是環境財政支出的重要方式,因此環境稅與綠色專項補貼的組合是實現環境治理轉型的方向。然而,現有文獻缺乏對環境稅與綠色專項補貼組合政策效果的評價機制研究以及對環境財稅體系的優化配置研究。
此外,基于不同的研究假設和研究方法,學者們對環境治理與經濟增長能否協調發展得出不同的結論。靜態視角下,環境治理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兩難選擇,即實現一個目標的同時需要以犧牲另一個目標為代價。在技術、資源配置和消費者需求固定的假設下,企業已實現資源最優配置,而環境稅收政策只會增加企業生產成本,削弱企業創新能力和產品競爭力。從動態視角來看,環境治理和經濟增長間存在協調發展的可能。Porter等(1991,1995)指出,恰當的環境規制政策會刺激企業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技術的改進,刺激創新補償效應,提高企業生產率和競爭力。在動態視角下,政府通過環境稅收政策來約束企業污染排放行為,并以綠色財政專項補貼來激勵公眾和企業的環境治理行為,為經濟增長與環境治理的協調發展提供了可能性方案,但現有的研究對此少有關注。因此,動態模擬環境財稅政策的影響機理,優化配置環境財稅體系,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治理的協調發展,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內容。本文在異質性企業的差異化研發戰略假設下,構建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來模擬不同類型環境財稅政策的經濟收益和生態收益,并評估不同環境財稅政策組合的政策效果差異,以期找到最優的環境財稅政策組合來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治理協調發展。
二、模型構建與理論分析
環境稅是約束企業污染排放行為的重要手段,但在短期內可能抑制經濟活力。環境財政政策是指有助于綠色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包括綠色政府采購、綠色技術研發補貼、生產者綠色價格補貼和消費者價格補貼。由于生態效益在短時間內難以轉換成經濟效益,因而政府一方面需要開征環境稅,將環境的負外部性內部化,約束企業排污行為;另一方面需要實施環境財政政策直接對清潔產業加以扶持。綠色政府采購是政府直接創造清潔產品需求的措施,從而引導企業生產清潔產品,促進綠色經濟發展;綠色專項補貼是政府對消費者購買或生產者生產清潔產品進行相應補貼的政策措施,引導企業生產清潔產品。然而,綠色政府采購和綠色專項補貼并不會改變企業的技術水平。綠色技術研發補貼是政府對生產者的技術研發行為進行相應補貼的政策措施,引導企業進行技術研發,但對企業生產行為影響不大。此外,本文在模型中未考慮所得稅和消費稅,只考察了環境稅,非一般性稅源。因此,本文假定政府的各項環境財政補貼政策全部來源于環境稅收收入,實現環境自我管理的專款專用,為環境費改稅后建立相應的環境專項治理基金提供一系列的理論支持。本文將基于上述思想構建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來模擬不同類型環境財稅政策間的效果差異,并為政府提供環境財稅體系優化配置的方法。
(一)企業部門
依據單位產值的污染排放強度,現實經濟中完整的工業行業可以抽象劃分為污染密集型企業、清潔型企業和能源企業。污染密集型企業和清潔型企業的要素投入結構存在較大差異,污染密集型企業在生產設備上的資本投入較高,清潔型企業在生產設備上的資本投入較低。因此在面對環境規制時,污染密集型企業調整技術水平的難度較高,而清潔型企業調整技術水平的難度較低。在理論模型設定中,本文從兩種極端情形刻畫異質性行業在面對環境規制時技術調整的情況,假定在生產過程中,污染密集型企業的環境技術相對固定,而清潔型企業的環境技術會持續變化。
污染密集型企業通過投入資本、勞動和環境資源來生產最終產品,在消耗環境資源的同時產生污染排放,而環境資源是由能源企業投入資本和勞動開采所得,如煤炭開采等。企業的污染排放量不僅取決于環境資源消耗量,還取決于環境技術水平。環境資源消耗越多,企業的污染排放量越高;環境技術水平越高,企業的污染排放量越低。由于污染企業的環境技術水平相對固定,在環境稅較低時,污染密集型企業可能會增加產量來規避環境稅收成本,即“環境困局”;在環境稅較高時,污染密集型企業因生產設備的重置成本太高,只能被動接受稅費懲罰。因此,污染密集型企業的生產函數表示如下:
其中0Φ表示污染密集型企業的初始環境技術水平,A1t表示污染密集型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K1t、L1t、E1t分別表示污染密集型企業的資本投入、勞動投入和環境資源投入量。
清潔型企業也通過投入資本、勞動和環境資源來生產最終產品,且消耗環境資源的同時產生污染排放。清潔型企業具有較強的技術研發能力,當國家環境規制強度提高時,清潔型企業實施綠色技術戰略動機更大,刺激企業環境技術創新。清潔型企業環境技術研發還取決于清潔型企業的綠色技術研發投入,而綠色技術研發的正外部性會提高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因此,清潔型企業的生產函數描述如下:

其中,A2t表示清潔型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K2t、L2t、E2t分別表示清潔型企業的資本投入、勞動投入和環境資源投入量,Krd,t表示清潔型企業的綠色技術研發投入,φ表示環境規制強度,Φ1表示清潔型企業環境技術初始水平;Φφ′(φ,Krd,t)>0和分別表示環境規制強度越高和企業綠色技術研發投入越多,清潔型企業環境技術水平越高。
污染密集型企業和清潔型企業在使用環境資源的過程中會產生污染排放。清潔型企業可以通過提高環境技術或減少能源消耗來降低污染排放,而污染密集型企業只能通過減少能源消耗來降低污染排放。由于環境具有自降解能力,環境污染存量是上一期的環境污染存量和當期污染排放量的函數。因此,污染密集型企業和清潔型企業的污染排放方程表示如下:

其中,EM1t、EM2t分別表示污染密集型企業和清潔型企業的污染排放量,Φt表示清潔型企業的環境技術水平,Xt表示環境污染存量,服從一階自回歸過程。1-η表示環境污染的自降解能力。Ψ′Φ(Φt,E2,t)<0表示環境技術水平越高,企業在使用相同環境資源時所產生的污染排放量越低。Ψ′E2(Φt,E2t)>0表示企業使用的環境資源越多,污染排放量越高。
污染密集型企業和清潔型企業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環境資源是能源企業投入資本和勞動開采所得,例如煤炭開采業等。能源企業的生產函數表示如下:

其中,A3t表示能源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K3t、L3t分別表示能源企業的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
因此,污染密集型企業、清潔型企業和能源企業的利潤函數分別表示如下:

其中,P1t、P2t、Pte分別表示污染品、清潔品和環境資源的價格水平,r1t、r2t、r3t、rrd,t、wt分別表示污染密集型企業的資本回報率、清潔型企業的資本回報率、能源企業的資本回報率、清潔型企業的綠色技術研發資本回報率和工資報酬,τ表示政府對企業針對污染排放征收的環境稅率,?表示政府對清潔品生產的綠色價格補貼,ν0表示政府對綠色技術研發投入的稅率補貼。
(二)公眾部門
公眾通過在污染品和清潔品之間的選擇,以及在消費和儲蓄之間選擇,實現終生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公眾的目標函數表示如下:

其中,C1t、C2t分別表示污染品和清潔品消費量,σ1、σ2分別表示污染品和清潔品消費的跨期替代彈性。ζ刻畫了公眾的綠色偏好程度,ζ>1表示公眾偏好于清潔品,ζ<1表示公眾偏好于污染品。ζ越大,表明公眾的綠色偏好程度越強。公眾的預算約束方程表示如下:

其中,?表示政府對公眾消費清潔品的綠色價格補貼;S1t、S2t分別表示公眾對污染品和清潔品的儲蓄量,St表示兩種商品形成的加總儲蓄品,1θ表示兩種儲蓄品之間的替代彈性,Qt表示加總儲蓄品的價格水平。G1t、G2t分別表示政府對于污染品和清潔品的消費量。Gt表示兩種商品形成的加總政府消費品,2θ表示兩種政府購買品之間的替代彈性,Πt表示加總政府購買品的價格水平。式(12)的左邊是公眾對污染品和清潔品的消費、儲蓄及政府購買量的總支出,右邊是公眾的勞動報酬和資本收益的總收入,因此,式(12)是公眾的預算約束方程。
資本形成方程式表示如下:

其中,1δ、2δ、δrd、3δ分別表示污染密集型企業資本折舊率、清潔型企業資本折舊率、清潔型企業環境技術研發資本折舊率和能源企業資本折舊率,I1t、I2t、Ird,t、I3t分別表示 t期污染密集型企業新增投資、清潔型企業新增投資、清潔型企業環境技術研發新增投資和能源企業新增投資。
(三)政府部門
政府通過對企業的污染排放征收環境稅,再將環境稅以財政政策形式補貼于企業的環境技術研發、公眾的清潔品消費、企業的清潔品生產及綠色政府采購。因此,政府的預算約束方程表示為:
(四)市場出清條件
(五)政策目標
本文將從經濟收益和生態收益兩個目標來分析穩態下不同環境財稅政策的效果差異,其中經濟收益用實際 GDP表示,生態收益用污染排放量表示,具體計算公式表示如下。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是污染品和清潔品價格的加權之和,具體表示為:

實際 GDP是污染品和清潔品產出的名義價值除以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具體表示如下:

污染排放量:

基于上述一階條件,通過求解企業的利潤最大化問題、公眾的效用最大化問題,并結合市場出清條件,可得出市場均衡下的穩態解。
三、參數校準
(一)數據來源
根據行業劃分標準的一致性和數據可獲得性,本文最終選取的樣本區間為2001—2014年。其中,分行業的工業總產值、固定資產投入以及年均從業人員相關數據來源于《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分行業的能源消耗數據來自《中國能源統計年鑒》。本文采用“三廢排放”來衡量污染排放情況,工業廢水排放、工業廢氣排放以及工業固體廢物排放的不同省份的各行業數據來自《中國環境統計年報》。行業總產值數據來源于《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分行業的 PPI數據來源于中國經濟信息統計網。其他相關的環境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環境統計年報》。
(二)參數校準
1. 污染密集型行業、清潔型行業和能源行業劃分
在剔除能源行業后,本文將基于污染排放數據來測算剩余行業的污染排放強度,具體計算方法如下。
① 計算各行業污染物單位產值的污染排放量,即UEij=Eij/Yi,其中Eij為行業 i的主要污染物j的污染排放量,Yi為各行業的工業總產值。
② 對各行業污染物單位產值的污染排放量進行標準化處理,計算各行業污染物單位產值的污染排放標準化值UEi′j,其中UE為各行業污ij染物單位產值的污染排放原始值,max(UEj)和min(UEj)分別表示主要污染物 j在所有行業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③ 將上述各種污染排放標準值等權重平均,計算廢水、廢氣和固體廢物的平均得分,即各行業的污染排放強度。
本文以各行業污染排放強度的中位數作為劃分依據,將剩余行業劃分為污染密集型行業和清潔型行業。表1是污染密集型行業、清潔型行業和能源行業劃分一覽表。

表1 污染密集型行業、清潔型行業和能源行業劃分一覽表
2. 環境規制強度計算
參考沈能(2012)等研究,本文從治污設施運行費用角度出發,選用各行業污染治理運行費用占工業產值的比重作為環境規制(ERI)的代理變量,由于《中國環境統計年報》未統計各行業的工業固廢治理運行費用,因此污染治理運行總費用僅包括各行業工業廢水和廢氣的治理運行費用。
3. 污染密集型企業和清潔型企業的生產函數估算

表2 生產函數及技術進步率回歸結果
4. 污染排放函數估算
考慮到工業廢水排放量和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數據存在缺失,本文分別使用污染密集型行業和清潔型行業的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作為污染排放量的代理變量,污染密集型企業和清潔型企業的能源消耗量、不同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對污染排放量的回歸結果見表3。

表3 污染排放函數估算結果
5. 模型其余參數設定
由于政府綠色采購、消費者的消費數據難以獲得,筆者借鑒董直慶等(2014)、Acemoglu等(2012)、黃茂興和林壽富(2013)等文獻給出模型其余參數的設定,具體如下:
四、環境財稅政策的作用機理分析
考慮到理論模型求解①考慮篇幅關系,模型求解過程并未給出,有興趣者請向作者索取。無法求出實際 GDP和污染排放的顯示解,因此當模型中某個參數變化時,無法直觀地知道這一變化對經濟收益和穩態下環境收益的影響。但是,我們可以使用模擬運算的方法來解決這一問題。基于前面參數校準數據和現實數據,我們可求出“基準模型”,進而可以對該基準模型進行參數穩健性檢驗和模擬預測能力檢驗,以判斷其能否較為準確地模擬中國經濟運行情況。在此基礎上,我們采用比較靜態分析方法來研究不同類型環境財稅政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機理。
(一)模擬中國經濟的基準模型及參數穩健性檢驗
通過前面的參數校準,我們可以在理論模型的基礎上設計出一個模擬中國經濟的“基準模型”。考慮到我國環境規制政策體系中并沒有環境稅,僅存在排污費,且排污費比重相對較小。因此,在基準模型中,本文假定環境稅τ=0.1,代入校準參數進行模型求解,可求得穩態下社會福利、經濟增長和污染排放分別為-0.1993、0.9266和0.1713。
理論模型的穩健性將直接決定不同類型環境財稅政策效果的可信度。因此,為考察各項環境規制政策對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影響是否穩健,本文對理論模型做了一系列的敏感性分析,以考察基準參數值在合理區間內變動時環境財稅政策對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機制是否符合宏觀經濟理論。表4為基準模型及參數的穩健性檢驗。穩健性檢驗設計的基本參數包括 5個:效用的時間偏好程度β、污染品消費的跨期替代彈性1σ、清潔品消費的跨期替代彈性2σ、資本折舊率δ和環境稅τ。如表4所示,上述8個參數的變化對模型均衡解的影響與經典模型結論基本保持一致,以環境稅為例,當環境稅τ上升時,污染排放量、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均下降。這表明在模型中考慮環境因素并引入環境財稅政策后,模型與經典理論是一致的。同時,模擬檢驗的結論也表明,本文的基準模型具有較好的實際經濟意義,模型參數具有良好的穩健性。

表4 基準模型和模型基本參數的穩健性檢驗
(二)不同類型環境財稅政策對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機理分析
圖1至圖5分別表示環境稅、綠色技術研發補貼、綠色政府采購、消費者綠色價格補貼和生產者綠色價格補貼對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影響。

圖1 環境稅上升對經濟收益和污染排放的影響
如圖 1所示,環境稅率上升會增加企業的環境成本,污染密集型企業依然按照原來的生產方式進行生產,但均衡點會沿著原有生產函數下降,這主要是由于環境技術相對固定,污染密集型企業在環境稅收成本上升時只能降低產出。清潔型企業在環境稅實施過程中具有主觀能動性,降低產出無法讓清潔型企業在市場中獲取競爭優勢。為此,清潔型企業需要加大環境技術研發投入來降低企業的環境稅負水平。企業環境技術創新動力取決于環境稅收成本與環境技術研發成本之間的關系。長期來看,清潔型企業需要支付的環境稅收成本必然高于研發成本,清潔型企業的技術創新會帶來清潔品質量提升,但環境稅對環境技術水平的激勵效應較弱。總的來看,環境稅率上升會帶來實際GDP下降,繼而降低企業的環境資源使用,污染排放總量下降。
如圖2所示,綠色技術研發補貼上升,清潔型企業實施環境技術研發的成本降低,使其有意愿加大環境技術研發投入,促進環境技術進步。清潔型企業綠色技術研發的正外部性會提高企業的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清潔型企業產出中可用于資本積累比例的上升,由于財富效應,污染密集型企業中可用于資本積累比例上升,產出增加,因而總的實際GDP就會上升。同時,由于清潔型企業環境技術進步增速高于污染密集型企業環境資源使用的增速,企業的污染排放總量下降。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于清潔型企業的環境技術研發效率較高,隨著環境技術研發補貼的上升,污染排放量下降的增速在上升。
如圖3所示,當政府綠色采購意愿上升時,政府加大對清潔品的采購量,這會對清潔型企業綠色生產戰略和綠色技術研發起到激勵作用。同時,政府的綠色采購會引導消費者的綠色消費行為,拉動綠色需求,引導清潔型企業增加綠色技術研發投入和生產資本投入,激勵清潔型企業的環境技術創新,提高生產率,拉高經濟增長水平。由于政府綠色采購是對清潔品的事后補貼,對清潔型企業環境技術研發的激勵效應有限,因此,污染排放總量略有下降,但變化幅度并不明顯。
如圖 4所示,政府給予消費者綠色價格補貼的上升會引導消費者的綠色消費行為,拉動綠色需求,誘導清潔型企業加大綠色技術研發投入和資本投入,提升清潔型企業產出。由于受到消費者財富效應的影響,消費者也會增加對污染品消費,誘導污染密集型企業加大資本投入。因此,總產出提高。但是,消費者綠色價格補貼是對清潔型企業生產最終品的事后補貼,對環境技術研發的激勵作用不強,加上消費者財富效應的影響,污染排放量則略有上升。

圖2 綠色技術研發補貼上升對經濟收益和污染排放的影響

圖3 綠色政府采購上升對經濟收益和污染排放的影響

圖4 消費者綠色價格補貼上升對經濟收益和污染排放的影響
如圖 5所示,生產者綠色價格補貼上升會直接刺激生產者的綠色生產行為,激勵生產者加大資本投入、勞動投入和環境技術研發投入,提高清潔型企業產出水平。由于受到消費者財富效應的影響,消費者也會增加對污染品消費,激勵污染密集型企業增加資本投入,提高污染密集型企業的產出水平,經濟總產出提升。然而,由于消費者綠色價格補貼也是對清潔型企業生產的事后補貼,環境技術研發投入的激勵效應不大,故污染排放總量上升。
圖 6是不同類型環境財稅政策對環境技術創新的影響。如圖 6所示,綠色技術研發補貼對環境技術創新的影響最明顯,且呈現邊際影響遞增的趨勢,而生產者綠色價格補貼對環境技術創新略有正向影響,環境稅、綠色政府采購和消費者綠色價格補貼對環境技術創新幾乎沒有影響。因為綠色技術研發補貼是直接對清潔型企業的環境技術研發投入要素進行補貼,等價于降低了環境技術研發投入要素的相對價格,補貼效率最強;而生產者價格補貼是對清潔型企業全要素投入的補貼,而全要素投入的補貼不會改變原有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補貼效率相對有效。政府綠色采購、消費者價格補貼是對清潔型企業的事后補貼行為,對環境技術研發創新的影響并不明顯。當然,不難發現環境稅對技術研發的投入效果也不明顯,這與本文模型設置有關。為突出研究不同類型環境財稅政策的效率差異,本文對環境污染造成的負外部性影響進行了簡化處理,只保留了技術研發技術的外延效用。

圖5 生產者綠色價格補貼上升對經濟收益和污染排放的影響

圖6 不同類型環境財稅政策對環境技術水平的影響
總體而言,不同類型環境財稅政策對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影響效果有所差異。環境稅是政府約束企業環境污染行為最有效的政策工具,而生產者綠色價格補貼是政府實現經濟增長目標最大化行為最有利的工具,但這一政策實施會損害環境質量。綠色技術研發補貼是激勵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最有效的政策工具,也是實現生態效益最直接的方式。
五、環境財稅政策的優化配置研究
經濟增長與環境治理的協調發展是單一環境財稅政策所無法實現的,那么以環境稅為核心的政策優化配置如何才能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治理的協調發展?在沒有外部性的經濟系統中,任何環境規制政策都會帶來效率損失,但環境污染負外部性的存在為環境規制政策的實施提供了空間。從上文分析可知,環境稅是政府約束企業環境污染行為最有效的政策工具,而綠色技術研發補貼是激勵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最有效的政策工具,對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改善效果顯著。綠色技術研發補貼需要消耗資源,如果環境技術研發不足以支撐經濟發展,那么政府實施環境財政政策支持環境技術研發的動機不足。這就是在我國以經濟發展為考核目標的三十多年綠色技術研發補貼不足的原因。從發展角度來看,生產者綠色價格補貼也有利于經濟增長,但不能從根本上降低環境污染,其原因上文已經闡述。各項政策對經濟和環境的影響側重點不同,這為本文通過政策間優化配置組合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治理的協調發展提供了操作空間。本文假定政府的各項財政補貼全部來源于環境稅收收入,實現環境自我管理的專款專用,為環境費改稅后建立相應規模的環境專項治理基金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持。下面本文將檢驗“環境稅+X”的組合政策在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雙重目標下的政策效果。
圖 7、圖 8、圖 9分別給出了“環境稅+生產者綠色價格補貼+綠色技術研發補貼”、“環境稅+綠色技術研發補貼+政府綠色采購”和“ 環境稅+綠色技術研發補貼+消費者綠色價格補貼”等組合政策在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雙重目標下的政策效果。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政策效果評價基準為沒有環境規制時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當一組政策同時實現經濟增長高于沒有規制時的初始經濟增長水平和污染排放低于沒有規制時的初始污染排放水平,我們就認為該組合政策可以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雙重紅利”。
如圖7所示,當征收環境稅時,經濟增長水平下降,政府可以通過生產者綠色價格補貼來提高經濟增長水平。但是,隨著生產者綠色價格補貼的提高,由于規模效應,環境污染排放量也提高了,環境稅所要實現的環境治理改善作用消失。因此,本文在政策組合中增加了綠色技術研發補貼。隨著綠色技術研發補貼的增加,迅速矯正了由生產者綠色價格補貼造成的環境污染排放量上升。如圖 7所示,經濟效益(左圖)的橫向等值切面以上和生態效益(右圖)的橫向等值切面以下的“生產者綠色價格補貼+綠色技術研發補貼”組合均能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治理協調發展。

圖7 “生產者綠色價格補貼+綠色技術研發補貼”組合政策對經濟效益(左)和生態效益(右)的影響
如圖 8、圖 9所示,征收環境稅后,經濟增長水平和環境污染排放量均下降,政府可以通過政府綠色采購或消費者綠色價格補貼來激勵清潔型企業加大生產以提高經濟增長水平,但環境污染排放量會略有上升。同時,由于政府綠色采購或消費者綠色價格補貼均是事后激勵行為,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不強。因此,本文在政策組合中增加了綠色技術研發補貼。隨著綠色技術研發補貼的增加,清潔型企業的環境技術研發行為受到激勵,技術的正外部性會帶來生產率的提升,最終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治理的協調發展。如圖 8、圖 9所示,經濟效益(左圖)的橫向等值切面以上的“政府綠色采購+綠色技術研發補貼”組合或“消費者綠色價格補貼+綠色技術研發補貼”組合均能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治理協調發展。
綜上所述,“環境稅+綠色技術研發補貼+生產者綠色價格補貼”、“環境稅+綠色技術研發補貼+政府綠色采購”、“環境稅+綠色技術研發補貼+消費者綠色價格補貼”均存在實現經濟增長和環境治理協調發展的組合政策空間,但“環境稅+技術研發補貼+生產價格補貼”的組合政策空間范圍要大于其他兩組政策組合的組合政策空間范圍。這表明,從實現經濟增長和環境治理協調發展雙目標出發,補貼生產端優于補貼消費端,過程補貼優于事后補貼。同時,如果以生態效益為首要目標,“環境稅+技術研發補貼+政府綠色采購”和“環境稅+技術研發補貼+消費價格補貼”的組合政策效果要優于“環境稅+技術研發補貼+生產價格補貼”組合政策效果;如果以經濟效益為首要目標,“環境稅+技術研發補貼+生產價格補貼”組合政策效果要優于“環境稅+技術研發補貼+政府綠色采購”和“環境稅+技術研發補貼+消費價格補貼”的組合政策效果。因此,政府需要優化配置環境財稅政策組合來實現經濟增長和環境治理的協調發展,但在短期內政府需根據其階段性目標來選擇不同類型的環境財稅政策組合。

圖8 “政府綠色采購+綠色技術研發補貼”組合政策對經濟效益(左)和生態效益(右)的影響

圖9 “消費者綠色價格補貼+綠色技術研發補貼”組合政策對經濟效益(左)和生態效益(右)的影響
六、結論及政策建議
在本文構建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中,環境資源是一種生產要素,在使用過程中會產生環境污染排放,損害生態效益,環境財稅政策的實施能有效約束企業的生產行為和環境污染行為,但不同類型環境財稅政策對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影響存在差異。理論研究發現,從環境治理的效果來看,綠色技術研發補貼、環境稅、綠色政府采購、消費者綠色價格補貼和生產者綠色價格補貼的政策效果依次降低;從經濟發展的效果來看,綠色技術研發補貼、生產者綠色價格補貼、綠色政府采購、消費者綠色價格補貼和環境稅的政策效果依次降低。其中環境稅是政府約束企業環境污染行為最有效的政策工具,而綠色技術研發補貼是激勵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最有效的政策工具,是實現經濟收益和生態收益雙重紅利最直接的途徑。
中國目前處于工業化后期,傳統的直接“經濟趕超”型環境政策已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環境政策更為重要的功能是激發企業內生性環境治理動機,完善有利于環境技術創新的市場制度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從而保證可持續性的經濟增長。因此,環境政策應向功能型環境政策組合轉變。本文驗證了“環境稅+綠色技術研發補貼+X”的組合政策在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雙重目標下的政策效果,發現“環境稅+綠色技術研發補貼+生產者綠色價格補貼”、“環境稅+綠色技術研發補貼+政府綠色采購”、“環境稅+綠色技術研發補貼+消費者綠色價格補貼”均存在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雙重紅利”的組合政策空間,但針對不同的階段性政策目標,政策組合的選用須有所區別。如果以生態效益為首要目標,“環境稅+綠色技術研發補貼+政府綠色采購”和“ 環境稅+綠色技術研發補貼+消費者綠色價格補貼”的組合政策效果要優于“環境稅+綠色技術研發補貼+生產者綠色價格補貼”組合政策效果;如果以經濟效益為首要目標,“環境稅+綠色技術研發補貼+生產者綠色價格補貼”組合政策效果要優于“環境稅+綠色技術研發補貼+政府綠色采購”和“環境稅+綠色技術研發補貼+消費者綠色價格補貼”的組合政策效果。
上述政策組合效果表明,環境稅收可以作為政府環境治理專項補貼的主要資金來源,通過專款專用的方式實施環境財政政策,從環境污染排放處罰和環境技術研發激勵兩方面約束企業生產行為,實現經濟增長和環境治理的協調發展。因此,在我國環境稅出臺后,政府可借鑒 PPP模式,通過投入母基金的形式,引入社會資本,設置環保專項基金,以實現專款專用、保證財權和事權的對等。
[1]董直慶,蔡 嘯,王林輝. 技術進步方向、城市用地規模和環境質量[J]. 經濟研究,2014(10):111-124.
[2]何小鋼. 綠色技術創新的最優規制結構研究[J]. 經濟管理,2014,36(11):144-154.
[3]黃茂興,林壽富. 污染損害、環境管理與經濟可持續增長——基于五部門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的分析[J]. 經濟研究,2013(12):30-41.
[4]逯元堂,吳舜澤,蘇 明等. 中國環境保護財稅政策分析[J]. 環境保護,2008(15):41-46.
[5]沈 能. 環境效率、行業異質性與最優規制強度——中國工業行業面板數據的非線性檢驗[J]. 中國工業經濟,2012(3):56-68.
[6]王文普. 環境規制、空間溢出與地區產業競爭力[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23(8):123-130.
[7]魏 瑋,何旭波. 節能減排、研發補貼與可持續增長[J]. 經濟管理,2013,35(11):1-12.
[8]武康平,童 健. 環境稅收政策抉擇機制優化研究[J]. 經濟學報,2015,2(3):115-135.
[9]嚴成樑,龔六堂. 資本積累與創新相互作用框架下的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J]. 世界經濟,2009(1):40-51.
[10]姚 昕,蔣竺均,劉江華. 改革化石能源補貼可以支持清潔能源發展[J]. 金融研究,2011(3):184-197.
[11]Acemoglu D.,Johnson S.,Robinson J. A.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Reply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2,102(6):3077-110.
[12]Bayindir-Upmann T.,Raith M. G. Should High Tax Countries Pursue Revenue-neutral Ecological Tax Reforms? [J]. European Economy Review,2003,47(1):41-60.
[13]Busom I.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s of R&D Subsidies [R].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urch Center Working Paper No. 99,1995.
[14]Fischer C.,Greaker M.,Rosendahl K. E. Robust Policies Against Emission Leakage:The Case for Upstream Subsidies[R].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4742,2014.
[15]Glomm G.,Kawaguchi D.,Sepulveda F. Green Taxes and Double Dividends in a Dynamic Economy [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ling,2008,30(2):19-32.
[16]Greaker M.,Rosendahl K. E. Environmental Policy with Upstream Pollution Abatement Technology Firm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 Economic and Management,2008,56:246-59.
[17]Greenstone M. A Reexamin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Responses to the 65-MPH Speed Limit[J]. Economic Inquiry,2002,40:271-78.
[18]Jorgenson D. W.,Wilcoxen P. J. Reducing US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An Assessment of Different Instruments [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ling,1993,15(5/6):491-520.
[19]Koskela E.,Schob R. Alleviating Unemployment:The Case for Green Tax Reforms [J]. European Economy Review,1999,20(1):1723-46.
[20]Krutilla K.,Jung C.,Boyd R. Incentives for Advanced Pollution Abatement Technology at the Industry Level:An Evaluation of Policy Alternative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6,30:95-111.
[21]Laplante B.,Rilstone P.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s and Emissions of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in Quebec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 Management,1996,31(1):19-36.
[22]Lewis J. I.,Wiser R. H. Fostering a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 Industry: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Wind Industry Policy Support Mechanisms [J]. Energy Policy,2007,35(3):1844-57.
[23]Magat W. A.,Viscusi W. K. Effectiveness of the EPA's Regulatory Enforcement:The Case of Industrial Effluent Standards [J].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1990,33(2):331-60.
[24]Milliman S. R.,Prince R. Firm Incentives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Pollution Control[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89,17:247-65.
[25]Nemet G. F.,Baker E. Demand Subsidies versus R&D:Comparing the Uncertain Impacts of Policy on a Pre-commercial Low-carbon Energy Technology[J]. Energy Journal,2009,30(4):49-80.
[26]Oueslati W. Environmental Tax Reform:Short-term versus Long-term Macroeconomic Effects[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2014,40:190-201.
[27]Panayotou T. Demystify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Turning a Black Box into a Policy Tool [J].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7,2:465-84.
[28]Petrakis E.,Poyago-Theotoky J. R&D Subsidies versus R&D Cooperation in a Duopoly with Spillovers and Pollution [J]. Australian Economic,2002,41(1):37-52.
[29]Porter M. E. America′s Green Strategy [J]. Scientific American,1991,264(4):168-264.
[30]Porter M. E.,Van der Linde C.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9(4):97-118.
[31]Poyago-Theotoky J. The Organization of R&D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2007,62:63-75.
[32]Ulph A.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When Governments and Producers Act Strategically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6,30:265-81.
[33]Van den Bergh J. C. J. M.,Faber A.,Idenburg A. M.,et al. Survival of the Greenest: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Policies for Energy Innovation [J]. Environmental Sciences,2006,3(1):57-71.
[34]Requate Till,Unold Wolfram. Environmental Policy Incentives to Adopt Advanced Abatement Technology:Will the True Ranking Please Stand up?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3,47(1):12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