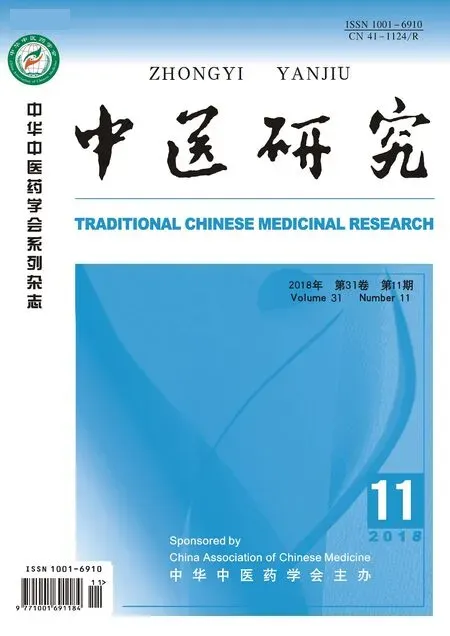論仲景“通腑安臟”思想
張越美,張 毅,李金田,李 娟,郭宏明
(甘肅中醫藥大學,甘肅 蘭州 730000)
《素問·五藏別論篇》曰:“所謂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也,故滿而不能實。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簡潔地概括了五臟的生理特點,“藏而不瀉”“滿而不實”是強調五臟的精氣宜保持充滿,但必須流通布散而不應停滯。五臟藏精氣,故滿而不實;六腑則不藏精氣,但受水谷,故實而不滿。若感受外感六淫,五臟陰陽失調,則會出現氣機阻滯、血脈不通、水氣不化等癥狀;六腑瀉而不藏,如出現排瀉障礙,代謝受阻,必會影響五臟功能發生病變。對于某些疾病,因其臟腑關系,仲景選擇用“通腑安臟”的方法治療。
1 何謂“通腑安臟”
《說文解字》中,“通”即為“達”[1]。中醫學中,機體臟腑功能協調、氣血津液暢通等則為生理狀態;而外感內傷所致的郁、結、滯、壅等“不通”則為病理狀態[2]。正如《素問·六微旨大論篇》云:“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通腑安臟即是針對某些五臟的病變,用通腑的方法以使五臟元真通暢的一種治療法則。 縱觀漢代以前的醫學理論,因已蘊含通腑安臟的思想,所以“中滿”“小大不利”無論為本、為標皆歸首治之列。《素問·湯液醪醴論篇》亦提出對“五藏陽以竭”之水腫,用開鬼門、潔凈府、去菀陳莝之法以“疏滌五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又云:“中滿者,寫之于內。”意指病邪留滯于內使中滿腑實者,宜用攻逐通瀉法治療,這是對通腑安臟法的最初認識。漢代張仲景在其基礎上又進一步發展了通腑安臟的治療思想,并豐富其內涵。
2 “通腑安臟”法的理論基礎
機體復雜的生命活動均起源于內臟的功能,內而消化、循環,外而視聽、言行,無一不是內臟功能活動的表現,而內臟的活動實質是機體整個生命的活動[3]。《素問·五臟別論篇》已對機體五臟六腑的生理特征有了較完整的概括。《靈樞·本輸》云:“肺合大腸……心合小腸……肝合膽……脾合胃……腎合膀胱。”從臟腑生理上看,五臟功能主藏精氣,故屬陰;六腑功能主消化和排泄,故屬陽。陰主里,陽主表,形成陰陽表里相合關系。此外,從經絡循行路徑來看,每條經所屬一臟(腑)即絡一腑(臟),因此,通過經絡的作用,臟腑之間亦形成了相合關系。因此,機體不僅是一個有機整體,而組成機體的各臟腑形體官竅之間也是相互關聯、相互為用。通過這些聯系,臟與臟、腑與腑、臟與腑之間關系更加密切。同時也遵循了中醫學整體觀念的原則。
《素問·通評虛實論篇》指出:“五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生也。”通腑安臟,重在通腑。六腑以通為用,以降為順。一方面,可以通表里相合之腑,經脈的相互絡屬關系構成了心與小腸、肺與大腸、脾與胃、肝與膽、腎與膀胱等臟腑的表里關系;生理上相互促進,病理上相互影響。另一方面,可以通氣化相通之腑,根據各經絡之間的生理活動,臟腑之間的氣化相通主要有心與膽相通、肝與大腸相通、肺與膀胱相通、脾與小腸相通、腎與三焦相通等[4]。如膽郁痰熱內擾心神所致的驚悸、煩躁、失眠等癥狀可通利膽腑以寧心安神;邪毒壅滯大腸可擾及肝,使之疏泄功能失常,故可通下大腸,使肝火從大便而解。《素問·咳論篇》云:“五藏之久咳,乃移于六府。脾咳不已,則胃受之……肝咳不已,則膽受之……肺咳不已,則大腸受之……心咳不已,則小腸受之……腎咳不已,則膀胱受之。”即說明病理上臟病不愈,則影響所合之腑發病。反之,腑病亦足以影響所合之臟發病。由此可見,六腑失于通降,可涉及五臟,所謂“腑氣不通則臟氣不安”。反之,五臟邪實內盛,亦常涉及六腑,腑氣通暢,給邪以出路,則臟氣可安。這種臟腑間病理上相互影響的整體觀,正是“通腑安臟”法確立的重要依據。
3 《傷寒雜病論》“通腑安臟”法辨析
3.1 通腸瀉熱,安神定志
《傷寒雜病論》第106條,因太陽病不解,隨病情發展,在表之邪化熱入里,深入下焦與體內瘀血相互搏結,于是便形成血熱互結于下的蓄血證。其臨床表現除有太陽病不解的癥狀外,最主要的是血熱互結下焦,致少腹拘急、脹痛;還因心主血脈,主神明,亦上擾于心神,導致神志異常,有如狂之狀。仲景給予桃核承氣湯,方中桃仁活血化瘀;桂枝溫通血脈,以助桃仁;配合調胃承氣湯苦寒瀉下,導瘀熱下行,下熱散血,邪熱隨瘀血而去,心神則安。第237條中陽明蓄血影響心神出現健忘給予抵當湯治療亦是此理。第207條曰:“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陽明病,未經吐下,則實熱留駐,燥結為患,故心煩。胃脈通于心,胃中燥實熱邪循經上擾,則神明不安而心煩。故予調胃承氣湯上承火熱之氣調胃中之實邪,芒硝承君火之熱以解心煩,甘草片調中,大黃引熱從腸胃而出,心煩自除,神明自安。以上均是仲景通過通腸腑除瘀熱,以安心神,體現了其“通腑安臟”的思想。
3.2 分消二便,健脾除濕
陽明郁熱在里發黃,濕熱壅滯中焦,致土壅木郁,肝膽疏泄失常,濕熱與郁熱郁蒸于肌膚導致的黃疸,對此,仲景給予茵陳蒿湯,利小便、退黃、逐熱。條文后注曰:“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黃,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由此可見,使用茵陳蒿湯的目的是利尿退黃而祛脾經濕熱。又有第159條曰:“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糧湯主之。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脾主濕,脾困濕阻則易發生泄瀉,仲景治療此類泄瀉采用通利小便法。因脾被濕困,用健脾溫中的理中湯無效,其主癥是下利,故采用清瀉脾濕法無效,只能給予滲利小腸、分消二便的方法,使體內濕邪從小便而出,脾濕得解,瀉利自止。
3.3 急瀉胃火,腎陰得救
《傷寒雜病論》第320,321,322條統稱少陰三急下證。所謂少陰病,已提示有腎陰枯竭之證,其總病機皆為陽明燥實灼爍真陰,腸腑不通,土燥水竭,患者因轉屬陽明,致胃熱亢盛、胃火上炎、津液愈虧,故有自利清水、腹脹、不大便、口燥咽干等癥狀。仲景投以大承氣湯,當急下陽明之實,以救少陰欲竭之陰。《醫宗金鑒》有云:“邪至少陰二三日,即口燥咽干者,必其人胃火素盛,腎水素虧,當以大承氣湯,急瀉胃火以救腎水,若復遷延時日,腎水告竭,其陰必亡,雖下無及矣。”[5]即用通瀉陽明燥熱以救將竭之腎液。同時,必須明確急下之意,刻不容緩。若有拖延,則后果堪憂。
3.4 通腸利水,理肺健脾
太陽中風而水飲積于胸脅,出現心下痞硬滿、引脅下疼痛等病癥。若飲邪上迫于肺,肺氣不利則呼吸短促;影響及胃,則胃氣上逆而發生干嘔。第152條中,仲景采用十棗湯通過峻下逐水的藥物,使體內水邪不能阻礙肺絡,從而使肺氣得以宣發。柯韻伯亦注曰:“……此則外走皮毛而汗出,上走咽喉而嘔逆,下走腸胃而下利,浩浩莫御,非得利水之峻劑以直折之,中氣不支矣。此十棗之劑,與五苓、青龍、瀉心等法懸殊矣。”此外,亦可見于第71,72,74條五苓散證,因水氣停蓄、脾失轉輸、膀胱氣化不利所致,以通陽化氣利小便法,使蓄水去,則肺可化氣,脾可升精,膀胱可氣化,諸癥得解。正如《素問·經脈別論篇癥》所說:“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并行。”《金匱要略·咳嗽痰飲病篇》第26條曰:“支飲胸滿者,厚樸大黃湯主之。”因水飲停于心下,凌心射肺,后水結氣滯,郁而化熱,飲熱交結心肺,致肺失宣降,故有胸中脹滿、咳逆倚息不得臥、腹滿、大便秘結等癥狀。仲景對飲熱交結于胸的支飲實證,治宜蕩熱逐飲、行氣開郁。通過瀉腸以開肺,使腸腑通利,因勢利導給邪以出路,郁熱從大便而除,病癥自然解除。以上仲景將臟腑關系運用到疾病的辨證論治過程中,就是“通腑安臟”思想的典型表現。
4 小 結
綜上所述,《傷寒雜病論》中“通腑安臟”法的運用已相對成熟,特別是蓄水、蓄血、下利、陽明熱實證等均用此法治療。對此,首先要認識到整體觀念、辨證論治在整個疾病治療過程中的重要性。任何情況下,通腑安臟的前提是正確的辨證論治,也是臟腑辨證的具體體現,其病理性質應屬本虛標實,實證且病勢較急,有腑氣不通的表現,臟邪需從腑出,臟腑升降相因,腑氣通降則臟氣安和,體現了臟腑之間的動態平衡,且不應局限于單純的臟腑表里關系以及臟腑氣化關系。其次,通腑時可根據病邪性質、病勢變化,審時度勢,因勢制宜,導邪外出,關鍵在于祛邪勿傷正氣,使邪去正安。另外,注意中病即止,以防生變。值得注意的是,《傷寒雜病論》中還有諸不可下的論述,主要闡述五臟虛時不可用下法。還體現了張仲景邪氣實則諸腑宜通,正氣虛則諸臟宜固的辨證思想。宜通腑或是補臟,應當視機體正氣強弱而定,不可諸證均用通腑之法。總之,通腑安臟這一思想的提出是《黃帝內經》理論與歷代各醫家理論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其思想內涵和價值就在于告訴臨床它并非只是一種治療手段,而是一種中醫理念和思維模式,值得繼承、探討并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