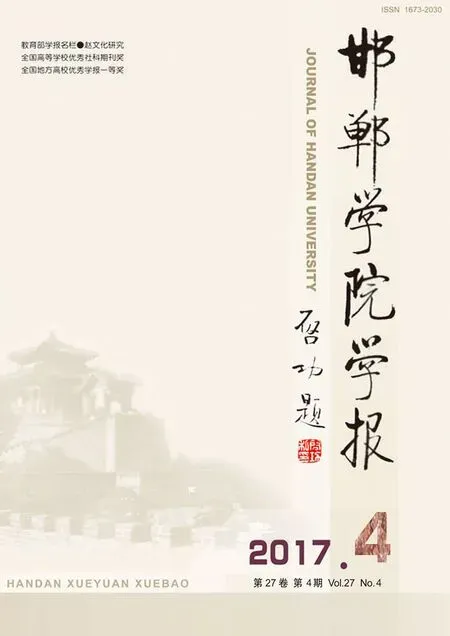先秦巫者的祝詛放蠱活動
[韓]趙容俊,[韓]金炫抒
?
先秦巫者的祝詛放蠱活動
[韓]趙容俊1,[韓]金炫抒2
(1. 中國人民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 100872;2. 北京外國語大學 亞非學院,北京 100089)
運用商代甲骨卜辭的記錄,并與先秦的傳統文獻及出土文獻、考古學的報告,互相印證,探討先秦巫者曾從事的祝詛放蠱方面的巫術活動。巫者職司交通鬼神,其本身雖不具超乎自然的力量,但古人相信巫者可藉鬼神之力以成就諸多事。祝詛放蠱之事,因古人相信巫者能為祝詛放蠱之事,遂成為巫者從事之重要職事。巫者不僅能解除人之災禍,尚且能以其術害人,學術術語稱為“黑巫術”、“兇巫術”,于制敵、制人、作弄敵對者時,便施行此法。
巫術;祝詛;放蠱毒人;傳統文獻;出土文獻
一、緒 論
祝詛放蠱之事,因古人相信巫者能為祝詛放蠱之事,遂成為巫者從事之重要職事。巫者不僅能解除人之災禍,尚且能以其術害人,學術術語稱為“黑巫術”、“兇巫術”,于制敵、制人、作弄敵對者時,便施行此法。
二、甲骨卜辭所見之祝詛放蠱
首先,祝詛之術,又稱詛咒、詛語、咒語、巫辭、巫術語言等,因以朗誦或歌唱的形式表達巫術語言,或屬于其人的物件上施行祝詛巫術,故從而成為祈求危害對方的巫術形式。



蠱,以鬼物飲食害人。[3]683
此種放蠱毒人之術,于古籍文獻中則多見之,如在《前漢書·江充傳》中便有其記載,其云:
后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后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奸,奏言:“上疾祟在巫蠱”。于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污令有處。[4]206
由此可知,漢代喧鬧一時的巫蠱之獄,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
對于放蠱毒人之術的記載,可追溯至三千年前的商代,于商代甲骨卜辭中,即可見之,玆略舉數例于下:
貞:母丙亡蠱?
貞:母丙允有蠱?(以上皆見于《合》02530正)
有疾,不蠱?(《合》13796)
貞:有災,不隹(惟)蠱?(《合》17183)
貞:隹(惟)蠱?二告。不牾蛛。
不隹(惟)蠱?(以上皆見于《合》17184)
據此可以得知,于殷商時期,已盛行放蠱毒人之術。
由此觀之,于殷商時期,此種祝詛放蠱巫術的流行,已可證實。尤其,于商代的甲骨卜辭中,放蠱毒人巫術的辭例,屢見不鮮,故可知此種放蠱毒人的巫術,已于商代之前便盛行。[2]644-646
三、兩周文獻中的祝詛放蠱
(一)祝詛巫術
1. 祝詛盟誓
巫者從事祝詛盟誓之術,由于其中保留不少晦澀的語言,以及屬于其人的物件上施行的祝詛巫術,足以影響對方的觀念,則加上更大的神秘性,正因為如此,頗為盛行于一般民間之中。此事如《尚書·呂刑》便有其記載,其云:
民興胥(相)漸(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反)詛盟。[6]247
由此可知,此種祝詛盟誓之術,于中國古時,頗為流行于一般民間之中。
不寧唯是,于兩周古籍文獻中,已記載祝詛盟誓巫術流行之甚廣,又盛行于朝廷之中等事,如《周禮·詛祝》曰: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6]816
又《周禮·司盟》亦云:
司盟:掌盟載之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旣盟,則貳之。[6]881
由此不難得知,于周朝朝廷中,已設負責詛祝盟誓之官之可能①。
除此傳世文獻之外,若視兩周出土文獻的記載,亦可多見盟誓的記錄。如在2009年4月,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入藏一批戰國楚簡,此楚簡的年代,約為公元前340年。[7]1
其中在《春秋左氏傳》篇中,便有諸侯在相會舉行盟誓儀式時,古人重視執行其盟誓之言的內容,其簡文曰:

由此可知,古人在舉行盟誓儀式時,便重視其盟誓之言的執行。
除此在諸侯相會時舉行盟誓載書儀節之外⑧,又由《詛楚文》⑨的“箸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8]298之句可知,巫者將盟詛之辭上告鬼神,且作為盟詛之監察者。此事在侯馬盟書“委質類”的載書中,亦有其記載,其云:
由此可見,巫覡祝史所薦的“說釋”即盟辭,其盟書之陳告必能溝通人神意旨,故證明巫者確實負責將盟詛之辭上告鬼神[10]327-328。由此觀之,祝詛巫術,除民間之外,亦盛行于朝廷、貴族社會之中。
2. 詛咒巫術
(1)傳世文獻所見之詛咒巫術
就詛咒巫術而言,于浩如煙海的兩周古籍文獻中,亦屢見不鮮,如《尚書·無逸》便有其記載,其云: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6]222-223
孔穎達疏于其下,曰:
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6]222-223
又《尚書·湯誓》亦云:
〔湯〕王曰:“……今汝其曰:‘夏罪其如臺(何)?’夏王率遏(止)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何)喪?予及汝皆亡!’”[6]160
此文因夏桀兇德日深,百姓便欲與之俱亡,乃如此詛咒之。
又《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亦有其記載,其云:
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于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6]1972
此文中的食肉、寢皮等言,則為憎惡敵人的最惡毒詛咒。[5]332
又在《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年》中,記載晏子力諫于齊景公免殺祝、史之事,其云:
〔晏子對曰:〕 “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尢(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后可。”[6]2093
故晏子認為,當時百姓向暴虐君主的詛咒,具有相當巨大的作用⑤。
此外,若視詛咒巫術的施術之例,尚有“祝移”之術,此術乃為巫者將罹禍人之災難,轉移至肇禍人身上,并使其人罹禍的巫術。又如“詛軍”之術,此術不僅免除施術者一方遭遇敗軍之禍事,并且施以事先詛敗對方為獲勝免禍之手段。詛咒巫術活躍于戰場的例證⑥,如《前漢書·匈奴傳》便有其記載,武帝征伐匈奴(公元前92年至前89年),漢軍追至漠北的范夫人城,范夫人則以詛咒巫術攔阻漢軍。[4]350
(2)出土文獻所見之詛咒巫術
若視出土文獻的記載,自1979年始,于河南省溫縣武德鎮公社西張計大隊,曾出土春秋末期(公元前497年)的溫縣盟書。此溫縣盟書,目前共發現一百二十四土坑,其中十六土坑出土書寫盟辭的大量石片。[11]78
若視其中在T1坎1:2182出土的載書記錄,便有詛咒巫術的內容,其文曰:
上引盟誓辭文的答疑是說,乃為今后忠心服侍主君,若與亂臣為友,丕顯的晉國神靈,將仔細審察,便絕子絕孫。[11]79-81
不寧唯是,于2009年4月,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入藏一批戰國楚簡,此楚簡的年代,約為公元前340年[7]1。其中在《春秋左氏傳》篇中,亦有詛咒盟書辭文,其簡文曰:
由此可知,于兩周時期,便盛行盟誓詛咒巫術。
除此之外,古人將一切的疾病與災殃,皆認為惡鬼作祟或受神靈懲罰的結果,故巫者以法術驅除纏身的惡鬼,以排難解憂且脫離其桎梏。此時巫者或用詛咒法,祓禳山川邪鬼作祟的癘疫與災殃⑧,此乃屬于巫者的一種祝詛法術之類,殆毋庸置疑矣。
若視出土文獻的記載,此種巫者施行的詛咒法術,則不乏得見。如在1975年末,在云夢睡虎地M11號墓葬發現的秦簡《日書》中,便有其記載。茲舉其一二文為例,其簡文曰:
行到邦門困(閫),禹步三,勉(進)壹(一)步,謼(呼):“皋,敢告曰:某行毋(無)咎,先為禹除道。”即五畫地,掓(拾)其畫中央土而懷之。(此簡文見于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第111簡背至第112簡背)[12]223-224
據此不難得知,于睡虎地秦簡《日書》中,便有巫者施行詛咒法術的事實⑨。
此外,日本學者白川靜認為,《大祝禽鼎》乃為周器,故可知周代時,祝官的設置已極普遍,此時人亦深信祝具咒詛之能⑩。
3. 小結
綜上所陳,由上述幾例可知,祝詛與詛咒之術,除民間之外,亦盛行于朝廷與貴族社會之中。不僅如此,亦可證明兩周時期已有祝詛與詛咒的施術。尤其,中國古代的巫者運用咒術巫術,即運用某種特殊之語言、物品、符號、符箓,乃至配合其他器物、祭祀儀式之運用,以從事詛咒對方之巫術。
(二)放蠱巫術
1. 放蠱毒人之術
兩周文獻中的放蠱毒人之術,如《春秋左傳·昭公元年》云:
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于文,皿蟲為蠱。谷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皆同物也。”[6]2025
此文之下,孔穎達疏云:
以毒藥藥人,令人不自知者,今律謂之蠱毒。[6]2025
《周易·蠱》亦云: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6]35
孔穎達疏于其下,曰:
褚氏云:“蠱者,惑也。物旣惑亂,終致損壞。”[6]35
由此可見,放蠱毒人之術法,淵源悠久。
不寧唯是,對于中國古代原始毒人巫術的情形,如《論衡·言毒篇》便有其記載,其云:
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脤胎,腫而為創(瘡)。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移)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于江南,含烈氣也。[13]950
此種記載未免夸大,即使如此,卻充分表現秦代的社會心理。[14]304-305
此外,有關口舌有毒與毒人巫術的出土文獻記錄,于1975年末,在云夢睡虎地M11號墓葬發現的秦簡《封診式·毒言》篇中,便有其記載,其云:

此篇記載里人士伍丙口舌有毒,里人送府共同報告,且其外祖母曾因口舌有毒論罪,30歲時處以流放。由此可知,依其判例,若有毒言之疾,于當時的法律規定上,應將之處以遷刑[14]304。
此種放蠱毒人之方法極其為多,例如金蠶蠱、疳蠱、癲蠱、胂蠱、泥鰍蠱、石頭蠱、蛇蠱、篾片蠱、蜈蜙蠱等等[15]230。此外,亦有養鬼放鬼作害于人,以及致人于死地為莫上之樂的黑巫術等,甚為無稽,此種放蠱毒人巫術之例甚多,舉不勝舉。
2. 治蠱之法
就治蠱之法而言,有關巫術性治蠱之術的記錄,如《周禮·翦氏》便有其記載,其云:
翦氏:掌除蠧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6]889
又《周禮·庶氏》亦云: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以〕嘉草攻之。凡敺(驅)蠱,則令之比之。[6]888
其下鄭玄注云:
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燻之。[6]888
此文中的“嘉草”,今人胡新生認為特指治蠱的蘘荷。[16]444-445
據此《周禮》的二文不難得知,巫術性治蠱之法有二,一為以“攻說”禳法祈求神靈除蠱,二為以草藥“攻之”而燻蟲殺蠱?。因此,于中國兩周時期,不僅流行放蠱毒人之術,又有巫術性治蠱之法。
除此巫術性治蠱之外,亦有勸時王禁止放蠱毒人之術的記錄,如傳為周初呂望(即姜太公)所撰的《六韜·上賢》篇中,便有周文王問姜太公治國之道的內容,其中則有太公回答王人者應慎重六賊、七害之事,其云?:
〔太公曰:〕“七害者,……。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
由此可知,于王人者應慎重的六賊、七害之事中,便提及放蠱毒人之術,且勸王止之。
尤其,如《禮記·王制》便記載周代制定的治蠱之法,其云:
析(巧)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6]1344
其下鄭玄注云:“左道,若巫蠱及俗禁。”,可知巫蠱“左道”與“邪門”,已列入于周代的法制之中,乃變為嚴厲懲治之對象。[17]306-307
由此觀之,于兩周時期,隨著中央王朝的逐漸確立,又基于維護統治者的利益,原始時代的宗教、政治并存的局面,已發生變化,故制定各種措施,以防范危害社會的行為。[17]307
四、結語
巫者職司交通鬼神,其本身雖不具超乎自然的力量,但古人相信巫者可藉鬼神之力以成就諸多事。古代巫者其主要的活動類型,則可分為交通鬼神、醫療巫術、救災巫術、生產巫術、求子生育、建筑巫術、喪葬巫術、祝詛放蠱、神明裁判等九項。
祝詛放蠱之事,因古人相信巫者能為祝詛放蠱之事,遂成為巫者從事之重要職事。巫者不僅能解除人之災禍,尚且能以其術害人,學術術語稱為“黑巫術”、“兇巫術”,于制敵、制人、作弄敵對者時,便施行此法。
古人對于祝詛放蠱的巫術十分注意,此事由商代甲骨卜辭的記錄、先秦傳統文獻與出土文獻的記載、考古學的報告等不難得知,古時巫者曾擔任祝詛放蠱巫術的職責,則從事祝詛盟誓、詛咒巫術,以及放蠱毒人之術、治蠱之法等的巫術活動。
[1]許進雄. 古文諧聲字根[M].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2]詹鄞鑫. 心智的誤區——巫術與中國巫術文化[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3]許慎. 說文解字注[M]. 段玉裁,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上海書店編寫組. 二十五史(全十二冊)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許進雄. 中國古代社會——文字與人類學的透視[M].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6]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全二冊)[M]. 阮元,校刻. 北京:中華書局,1980.
[7]曹錦炎. 浙江大學藏戰國楚簡[M].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8]郭沫若. 石鼓文研究——詛楚文考釋[M]. 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
[9]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 侯馬盟書[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
[10]林志鵬. 殷代巫覡活動研究[D]. 臺北:臺灣大學中文所,2003.
[1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河南溫縣東周盟誓遺址一號坎發掘簡報[J]. 文物,1983(3).
[12]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睡虎地秦墓竹簡[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13]黃暉. 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全四冊)[M]. 北京:中華書局,1990.
[14]徐富昌. 睡虎地秦簡研究[M].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15]宋兆麟. 巫與巫術[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
[16]胡新生. 中國古代巫術[M].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
[17]鄧啟耀. 中國巫蠱考察[M].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
(責任編輯:賈建鋼 校對:朱艷紅)
① 若視盟誓載書的基本儀節,如《周禮·司盟》便有其記載,于“司盟:掌盟載之灋(法)。”之下,鄭玄注云:“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上冊)《周禮·秋官司寇》卷第36《司盟》第881頁。
② 曹錦炎編《浙江大學藏戰國楚簡·春秋左氏傳》第154-155頁。此文亦可見于《春秋左傳·襄公九年》之中,其云:“子駟、子展曰:‘……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潔)要盟,背之可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下冊)《春秋左傳》卷第30《襄公九年》第1943頁。

④對于《詛楚文》寫成的背景,楊寬在《戰國史》書中曾提及,其云:“當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公元前313年)秦、楚初次大戰前,秦王曾使宗祝在巫咸和大沈厥湫兩個神前,舉行這樣咒詛楚王的祭禮,北宋出土的《詛楚文》石刻,就是當時宗祝奉命所作,把楚王咒詛得如同商紂一樣的暴虐殘忍,請天神加以懲罰,從而‘克劑楚師’。”楊寬《戰國史》(增訂本)第54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⑤ 除此《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年》的記載之外,晏子的此種多人詛咒具有相當巨大的作用的見解,如《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中,亦可見之,其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眾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吳則虞編《晏子春秋集釋》(上冊)第一卷《內篇諫上·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43-46頁,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⑥ 有關戰場上施行的詛咒巫術,楊寬在《戰國史》書中曾提及,其云:“對敵國君主咒詛的巫術:當時宋、秦等國流行在天神前咒詛敵國君主的巫術。他們雕刻或鑄造敵國君主的人像,寫上敵國君主的名字,一面在神前念著咒詛的言詞,一面有人射擊敵國君主的人像,如同過去彝族流行的風俗,在對敵戰斗前,用草人寫上敵人的名字,一面念咒語,一面射擊草人。”楊寬《戰國史》(增訂本)第542頁。
⑦曹錦炎編《浙江大學藏戰國楚簡·春秋左氏傳》第148-150頁。此文亦可見于《春秋左傳·襄公九年》之中,其云:“將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閑(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至)告。自今日既盟之后,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下冊)《春秋左傳》卷第30《襄公九年》第1943頁。
⑧ 有關巫者用詛咒法祓禳山川邪鬼作祟的事實,如《說苑·辨物》便有其記載,其云:“扁鵲曰:‘入言鄭毉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毉者曰:苗父。苗父之為毉也,以菅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轝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前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卷第18《辨物》第471頁。


? 鄧啟耀《中國巫蠱考察》第48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亦可參見詹鄞鑫《心智的誤區——巫術與中國巫術文化》第641-642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 [周]呂望撰《六韜》卷第一《文韜·上賢》,載于《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26冊《子部三二·兵家類》,第726-15頁。亦可見于曹勝高、安娜譯注《六韜·鬼谷子》(重印本)《文韜·上賢》第36-38頁,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B99
A
1673-2030(2017)04-0043-07
2015-08-15
趙容俊(1968—),男,韓國慶尚北道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專任講師,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