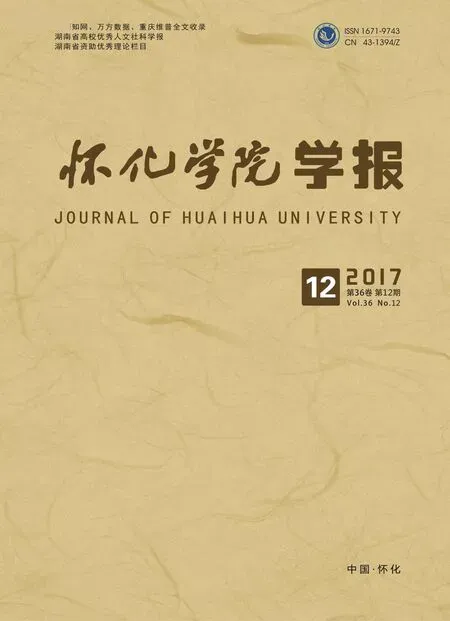胡文蔚對《莊子》結構整體性的探索及其莊學意義
彭時權
(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重慶401331)
自北宋王安石科舉改革以經義取士后,經義、策論文章地位愈來重要,至南宋時期出現文章“定格”,“南渡以后,講求漸密,程式漸嚴,試官執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論學繩尺》提要)[1]1702“至宋季則其篇甚長,有定格律。首有破題,破題之下有接題,有小講,有繳結,以上謂之冒子。然后入官題,官題之下有原題,有大講,有余意,有原經,有結尾。篇篇按此次序……”(元·倪士毅《作義要訣自序》)[2]1498由此相應也產生了一些對文章結構文脈和創作方法等深入研究的作品,如周密《浩然齋雅談》、樓昉《過庭錄》、《朱子語類》中的《論文》等隨散型文話,陳骙《文則》、李淦《文章精義》等文章學專著,一時文章學作品煌煌而興,王照水就說“古文研究與批評真正成為一門學科,即文章學之成立,殆在宋代。”(《歷代文話序》)[3]2延及明代,時文在官方科舉中地位的確立,研究時文、古文的文章學理論也因此得到極大發展,此時文章學作品更是層出不窮,一時蔚為大觀,如宋濂《文原》、曾鼎《文式》、吳訥《文章辯體》、楊慎《升庵集·論文》、王文祿《文脈》、歸有光《論文章體則》、唐順之《文章雜論》、徐師曾《文體明辨》等等。中后期受王陽明心學的影響,學者們紛紛轉向崇尚心性自由的莊學中去。因此,治莊家們往往能夠以文學視角審視《莊子》,關注其內在的文章結構。盡管此時從文學視角研治莊學的作品良莠不齊,缺乏系統性,“卻從整體上推動了《莊子》散文評點的向前發展,從方法上與理論上為清代《莊子》散文評點的高潮與成熟打下了較為堅實的基礎。”[4]45清初治莊家胡文蔚《南華真經合注吹影》 (以下簡稱《吹影》)因循了明代治莊思路,以義理解莊為主,同時關注《莊子》的整體結構,對內外雜三篇整體性進行探索,首次提出了通篇可作“一篇讀”,內七篇“次第終始,井井有條”[5]153。由此也影響了清代之后的治莊家們,為清代莊子文學研究的繁盛做了堅實的奠基。
一、胡文蔚對《莊子》結構整體性問題的辯駁與探索
清代方苞曾對文章“結構”思想的進行溯源考證,其《又書貨殖傳后》中說:“《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6]58方苞認為“成體之文”乃由“義法”經緯輔成,正是《易》中的“言有物”“言有序”。而這里的“義法”其實正是指文章結構,具有兼含義旨命意與布局陳列兩者的思想。劉勰《文心雕龍》中《附會》篇對文章結構論述道“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涂于同歸,貞百慮于一致,使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7]378其“總文理”“雜而不越”“附辭會義”“務總綱領”無疑承襲“義法”思想,并且可以看出,傳統文章學中的結構不同于近代西方文論中所謂的“形式”結構,它是以“義”統“法”,“辭”會于“義”而非“形式即意味”的“結構”思想。傳統的“言有物”“文以載道”思想注定了中國傳統文章學中的“結構”思想始終是以“義”為中心,而“法”“辭”相輔佐,而非純粹的“形式”結構。而《莊子》自蘇軾《莊子祠堂記》中提出《讓王》 《盜跖》 《說劍》 《漁夫》為“偽四篇”以來,作為一部具有完整結構意義的文本愈來受到質疑,不少治莊家因循蘇軾“偽四篇”說,如羅勉道《南華真經循本》將其錄入《黜偽》篇,并將《刻意》 《繕性》兩篇也視為偽作,陳深《莊子品節》徑直刪去“偽四篇”,其他治莊諸家對“偽四篇”或不予注解,或置于卷末。胡文蔚則對此輕開疑竇的現象表示不滿,他說“或以為中多假托者,非也……說者又謂《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為偽作,考太史公本傳,獨稱其作《漁父》《盜跖》 《胠篋》以明老子之術,設果非莊生之所著,太史公寧復稱之,觀此而疑可釋矣。”[5]154-155他依據司馬遷對《莊子》篇目的引述,認為若真為偽作,為何太史公不曾提出,學者們看到此處,疑竇之心當釋然。而對于“偽四篇”中疑慮最大的《說劍》篇,學者們往往認為類戰國策文,語言粗淺。如陸西星評道“《說劍》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談,意趨薄而理道疏,識者謂非莊叟所作,誠然誠然!”(《南華真經副墨》)[8]六683程以寧評“此篇即非莊子所作,亦戰國時人文也。”(《南華真經注疏》)[8]六683俍亭凈挺評“策士余風,或為鼓琴,或為擊劍。”(《漆園指通》)[8]六683胡方評“此篇與學者分上毫無干涉,所作世諦亦粗淺,不足有無也。”(《莊子辯正》)[8]六683胡氏面對當時質疑成風的局面,依然給與積極辯護:
彼策士縱橫變詐,規圓名利,全不知理會身心,尊崇道德。惟魯仲連一人,能排難解紛,義無所取,其人亦未嘗聞道也。今觀莊叟,卻千金而就天子悝謀,策士輩能之乎。至《說劍》曰,“示之以虛”,是為而不恃也。“開之以利”,是動而愈出也。“后之以發”,迎之不見其首也。“先之以至”,后其身而身先也。無非至人知雄守雌之道,策士輩之知乎。又曰“裹以四時,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無非至人存神保光之道。又曰“持以春夏”者,遂生長以養萬物;“行以秋冬”者,應肅殺以振威神,無非至人過化時雍之道。所謂以之治劍則無敵,以之治世則陶鑄堯舜者也。策士輩會見及此乎!策士以術,莊叟以道;策士陰陽恐嚇以詭譎嘗,莊叟光正端方以義理諷[5]1163-1164。
胡氏認為《說劍》中所體現的莊子精神與策士輩全然不同,而對文中的具體語句詳加體味,正是老子“為而不恃”“動而愈出”“迎之不見其首也”“后其身而身先”的知雄守雌之道,策士輩哪能有這般見識。最后總結策士以陰陽詭譎之術游說君王,而莊子以光正端方義理之道諷諫,兩者截然不同。胡氏的憑據固然不能完全成立,但對于當時學者們輕易將《莊子》完整的結構文本進行刪除或擱置確有抵制之效,維護了《莊子》文本結構的完整性。在他看來,《莊子》一書,整體結構旨義貫然,內外雜篇可作“一篇讀”,“一篇可作一句讀”[5]153。
除了從辯駁黜偽的角度將《莊子》視為一個整體結構外,胡氏更是從《莊子》一書的內在義旨結構進行分析。而在此之前,對于整體結構,成玄英認為《莊子》“內篇明于理本,外篇語其事跡,雜篇雜明于理事。”[9]2從內容上對莊子內外雜三篇結構進行分析,開啟了莊子結構問題的探討。其后宋代王雱《南華真經新傳》中運用連扣式評注以題解方式將前篇內容相串聯,形成完整的結構體系。之后明代陸西星從“《南華》者,《道德經》之注疏也”[10]1的角度認為“內篇七篇,其言性命道德,內圣外王,備矣。外篇蓋所以羽翼內篇而盡其未盡之蘊者。”[10]123“雜篇……總之則推本道德,為《老子》一經之疏注。”[10]331將《莊子》也視為一個完整的結構體系。胡文蔚承續陸西星的思維,認為“莊實老之注疏”[5]478,并對“南華真經”中“南華經”三字進行解釋“南,陰方也,柔能克剛,正老莊守雌之旨;華者生機,男女構精,非陰不生,所以明無為之用也。得此道者可以治身,出其緒余,可以治國與天下,斯為萬世不易、千圣同揆之道,故曰經。”[5]182胡氏從義理上進行題解,將《莊子》一書全然視為“老子注疏”,對《莊子》結構的整體義旨進行肯定。隨后,對《莊子》內外雜三篇義旨及關系進行探索,揭示其篇章結構中內在義脈對全篇的貫穿與統攝,認為“說者謂當是郭氏刪訂時,隨手纂輯所成,故頭緒別起,不可串合為一章,是誠未探源之論。”[5]154。故而從結構整體性著手,將內外雜全篇進行統合。
(一)“真”義闡發貫穿內篇
胡氏認為:“按內篇以三字命題,旨趣深永,應是漆園原本,次第終始,井井有條,七篇可作一篇讀。”[5]152-153在他看來內七篇之間具有完整連貫的結構,次第終始,井然有序,完全可以當做一篇讀。為此,胡氏將“南華真經”中“真”字內涵發揮,通貫整個內七篇旨義:
“真者,大道真神,見性復命,以天為師,一真自如,活活潑潑,獨往獨來,自然逍遙,無入而不自得,所以能游,所謂心有天游也,言乎天游則無物不在范圍。一與不一,何所不齊,齊則綱維運旋,心君常定,出世入世,物不能傷,至紛至賾,而悉合于符,千變萬化而不離于宗,何難陶鑄堯舜以應帝王哉!要惟神者宰之內,所以兼乎外也。”[5]182
胡氏將“真”字涵義解為自如活潑,來往逍遙,對應《逍遙游》篇;而“心有天游”,則“無物不在范圍”,故而可以“何所不齊”,正應《齊物論》旨;“齊則綱維運轉”,自然“心君常定”,暗合《養生主》;“心君”能定,故能“出世入世,物不能傷”,正契《人間世》旨;由此“至紛至賾,而悉合于符”,正是《德充符》義;“千變萬化”而能“不離于宗”,對應《大宗師》一篇;能守宗不變,自然“何難陶鑄堯舜以應帝王”,歸終于《應帝王》。由此可見,胡氏一義貫穿內七篇,將七篇宗旨次第連鎖,而結構之完整,豁然顯現。而在其內七篇章的總論或注解中胡氏也將其主旨突出,以聯合映證這種邏輯。在《逍遙游》總論解題道:“夫人心體原自廣大,止緣塵綱系縛,物欲蔽之,囿于偏曲,去道滋違,學道者必先要克擴其心,故廣之以游,欲其破籬而自適也,大之以逍遙,欲其放浪而漫衍也……意所謂出入六合,獨往獨來,處乎無鄉,行乎無方也。然是逍遙游也,何往不存,無物不具。”[5]185此處“囿于偏曲,去道滋違”“何往不存,無物不具”雖是解《逍遙游》一題,而實已經暗含《齊物論》篇“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的偏執之“是”和“道惡乎往而不存”的“道在萬物”思想。而在《齊物論》首段子綦回答子游發問時注解道“汝知此理乎,即首篇‘至人無己’意。”[5]243如此又關聯了《逍遙游》。在《養生主》總論中胡氏又解道“養生主者,養其所以主,吾生者也……即《齊物論》所謂‘若有真宰,其有真君存焉。’”[5]295這顯然將《齊物論》與《養生主》兩篇進行了很好的關聯,確實把握住了莊文思想的關鍵連接點。并對《養生主》“庖丁解牛”一則寓言中“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句注解道“此處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攖拂,其心泰然,故物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為養生之法也。”[5]309這無疑又暗度到《人間世》篇。隨后又在《人間世》總論中“養生之人,既處世間,安能斷絕人事。按人事之大者無過君臣、師傅而已。”[5]313如此,則輕易地將《養生主》與《人間世》形成了緊密的關聯。由此也可見胡氏解莊的內在思路,即莊子養生思想不能截然斷絕人事,必然關涉人事的“君臣”“師傅”。這其實也正是他“莊實老子注疏”的解莊思想導致的,而這對于他構建完整的莊子結構體系具有重要意義。此外,《大宗師》總論中“大宗師者,道也,莫大惟道也。道者,自然而已,所謂至真至卓者也。知自然者,能登假于道,故不悅生惡死。”[5]391則將《德充符》篇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中“自然”思想與《大宗師》主旨相連。最后,在《應帝王》總論中以老子思想統攝六篇,歸終于《應帝王》,“老子曰,王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又曰,道之精以治身,緒馀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故六篇之后以治天下終焉。應,如感應之應。言身為帝王則有所以應帝王之道。”[5]447至此,通過胡文蔚對莊子內七篇義旨的關聯,內七篇儼然形成一個義脈貫穿,次第終始,井井有條的完整結構,難怪胡氏說“七篇可作一篇讀”。
(二)“宗本”“大用”思想貫聯外篇
王夫之認為:“外篇非莊子之書,蓋為莊子之學者,欲引申之,而見之弗逮,求肖而不能也。內篇雖參差旁引,而意皆連屬;外篇則踳駁而不緒。內篇雖洋溢無方,而指歸則約;外篇則言窮意盡,徒為繁說而神理不摯。內篇雖極意形容,而自說自掃,無所粘滯;外篇則固執粗說,能死而不能活。內篇雖輕堯舜、抑孔子,而格外相求,不黨邪以丑正;外篇則忿戾詛誹,徒為輕薄以快其喙鳴。內篇雖與《老子》相近,而別為一宗,以脫卸其矯激權詐之失;外篇則但為《老子》作訓詁,而不能探化理于元微。”[8]三1王夫之對內外篇關系認識可謂深刻,將其行文結構、義理、風格、意蘊、情態等差異盡相陳述。但他認為外篇“踳駁而不緒”“繁說而神理不摯”“能死而不能活”“徒為輕薄”“不能探化理于元微”無疑又失之過當,事實上外篇大多結構完整,義理一貫,行文變化而蘊含妙理,可與內篇相互參證。林希逸就曾說“外篇雜篇則即其篇首而名之,內篇則立為名字,各有意義,其文比之外篇雜篇為尤精,而立言之意,則無彼此之意。”[11]1沈一貫評道“外篇者,內篇之輔也,大旨不出內篇。”[8]三1陶浚宣也認為外篇文章“微言奧旨,與內篇無異,但立意名篇之法不同。”[8]三4胡氏從“莊實老之注疏”的義旨整體性立場出發,對內外篇旨意進行綜合統攝,認為外篇發明內篇,且外篇結構義脈貫然:
或以外篇,但取篇首二字為題,是后人纂輯者,聊取名篇,故篇中頭緒別出,每段各為一則,意旨不相聯屬,此真蛙蠡之見,何足以讀南華?余謂外篇者,所以發明內篇未盡之意。七篇中作一篇讀,而十五篇亦可作一篇讀……其大宗大本,在“虛靜恬澹,寂寞無為”八字,大用在“無為而無不為”一句。《駢拇》以仁義為旁枝也;《馬蹄》以制度為傷性也;《胠篋》以圣知為大盜資也;《在宥》以治天下莫若無為也;《天地》以君道貴法天地也;《天道》以帝道無為,在運而無所積也;《天運》以三皇五帝務如天之應物而無窮也;《刻意》以有意尊尚,則德不全而神虧也;《繕性》以治性常自然,而無以知為也;《秋水》以水喻性,不得以一曲自足也;《至樂》以吾心有真樂,不藉外物,以養形活身也;《達生》以達生者達命,養神守氣,神生性復,與天合德而物累消也;《山木》以處才未善,難免于累,惟虛游者,偕逝而無傷也;《田子方》以抱道者正容悟物,斯葆真而不失其常也;《知北游》以無知無謂,始能行不言之教,默契大道也。惟外化而內不化,始能化,化而不為化所化,此莊子合外內而闡示道妙,注疏老子無為而無不為之旨也。要知莊實老之注疏,不讀老而讀莊,未能窮其蘊也[5]475-478。
顯然,胡氏以“老子注疏”思想觀照外篇,認為莊子思想大本大宗是“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其大用是“無為而無不為”。這與他在內篇總論中解“南華”二字涵義正相關合。此外,胡氏對具體各篇章義旨圍繞“大本大宗”和“大用”思想進行揭示,如“《駢拇》 《馬蹄》 《胠篋》三篇同一意,言仁義圣知,皆所以亂天下者也。總是《老子》‘絕圣棄知,絕仁棄義’注疏。”(《胠篋》末段評)[5]521《在宥》篇總論提出主旨“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5]523《天地》篇總論中“首節‘君原于德,而成于天’一句是通篇大綱”[5]563,《天道》篇總論“帝王之治,以天地為宗,道德為主,無為為常。”[5]607《天運》篇總論“出治者,貴法天。能法天之無為,則應物而不窮。”[5]638此三篇皆是“法天無為”思想,由此正可看出胡氏“老子注疏”的“大用”思想。又《刻意》總論中推尊的“純素之道”[5]670,《繕性》總論中“治性之要”[5]684,《秋水》總論中“無已而反其真”[5]702,《至樂》總論中“心性中自然之真樂”[5]740,《達生》總論中“不養形而養神”[5]762,《山木》總論中“養真全身之道”[6]796,可見胡氏以“虛靜恬淡”的內養“宗本”思想輻照各篇。而《田子方》總論“大道在未始有物之初,為萬物之紀,非知者所得說也。”[5]824和《知北游》總論中“老聃曰圣人行不言之教,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5]854無非釋知去言思想,終歸于老子“知者不言”。由此看來,《莊子》外篇誠然發揮內篇“未盡之意”,通過其篇章義旨的揭示,印證其各篇義脈關連,或言“釋知去言”,或言“法天無為”,或言“恬淡寂寞”,皆宗歸老子“無為而無不為”思想,由此正如他所說“十五篇亦可作一篇讀”。
(三)大旨淹貫,通篇一句
《莊子》雜篇因其內容駁雜或重復、語言奧峭或膚淺、義理幽隱或淺陋常被治莊者所質疑,或擱置不予評注,或抵斥其為偽作,蘇軾《莊子祠堂記》中就認為“《讓王》 《說劍》,皆淺陋不入于道。”[12]1120而其“偽四篇”的提出,更讓治莊者們對雜篇心生質疑。如朱得之《莊子通義》評雜篇《庚桑楚》“此篇敷流曼衍,固非老子之旨,亦非莊子之所述。”[8]五1盡管如此,不少治莊家還是給予整體性的認可,沈一貫《莊子通》言“雜篇者,零金剩玉,龐雜而出,其語非一端也。故其文不貫串,要之宗旨不異。”[8]五1認為雜篇雖然駁雜,語言風格與內篇不同,且文章不相連貫,但是所表達的思想與內篇無異。王夫之評“雜篇言雖不純,而微至之語,較能發內篇未發之旨。蓋內篇皆解悟之余,暢發其博大輕微之致,而所從入者未之及。則學莊子之學者,必于雜篇取其精蘊,誠內篇之歸趣也。”[13]270認為雜篇能夠發內篇之未發,對內篇具有很好的補充,而雜篇中的精義內蘊,也正合內篇的旨趣。而胡氏從思想大旨和文章表現手法上認為:
外雜篇皆取篇中首二字為題,彷《關雎》 《葛覃》名章之意,若《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刻意》 《繕性》 《達生》 《外物》 《讓王》《天下》等篇,皆通篇一意,人所能知也。其余奇論破荒,秘理日出,雖若各為一則而大旨實淹貫,至于指事類情,廣喻罕譬,原與內篇相表里。”[5]153-154
在他看來,外雜篇多數篇章都是通篇一意,早已為人共知,其他篇章雖然立論奇高,奧理秘旨源源而出,看似各自獨立,而大旨卻實相貫通。尤其是指事類情,曼衍設喻的表現手法更是與內篇相表里,如《庚桑楚》中“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至“三者雖異,公族也”一段,他評到“三說雖異,猶未遠于道,譬則楚之公族也,文法與‘謂之朝三’同。”[5]933此處將《庚桑楚》論述離道未遠的三種形態牽聯楚之“公族”的譬喻正是與內篇《齊物論》論及“知通為一”而牽聯“朝三”譬喻的表現手法相同。又如《則陽》中少知問太公調何謂“丘里之言”一段,胡氏引用陸西星注“此段專辟異同兩見,只以不執不拒為主,轉譬轉精,與內篇何異。”[5]1002可以看出,胡氏認為雜篇不僅是旨義上與內篇貫通,而且在文章的表現手法上也甚為相同。他在雜篇總論中對各篇章旨義揭示道:
雜篇大意,所謂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天下事物縱龐雜多端,而不離乎道也。寓言、重言、卮言,所以明道也。《庚桑楚》云圣人貴忘人忘己,不示仁義之跡。《徐無鬼》云治天下者,休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則陽》云抱道者見性復命,以天為師,不言而飲人以和,必不屑妄已干謁。《外物》云圣人抱神,心有天游,知外物不可必。《寓言》云假他端以寓意,隨言而隨化。《讓王》云化爭之道,莫過于讓。王而可讓,何有于事物。《盜跖》云道不同,不相為謀。即孔子不能化其強暴。《說劍》云道之所用,無往不利,能止世主之僻而安其國。《漁父》云精誠之至,與道合真,可以永銷疵患。《列御寇》云列子外諜成光,精神浮露,故不能使人無保汝,惟真人其神全,其功內,絕去人為,而純乎其天也。《天下》云道之散于天下也,方術多端。皆一察一曲之偏,自明已之道術,本于博大真人,而變化不測,非囿于方也。愚以為雜篇十一篇,除《天下》篇是總述著經之大旨,其十篇亦可作一篇讀[5]894-896。
胡氏將雜篇各篇旨義陳列薈聚,雖然他沒有直接以外篇提出“宗本”“大用”思想關涉雜篇各篇章結構,但不難發現在他揭示的各篇旨義中,確實隱含外篇所謂的“宗本”“大用”思想,《庚桑楚》“忘人忘己”,《徐無鬼》“休胸中之誠”,《則陽》“見性復命”,《外物》“抱神天游”,《列御寇》“純乎其天”,《盜跖》“孔子不能化其強暴”,《漁夫》“精誠之至”皆可看做正面或反面申說“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的宗本思想。《寓言》“假他端以寓意”闡明道旨,《讓王》“化爭之道”,以“讓”保生,《說劍》“道之所用”“能止世主之僻而安其國”,皆可視為“大用”思想。并認為“天下事物縱龐雜多端,而不離乎道也。”各篇章盡管略有旨義的差異而終歸于“宗本”“大用”思想。由此他說“愚以為雜篇十一篇,除《天下》篇是總述著經之大旨,其十篇亦可作一篇讀。”而這正是“驅萬涂于同歸,貞百慮于一致,使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7]378的結構效果。
至此,胡氏以“莊實老之注疏”的主導思想將內外雜篇旨義融匯貫一,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的“宗本”思想和“無為而無不為”的“大用”思想統攝莊子整個結構,最終歸宗于老子。在他的揭示下,內七篇一義貫穿,外雜篇義旨統一,內外相互印證,共同構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無怪于胡氏同學尹進治在其《序》中稱贊“內外篇互相表里,全部可合為一篇,一篇可合為一句,是則胡公之所獨也。”[5]138經過胡氏對內外雜篇旨義的結構性解讀,《莊子》一書內“七篇可作一篇讀”,外“十五篇可作一篇讀”,雜“十篇可作一篇讀”,最終成為通篇可作“一篇讀”的完整結構。
二、胡文蔚對《莊子》結構整體性探索的莊學意義
清初胡文蔚承續明代義理解莊思路,以宗旨統一的立場將整部《莊子》視為“可作一篇讀”,而這直接影響了后來孫嘉淦《南華通》中對《莊子》整體結構的認知和深入探討。孫嘉淦在《南華通序》中說“一部如一篇者,凡其所作,皆確有原委,又確有次第,增之損之而不能,顛之倒之而不可。”[14]135又在《逍遙游》題解中說:“《逍遙游》者,莊子之志也。其求道也高,其閱世也熟,閱世熟則思遠害,求道高則人虛無,以為天地并生,萬物為一,而徒以有我之故,遂有功名,是生利害,故必無己,然后心大而能自得矣。《齊物論》之喪我,《養生主》之緣督,《人間世》之無用,《德充符》之忘形,《大宗師》之人于天一,《應帝王》之游于無有,皆本諸此,實全書之綱領,故首發之,所謂部如一篇,顛之倒之而不可者也。”[14]135孫氏“一部如一篇”的整體思維簡直與胡氏一同己出,而孫氏以“逍遙”義貫聯內七篇而言“確有次第”“顛之倒之而不可”的思路,又與胡文蔚以闡發“真”義內涵貫聯內七篇而言“次第終始,井井有條”相契。當然,在孫嘉淦解讀下,莊子內七篇結構渾然一貫,其完整周密性更加推前一步。而之后藏云山房主人的《南華經大意解懸參注》也承續陸西星、胡文蔚“莊實老之注疏”的思想脈絡,進一步說道:“《南華》發《道德》未發之意,詳者略之,略者詳之,本末兼該,功效畢著,兩經如出一人之手。”[14]178“循其流,則《道德》自《道德》,《南華》自《南華》;溯其源,則《道德》即《南華》,《南華》即《道德》。《南華》也,《道德》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則《南華》與《道德》謂之出于一人之手,可乎?日:可!”[14]178這無疑又比胡文蔚“要知莊實老之注疏,不讀老而讀莊,未能窮其蘊也。”[5]478大大地拉近了老莊之間關系。此外,藏云山房主人所謂的“本末兼該,功效畢著”也正與胡氏“南華一經,非惟探道窮淵源,指示天人性命之秘,朗于星日,即下而治人涉世之津梁,莫不具備”[5]154的思想相關照。而更重要的是,在胡文蔚“七篇可作一篇讀”的整體結構觀影響下,孫嘉淦揭示出內七篇更嚴密的結構關系,而藏云山房主人則將莊子內七篇結構關系的完整周密性推向了極致,他在《藏云山房老莊偶談錄》中談到:
內七篇次第井然。《逍遙游》繼《道德經》首章而作,從坎離還返說到至人、神人、圣人為極則。此七篇之總冒,故以為首。《應帝王》從有虞氏之治外說到治內,從治內說到盡道之量,是應首篇之“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為寔得。此七篇之總結,故以為尾。《齊物論》 《養生主》 《德充符》 《大宗師》以知行道德,分布為四體,《人間世》恰在七篇之中心,以為樞機。首尾一氣貫注,四體血脈通連,中心運化周身。分之則七篇各為一篇,合之則七篇共為一篇,于千回萬轉之中,得圓規方矩之妙,非以至道為至文,其何能之[14]194!
藏云山房主人認為“內七篇次第井然”,《逍遙游》與《應帝王》首尾相照應,而其中間《齊物論》《養生主》 《德充符》 《大宗師》四篇結構關系之精密恰比人體之四肢,而《人間世》恰為七篇之中心樞紐。首尾一氣,四體血脈相通,而中心運化周身。他對莊子內七篇結構關系的論述在迄今為止莊學史上是最為精密深刻的了。方勇就對此評述道“以近乎苛刻的‘天人一體’觀將《莊子》最深刻的一面揭示出來。”[14]195而無論是孫嘉淦的“一部如一篇”,還是藏云山房主人所承續的“分之則七篇各為一篇,合之則七篇共為一篇”實發源于胡文蔚《吹影》中“可作一篇讀”的整體結構觀。
綜上所述,胡文蔚《吹影》對《莊子》整體結構問題的辯駁與探索,對莊學中輕易質疑黜偽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抵制之效,其以“莊實老之注疏”的思想對內外雜篇的義旨進行貫穿與統攝,形成了完整的結構體系。而其莊學的整體結構觀對之后清代治莊學者具有重大意義,使得后來的孫嘉淦、藏云山房主人將《莊子》的內七篇的結構關系推向了極致。
[1][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65.
[2]王照水編.歷代文話第二冊[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3]王照水編.歷代文話第一冊[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4]李波.清代莊子散文評點研究[M].北京:學苑出版社,2013.
[5][清]胡文蔚.南華真經合注吹影[M].北京:國家圖書館清代影印藏本.
[6]方苞著,劉季高點校.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M].北京:中華書局,2013.
[8]方勇.莊子纂要[M].北京:學苑出版社,2013.
[9]郭象,成玄英,曹礎基,黃蘭發點校.莊子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2011.
[10]陸西星撰,蔣門馬點校.南華真經副墨[M].北京:中華書局,2010.
[11]林希逸著.周啟成校注.莊子鬳齋口義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7.
[12]方勇,陸永品.莊子詮評[M].成都:巴蜀書社,1998.
[13]王夫之著.王孝魚點校.老子衍·莊子通·莊子解[M].北京:中華書局,2009.
[14]方勇.莊子學史增補版第四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