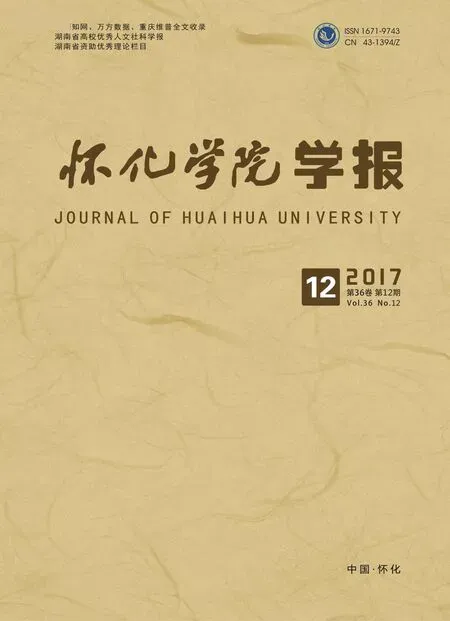民族文化生態變遷中的侗族文獻內涵界定
田 收
(懷化學院圖書館地方文獻研究中心,湖南懷化418008)
一、侗族文獻賴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生態
侗族文獻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它存在于以族系和地域為特征的自然生態和以侗族歷史更迭中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生態因子的社會文化生態環境中。它與侗族文化生態相互依存,相互耦合,既是侗族文化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承載者,也是其民族文化生態產生和發展的見證者和記錄者,并隨著侗族文化生態的變遷而不斷發展延續。
(一)侗族文獻存續和發展的自然環境
據《宋史·西南溪洞諸蠻》載:“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靖州有仡伶楊姓,沅州生界有仡伶副峒官吳自由”[1]14192。南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四記載:“在辰、沅、靖州之地,有仡伶、仡覽”。《老學庵筆記》為南宋陸游晚年所作,成書于公元1210年之前,上述文獻所記的辰、沅、靖州之地就是今天的新晃、芷江、玉屏、天柱、三穗、靖縣、會同一帶,正是侗族聚居區的中心地帶。證明侗族先民居住該地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在唐代就已成為單一民族載入史冊[2]1-2。
侗族主要聚居在我國大西南的東緣,東起雪峰山脈,西有苗嶺支脈,北至武陵諸山,南繞九萬大山,群山綿延,水江羅布,復雜多樣的自然生態不僅形成了豐富的動植物群落和多樣生態系統,為侗族人民創造多樣的文化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同時讓侗族長期處于一個相對封閉的文化單元,以致在其內產生的侗族文化呈現出復雜、多樣和相對穩定性,讓侗族人民能完整保存、傳承自己的民族文化,使其不易被外來文化所同化。
(二)侗族文獻存續和發展的社會文化生態
侗族地區的社會文化生態隨著時代更迭,不斷演變發展,其政治、經濟、文化等因子也隨之發生變化,以此為文化土壤的侗族文獻也在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的樣態。
1.侗族文獻萌芽階段
侗族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很長一段時間是處于沒有階級,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原始社會階段,侗族人民以漁獵為生,自給自足,沒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一直以刻木為契、結繩記事、口耳相傳等原始記錄方式傳遞著侗族的歷史記憶、神話傳說、故事史詩、民族歌謠等。
侗族人民認為天地間的一切皆有鬼神主宰,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樹有樹神,整個世界都充滿了神靈。為了取悅自然,侗族法師定期向大自然和上天獻祭,為了傳承延續法師掌握的民族歷史、風物掌故、天干地支、陰陽五行、占卜星相、念咒畫符、草醫草藥等知識,初期都是通過師徒、父子口口相傳流傳下來。
《侗族起源》中說:“古時人間無規矩......村寨之間少禮儀,內部肇事多,外患禍難息,祖先為了立款約,定出了侗鄉的規矩。”[3]43-44宋人朱輔在《溪蠻叢笑》中載:“當地蠻夷,彼此相結,歃血誓約,緩急相援,名曰門(盟) 款。”[4]4從款詞中記述的“漢王(男頭領)理事在巖穴,姝王(女頭領)理事在石洞”,可推知侗款產生于母系氏族衰亡、父系社會確立,原始社會解體、私有制確立的原始社會末期。此時侗族的款組織遵循“款場立規,以巖為證”習俗來作為侗族的習慣法,這類習慣法中的原始的款詞稱之為無文本的石頭法,初期只是依靠款首們口頭宣布,采用詞話的形式在侗族人民中傳頌。
這些原始記錄已無文獻可考,只是依據民間流傳的口頭文獻推斷而得。如侗族古老的傳說和歌謠《人的起源》、《祖公上河》等侗族口傳文獻的經典之作就是論述了侗族的族源等問題。這些原始記錄起初就是侗族文獻萌芽樣態。
2.侗族文獻形成階段
從秦漢開始,中央王朝就派兵入五溪。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秦王朝派“尉屠唯將樓土南攻越人”,“發卒五十萬人,分為五軍”,其中一軍進入湘西南“駐潭城之嶺”[5]1289-1290,光武帝劉秀派劉尚帥兵入五溪,屯兵辰溪縣東南,筑城戍守[6]23等等,但都未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統治五溪,從秦漢到隋唐五代千余年,中央王朝雖然在侗族地區建立了郡縣,但多為“入版圖者存虛名,充府庫者亡(無)實利響之地”[7]14182。但在此期間,也有一些文人,學者先后來到了侗族地區,宋熙寧(1068-1077)末,誠州大姓首領楊光僭父子“請于其側建學舍,求名士教子孫”,朝廷準其所請,并派長史執掌教育,開辦學校[8]14198。此后,在侗族一些地區紛紛建立了一批書院,這些舉措在一定程度促進了侗族地區的文化教育發展。但在整個唐、宋、元時期,由于歷史、社會和自然條件方面的原因,侗族社會的發展極不平衡。州縣治所所在地的封建經濟文化較為發達,而廣大農村和邊遠山區,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極為緩慢,因而未能形成侗族文獻傳承延續的肥沃土壤。
元、明、清王朝為了有效地控制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都竭盡全力地經營黔東,控扼進入云、貴的通道。元代,中央封建王朝在侗族地區設置軍民長官司,由當地首領任官員,邑子孫世襲其職。明清兩代,封建王朝對侗族地區采取“屯軍”、“圈地”、“改土歸流”等政策,加強對侗族地區直接統治,明末清初形成里甲制、保甲制與侗款制并存的社會組織形式,使得侗族地區頭領多為其封建統治服務。因而在侗族地區,中央王朝下發的告示和公文,都會以碑刻以及公文的形式曉諭地方,隨之效仿的,在侗族地區產生了大量的款組織條約的款碑和契約文獻。例如,在貴州錦屏地區,隨著中央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的滲透,到了清代雍正、乾隆時期,木材貿易十分繁榮,人工造林已成了錦屏地區人民賴以生存、社會賴以發展的強大支柱產業。相應地,產生了大量的買賣、租佃、典當的契約、字據、簿冊,官府文告,家譜,碑刻,以及反映錦屏縣歷史發展情況的有價值材料和民間文學(藝)作品、民間故事、古歌、傳說記錄和反映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經濟特色的各種實物。這些數量繁多的錦屏文書成為侗族文獻中亮麗的瑰寶。
中央強有力的控制,促使“科舉制度”,興辦“府學”、“縣學”、“義學”、“館舍”、“書院”之風席卷侗族廣大地區,“凡有子弟者皆令入國學授業”使得當地侗族青年也獲得較多的讀書機會,開始學習漢字和封建文化。其中不少侗族子弟考取了“秀才”、“廩生”、“貢生”。許多有志侗族青年和民間歌者利用漢字記侗音的方式記載了許多侗族文化。如款詞、巫詞、歌謠、戲曲等等。諸如流傳于民間的200余首《耶·薩歲》或《嘎·薩歲》以及《東書少鬼》、《占推遮地多藤》、《請神圣安社堂言語》、《招謝圣母咒語》等這些脫胎于侗族原始宗教手抄本,成為侗族文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此外,侗族人民侗族也仿借漢字構件偏旁以及造字法自制了一些酷似漢字的方塊侗字,但所占比例非常小,沒能形成新的文字系統,只是作為漢字記侗音的一種補充,但也為我們挖掘侗族文獻提供了新的思路。
文化的傳承與繁榮建立在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生態系統中,更源自于本民族對自身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侗族是一個民族自尊心很強的民族,雖然身處封閉的山區,卻也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侗族人民是一個非常樂意接受教育而且善于學習的民族,尤其是在文化適應性和包容性方面表現得非常突出,既能順應王朝勢力及其規章制度,又能主動吸收中原文化和本民族文化加以重新整合,然后將其轉化到本民族的本土文化中,從而使侗族文化更加豐富多彩,更具有生命力,因而侗族人民成為侗族文獻最虔誠的創造者和傳承者。侗族人民在追求文明進步的歷史過程中,與周邊民族不斷進行經濟、文化交往,創造了大量物質和精神文明財富,在諸多的神話傳說中,侗族與許多兄弟民族,尤其是苗族,都擁有類似的血緣始祖或民族起源傳說,并隨著口傳或其他方式流傳下來,形成了研究民族關系和起源的珍貴文獻。
3.侗族文獻的新生階段
20世紀50年代初期,為落實中央幫助尚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的指示精神,1958年8月18至23日,經各方專家的討論研究,《侗文方案》 (草案)表決通過。同年12月,經國家民委批準試驗推行。從此,侗族人民有了自己的規范文字。在此期間,成立民族語文學校,培育了侗文師資,開始了侗文掃盲工作。貴州民族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侗漢簡明詞典》、《農民侗文識字課本》、《干部侗文識字課本)、《漢侗簡明詞典》、《侗語方言調查》以及一些科普和通俗文學讀物。侗族文獻終于獲得了其民族承載體。但60年代以后,由于諸多原因,侗文的試點推行工作被迫停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侗文重新獲得新生,各項民族工作和民族出版社和雙語學校等機構開始恢復工作,期間,培訓了一大批侗族文字使用者,他們用侗文來撰寫各類文書、記錄詩歌故事。侗族文獻呈現了一派欣欣向榮之態。在侗族有些地區還出版了各類侗文版的報紙和書籍讀物。如《苗文侗文報》、《侗漢詞典》、《漢侗詞典》、《侗語課本》、《法律法規選譯:侗文譯本》等,這些讀物和工具書為侗族文獻的發展和研究奠定了較為扎實的理論基礎。同時,許多民間文學工作者深入侗族地區調研,搜集了大量侗族民歌、史詩、傳說、故事等并翻譯出版,如《侗族風情錄》、《侗款》、《侗族琵琶歌》、《侗族百年實錄》等等,形成了一大批侗族民間文學著作和侗族古籍資料。
4.侗族文獻的蓬勃發展階段
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國家和各省市頒布了諸多大力發展民族語文和民族語言文化工作的決定,侗族雙語工作迅速發展,培育了一批侗族雙語教學師資和雙語民族干部。相關的民族語文教材、讀物的編寫和出版取得突破,編制出版了諸如《侗漢詞典》、《侗語研究》等教材,與此同時,有關侗族文化的侗族文獻也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在侗族文獻內容研究方面,涌現了一大批就侗族服飾、建筑、音樂、習俗等文化要素的研究專著和論文,如《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總目提要———侗族卷》,這是侗族古籍文獻的綜合整理成果。在侗族文化研究成果方面,隨著研究成果的日益豐碩,一大批侗族優秀文化產物進入國家級、省(區)級和市(州)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也逐漸成為一種重要的侗族文獻。在侗族文化傳播方面,許多侗族有識之士,建立了獨樹一幟的侗族網站,侗族微信公眾號以及多種類型的侗族文化傳播自媒體。這些新興的新媒體承載了大量的有關侗族的文獻資料。同時,隨著侗族地區經濟文化發展,侗族地區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文化意識的不斷提高,侗族地區涌現出了許多侗漢雙語的各種旅游、文明道德標語等等雙語文獻。由此可見,侗族文獻正以各種新的樣態展現在人們面前。
二、民族文化生態變遷下侗族文獻的內涵確定
在民族文化生態變遷的過程中,侗族人民在不同時期、不同學科、不同地域、以不同方式進行著社會實踐,對這些知識和經驗總結記錄的侗族文獻呈現出來的特點與樣態,以及闡述的侗族文化內涵,都是基于其當時當地的民族文化生態中的各個因子。隨著其中自然、政治、經濟、文化等因子的變化,侗族文獻也不斷發展延伸,從而形成一個廣泛而豐富的概念系統。對于侗族文獻內涵的界定我們不僅要從侗族文獻的外部特征認識侗族文獻的基本樣態,同時要從侗族本身的民族屬性出發,形成系統的資料性,三者合一才能真正實現侗族文獻全部內涵的完整界定。
(一)從侗族文獻的外部特征看侗族文獻
侗族文獻的外部特征是侗族文獻構成的基本要素,同時也是侗族文獻內涵系統重要組成部分,是了解到侗族文獻內涵的外在因子。
1.布局分散,形式多樣
在地域和內容分布上,侗族文獻主要分布在貴州、湖南,湖北,廣西四省。另外,歷史上對于侗族的記載主要散落在中央王朝零散的官方文獻中,以及游歷到此的文人騷客的游歷筆記中,數量極少,內容極為分散。絕大多數侗族文獻都只是流傳于侗族人民的傳說和歌謠中。從其分布可以了解侗族文獻形成的主要地域狀況。
在載體形態上:侗族文獻呈現出多種多樣樣態,從傳唱、碑刻衍生到漢字記侗音文本,漢字文本到最終的侗文文本等等,都是民族文化生態因子變化的必然結果。可以推斷出侗族文獻是隨著其自身的民族文化生態的發展而發展的。
2.記載奇特,傳承曲折
侗族文獻的記載奇特主要是指口傳古籍,在1958年以前,侗族是沒有自身特定的文字的,唯一獨特呈現的就只是漢字記侗音侗族文獻,但由于這種記錄形式沒有統一規范的標準,以致此類侗族文獻也僅限內部交流,隨著朝代的更替和先輩的逝去、傳承的斷層,此類文獻出現了無人翻譯的“死文獻現象”,因而流傳下來的數量極少。因文字的缺失和弱化,侗族文化傳承絕大部分依托于侗族人民的口耳相傳,獨特的傳承方式使得口傳文獻成為侗族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在侗族文獻的收集和整理過程中,我們不能因口傳文獻傳遞的易變性而忽視其在侗族文獻中的重要地位,我們應積極采取有效的技術和手段對侗族口傳文獻加以保存和整合,盡可能完善侗族文獻的全部內涵。這為我們研究侗族文獻的內涵提供了良好的切入點。
(二)從侗族文獻民族性來看侗族文獻內涵
一個民族區別于另一民族在文獻中所反映的民族文化,是民族文獻的研究對象,即民族性或民族特色。從文獻分類學概念角度講,是“文化的民族性”[9]155。
侗族文獻的產生與發展,從一開始,就是侗族人民在本民族地域范圍內,依照本侗族的生活和生產方式去創造自己的文化而產生的記錄。從而使其文獻的產生和積聚就帶有鮮明的民族特色。由此可見,民族性即侗族文獻內涵的本質屬性。
1.侗族文獻的民族性的外部體現
從文獻的民族語言來看,語言和文字通常是民族感情的紐帶,是民族文化得以延續和傳播的途徑,也是鑒別文獻民族性的最明顯的標準。侗族口傳文獻中完全以其民族語言的傳承的主要是其神話傳說,故事歌謠,其中極具代表性的就是侗族各種敘事歌和琵琶歌,以歌相傳,涵蓋了侗族生產生活、民俗風情、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
從文獻的作者來看:侗族作者作為侗族共同體的成員,他們不僅能體現本民族特點的深刻內涵,并能將其熔鑄在作品中。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作者的民族成分不能決定文獻內容的民族屬性,只有致力于侗族傳統文化研究的成果才真正是侗族文獻內涵的主要組成部分。同時,非侗族籍作家創作的有關侗族各類體裁的作品,也應包括在侗族文獻的內涵中來。
此外,在侗族文獻內涵的確定過程中,我們還應對侗族作者進行整合和排序,形成一定的侗族作者體系,從作者出發,鏈接出其研究本民族文化相關文化成果,從而形成新一輪的侗族文獻體系,豐富侗族文獻內涵。
2.侗族文獻的民族性的內容體現
侗族文獻的民族性在文獻內容上的體現是界定侗族文獻內涵最重要的一個方面。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文獻內容涵蓋侗族內容的數量,不能說有點民族內容的文獻就算做是侗族文獻,需要我們進行提取匯集成冊,形成一定的知識體系,才能算作是完整的侗族文獻。
一方面,我們需要從侗族整個民族文化生態發展的過程中,梳理出侗族文獻獨特的形成狀況,這是侗族文獻民族性的歷史范疇,這種民族性歷史范疇正是侗族文獻逐步區分與其他民族的有力見證。但由于歷史上侗族文字的缺失和發展的滯后,侗族文獻民族性的歷史范疇文獻需要結合其重要的口傳文獻、其他民族以及各中央王朝對侗族地區記載的零星文獻進行闡述。
另一方面,侗族文獻中最集中體現其民族特色的就是侗族文化積淀。即在民族文化生態中的經濟、政治、宗教、宗族、傳統信仰等因素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獻,從侗族古籍中的各類傳說故事、敘事歌謠、契約文書到現在逐步形成體系的對侗族建筑、服飾、宗教信仰的研究性文章等等,都是侗族文獻中民族性的集中體現。
最后,侗族地區自然生態系統不僅是侗族文獻形成和延續的地理空間,同時侗族文獻所呈現出來的樣態大多數都能在當時當地的自然生態中找到對應的參照物,侗族文獻中記載的內容很大一部分也是反映侗族人民適應改造自然的活動。因而根據侗族自然生態系統的描述和記載也能體現出侗族文獻的民族性屬性。
(三)從侗族文獻的資料性屬性界定侗族文獻內涵
侗族文獻的資料性屬性也是侗族文獻內涵的本質屬性之一,它是基于對侗族文獻外部特征和民族屬性的梳理而形成的,對侗族形成延續和發展變化進行系統性概括的文獻體系。只有系統成套、不斷發展的侗族文獻體系才能體現出侗族文獻映古照今、傳承延續真正價值。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從侗族文獻的形成時間來看:
一是指侗族歷史文獻:一方面是侗族人民以各種形式,如漢字記侗音,銘刻、口傳等各種形式的侗族古籍文獻,另一方面是從其他民族歷史文獻上加以組織和綜合有關侗族的文獻形成的二次文獻。二是指侗族再生文獻:一方面是從侗族文獻中挖掘出來,重新認識和加以利用,另一方面是在民族振興和民族地區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過程中涌現出來并通過現人記錄而呈現。
2.從侗族文獻的構成部分來看
一是在侗族文獻內容上,應具備系統完整性。
侗族文獻內涵首先應包括該侗族地區的自然生態資料,這是侗族文獻形成發展的生存空間和民族地域特色,能很好地研究侗族民族生存、遷徙和民族融合的發展路徑;其次應涵蓋侗族形成、發展的歷史與政治演變、人口變遷、人物、生產生活、民族融合等資料,這是侗族自身延續的發展的歷史記載。最后就是民族文化特色資料,這是侗族文獻內涵中最具民族代表性的資料,一方面包括無文字記錄時期的神話傳說,故事歌謠等口碑文獻,另一方面包括從古到今,侗族形成的語言文字、風俗、宗教禮儀、文物、詩文戲曲等方面的文獻。
二是在侗族文獻內容上,應具備傳承延續性。
民族文化生態系統是不斷變化發展的,其中的文化因子也隨著不斷變化,對其進行記錄的侗族文獻在形式和內容上也是不斷豐富和發展的,我們不僅要看到侗族古籍中諸多的侗族文獻,目前收集的大多數是侗族口傳文獻,我們還應看到當今學者在研究古籍文獻以及對侗族地區民族文化生態調研過程中,基于侗族音樂、民俗等民族文化因子而形成的一大批侗族文獻研究成果。這是我們梳理侗族文獻內涵不可或缺的部分。
綜上所述,侗族文獻內涵的界定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也不是一個層面上的內容總結,而應從時間和空間的維度中,認識到侗族文獻內涵的研究是一個整體性、動態性的研究,需要通過在其民族文化生態系統中對目前研究成果和當下侗族文獻進行計量分析,梳理出侗族文獻全部內涵體系。其次,侗族文獻的研究是民族性、活態性的研究,需要我們走出書齋,進入田野,傳承已有侗族文獻,固化侗族文化精髓部分,構建侗族文獻內涵新樣態。
[1][元]脫脫,等撰.《宋史》卷494《蠻夷二·西南溪峒諸蠻下》[M].北京:中華書局,1977.
[2]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總目提要:侗族卷[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
[3]楊錫光,楊錫,吳治德整理譯釋.侗款[M].長沙:岳麓書社,1988.
[4]朱輔撰.溪蠻叢笑[M].北京:中華書局,1991.
[5]何寧.淮南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98.
[6]《侗族簡史》編寫組.侗族簡史[M].民族出版社,1985.
[7][元]脫脫,等撰.《宋史》卷493《蠻夷一·西南溪峒諸蠻上》[M].北京:中華書局,1977.
[8][元]脫脫,等撰.《宋史》卷494《蠻夷二·西南溪峒諸蠻下》[M].北京:中華書局,1977.
[9]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編輯委員會.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第四版)[S].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