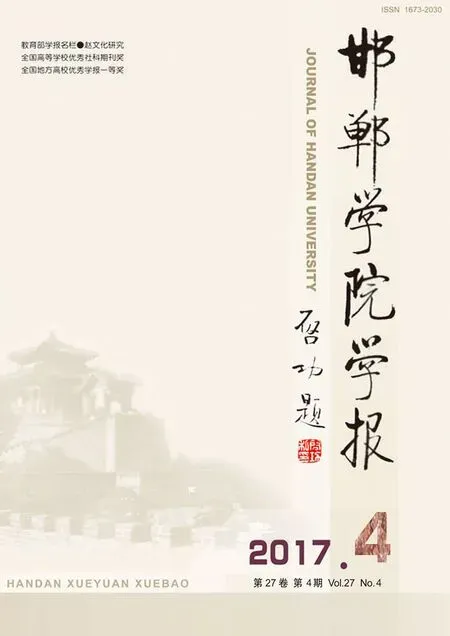論李春雷報告文學語言的詩化特征
李 錚
論李春雷報告文學語言的詩化特征
李 錚
(河北大學 文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李春雷創作的報告文學在語言上有著詩歌的風格與特點。注重語言的跳躍性,營造有韻味的詩意“空白”;同時講究語言富有節奏韻律之美;為傳達細膩、幽微的感覺,作者大力借鑒詩歌建構意象的方法。正是因為這些鮮明特點,李春雷在中國報告文學創作領域的地位和影響,顯得異常卓越。
李春雷;報告文學;詩化;跳躍;節奏;意象
河北作家李春雷從20世紀 80 年代后期開始發表作品,如今已發表作品 700 余篇,其中以報告文學的藝術成就最為突出,曾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全國“五個一”工程獎、蟬聯三屆徐遲報告文學獎。代表作品有長篇報告文學《鋼鐵是這樣煉成的》《寶山》等19部,短篇報告文學《木棉花開》《夜宿棚花村》《朋友——習近平與賈大山交往紀事》等200余篇。
著名文學評論家、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李炳銀在文章中明確指出:“鑒于此,他被評論界譽為“中國短篇報告文學之王”,這是當之無愧的。”[1]
報告文學脫胎于新聞類報道寫作,強調記錄真實,反映真實,被稱為“文學的輕騎兵”。隨著時代的發展,報告文學日漸繁盛,但也浮現諸多問題。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從藝術角度來看,現在的報告文學,不少只是報告,沒有文學,……過于粗糲和簡陋,缺乏藝術的再生力和感染力。”[2]20由此可見,文學性的不斷缺失已使報告文學的藝術性大大受損。有評論進一步指出:“我們很多報告文學的文學性缺失,主要是語言藝術的缺失。我們很多報告文學的語言已經公文化、新聞化,甚至垃圾化了。那些語言,沒有任何水色和靈氣,就像鋸木機下的木渣。”[2]21很明顯,在評論家看來,語言藝術的缺失正是報告文學文學性缺失的關鍵。
然而,李春雷的報告文學創作的語言卻非常富有文學性。如雷達指出,李春雷的作品有“出色的想象力,開闊的眼界”和“他那不時顯現的詩化的敘述格調”。[3]李良亦持同樣看法,“作家李春雷出道于新聞寫作而不為其羈絆,以詩化的語言、散文的筆法行文鋪排,文字不張揚卻很有質感,極富表現力。”[4]
有鑒于此,本文試圖結合具體文本,分析李春雷報告文學語言的詩化特征,揭示其作品的藝術魅力,或可為當代的紀實類文學的創作提供語言與敘述上的一些借鑒。
一、語言的“跳躍”與“留白”
詩歌語言的特點之一便是跳躍性。古典詩歌、詩詞的語言、詩句之間的內容和時空的跳躍十分明顯。小說和散文的敘述、描寫語言一般連貫而完整,然而在詩歌的創作中,由于文體本身字數所限,大多數情況下無法用充足的文字展開一個完整的場景或者敘述一個完整的事件。詩人常常讓詩歌句子中的詞匯、句子之間進行跳躍式的組接與拼貼而不使用任何過渡文字或關聯詞語,所以詩歌語言常常體現出不連貫、不完整的特點。但是,在詩人去掉想象、事物、時空之間的表面聯系及句子中表達詩意的關聯詞后,文本看似變得分崩離析,卻沒有使詩意變得支離破碎,反而從詩人情思的內在聯系上更大地概括和擴張了詩意。如溫庭筠在《商山早行》中的名句:“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這種語言的跳躍,既能使詩詞更加精練,又能使它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概括性。清代中期文學家及著名思想家方東樹認為,詩人寫詩“語不接而意接”[5]414,正是這種跳躍,使詩人減少了不少空間轉換和事件發展的敘述語言,反而使詩歌增加了反映現實生活與內心世界的深度和廣度,還促使讀者以想象去聯結、補充語言跳躍留下的各種空白,從而為想象展開了一番全新的天地。
正如這首《商山早行》,作者溫庭筠對意象進行跳躍式的組合,僅僅是“雞聲”、“茅店”、“月”和“人跡”、“板橋”、“霜”這六個意象的拼貼,就勾勒出了旅人商山早行的場景:清晨清冷空氣中回蕩的聲聲雞鳴,深藍的天幕上閃爍的星星和還未落下的月亮,彎曲道路上一座空蕩的木板橋,上面的白霜拓下了早行人的足跡。這樣的場景給讀者留下了無窮的思考空間,如此詩味,真可謂言有盡而意無窮。
在李春雷報告文學的創作中,亦廣泛采用了這種方法——借鑒詩歌語言方式,運用簡潔的字句進行意象的拼貼、組合,以進行審美的再造與審美場域的建立。
在2014年發表的《朋友——習近平與賈大山交往紀事》中,關于習近平與賈大山初次見面的場景,作者就巧妙地采用了這種方法。習近平與賈大山第一次見面時并不是很順利。由于習賈兩人相互之間并不了解,加之年輕的習近平剛到正定縣任職不久。兩人第一次見面,賈大山的反應讓習近平印象深刻。根據作者考證,2009年7月號出版的期刊《散文百家》,整理發表了習近平2005年回正定考察時的錄音:“我記得剛見到賈大山同志,大山同志扭頭一轉就說:‘來了個嘴上沒毛的管我們’……”兩人初次見面,遇上這樣的情況可以說非常尷尬,這種尷尬情況對作者的表現能力是一個挑戰。然而,更難的地方還不在此處,而在于兩人在最初的尷尬后,很快便相視一笑“泯恩仇”。這個過程在日常的生活中并不鮮見,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一般寫作者卻極難用文字恰如其分地傳遞出這種轉折的巧妙感覺。然而,在這里作者顯示出了極為深厚的功力,非常巧妙地寫到:
我們實在無法臆想當時的場景,抑或大山的語氣和表情。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時的賈大山還不到40歲,已獲得全國大獎,作品收入中學課本,聲名正隆,風頭日盛,加之天生淡泊清高的性格,面對這個比自己年輕十多歲的陌生的縣領導,有一些自負是可以想象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習近平并沒有介意,依然笑容滿面。現場的空氣似乎停滯了一下。但不一會兒,氣氛就重新活躍起來。主人和客人,已經握手言歡了。
作者在這里首先簡單交代了背景,然后選取了“停滯”、“尷尬”、“重新活躍”、“握手言歡”這幾個場景進行跳躍式的組合,故意略寫了其中微妙的轉化。最令人稱奇的是,聯系作者在上文寥寥數語介紹的背景后,這種充滿了詩化語言特征的“跳躍”非但沒有顯出缺失與不足,反而充滿了敘事的張力,使整個過程在讀者腦中豐滿和充盈起來,這無疑與古典詩詞的寫作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習賈二人由初見面的尷尬到握手言歡,這個極為微妙難言的過程對一般寫作者來說極難表達得恰到好處。然而在李春雷的筆下,這個困難被作者以充滿詩化特征的巧妙語言和精心布局給一一化解,不露痕跡不動聲色地將這個生動的見面場景傳遞給了讀者,充分展現出了詩化語言的奇妙之處。
同樣的手法在《南寺掌——“我的抗日戰爭”紀實之八》這篇文章中也有體現。文中的主人公——祿元媳婦,是南寺掌村中的積極分子,某天她接到任務要為八路軍制作一批軍裝。在作者筆下,制作軍裝的布匹染色過程運用了詩化的語言手法進行處理:
領回來的布匹全是白土布,需要染色。…… 火光熊熊中,水氣騰騰中,一塊塊土白布變了顏色,變成了石頭的顏色,變成了大地的顏色,變成了樹皮的顏色,變成了八路軍的顏色……
寥寥數語,勾勒簡練,沒有用寫實的手法具體寫白布染色的具體過程和步驟,而是用“變成了石頭的顏色,變成了大地的顏色,變成了樹皮的顏色,變成了八路軍的顏色”這樣的詩化的語言來一筆帶過。在這里,作者“省略”了很多內容。如何架灶支鍋,如何盛水燒火等等,這一系列具體而又詳實步驟,作者都沒有在文本中表現。然而,一塊白土布在大鍋中漸漸翻滾慢慢著色的這個過程,卻充滿詩意地在讀者心里扎下了根。作者用這種手法,寫出了一般報告文學語言缺乏的一種詩意之美。
在《太行八勇——華北民間抗戰人物之一》這篇文章中,作者寫到:
戰場上的破廢槍支、彈殼,拆毀的鐵軌、汽車,還有從民間收來的廢銅爛鐵,紛紛向這里跑來。大豐溝里熱火朝天。不長時間,龍泉觀院子里裝滿火藥的地雷、手榴彈便堆成了小山,像山民們秋后收獲的核桃、黑棗。而后,一夜之間,卻又全部飛走了……
這段文字記述了大豐溝槍械所,也就是后來聞名軍史的晉冀魯豫邊區最大的兵工廠——西達兵工廠前身最早的運轉情況。在作者筆下,“廢銅爛鐵”會“跑來”,“地雷、手榴彈”能“飛走”,在紀實類的作品中,一般作者很少會使用這樣的語言,因為一旦下筆不慎就極易被詬病為“不真實”或“虛構”。但事實上,“虛構”與“非虛構”之區別并不在于一兩個具體的詞語或是句子,而在于作者的敘事能多大程度上符合人們的“心里真實”。而作者的詩化“留白”語言,一方面滿足了文字表現的藝術需要,一方面又符合了人們內心可以接受的“藝術的真實。在這段文字中,作者仍然用詩化語言來藝術地處理這個槍械所的生產步驟。四處的破舊金屬都被運到這里來,然后很快生產的產品便“堆成了小山”,像村民們收獲的“核桃”與“黑棗”,然后一夜之間又“全部飛走”。同上文一樣,作者沒有將槍械所詳細的生產步驟一一寫出,但這一“來”一“走”,卻將槍械所生產的大致運行情況生動地傳遞給了讀者,那熱火朝天的生產場面與生產出的“累累碩果”,這個過程如同放電影一般在讀者的腦海中一遍又一遍地復寫著。
二、節奏韻律之美
詩歌語言的一大特點是句式整齊,韻律和諧。詩歌也因此讀起來節奏感鮮明,朗朗上口,便于記憶和傳頌。語言的音樂美,在詩歌中得到完美的體現。有學者認為,“詩歌是一種最富于音樂性的語言藝術,特別講究韻律諧美,悅耳動聽。……因此,它要根據感情的性質、變化安排語言的節調、韻律,從而準確地傳達生活的節拍、音響,恰如其分地表現跌宕起伏的感情,形成一個情思、聲調諧美的藝術整體。”[6]160
從這里可以看出,節奏與音韻是詩歌獨有的傳情達意的利器,詩歌的這種特點是其他任意文體都難以比及的。郭沫若說;“節奏之予詩是它的外形,也是它的生命,我們可以說沒有詩是沒有節奏的,沒有節奏的便不是詩。”[7]229這其中,《詩經》是最為典型的例子。《詩經》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一部詩歌典籍。其中的詩歌,為后世的詩歌創作提供了一個典范。“《詩經》作為詩歌需要達到語言優美、韻律和諧、節奏鏗鏘、句式整齊等詩化語言的基本要求,逐漸形成了以四言二拍為主的基本旋律。”[8]100節奏和音韻都是詩歌傳情達意的重要手法,《詩經》之所以能夠成為經久不衰的經典,無論是內容上充滿感情色彩的渲染抒情,還是朗朗上口的口頭吟詠傳唱,都與它自身的節奏與音韻形式有著密切的關系。
李春雷在報告文學的創作中吸取了古詩在音韻、節奏上的這些特點,接納了詩歌語言中押韻、對偶、疊詞等這些修飾手法;同時借鑒詩歌語言短小精練的特點,有意運用一些文言句式,同時對長句進行合理的拆分,精當地運用標點符號增加停頓。這些手法的綜合運用使作品的語言精短,玲瓏精美,節奏和諧,頓挫有致,更具詩化特征。
在李春雷的成名作《鋼鐵是這樣煉成的》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密密麻麻的人們粘在高爐上,白天太陽是燈,夜晚燈是太陽,像螞蟻搬家一樣把一塊塊耐火磚、一塊塊冷卻壁銜接上去,像蜘蛛結網一樣把一道道進水管、進風管、測溫管盤繞在爐體內外;像蜜蜂筑巢一樣把一個個渣口、風口、鐵口鑲嵌在爐壁上……
這段描述有很強的節奏感,“白天太陽是燈,夜晚燈是太陽”;同時又有著類似于近體詩的對仗,“像蜘蛛結網一樣把一道道進水管、進風管、測溫管盤繞在爐體內外;像蜜蜂筑巢一樣把一個個渣口、風口、鐵口鑲嵌在爐壁上……”這樣的手法既突出了工人們夜以繼日的辛勞,也從側面將高爐的建設介紹給了讀者。螞蟻搬家,蜘蛛結網,蜜蜂筑巢,這三個詞語不僅能從敘事上將高爐建設過程生動形象地展現給讀者,也能構成修辭上的排比,可謂是一箭雙雕、一舉兩得。
在《朋友——習近平與賈大山交往紀事》中,作者記述了賈大山的創作過程:
他的創作習慣也迥異常人:打腹稿。構思受孕后,便開始苦思冥想,一枝一葉,一蘗一苞,苞滿生萼,萼中有蕊,日益豐盈。……三番五次之后,落筆上紙,字字珠璣,一詞不易,即可面世。
這段描述充滿了詩歌語言的特色,不僅讀起來朗朗上口,而且還抑揚頓挫、節奏鮮明,如江河直泄,滔滔不絕。這樣的行文將抽象的創作過程一一具象,讓讀者讀起來氣脈暢通,酣暢淋漓。
同時,這樣的方式更加突出了賈大山本身的創作能力。1978年,賈大山以小說《取經》榮獲全國首屆短篇小說獎,一舉成名。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全國文學界,一度與賈平凹齊名。這樣一個作家,他究竟是如何創作的?又有哪些異于常人的地方?顯然,作者通過這樣詩意化的敘述,跳出了過分拘泥于細節“現實”的窠臼,不僅生動而鮮活地向我們勾勒出了賈大山異于常人的創作過程,更著重體現了賈大山本人作為一個優秀作家所擁有的敏捷才思。
同樣還是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在寫景鋪陳時同樣運用了充滿節奏張力的詩化語言。如“春雨潤青,夏日潑墨,秋草搖黃,冬雪飛白。歲月如歌,他們共同享受著友誼的芬芳……”春、夏、秋、冬的一聯四字句,季節上春夏秋冬依次承接,語言上采用了四字句并列,不僅在景物描寫上有類似于國畫技法中淡筆勾勒的手法,而且讀起來節奏鏗鏘,簡短有力,鋪排適當。這無疑在報告文學的語言中是頗為少見的。
在《木棉花開》中,當任仲夷剛到廣州任職時,作者這樣寫到:
省委大院里植滿了榕樹,這南國的公民,站在溫潤的海風中,掛著毛毛絨絨、長長短短的胡須,蒼老而又年輕,很像此時的他。但他似乎更喜歡木棉樹,高大挺拔,蒼勁有力。二月料峭,忽地一夜春風,千樹萬樹驟然迸發,那碩大豐腴的花瓣紅彤彤的,恰似一團團灼灼燃燒的火焰,又如英姿勃發的丈夫,用剛健的臂膀傲然挽起嬌美的新娘,雖然來去匆匆,卻也轟轟烈烈。
任仲夷剛到廣州時,肩負著廣東改革開放建設的艱巨任務。然而,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試辦經濟特區、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是一項前途未知的工作。面前不平坦的路途之下隱藏著一個個地雷炸彈,背后則更是十幾億人聚焦的目光。所以,在這種背景下,作者用巧妙的文學語言將任仲夷的心境寫出。
到廣東上任時,任仲夷已經66歲了,但是他即將開展的工作則是中國歷經了苦難之后嶄新的探索,作者首先用“掛著毛毛絨絨、長長短短的胡須,蒼老而又年輕”這樣的語言,而后又巧妙地化用了唐代詩人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中的名句“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來寫木棉樹,他筆下的木棉樹花瓣是“紅彤彤”的,“恰似一團團灼灼燃燒的火焰”,像一位英姿勃發的丈夫,“雖然來去匆匆,卻也轟轟烈烈。”
這段文字描寫運用疊詞,巧用標點,在音韻上回環往復,在句法上短小精煉,是李春雷語言詩化特征的集中體現。雖然如此,在這詩意的語言背后,卻傳遞著更為深廣的內涵。
熟悉時代背景的讀者都十分清楚,這段文字的描寫雖然充滿詩意,但是這背后,不正是任仲夷克服千難萬險,下定決心在廣東力行改革的真實寫照嗎?作者雖用詩意的描寫將這個過程與心境寫出,但現實往往是真實而殘酷的。用詩化語言的柔美來處理堅硬如鐵的事實,兩下對比,體現了跨越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審美張力,體現出了獨特的審美效果。
三、以意象傳遞感覺
意象在詩歌的語言當中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事實上,詩歌的創作就是詩人尋找客觀事物作為意象、建構意象語言、從而使其主觀情感能夠生動形象地表達出來的過程。意象在表情達意方面有著強大的力量,它借用生活中常見的具體形象或畫面來比擬地表現人們在理智和感情等諸多方面的獨特體會和經驗;從形象描繪和感情描繪相結合的角度寫景抒情,寓主觀情感、深刻哲理于客觀事物的形象描繪之中;它還具有豐富的審美屬性,帶給人們美的感受和啟迪,具有突出的美學功能。總之,詩歌意象語言的形象描繪功能和感情描繪功能,使詩歌意象語言帶給人們外在形式和內在意蘊的雙重美感。
除了上文列舉的兩個特點之外,李春雷在創作中擅長利用各種意象傳情達意。他把難以捉摸的感覺用可視可觸的客觀物質來形容,用具象形容抽象;同時擅用富有想象力的詩化語言來逼真地描摹事物細節;他的描寫極富張力,不僅可以用極具詩意的語言睥睨山河,又能用極細微的筆觸舉重若輕。大小對比之間,文字的張力畢現。這種特征鮮明的詩化語言不僅使文本更加形象生動富于可讀性,更重要的是,它使文本從清晰的真實中蒸騰出一種詩歌一般的亦真亦幻意境之美,從審美上更上一層樓,直擊了人心深處被日常語言與感覺所麻木和遮蔽了的那種最微妙的突觸。
人內心抽象的感覺最難用語言進行具體地描繪。但在反映汶川大地震的名篇《夜宿棚花村》中,作者用獨特的語言傳遞了遭受震災的小村之痛:
震后又下起大雨,全村人跪在山坡上,以手掘土,就地葬埋了死者,大人們像孩子一樣嚎哭著,孩子們則像大人一樣冷峻。恐懼像四周的大山一樣黑魆魆的,那是鬼魅的影子?直到兩天后,外面的援救才進來。但是,身受重傷的小村像一條刮去鱗片的魚,時時疼痛,撕心裂肺的疼痛。[9]205
遭受了災難的小村是無疑是痛苦的,然而這是怎樣一種痛?又該怎樣將這種感受真實地傳達給讀者?顯然,抽象的痛是無法直接描寫的。然而,作者在這里,卻充分發揮了自身獨特的語言功力,“大人們像孩子一樣嚎哭著,孩子們則像大人一樣冷峻。”這描述很值得玩味,大人像孩子一樣嚎哭,孩子像大人一樣冷峻,大人與孩子的身份與表現令人驚奇地出現了與正常生活秩序下截然不同的異位。雖然初看奇特,但細細想來卻符合情理。在大自然的偉力面前,崩摧異位的不僅只是客觀的物質世界,人的精神世界也同受重創。從大人與孩子產生近乎“精神分裂異位”式的表現這一點來看,大地震之下山河的崩摧異位,同樣也帶來了人們精神世界中秩序的崩潰與錯置。這場地震的威力無疑給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帶來了巨大的雙重打擊。作者的描述還沒有結束,在第一輪的精神打擊過后,“恐懼像四周的大山一樣黑魆魆的,那是鬼魅的影子?”在這里,人們從最初慌亂中稍微平靜下來的內心又開始顫動,恐懼的滕蔓在人們心底滋生蔓延出來,緊緊地絞纏著人們已經脆弱不堪的內心,“身受重傷的小村像一條刮去鱗片的魚,時時疼痛,撕心裂肺的疼痛。”作者將小村比作一條魚,魚刮去鱗片后的痛苦不難想象,借用這種痛來借比小村所遭遇的苦難,可謂是直抵人心的神來之筆。
痛苦與快樂是人最為重要的兩種情緒。作者的語言不僅能極為微妙地將人心底的苦痛描繪,同樣也能將人眉宇間難察的歡愉托出。
在《木棉花開》中有這樣一段描寫任仲夷愉悅心情的文字。當時,廣東省委擬派梁湘赴深圳特區任職,但出于種種原因,梁湘不愿赴任,矛盾在此激發。面對這種情況,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任仲夷約談梁湘,兩人暢談至深夜方才云開霧散。在結尾處,作者這樣寫到:
任仲夷猛然哈哈大笑起來。他仰躺在竹椅里,一前一后地晃悠著。雪亮的燈光下,渾圓的銀白色的笑聲在四壁間清脆地撞擊著、回響著,他頭上的絲絲白發也仿佛是一綹綹導電的鎢絲,在閃爍著明晃晃的輝光。
迷霧散盡,玉宇澄清,雙方自然是皆大歡喜。作者在這里同樣運用充滿詩化特征的語言充滿想象力地描寫了任仲夷的“笑聲”與“白發”。在作者筆下,笑聲是“渾圓的”,是能一掃陰霾的亮亮的“銀白色”;同樣,它也能在“四壁間”清脆地“撞擊”、“回響”的。任仲夷頭上的白發則成為了“導電的鎢絲”,在雪亮的燈光之下,“閃爍著明晃晃的輝光”。這段描寫中,作者通過形象的比喻和語言節奏、色彩來將笑聲賦予了形狀、顏色、甚至聲音之后的“聲音”,將帶來歡愉的因素由單純的笑聲本身擴展到了顏色,甚至是笑聲“碰撞”帶來的又一重聲音;將白發形容為導電的鎢絲,閃爍著光芒,這不僅僅是燈光的光芒,更是智慧如電,在思維的網絡中暢游而發出的光輝。在這幾個方面的詩意描寫下,作者將各種無形、無色、無聲的客觀事物一一具象化,單純的笑聲超越了僅僅是難題解決之后狹義的愉悅,而更多的擴展到了更大的空間中,閃耀的白發也不僅僅是燈光下的景象,而是被涂抹了象征著未來更加光明的色彩。
李春雷的語言極富想象力,在對事物富有想象力的精細描摹上,突出體現了他語言的詩化特征。在《棗花吹滿頭》這篇文章中,作者就運用充滿詩化想象的語言進行了書寫:
在中國北方平原鄉村,棗樹可能是春天里最后一個醒來的植物。驚蟄清明,谷雨小滿,當春天的鑼鼓鏗鏗鏘鏘地敲響的時候,當敏感的春花如花蕊夫人般爭先恐后地粉黛登場的時候,它卻像一個懶散的老農,穿著皂黑的粗布棉襖,仍然蹲在陽光下打盹兒。直到芒種過后,它才瞪開惺忪的眼。一旦醒來,便厚積薄發,排山倒海。
這段文字對小堤村的棗樹進行了富含詩意的描寫。將棗樹比作一個“懶散的老農”,在春季的鑼鼓“鏗鏗鏘鏘地敲響的時候”仍然在打盹,等到芒種過后,才“厚積薄發,排山倒海”。作者用極具特色的詩化語言進行書寫,充滿美感地寫出了春季棗樹的生長特點。
他的描寫極富張力,收放自如。睥睨山河的氣勢將宏大的環境描寫微縮于股掌之中:
在《搖著輪椅上北大》中:
如果說南方是一株四季常綠的大榕樹的話,那么一條條大江大河就是它粗壯的軀干。那一條條橫七豎八的支流呢,就是它茂密的枝杈了。那些密如蛛網的無名的河流汊灣呢,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大榕樹身上千千萬萬根毛茸茸的胡須了。而那些生活在水邊的人群呢,就是它枯枯榮榮的葉片了。它們共同組成了南方深密的歷史,又鮮活地站在南方的晚風中,不知疲憊的搖曳著,細語著,釀造著南方特有的風情和靈秀……
作者將廣闊的南方地區比作一棵榕樹,粗壯的軀干是大江大河,橫七豎八的支流是茂密的枝杈,再小一些的汊灣則是樹上掛著的毛茸茸的胡須,人們則是枯枯榮榮的葉片。這種充分發揮的想象力與藝術的感受力,不僅準確把握了南方地區、流淌的江河、隨處可見的河流汊灣、依水而生的居民之間的關系,更用詩一般的語言極為形象地表現出了他們之間的關系。這樣的書寫,充分體現出了作家超強的藝術感受力、想象力、表現力。作者站在高山之巔的廣闊視野與心細如發的纖毫筆端構成的文本張力在這里顯現無遺。
四、結語
在當今紀實類文學的創作中,“記錄真實”的旗幟高揚,但“文學性與藝術性”的大纛卻沒有真真正正地飄揚起來。或許,如何處理真實性與文學性的關系正是讓這兩面大旗同時飄揚的一個極大障礙。與此同時,近年來國外的非虛構寫作傳入中國,引發了一股新的熱潮。然而在這股熱潮背后,大量應運而生的作品仍舊存在著語言的文學性與藝術性的巨大缺失。在這雙重背景下,李春雷報告文學作品的語言詩化特征,或許能給我們處理類似問題以極大的啟示,而此亦是本論文的意義所在。
[1]李炳銀. “天機云錦用在我”[N]. 光明日報,2013-04-16(014).
[2]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 報告文學藝術論[M].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3]奏響時代的音符:李春雷報告文學創作回眸[J]. 文藝報·周六版,2009(15).
[4]李良. 報告文學的“硬”與“柔”——從李春雷《木棉花開》說起[J]. 長城,2010(3).
[5]方東樹. 昭味詹言[M]//張葆全. 中國古代詩話詞話詞典.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
[6]張海寬. 詩歌創作漫談[M]. 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83.
[7]郭沫若. 論節奏[M]//文藝論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8]孫力平. 中國古典詩歌句法流變史略[M].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9]傅溪鵬. 2008中國報告文學年選[M]. 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
(責任編輯:蘇紅霞 校對:李俊丹)
I207.5
A
1673-2030(2017)04-0102-06
2017-09-10
2017年河北省社會科學發展研究重點課題(項目編號:201702050101)階段性成果
李錚(1992—),男,河北邯鄲人,河北大學文學院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