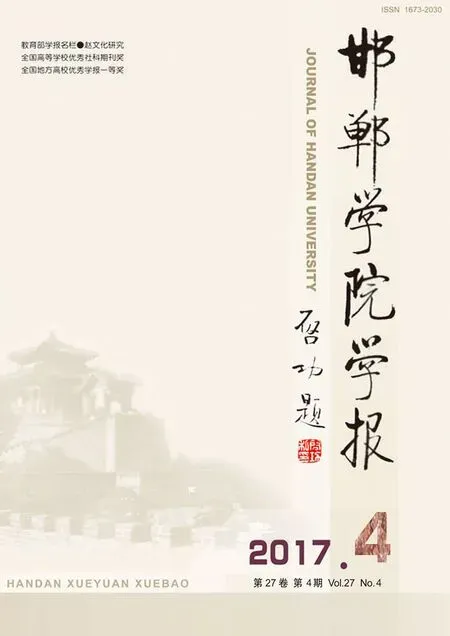日本侵華時期蒙疆淪陷區的學校教科書研究
吳洪成,蔡曉莉,李陽陽
?
日本侵華時期蒙疆淪陷區的學校教科書研究
吳洪成,蔡曉莉,李陽陽
(河北大學 教育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抗戰時期,日軍為實現對蒙疆地區奴化教育需要,積極推行“防共親日”、民族協和、“分而治之”的殖民奴化教育政策,設置教科書編審機構,肆意刪除、篡改教科書內容,編纂奴化教育所需的學校教科書,使學校教科書受到嚴重的扭曲,從而為毒害青少年學生的精神,實現殖民統治服務。
日本侵華;蒙疆偽政權;奴化教育;學校教科書;學校課程
近代社會以來,中國的邊疆地區,尤其是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一直是帝國主義列強侵華行動中的重要棋子,蒙疆地區亦不列外。“蒙疆”是日本在侵華時期炮制出來的專有名詞。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隨著東北三省全境和內蒙古東部地區完全劃入日本殖民地版圖后,日軍為迅速實現“全面亡華”和“防共、反共”的目的,先后分別建立察南、晉北與蒙古三個自治政府。1939年9月,日軍為發揮“防共”特區的作用,又將三個自治偽政權合并為以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為主席的偽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日本帝國主義及其扶持下的建立起來的蒙疆偽政權極為重視奴化教育的推行,因而,在制定奴化教育方針政策,并建構起奴化教育管理體系的同時,又為各級各類的學校設置課程,編定教材,實施奴化教育的微觀、具體而實質性的操作。依據教學論的原理,課程與教材在教學活動中是相互聯系的,又有各自獨立性的兩個教學要素,而教材在教育內容的包容性上比教科書更為泛化的概念,無疑教科書是教材的精髓或核心。本文主要在分析日本侵華時期蒙疆淪陷區的課程編制基礎上,探討學校教科書的相關問題。
一、蒙疆淪陷區奴化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學校課程
蒙疆淪陷區的奴化教育是受日本侵略者支配,在蒙疆偽政權的設計和推行中實施的,偽政權所轄的教育行政部門直接并控制其中的相關因素與環節,課程的編制是其中的重要舉措,它又直接影響學校教科書的編審和使用。
1936年5月,在當時的察哈爾盟化德縣策劃成立“蒙古軍政府”,隨后日軍占領內蒙古西部地區的綏遠省大部分地區。1937年10月,在當時的綏遠省省會歸綏(今呼和浩特市)將蒙古軍政府改組成立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云王(云端旺楚克)任偽自治政府主席,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任副主席。由于云王稱病,德王縱攬政權一切事物。通過了偽“自治政府組織大綱”,規定“以蒙古固有之疆土為領域,暫以烏蘭察布盟、錫林郭勒盟、察哈爾盟、巴彥塔拉盟、伊克昭盟及厚和市、包頭市為統治區域”;“以防止共產、協和民族為基本方針”;以“生、聚、教、興、養、衛六事”為綱領;以成吉思汗紀元為年號,定都于歸綏市。[1]83該偽政府下設政務院,德王兼任院長。并于同年11月在張家口由德王為主成立統轄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的偽蒙疆聯合委員會;1939年9月,撤銷上述三個政權,并將“察南自治政府”改為“察南政廳”,“晉北自治政府”改為“晉北政廳”。至此,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壽終正寢,同時以德王為首的內蒙古分裂勢力的“蒙古帝國”夢也宣告破滅。在偽蒙疆聯合委員會基礎上于1940年正式成立了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確定以張家口為“首都”,用成吉思汗元年號(簡稱“成紀”),并特地制定從上而下橫條黃、藍、白、赤四色七條的偽政府旗幟。1941年8月又改稱偽蒙古自治邦。日本帝國主義嚴格控制其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其實質已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隨著合并后的偽政權的建立,其殖民地化進一步加深。
蒙疆淪陷區奴化教育由偽政權所轄各級教育行政機構負責,形成了一個殖民教育的體系。偽政府內部主管機構先后有總務部教育處、民政部教育科,盟偽教育廳,民政廳文教科,旗縣有文教股。1941年偽蒙疆政府機構改革,設立興蒙委員會,教育上也職權分開,蒙古族的教育由偽興蒙委員會教育處掌管,漢族和回族的教育由偽內政部文教科掌管。實際上,蒙疆的教育完全由日本人控制,不僅在各級教育行政機關的日本人顧問、參與官擁有決策權,就連各個學校的日本人校長、副校長、甚至普通教師都握有實權。如日本人直接掌管的總務部,就對其直屬的蒙疆學院擁有很大的管轄權力。1939年9月1日發布的《蒙疆學院官制》規定:“第十四條,蒙疆學院之編制、教育科目及其他必要事項,通過總務部部長經政務院長認可后由院長定之。第十五條,蒙疆學院之分科規程,通過總務部長經政務院長認可后,由院長定之。”[2]193可見,蒙疆地區的教育管理權掌握在日本人的手中,中華民國政府基本喪失了蒙疆地區的教育主權。
(一)蒙疆淪陷區奴化教育政策的制定
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建立之初,于《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組織大綱》第三條中就明確宣示:“以防止共產、協和民族為基本方針”;“以生、聚、教、興、養、衛六事”為綱領。這里的所謂的“民族協和”,除了其淺層所表示的蒙疆地區蒙、漢、回諸民族之間的“協和”外,還有其深層次的與日本“協和”的含義。1939年偽蒙疆聯合委員會的《教育綱領》指出:
第一,方針:基于蒙疆政權創建宗旨,發揚民族協和精神。和東洋道義之精華,陶冶德性,授以實際技能,養成堅實人物。第二,要領:根絕共產、抗日思想宏揚東方精神;著重勞作教育振作勤勞風氣;重點置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著眼實業教育,高等教育將來伺機建立所需設施并施行之;普及日語;獎勵體育,涵養健全之精神;指導訓練一般青少年,振作樸實剛健風氣;婦女教育著眼于培養婦德和實務性訓練;學校以觀公立為原則,與社會保持緊密聯系,使之成為教化之中心;教育與實際方法適應民情和地方使態;教師的培養和鑒定由政府行之。[1]108
由此可知,任何政權教育政策的制定,都是該政權大政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教育政策的實施,則是該政權性質的外在而具體的反應。“防共”、“反共”、“協和”日本并最終將蒙疆地區納入日本“東亞新秩序”之中,其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必然以實現日寇分裂并占領蒙疆地區的根本目的為其指導原則,因此,教育政策也就具有明顯的“防共”、“反共”特征和殖民地化的特征。
而日本一手扶植起來的偽蒙疆政權,其實質也不過是日本實現“全面亡華”和“防共”、“反共”的工具而已。日本通過這一政權,在蒙疆地區實行“分而治之”的教育方針,即日本侵略者對蒙、漢、回采取不同的奴化政策:
教育方針是:“基于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成立的宗旨,發揚防共、民族協和東洋道義的精華,陶冶德行,傳授實際知識技能,培養有用的人才”。實施要領是:“拒絕共產主義、抗日思想,確認東亞民族團結的必要性。”具體指導方針如下:其對蒙族之方針有四:一、徹底實施產業實務教育;二、徹底推行體育、衛生、及宗教教育;三、日本語及其文化之徹底吸收;四、常識之養成及生活之改善。其對漢族之方針有三:一、徹底實施日本教育之精神;二、日滿支協同體之精神培植;三、徹底恢復禮數并施產業教育之訓練。其對回族之方針有二:一、除前述外,徹底實施道德教育;二、樹立親日思想,逐漸陶冶于日本教育之訓練。[1]117
對蒙古人民,責其“徹底吸收日本語及其文化”;對漢族人民,“徹底實施日本教育及其精神;配制日、滿、支、同一體之基本精神培植;徹底恢復禮教并實施產業教育之訓練”;對回族人民,責其“樹立親日思想,逐漸陶冶于日本之訓練”。日本侵略者在蒙疆地區實行“分而治之”的教育方針的根本目的在于使蒙疆人民成為日本的附庸。這一教育方針,決定了親日、反共、民族協和的奴化教育和實務教育的殖民化教育成為以后蒙疆教育的主題,而蒙疆淪陷區的課程設置與教科書編寫及審定也是為此目的服務的。
(二)蒙疆淪陷區學校課程設置
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成立之初,偽總務部教育處長陶布新曾主持召開過蒙古教育會議,討論教育宗旨和學制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各盟的偽文教科長、厚和市和包頭市的文教股長、蒙古學院的教導主任和顧問,還有蒙古文化館的代表。因為提交會議討論的草案是參照原來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學制制定的,這顯然與蒙疆聯合委員會提出的“民族協和”、“防共親日”的教育宗旨和“奴化”、“分化”教育政策有所不符,所以遭到偽教育處日本顧問岸川兼輔等人的強烈反對,會議沒有形成任何決議。當蒙古學院教務主任那蘇圖提出學生應當學習英文時,更惹起日本人的反對,因而學制暫時沒有確定。[3]513
1939年9月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成立,由主持教育的日本人在偽蒙疆聯合委員會制定的《教育綱領》的基礎上,重新制定了《學制綱要》,規定了各級各類學校的學制。新學制規定,蒙疆淪陷區的教育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兩個階段,還有特殊教育及留學生教育、官吏培養教育等幾個門類。初等教育分為初級小學、高級小學兩種。小學學習科目為修身、國語、日語、算術、自然作業、體育、音樂、圖畫、實務、地理等11個科目,使用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編纂的教科書。
中等教育包括普通中學、師范學校、女子中學、實業學校及實務學校。中學分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兩種。1939年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曾制定公布了《公立中等學校官制》,1940年5月又修正公布了《官立中等學校官制》,規定各種中等學校設校長、副校長、教諭(一般學校)、主事(設有附屬國民學校及高級國民學校的師范學校)、教導、書記等職員。官立中等學校歸民政部部長管理,具體管理職責則由偽民政部部長委托盟長及政廳長官負責。[2]196普通中等學校學習科目為國民道德、國語、日語、歷史、地理、數學、理科、圖畫、音樂、體育、作業工11科。每周授課時間36小時,日本語授課7小時以上。使用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編纂和檢定的教科書;女子中學入學資格、修業年限與男子中學無異,學習科目中加授女子所必要的家事、實業、裁縫、手藝等;師范學校則以培養初等教育所需之師資為目的,其學習年限、入學資格等與普通學校沒有多大差別;實業學校及實務學校則以接受實業、實務所需的知識、技能、養成勤勞的習慣為目的,入學資格與普通中學相同,實業學校學習年限為四年,實務學校為2至3年。[4]
蒙疆淪陷區的學制完全適應日本奴化政策的需要,將“親日”、“防共”、“反共”的原則精神貫穿到學校教育中,高等教育是為培養各級傀儡官吏和高級奴才服務的,如在蒙疆學院中“讓學生認識本地區歷史、地理上的特殊性,整備防共第一的總動員體制”,并認定“共產主義思想是產生抗日思想及運動的溫床”,“不僅是蒙疆政權的課題,而且是世界性的課題”。[5]322把如何克服這一思想當成學校教學任務的中心任務。總括上述蒙疆淪陷區學校教學課程設置有如下特點:
1. 日語成為各級各類學校的主課
從表面上看,日偽在蒙疆淪陷區開設的中小學均設有國文、數學、歷史、地理、修身、音樂、體育、美術、勞作等普通課程,但在課時安排上和實際教學中卻把日語放到主要位置,日語成為各級各類學校的主課。如1938年,巴彥塔拉盟制定的教育計劃,在促進各縣小學開學、開設師范學校、開設教員講習所和開設盟立蒙旗青年學校各項計劃中,均有日本語教育的內容。[6]639-640并且在1940年1月,偽蒙疆政府民政部教育科規定,日本語的授課時數,小學每周為6課時,中學每周為7課時以上。1943年2月,偽蒙疆政府內政部發布訓令第50號《視學及特別市視學學事視察指導規程》,其中第十七條規定,視學的任務包括調查“日語之普及情況”。[7]16蒙疆教育會也把普及日本語教育當作該組織的主要任務之一。要求所有學校必須開設日本語。日本語授課時間之長,甚至超過漢語、蒙語,連日常用語、體操口令都使用日語。
興和縣實驗小學的課程設置包括漢語、日語、修身、自然、算術、圖畫、體操、音樂等。此學校從一年級就進行日語學習,每天至少一節課,甚至竟把日語列為“國語”之一。另外,校長到縣公署請示匯報工作、領取薪水等,都要用日語向日籍顧問、參事官問好。托克托縣第一完全小學,1941年后“取消了歷史、地理、公民等科,增加了日語”。在包頭的鐵路職工子弟學校——扶輪學校,學生問候教師、進出辦公室喊報告都要使用日語。[8]
中學的日本語教育比小學更甚。巴彥塔拉盟師范學校的日語課,授課時數由原先每周的6節最多增加到12節,此外還要求課外加授。在日本分化教育的政策方針下,從事蒙古族教育的學校如蒙古學院、厚和蒙古中學、包頭蒙古中學等,禁止學習漢語,除蒙文、日語課外,即使一般的中學課程,也要求蒙古老師上課用蒙語講,日本老師上課用日語講。對此,蒙古學院的學生指出:“學習任何一種語言都是有益無害的,但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下,專設日文課和軍訓、做操用日語口令等,赤裸裸的展示了偽蒙疆政府無恥的要求蒙古族學生踐行‘日本話及其日本文化之徹底吸收’的教育方針。”[8]
厚和農科實業學校的情況也是如此。據在該校任教的日本人回憶:該校日本語的授課,比現在日本國內學校學習英語的時間還長。學校的校歌用中文和日文兩種語言創作,學校集會的場合經常合唱校歌,畢業典禮等場合還特別用兩種語言合唱校歌的方式,為即將離開的年輕人振作士氣,鼓勵他們的活動。校歌為該校教諭前田實則作詞,由副校長上原淑助翻譯成中文。校歌中有這樣的詞句:“地上和平溢歡喜,民族協和旗下立。新生東亞欲黎明,我們立志作先驅。”“巋然不動我決意,新生蒙疆之王基。將于東亞放光輝,大家攜手志向立。”在包頭蒙古中學的日本教師用日語寫作校歌然后教給學生。歌詞中充斥著反共反蘇、大亞細亞的內容。[8]讓學生用日語合唱校歌,既普及了日本語學習,又向學生灌輸了民族協和、東亞共榮的奴化思想,對學生毒害之深,可想而知。
為強制日語教育,在教材方面,蒙疆地區使用過日本國內、偽滿、善鄰協會和蒙疆政府編審室編纂的各種教材,也有教師自己編寫的講義。1943年春,蒙古教育會發行了《日本語新教材集》,含有決戰時局、日本精神的認識等奴化內容。是日本強制日語教育的教材之一,在各級機關和學校中供學習日語使用。[8]
日本侵略者強制推行日本語教育,造成惡劣的后果。“有些中學畢業生,不能用蒙、漢文寫通順的文章,卻能說流利的日語,甚至有的說漢語也夾雜著一些日語名詞,變成不倫不類協和式語言。”[9]184-185
2. 設置各種奴化思想課程
日本帝國主義針對蒙疆制定的教育方針、政策和進行的教育活動,以奴化、殖民化教育為主題,向師生灌輸日蒙親善、親日反共反英美的奴化思想,其具體表現為:通過課堂教學與精神講話、朝會與遙拜、武士道與軍事訓練、休學旅行、勤勞奉仕等方法,向師生灌輸反共反蘇、民族協和、日蒙親善、反英美的思想;培養學生的服從意識和尚武精神;在學生中煽動民族仇恨,制造民族分裂。
蒙疆的小學設有修身課,中學設有國民道德課(類似偽滿的建國精神課)。偽蒙疆民政部頒布的《中等學校用認可教科書之件》規定:“國民道德(或修身)之教材以修養人格為基礎,由齊家之德進而達及對于社會之人任務,以宣揚東亞之道義、防共、民族協和之精神為原則,給與以邁進東亞新秩序之自覺。”[2]296-297修身課和國民道德課,成為日寇對蒙疆地區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的主課。
朝會和遙拜,是日寇向學生灌輸奴化教育思想,實施奴化教育的常用手段。日本侵略者強迫各級學校每天早晨集合全體師生,舉行升旗儀式,向日蒙國旗敬禮,向東方的日本天皇遙拜。如偽安北縣公署于1939年建了一所小學,設在縣公署院內。招收學生50多名,有教師5名。采用“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統編教科書,開設日語、漢語、算術、唱歌、圖畫、體操等課程。灌輸“天皇至上”的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及法西斯的服從觀念,每天向東方遙拜。[10]821
3. 開設“輕工”、“重農”職業教育課程
日偽在蒙疆的中等學校教育中加強職業教育。這是日寇實行“工業日本,農業蒙疆”政策的具體體現。蒙疆的職業教育以實業學校與實務學校為主,實業學校學制四年,實務學校二至三年。從表面上看,日本推行實業教育的目的,是以教授從事農牧業生產所必須的知識技能、培養勤勞的習慣為目的,以掌握實務為重點。實業教育與基礎教育相配合,適當地推行是有益的,但日偽單純地推行實業教育可見其用心險惡。[11]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實行‘工業日本,農牧業蒙疆’的侵略政策,僅準設立農牧業中等學校,禁止設立工業中等學校。”[11]45此舉亦表明日本將蒙疆地區變為日本殖民地的不軌意圖。
1938年,巴彥塔拉盟師范學校在師范部、臨教部之外,成立了實業中學部,招收實業班。翌年該部改稱為巴彥塔拉盟立農科實業學校,也稱厚和農科實業學校,招收農科班,1941年學校遷到新城的關帝廟街。該校的課程設置分為文化課、基礎課和專業課,基礎課有植物學、動物學和生理衛生課,專業課有農業泛論、畜牧泛論、農業課、畜業課、商業薄記、商業算術等科目。學校還設有農場、氣象觀測站。該校從第六期又開始辦土木工程專業班,但學生未及畢業日本就投降了,學校由原綏遠農科職業學校接收。[12]日本侵略者“工業日本,農業蒙疆”政策,雖然沒有以文件的形式公開出現,但在課程設置上所體現的“輕工業、重農業”特征證實了此政策確實是客觀存在的,這也是日寇在華推行奴化教育活動的重要手段。
二、蒙疆淪陷區學校教科書的編審
眾所周知,課程、教科書是教育內容的主要載體,集中體現了教育的宗旨以及人才培養的目標取向。教育目的及培養目標的實現也正是借助于課程及教學內容才能達到或完成的。可以說,學校教育的育人活動是通過課程、教材的實施及教學活動而實現的。奴化教育雖然是一種扭曲的或畸形的教育,但有教育行為及方式的特點,只不過其中實質本性發生了變異。以下集中探討教科書編審問題。
(一)蒙疆淪陷區學校教科書的編寫
教科書是實施教學的主要工具,它對實現教學目標關系極大,因而得到日偽當局的特別重視。偽蒙疆政權成立伊始,日寇便極力摧殘原有教育設施,禁止學校使用原有教科書,并將“各校所有書籍,盡數查封,不允閱讀”。下令“家有藏書,限10日內,如有抗命不交者,一旦查獲,嚴懲不貸!”對已查獲管制的舊日各種教科書及參考書,全部焚毀”,對于各地教會所辦中小學和村鎮私塾,“偽官方初不限制,仍照常上課,教科書亦未限制,惟邇來偽政府擬調查私塾用書,必將加以嚴格之統制矣。”[13]
1936年3月后,日寇在強化奴化教育的政策宗旨下,著手整頓教育內容,重點放在教科書方面。“為達到麻木兒童腦筋,灌輸親日思想之目的,故對已往課本及教材,一律摒棄不用。唯偽組織甫定,凡應興應革之事,正在草擬,故迄今尚無適當課本頒發。只頒教材大綱一紙,令教員以此自編教材,印發兒童。因而一般奸人,為博日人之歡心,則所編教材,不曰‘解民倒懸者,為友邦志士’;便云‘中國政府,為政不仁’。類此言語,竟為彼輩教材之中心”。[13]
然而,編纂符合日寇奴化教育目的的教科書一時并未完成。1936年5月,蒙古軍政府成立后,當局只好在其轄區內的小學暫時采用偽滿洲國編纂出版的教科書,直至1937年10月,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成立后,在繼續采用偽滿所頒教科書的同時,還對其中一些內容進行了特別處理。把小學教科書國語一科中某些不適合蒙疆政權的內容刪除,加入一些具有地方和民族色彩而同時適合政治需要的內容,供各地小學使用。
1937年11月22日,日偽在張家口組建蒙疆聯合委員會,在其內部附屬一編纂委員會著手編纂適用于“蒙疆區域”之教本,“其主要內容,不外以‘防共親日’、‘民族協和’造成亡國奴的思想為目的”。[14]“而此時的察省淪陷區中等教育所用課本,亦‘皆由偽滿洲國學校課本脫胎’”。[15]興蒙委員會教育處輔佐官中村勇在編纂教科書上仿照偽滿洲國教科書,使得國文教科書出現“殲滅元寇日本紀念日”的文字,這無異于“等于當著蒙古人的面罵蒙古人的祖先是強盜,對于蒙古民族是奇恥大辱。”[9]175
1940年,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確定了民政部教育科制定的教科書修訂編寫計劃,準備全面實施偽蒙疆淪陷區中小學教科書的編纂工作。為了保證在教材中貫徹奴化教育的思想內容,使教育更好地為殖民統治服務,日本侵略者特制定了教材《編纂要領》:1、為了建設作為東亞新秩序一翼的蒙疆,強調團結一致的精神;2、發揚東洋道義的精華;3、針對各民族的特點,突出其特征;4、特別強調民族協和、防共、厚生;5、認識到本地區的特殊性;6、適應時代的趨勢;7、順應高度國防政權的完成。[13]當時,教育科編審室共配備了9名教科書專業編審人員,計劃編寫小學日語、漢語、蒙語教科書和與思想教育有關的如國民道德、地理、歷史、漢語和日語等中學教科書,而中小學其他學科科目編寫則委托給相關部門。上述教科書的編纂工作歷時一年時間便初步完成了。到1941年6月,準備印刷、制本小學的漢語教科書18種25萬冊,蒙語教科書6種1萬冊;到1941年底,準備完成小學的漢語教科書34種100萬冊,蒙語教科書6種13000冊,中學的漢語教科書27種27000冊。三年內,計劃總共發行60余種130萬冊。[13]
因偽蒙疆政權境內蒙古、漢、回等民族交互聚居,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日本為進行奴化教育,意圖通過語言侵略來養成親日的氛圍。日本侵略者強制把日語作為蒙疆境內民眾的共同語,各民族間不能相互學習對方語言,嚴禁蒙古人學習漢語。日本善鄰協會(專門對蒙古人進行教育的機關)在編撰教科書時就指出:“蒙人的漢化毫無益處,如有固有名詞,用日本假名代替,在括號內添上蒙古文字。”如此,在偽蒙疆政權各學校中,“科學的書都是日文的,為日本人做事都靠日文吃飯”,這就“使得蒙文、蒙語實用不大”。[16]104
日本善鄰協會還極力強調教科書編纂中的思想性,表現在“由本協會編寫的蒙古兒童用小學教科書,不只在本協會,應在所有從事于對蒙文化工作的機關使用,而且由于該規定關系對蒙古國策的根本和數十年后的日蒙關系,具有重大的教化意義,有必要將以下各點作為重心:(1)喚起蒙古人的自豪;(2)認識烏拉爾、阿爾泰人種的蒙古人的世界歷史地位;(3)使其關心蒙古國運的重大問題;(4)使其了解日蒙親善的必然緣由;(5)重視產業教育;(6)使其認識教育的重要性。”[13]
蒙疆奴化教育組織管理及教科書編審活動,還受蒙古教育會團體組織干預或影響。1939年11月成立蒙疆教育會,表面稱以改進蒙疆教育和加強文化教育界人士的團結為目的。在偽蒙疆政府內政部設立會務機構,由偽內政部部長擔任會長;各政廳、盟設立支會。1941年偽政府機構改革后,改組為蒙古教育會。后與日本人的教育組織合并,變成了一個以日本人為主的組織。所從事的活動主要包括:一、調查與研究有關教育事項;二、編纂刊行有關當地教育的圖書雜志;三、召開有關教育的研究會、講演會;四、培訓教員及講習;五、普及日語、蒙語、漢語;六、介紹教育事業及教育團體的國際聯絡;七、與各種文化事業團體的聯絡和協作;八、教育視察;九、表彰教育功勞者;十、日語教育用圖書及其教材、教具之斡旋;十一、當地學生用品的輸入和配給。1942年4月18日,又召開該年度第一次理事會,確定舉行全蒙教育狀況報告會、時事講演會、展覽會、演劇,征集日語作文,繪制“大東亞共榮圈”地圖及中學地理附圖等工作計劃。1943年春,又編纂出版《日本語教材集》,作為中等學校高年級學生及其他日語教育機關研究班學員的日語教材。當時日本駐張家口公使館出資購得全部教材,轉贈偽蒙古自治邦政府,并配送給有關學校及機關使用。
由此可見,“蒙古教育會”雖以民間組織形式出現,但其從事的業務不僅僅調查、研究蒙疆民族教育和舉辦有關教育的各種活動,而且還參與教科書編審、經營學生學習用具等,事實上已經具有半官方機構性質,成為日本在蒙疆地區確立的殖民地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
為強化對在校學生的奴化思想滲透,偽蒙疆當局在小學《歷史》《地理》教科書中,特別強調日本和滿洲國,“而反無中國字樣”。《暫行初等學校規程》第八條規定:“歷史以使知我蒙疆地區,友邦大日本帝國,‘滿洲帝國’,及東亞之史實大要,闡明政府并蒙疆政權創建之意義,及東洋精神,以涵養蒙疆精神為要旨。”第九條規定:“地理以使知我蒙疆地區之地勢、氣候、區劃、都會、物產、交通之概要,并鄰接各國及日本國勢大要,并與我蒙疆區及日本有重要關系之各外國國勢之簡單知識,更進而及于地文之初步,養成愛蒙疆心為要旨。”在教授課程表內,歷史程度為“蒙疆地域日本及東亞史之大要”,地理程度為“蒙疆地域日本及東亞地理之大要”,而對中華民國的歷史地理知識毫無關注。在《教科規程》第二條中又有如下規定:“確認與友邦日本大帝國、‘滿洲帝國’之親善不可分之關系,并體認防共民族協和之精神,因教育上最重要務期于在全學科目及凡設施之機會徹底之。”第三條規定:“修身以咸使體會友邦大日本及‘滿洲帝國’之親善不可分之關系,并防共民族協和陶冶德性與指導道德之實踐為宗旨。”[17]40-41以上各點,充分反映了偽蒙疆政權所謂“樹立親日思想”及培植日“滿”支協同體的奴化教育的精神實質。而該思想指導下所編制的一系列的教科書內容中與中國民族國家政治及文化之間的聯系消失的無影蹤,以此來麻痹學生,泯滅蒙疆地區兒童的民族性,充分暴露出日偽侵略者的險惡用心。
(二)偽蒙疆政權對學校教科書的審定
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在政務院民政部下設教科書編審室。編審室作為專門機構,主要負責以下事物:“1.關于教科書的編纂、審定及檢查事項;2.關于教科書之發行事項。”但其具體內容由日本顧問全權決定和直接掌握。日本顧問在其制定的《蒙古國史教科書》“要領”中明確規定,要求教授蒙古史內容須主要反映:“1.帶來蒙古人的自覺及自豪;2.知道民族的產生過程;3.對成吉思汗個人及其偉業的強調;4.元及其他蒙古帝國的大概情況;5.明代以后雄踞北方及其地位;6.援助清朝君臨中國的史實;7.中華民國與蒙古——漢人移民;8.外蒙古和赤化;9.滿洲蒙古;10.蒙古的地位和使命。”[13]到1939年底,該編審室編審了全部高級小學用的日本語讀本,初級小學用的蒙古語讀本4冊、蒙古語算術教材4冊。當時在蒙疆地區的中、小學校使用的主要教科書有算術、日語、自然、國(漢)文、修身、日本史、地理等四十余種。1941年,偽蒙疆政府機構改革后,原來的民政部編審室分別屬于內政部文教科和興蒙委員會教育處,前者編寫漢回教材,后者編寫蒙文教材。1942年12月,上述兩個機構又合并為總務廳臨時編審室。
為了加強對教科書的編寫與發行實施更有效的管理,偽蒙疆政府還專門頒布了一些法令。如1940年4月17日,民政部以第54號訓令《中等學校認可教科書之件》,規定了1940年度認可中學教科書的注意事項:“辦理本年度認可的教科書之教材時應嚴守下記事項:應適于本政府成立的意義及使命;闡明本政府之特質;合于當地區的特殊性。”并對國民道德(或修身)、歷史、地理等有關思想教育的教科書,提出了特別注意事項。其主要內容為:“國民道德(或修身)之教材以修養人格為基礎,由齊家之德進而達到對于社會之任務,以宣揚東亞之道義、防共、民族協和之精神為原則,給予以邁進建設東亞新秩序之自覺”。[2]296-297其中《歷史》教科書:“歷史之教材使明了歷史上之重要事跡,理會社會變遷文化發展之過程、并闡明本政府成立之意義,以養成蒙疆人民之信念;東亞史以蒙疆為中心而研究各國歷史之發展;關于民族爭斗史實應以民族協和精神為原則留意辦理”。地理教科書:“地理之教材使理會地球及人類及生活狀態,并闡明兩者之關系,尤須使知蒙疆之現勢,而促進蒙疆人民之自覺;關于蒙疆之地理,使知自然狀態政治、經濟、產業、交通之狀態和其關系,并授以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之概要”。[13]
偽蒙疆政府還仿照偽滿的做法,于1940年8月20日成立了“教育用圖書審議會”,頒布了《教育用圖書審議會管制》,規定“教育用圖書審議會屬于政務院長監督,而應其咨問審議關于教育用圖書編纂重要事項。”[7]24-25同年12月18日,民政部又頒布第19號令頒布《教育用圖書采定規程》,其中規定:“初等學校、中等學校及臨時地方教員訓練所、青年訓練所等類此訓練機關,須有民政部長著作權之教育用圖書或經民政部長檢定或審查之教育用圖書,經監督官廳之認可方可使用”。[2]294-295
從這些法令中即可看出,蒙疆偽政府嚴格控制教科書的編審與使用,各科教材的審定內容都以圍繞“建立大東亞新秩序、”“防共反共”、“中日親善”、“蒙疆中心論”展開,其中有關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的內容已被刪改,以此制造民族分裂,以絕斷中國人民的愛國意識。
日本勢力為便于教育分化,還積極勸誘內蒙古王公一心向日,此舉反映在學校《歷史》教科書中便十分明顯:學校所教的歷史,都是明治維新的故事,對于三皇五帝的盛績,則一字不提。唯有提到成吉思汗,則竭力恭維贊揚,甚至不惜“矮化”本民族,篡改歷史,向內蒙古百姓撒下彌天大謊,聲稱成吉思汗是日本人的祖先輩,把蒙古人的元太祖,假說成日本人。[13]這種謬論對蒙疆兒童產生相當嚴重的思想毒害。
(三)蒙疆淪陷區學校教科書的發行
為適應培養忠于日本“良民”的奴化教育的需要,偽蒙疆政權指使偽民政部發行系列教科書,供應淪陷區中小學校采用,這些教科書有些采用偽滿洲國編纂的,有些由偽滿組織人員對原來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機構出版教科書加以篡改后印刷發行的,有些教科書編纂和發行都由偽滿洲國機構負責,直接輸入蒙疆淪陷區供學校教學使用。甚至有些學校還直接選用翻譯日本學校教科書。這些教科書的封面設計主要有三種:一種是封面有“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國民學校用”、或“高級國民學校用”、“中等學校用”字樣;第二種是封面有“蒙古自治邦”“國民學社用”“初級國民學校用”的字樣;第三種則是封面有“滿洲圖書株式會發行”字樣(此書多為中等教科書)。各種教科書版權頁信息則用“成紀”年(成吉思汗紀元),說明使用地區;編著者一般都署名“民政部”或“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民政部”,也有“蒙古聯合自治邦政府”的,同時多有“民政部檢查”字樣,一般是標注“成紀”735—738年間發行(成吉思汗元年為1206年,735—738為公元1941—1944年)。
在1939年之前(包含1939年),偽蒙疆聯盟自治政府、偽察南自治政府及偽晉北自治政府都編寫出版和發行教科書。1939年9月,撤銷上述三個政權,成立了偽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所以教科書編輯出版的署名就是“蒙古聯合自治政府”,1941年8月改為偽蒙古自治邦,教科書署名就改為“蒙古自治邦政府”,出版時間對此也有一定的體現。
日偽統治初期,為使淪陷區中小學教育適合形勢需要,在查禁原政權通行教科書同時,一一制定各學校教學用書。綏遠抗戰前,日軍控制下的百靈廟小學的“教材和教本都是東洋方面預定好的”。厚和蒙古中學成立后,對于蒙授課目,學校“當時根本沒有現成的蒙文數理科課本”,所需教材全都是由教職員自己用蒙文編成后再“油印發給學生”。例如,蒙文教師額爾恒畢勒格所編輯的油印課本內容“都是他從漢文書上選譯來的”,在該校女子部,學生程度參差不齊,有些教師“只好根據大家的文化程度自編教材,進行分組教學輔導”。在包頭蒙古中學,除蒙語課外,日語、數學、歷史等所有課本都是日本國內用的課本。
在初等學校教育用圖書的漢、蒙語文選擇方面,日偽當局進行了明確劃分,“施行市縣制之地域內采定漢語,其他之地域內采定蒙古語,縣旗并置及市旗并置之地域內,須依管轄該地盟長之規定而采定或蒙古語”。“對于蒙古中學校得使用日本語、蒙古語,對于其他中等學校得使用日本語、漢語圖書。但關于語學之教授不在此限”。關于各類教育用圖書的使用,日偽當局規定,經偽民政部檢定或審查的教育用圖書及中、初等學校用教育用圖書,須經市(縣)長、札薩克或總管認可;“中等學校、臨時地方教員訓練所用教育用書,須經過政廳長官、盟長受民政部長之認可,由校長或所長采定之;青年教練所及類此訓練機關教育用圖書,由政廳長官、盟長或市縣長札薩克或總管采定之”。如果上述規定實施有特別困難時,“由民政部長決定之”。同時,當局如發現某學校“不法采用”“有民政部長之著作權教育用圖書或經民政部長之檢定審查教育用圖書以外之書籍”,“或令采用為初等學校、中等學校并臨時地方教員訓練所、青年訓練所及類此訓練機關之教育用圖書者”等擅自行為,或者某些學校對“有民政部長之著作權教育用圖書或經民政部長之檢定審查教育用圖書”隨意增加書價,仍然讓師生采用,“或令其采用為初等學校、中等學校并臨時地方教員訓練所、青年訓練所及類此訓練機關之教育用圖書者”等行為,明令處以“二百元以下之罰金”。[2]294-295
到1943年初,鑒于戰爭局勢的緊張,侵華日軍加緊了對偽蒙疆的教育文化滲透。7月14日,偽蒙疆組織所屬各盟旗興蒙學校、喇嘛寺院義務教育部教師及有關人員參加了在錫盟西蘇尼特旗興蒙學校舉辦的興蒙教育練成會,后轉到張家口召開文教人士報告會。會議就“大東亞地理教育”和“配置教材”等問題進行了討論,關于“大東亞地理教育”問題,會議認為“在大東亞共榮圈體制下激發蒙古人的氣勢,所以僻處草原一隅的學校也應讓他們了解大東亞全境的地理、歷史及其他,以增強其熱情。倘利用掛圖、照片、圖片等參考用品講解,便能充分理解,現在西蘇尼特家政女子學校女學生關于大東亞地理問題的解答已達到驚人的程度,她們對日本地理也特別明了。”關于“配置教材”,會議認為,“最近草原教育熱驟然興起,教材的配給無法保證。現擬以行政力量解決對符合蒙疆特殊條件的新教科書等學習用品的妥善配給,同時開拓些新的學問領域。隨著一些新詞匯的引進,需編纂日蒙新辭典,否則會出現諸多不便”。[13]日偽政權對教育教科書的使用規定之嚴格,并以此來控制蒙疆淪陷區中小學所受教育的內容和范圍都在“反共親日”、“分而治之”的奴化教育之下。
三、蒙疆淪陷區學校教科書的特點
日偽在蒙疆淪陷區推行的奴化教育是一種典型的殖民教育,這種教育必須有相應的內容、組織及方法為保障,其中教學內容是以課程編制及教科書的媒介形式出現的,尤其是學校師生教學中使用的教科書最能體現殖民主義教育侵略的特色。
(一)教科書的設計以殖民者的利益需要為中心
偽蒙疆政府所編寫發行教科書的目的旨在為日本侵略者培養“良民”,為了體現侵略者意圖,在教科書的封二,都刊有所謂“政府施政綱領”五條,包括:“昂揚東亞教育以期其實踐”,“大同協和各民族以國民之總意為宗旨”,“與友邦同盟相結合”,“同志相契以參翼建設東亞新秩序”。在部分教科書的扉頁,則印有“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宣言”。教科書在形式上卻力求圖文并茂,旨在更有效地感染學生,傳播奴化思想。[18]483-484
蒙疆淪陷區中小學在課程設置中非常重視日語的教學,把它作為必修課和主課來看待,在教學時間安排上也有很大的傾斜。如小學三年級課程表規定:每周總計教學時間為34學時,其中,日語占12學時,蒙語占6學時,算術占6學時,還有修身、地理、講話、時事常識也多講日語。各級偽政府人員均需參加日語講習班,經常舉行日語考試。并為鼓勵學生學習日語起見,舉辦日語作文比賽、日語學會等。日偽甚至在學校之外的社會教育機構中也將日語列為奴化教育的主要科目,如通過開辦日本語學校、講習班、夜校、青年訓練所,推行日本語教育。日本語學校及其場所,有的是偽蒙疆地方政府開設,有的是日本人團體開設;學習期限不等,學員年齡、性別也沒有限制,大部分免費。日偽妄圖依靠日語的推行來打下同化蒙疆地區人民的基礎。強化日語教學的同時,弱化、甚至限制學生學習漢語。與此相應,教科書的種類及編寫設計也明顯這種計劃方案。
從世界殖民主義文化侵略的共性來看,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一旦被他國殖民地化或是軍事占領,一個共同的問題便會出現,那就是通過教育,支配者的語言被強制性地根植于被支配者。其方法有時是懷柔的,有時是強制的,甚至是暴力的,同時被支配者學習母語,使用母語的權利也被限制或禁止。支配者用強制與根植自己語言的手段,將自己的語言定為新的公用語,或者置于國語的地位,并且通過教育來普及它。同時,被支配著的語言被排斥,被無價值化,進而從教育對象中被刪除。
被支配者若是使用自己的語言則被視為“違章”,作為懲罰規則,“言語懲罰”曾經被實行。這些主要指是的學校教育中,殖民地的兒童若是講母語,會受到教員的警告,有的會受到體罰。母語本是從母親或是地域社會中很自然地付之于自身的民族屬性,使用母語會成為懲罰對象,這種非人性的事情在殖民地與占領區總是出現。而在中國淪陷區,日偽所實施的教育中,這種民族文化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到了無法復加的地步。
關于史地教科書,蒙疆淪陷區實際上是完全按日本意圖編寫的。《中國地理》《歷史》大講特講日本、蒙疆的地理、歷史,在淪陷區的學校連張中國地圖都不許掛。日寇還成立兒童讀物審議會,銷毀抗日進步書刊和與其謊言不一致的書刊,編撰以奴化教育為主要內容的兒童用書。他們篡改歷史,混淆是非,完全按殖民統治的需要杜撰歷史,蒙騙中國幼童,同時又假手漢奸、文人或媚日知識者肆意篡改《歷史》教科書,刪去書中愛國主義和民族主權的內容,換上“中日親善,共榮共存”、“同文同種”、“日本皇軍來解救中國人民”之類的鬼話,把偽滿洲國說成是合法的獨立國家,中國人民是“侵略者”。其中,關于“國家”的內容竟然是:建國精神、萬壽節、滿洲國民、國運、皇道等;宣揚的都是“日滿一德一心”、“五族協和”等。
(二)教科書內容滲透封建道德倫理及宗主國殖民奴化思想
日偽統治者還利用封建倫理道德對學生進行奴化教育。在蒙疆淪陷區開設的學校中,通過“修身”、“國民道德”課對學生進行封建道德教育,養成他們逆來順受、絕對服從的性格;他們通過漢奸之口叫嚷要從根本上鏟除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就要學習日本實行“圣道”;課外活動中還有供日偽驅使奴役的義務勞動課“勤勞奉仕”,這是中小學學生均不得免的,這種強化的苦力勞動,造成了對廣大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嚴重摧殘。這些實質上都是為其對外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野心服務的。
小學使用《修身》教科書中,重點向小學生開授“禮義廉恥”等封建思想,并加以歪曲,給以奴化解釋。其中對“禮義廉恥”是這樣講授的:“中國人對日本人要有禮貌,出入城要向日本士兵行禮,這就是‘禮’的具體表現與行動。”所謂“義”,解釋為:“日本并沒有占領中國領土的要求,皇軍是用來幫助中國驅逐歐洲白種人,以建立王道樂土,所以中國人不應當敵視日本人。”所謂“廉”,就是要中國人吞糠咽菜,勒緊褲帶想日軍提供各種的物資,任其掠奪。所謂“恥”,解釋為對日本不“義”不“禮”,對自己不“廉”即為“恥”。[19]這實際上是要蒙疆青少年忘掉國恥,心悅誠服地接受日本奴役。
《體育》教科書主要是對于法西斯訓練,向學生進行武士道教育,《歷史》教科書則向學生宣傳日本的“天照大神”、“三件神器”、“日俄戰爭的勝利”。《地理》教科書的項目內容及知識技能加以介紹則向學生描繪日本東京、大阪等城市景象和建設成就。
作為課堂組織教學中使用上述教科書的延伸與補充,日偽在蒙疆淪陷區還作出許多強制性命令:各級各類學校每日清晨必須舉行升旗典禮,集合全體師生向日本太陽旗敬禮,并向東方遙拜;經過日本神社時,必須鞠躬致敬;每逢“天長節”等日本節日來臨,各機關、團體、學校必須舉行放假紀念儀式,懸掛日本國旗致慶。甚至還強迫廣大師生經常參加為被抗日軍民打死的日軍將領舉行的慰靈祭,參加為日軍攻陷我南京、武漢等大城市而召開的“慶祝”儀式和游行。總之,利用一切手段營造日式社會、學校的環境氣氛,以潛移默化影響學生。[3]549
日偽強迫蒙疆淪陷區青少年通過學校教科書學習日語及其他服務于軍事侵略和殖民占領所需的課程,壓縮其他學科課程,注重宣傳“王道精神”,忽視基礎知識學習,所有這些一方面是為了淡化中國青少年的民族意識,使他們逐漸淡忘自己祖國的語言和歷史,降低他們的文化科學素質;另一方面欲使他們從語言、習慣、感情上盡快日本化,成為其二等臣民,以達到其最終滅亡中國,同化中華民族的險惡目的。
今天,部分正直的日本學者通過深刻反省,對此也深有認識,如日本宮城學院女子大學宮脅弘幸先生就認為:
殖民地的居民,在被迫要求與宗主國一體化后,無意識地同化于支配者文化,漸漸地失去了固有的民族性,民族意識和共同體意識(國家意識)。另外,原有的傳統習慣,文化生活方式也有所改變。這樣,在所有的文化領域,支配者與被支配著這兩種文化形態的混在,以及兩種文化的變種形態出現了。特別是情報,教育領域,因為支配者的語言變成了主流。被支配者的文化開始被侵蝕、被侵略、被同化。報紙、廣播、教育均使用支配者的語言進行的。殖民地原居民對原有文化額歸屬意識喪失,民族自豪感脫落,民族意識也變得淡薄。這就所說的“自我認識”與“歸屬意識”喪失現象。也是原日本殖民地與被占領區中漢奸身上所見到的現象。[20]8
教科書作為教育材料的核心,是教學的要素之一,成為教師或教育者向學生或學習者實施教學活動的中介或媒體,教科書是課程向教學活動工具性的轉化,這之間是相互聯系并相互貫通的。課程與教科書的設計不僅是純粹內容問題,還體現了教育觀念及組織管理的因素。日本侵略者聯合中國淪陷區偽政權規定課程與教科書,實施教學組織控制,在蒙疆淪陷區學校中強制使用合乎其殖民統治利益的教科書,惡意篡改中國原有教科書,加入“反共親日”、“民族協和”、“共建大東亞”等等奴化的思想內容,強化日本教學,企圖淡化蒙疆淪陷區學生的民族國家意識,對其進行精神毒害。與此同時,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殖民侵略,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抗。在國家危亡之際,蒙疆淪陷區的中國人民前赴后繼地與日寇進行斗爭,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反奴化教育洪流。日偽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教育、領導下建立起來一批群眾性的抗日愛國團體組織,如綏蒙各界抗日救國會(簡稱抗救會)。他們曾以“蒙疆道教會”作掩護進行各種抗日斗爭。到1940年初,抗救會已擁有會員200余人,會員們大力宣揚抗日救亡思想,揭露日本的侵華暴行,反對日偽的奴化教育,號召各階層人士團結一致,共同抗日。同時,搜集政治、軍事情報,籌集糧款,購買軍需物資,支援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斗爭等,他們為蒙疆地區的抗日救國事業做出巨大貢獻。作為抗救會的主要負責人劉洪雄就是其中典型榜樣,他在生死危亡時刻,不畏敵人威逼利誘,堅決與日寇作斗爭,為了表達自己的心志,鼓勵難友們堅持斗爭,他舉起戴著鐐銬的手,咬破中指,在獄中的墻壁上寫下了明代愛國將領于謙的著名詩句:“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梵燒若等閑;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間。”這種抗日愛國的大無畏精神深深的感動蒙疆人民,并激勵蒙疆人民在抗日救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殖民侵略的斗爭道路上不斷前進。這種反奴化教育的英勇斗爭,為瓦解日偽通過教科書實施奴化教育的陰謀,并促進整個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杰出貢獻。他們的功績彪炳史冊,他們的精神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1]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 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汪偽政權[M]. 北京:中華書局,2004.
[2]內蒙古教育志編委會. 內蒙古教育史志資料:第1輯上冊[M]. 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5.
[3]宋恩榮,余子俠.日本侵華教育全史:第2卷[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4]金海,姚金峰.蒙疆政權時期內蒙古西部地區教育述略[M]//蒙古史研究:第9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5]齊紅深.日本侵華教育史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6]北支那經濟通訊社.北支·蒙疆現勢[M]. 北支那經濟通訊社,1938.
[7]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總務部.蒙古法令輯覽:第1卷[M]. 蒙古行政學會,1941.
[8]任其懌.日偽時期內蒙古西部的日本語教育[J]. 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6).
[9]陶布新.偽蒙疆教育的憶述[M]//內蒙古文史資料:第7輯. 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10]烏拉特前旗志編委會.烏拉特前旗志[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
[11]德穆楚克棟魯普.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的成立與瓦解[M]//內蒙古文史資料:第7輯. 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12]任其懌.日本帝國主義對內蒙古的文化侵略活動[D]. 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2006.
[13]張建軍.偽蒙疆時期蒙古學校教科書編輯與使用情況淺述[J]. 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1).
[14] YC.日寇宰割下的察哈爾[J]. 察省青年,1941(4).
[15]建設廳.察哈爾省現狀調查[J]. 察省青年,1942(2).
[16]云澤.關于蒙地工作問題的報告(1946年7月)[M]//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檔案史料選編[Z]. 檔案出版社,1988.
[17]察哈爾蒙旗特派員公署編.偽蒙政治經濟概況[M]. 南京:中正書局,1943.
[18]石歐,吳小鷗,方成智. 中國近現代教科書史[M].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
[19]張理明,張靜嫻. 日本侵華期間對山西淪陷區的奴化教育[J]. 教育史研究,2001(1).
[20]齊紅深. 日本侵華殖民地教育研究——第三次國際學術研討文集[M]. 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責任編輯:賈建鋼 校對:朱艷紅)
A Study on the School Textbook of the Mongolia Occupied Areas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s Invasion
WU Hong-cheng, CAI Xiao-li, LI Yang-yang
(Educational College of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Chin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order to achieve enslaving education in Mongolia and Sinkiang area, Japanese and puppet regime actively carry out the policy of colonial rule and enslaving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pro- Japanese”, “ national union”, “divide conquer”.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lonial rule, they set up textbook editorial organization, delete and distort the textbook content recklessly, compile the textbook for enslaving education, make the textbook distorted seriously, the aim of these policies is to poison young students, service implementation rule.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the enemy occupied area; Mongolia and Sinkiang puppet regime; Enslaving education; School textbook; School curriculum
G529;K265.62
A
1673-2030(2017)04-0089-10
2017-11-10
吳洪成(1963—),男,浙江金華人,河北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蔡曉莉(1993—),女,河北邢臺人,河北大學教育學院在讀碩士;李陽陽(1989—),女,河北沙河人,河北大學教育學院在讀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