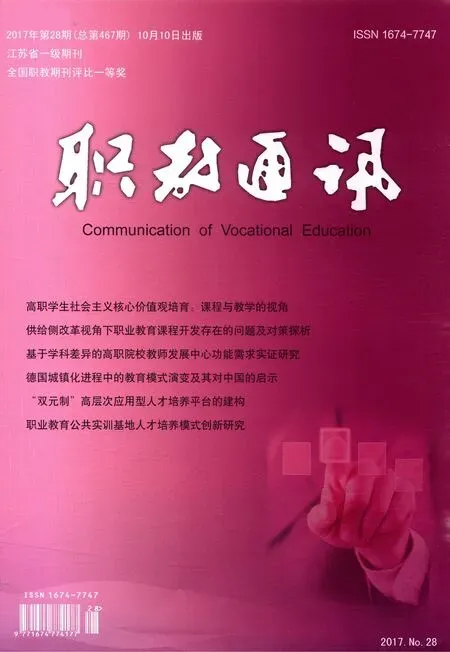德國城鎮化進程中的教育模式演變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李 俊
德國城鎮化進程中的教育模式演變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李 俊
在18世紀晚期至20世紀初期的德國城鎮化進程中,隨著產業的轉型與發展、人口的流動及政治結構的變化,德國的教育模式也經歷了深刻而又廣泛的變化,這主要體現在教育世俗化與教育普及、中等學校體系的建立和發展、雙元制職業教育的雛形初現以及高等教育的改革等多個方面,在此過程中,產業結構變化、技術進步、國家權力的擴張以及社會問題的產生和傳播對教育模式的變遷影響巨大。教育模式的變遷也對德國的城鎮化和工業化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一方面,通過培養各級各類高素質的人才,德國教育為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提供了大量高水平的勞動力,推動了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另一方面,通過教育系統對社會結構的影響和塑造,德國城鎮化進程高速推進的階段較少受到社會革命等動蕩的干擾,從而進展較為順利。
城鎮化進程;教育模式演變;德國;中國
城鎮化是一個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城鎮化的過程則伴隨著產業發展與社會轉型,在此過程中,教育模式的變遷也至關重要,一方面,城鎮化進程中的人口流動和產業發展會推動教育模式調整與改變;另一方面,教育模式演變也會通過不同類型層次的人才培養影響城鎮化進程。每個國家的城鎮化進程與教育模式的演進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德國職業教育今日的聲譽和影響,與其在影響德國城鎮化進程中的作用密切相關。本文試圖分析和探究,在德國城鎮化進程中的教育模式演變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并從中歸納和概況對于我國城鎮化與教育發展改革的啟示。
一、德國城鎮化的主要階段與特征
德國城鎮化的歷史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840年之前,是德國城鎮化興起的準備階段,在此期間農村人口遠超城市人口,農業產值占絕對優勢;1840年至1871年德國統一,是德國城市的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工業革命對城鎮化的推動作用明顯,大量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1871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是德國城鎮化極大繁榮和迅速發展時期。[1]由此看來,整個19世紀至20世紀初,是德國城鎮化發展的至關重要的時期。19世紀初期,德意志地區(不含瑞士和奧地利)住在農村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3/4,而到了19世紀末期,這個比例剛好倒過來。[2]
德國的城鎮化與工業化進程有著緊密的聯系,在這個過程中德國社會也經歷著全面而又深刻的變化,這些經濟、技術、社會及政治層面的變化是德國城鎮化和工業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分析城鎮化與教育模式變遷之間互動關系應當充分考慮的影響因素。概括來說,德國城鎮化過程中有以下一些重要的社會變化值得關注。
1.產業的轉型與發展。在19世紀以及20世紀初期,德國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農業和小手工業的雇傭人數大幅減少,而紡織業、煤炭產業和鋼鐵工業等工業部門的企業和雇傭人數則大幅增加。紡織業在19世紀下半葉的較短時間內從家庭散工集中到大企業,雇傭人數大幅增加,且機械化程度也穩步提高;煤炭產量在19世紀中葉到1910年代的幾十年間增長數倍,礦工人數大幅提高;此外,鋼鐵產業、機器制造業、化學工業和電力產業等工業部門的規模也顯著提高。[3]產業結構的變化帶來了德國社會職業結構的變化,專業分工日趨明顯,這自然對勞動者的素質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人們需要在新的環境及場所工作,如何通過教育培訓等方式來使人們適應這些變化,成為滿足新的產業及崗位要求的勞動者,對于社會機構尤其是教育構成了挑戰。[3]
2.社會穩定與治理。城鎮化和工業化帶來了德國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化,新的產業逐漸壯大和深化,大量產業工人的出現,這在之前的德國社會是從來沒有的,由此帶來許多新的社會問題,并對當時的社會穩定和治理構成了一定的挑戰,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將工人階級的年輕人整合進入主流社會之中,而不至于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當時所謂的“工人問題”(Arbeiterfrage)的核心在于,工人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長時間的工作,且承受巨大的工作負荷與壓力,他們工作之余的閑暇時間非常有限,在法國革命及當時的社會思潮的影響下,希望通過革命等途徑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帶來了顯著的影響,工人能否以及如何在社會及政治意義上容納和整合到社會中成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社會問題。[4]
3.政治結構的轉變。城鎮化和工業化改變了原有的政治結構,部分傳統的容克地主開始投資工業,參與銀行事業,逐漸變得資產階級化,原來屬于市民社會中間層的小手工業者逐漸加入到工人隊伍,與大量涌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和城市中下層人口一起逐漸無產階級化,職員階層開始出現,新興城市資產階級則逐漸獲得城市自治權,這些一起推動德國的政治制度也逐漸改革。[1]
二、城鎮化進程中的教育模式演變分析
如前所述,德國城鎮化進程的關鍵時期在于19世紀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百多年間。因此,筆者接下來將重點介紹分析這段歷史時期德國教育模式的演變與發展。
(一)教育的世俗化、教育義務與普及
早在1763年,普魯士的腓特烈二世即發布詔令,規定普魯士的兒童應在5至13或14歲之間進入學校學習,學習有關基督教的基本知識以及閱讀和寫作。[5]
在19世紀上半葉,洪堡的教育改革對以普魯士為首的德意志地區的教育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09年,洪堡被任命為普魯士內政部教育大臣后,開始推進教育改革,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加強世俗國家對教育事業的控制和管理;建立國家考試制度;嚴格教師的錄用及發展師范教育。[6]
教育世俗化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之一,是于1849年在法蘭克福召開的國民議會上通過的德意志聯邦的《德意志帝國憲法》,該憲法特別規定了公民基本權利,并宣布了宗教信仰自由和高等學校教學自由,宣布教育由國家管理,只有宗教和教士教育除外。[3]
然而,世俗化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此過程中,伴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而發生的工人革命運動也引發了對學校教育的討論,部分國民學校的教師認為,即使是下層學校的學生也應擁有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機會,而不只是被限制在較低的教育軌道上,政治革命刺激了普魯士的統治階層的神經,而相應的教育議題也讓其不安,他們于是通過宗教教育來加強對兒童和青少年的思想控制。[7]1854年,普魯士頒布針對初等學校的《法令》,規定小學教育的任務就是訓練溫順的性情,祈禱的習慣和虔敬的精神。這一狀況在19世紀下半葉,尤其是1870年代之后得到改善。[8]
19世紀上半葉的教育改革所取得的另一個重要成就在于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在此期間兒童入學率的增長明顯高于同期人口的增長,1816年,普魯士的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了60%,1848年,這一數字提高到82%,到1890年左右,德國人口的文盲率已經下降到1%以下。[6]與此同時,德國教育開始出現現代教育所必備的重要功能,即服務于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服務于社會生產發展的需要。這一時期德國的教育改革在與工業化及政治現代化的協調適應上甚至走在了英國與法國之前。[9]
概括地說,德國初等教育的發展、教育的普及和世俗化與德國國家的發展以及國家權力的擴張有著密切的聯系,正是普魯士及后來的德國政府的強制規定及實施才推動了德意志地區初等教育的普及。
(二)中等學校的建立與發展
近代以前,在歐洲幾乎只有教會神職人員和貴族等少數特權階層才有機會接受教育;在16世紀之后,社會中下層的普通民眾也成為了教育的受眾,由此,德國的受教育群體出現了明顯的分裂,形成了由教會僧侶、時速貴族、部分中等階級受教育者組成的有教養階級和由普通民眾組成的無教養階級兩大教育群體。[6]
德國現代教育體系的發端與文法中學(Gymnasium)所面臨的危及及現代化過程緊密聯系在一起。[9]隨著社會經濟與技術的發展,商業、制造業、交通及金融等行業雇用人數逐漸增加,且對就業人員的素質和技能要求也逐漸提升,原有的主要傳授古典科目的文法中學難以培養大量新興經濟與產業所需要的人才,教育系統對此進行了兩方面的回應;一是文法中學等原有的學校對其課程內容和專業設置進行了調整;二是實科中學等一些新型學校逐漸出現。
文法中學課程內容的調整涉及其辦學方向和課程內容,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在新人文主義運動以及洪堡改革的推動下,拉丁語語法等古典學科的內容被削減,數學等普通基礎學科的教學被增加,歷史、地理和自然科學等科目被增加,教師選擇的標準也在這一時期被改變,國家考試制度被引入到教師選拔中,這就改變了此前文法中學的教師被牧師和神學者等壟斷的局面。[8]
實科中學的發展其實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席姆勒(Zemler)于1708年在哈勒市(Halle)建立的數學工藝學校,教授數學、物理學和機械學等內容,它可以被看作是德意志地區實科中學的前身;赫克(Hecker)于1747年在柏林市創辦了德國第一所真正意義上的實科中學——經濟與數學實科中學,設置有數學、幾何、建筑和地理等多個班級。[10]
然而早期的實科中學的發展路徑卻因為宗教保守勢力等原因變得較為復雜和分化。部分實科中學自1820年代開始就增加了神學科和拉丁文課程的傳授,在1848年以后,部分學校改成了古典與實科并重的中學,即文實中學,在某種程度上也適應了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與貴族平起平坐以及部分貴族因兼營工商業而資產階級化的社會及階級基礎;在19世紀后半期,實科中學就已經實際上分化為實科中學和文實中學。[8]
1872年,德國原有的教育系統被進一步改革和調整,原本為期八年的義務教育的國民學校被分成前后各為四年的兩個階段,前四年叫基礎學校,后四年叫高等國民學校,在此之上就是職業補習學校等職業教育學校;此外,為了滿足中等階層居民及小資產階級子弟以適應期階級地位的教育,在基礎學習之上增設了中間學校(Mittelschule),其程度略高于國民學校,但又低于文法中學。[11]中間中學也是今日的實科中學的前身,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下層學校系統分離出來的,原來的城市國民學校和市民學校加上為新興中產階級的女兒開設的教育機構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新的學校類型,即處于中學階段、為期6年的中間中學;其建立也是為了響應工業、手工業及貿易的不斷發展,部分高水平的企業職業培訓越來越以實科中學畢業資格作為進入培訓的基本條件,1910年,中間中學成為了德國教育的重要支柱,構成了三級分類中的中間水平。[5]
自此,德國中學階段教育的三種學校類型并存的狀態已初具雛形,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初中即分流、中等學校分為三種不同形式的教育形態延續至了今日。德國中等學校的發展,一方面,受到了國家權力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與經濟技術環境的變化有著密切的聯系,正是為了適應社會生產的發展和技術的革新,教育系統才在學校類型及課程內容等方面做出了調整和改變。在這個過程中,教育政策的變化與城鎮化過程中德國社會政治結構的變化無疑也有一定的關聯。
(三)職業教育的發展
德國職業教育與培訓的早期發展離不開兩個重要的社會經濟背景,它們均與城鎮化密切相關,一方面,是城鎮化和工業化過程中技術工人的知識與能力要求不斷提升,職業教育與培訓自然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途徑;另一方面,是文章開頭提到的工人問題,即社會對工人階級的容納和整合,除了經濟界和社會政策領域的制度及政策干預之外,職業教育也不能置身事外。實際上,今日德國在全世界受到廣泛和高度認可的雙元制職業教育與培訓,正是在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德國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初步成型的,正如今日雙元制職業教育由企業職業培訓和學校職業教育兩個部分組成,當時的企業培訓與學校教育也是分開發展的。
在企業職業培訓方面,傳統手工業與新興的技能密集型制造業之間的競爭與互動,以及對培訓及職業資格證書相關制度及政策產生的影響至關重要,且這一過程受到自由派與保守勢力之間就德國經濟社會政策等議題所展開的斗爭的影響;傳統的職業培訓體系由手工業部門所把持,盡管1860年,出現的經濟政策的自由化轉向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傳統手工業部門在職業培訓中的主導地位,但是為了應對強大而激進的勞工運動,保守政治勢力嘗試扶植手工業以作為抵抗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平衡力量;1897年,國家干預下通過的《手工業保護法》為組織化的手工業部門所控制的學徒培訓創立了制度框架,在其規定下,各地的手工業協會(Handwerkskammer)被賦予更大的管制權力。[12]
到19世紀末期,為了應對手工業技能培訓體系供給不足的問題,大型機械制造和金屬加工企業開始制定開發工廠內部的技能培訓策略,同時,建立內部勞動力市場制度;然而,技能資格認證的權力仍然掌握在手工業手里,這些企業不能對其培訓的技術工人進行技能認證,于是,它們與手工業主之間就展開了關于技能資格認證和考核的權限問題的曠日持久的爭斗。[12]為了應對1907-1908年爆發的技能短缺危機,1908年,成立了德國技術學校委員會(DATSCH),其早期政策和行為大部分反映了大型機械制造企業的利益訴求,他們宣稱年輕人的培訓屬于社會公共物品,并希望說服國家增加投入以分擔職業培訓的成本。[12]
學校形式的職業教育在同一時期也經歷了重要的發展和改革。1871年,即德國建立的同年,帝國營利事業法(Reichsgewerbeordnung)將職業教育的管轄權賦予工商會及手工業商會,第一批職業和進修學校從而被建立;1897年,非學術的職業教育被規范為早期雙元制之中,學校的職業教育被看作是企業培訓的補充。[5]
1920年,一個由工會代表、雇主組織代表、職業教育專家、政府教育部門官員和年輕人協助組織代表所組成的調查委員會就已經完成了一個關于職業教育專門立法的報告,但在1929年議會的討論中,各方無法就諸如該法律的覆蓋范圍、工會的介入形式以及質量標準等多個方面的問題達成一致。這種爭論在二戰之后在不同黨派和利益集團之間仍然繼續,直到1969年,各方才達成一致,通過了聯邦職業教育法。[13]
職業教育的發展,一方面,受到經濟界產業界對勞動力能力素質的需求等經濟和技術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與由城鎮化及工業化所引起的社會問題有著較強的相關性。除了上述手工業與新興制造業之間的博弈受到社會問題及國家對其回應的影響,與學校形式職業教育聯系更加緊密的德國職業教育的奠基人凱興斯泰納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成功,也與當時的社會治理方面的問題緊密相關。
1900年,埃爾福特的皇家應用科學學院向社會各界進行征文,題目是“如何讓我們的年輕人,在從國民小學畢業后到參軍之前的一段時間內,最恰當的受到教育?”凱興斯泰納提交了一篇論文并獲得優勝以及600馬克的獎金,在他這篇被認為是德國職業學校奠基之作的論文中,凱氏給予了清晰的答案,即建立勞作學校,并把學校當作繼續學習的地方,通過讓學生們學習實踐技能,防止他們走上街頭參與革命和暴動。在凱氏開出的教育藥方中,這種學校應當提供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課程,教學應當和產業相關,并且包含一定的公民教育;凱氏清楚的指出,職業工作時公民教育的最好方式,其不僅能夠培養不同方面的能力和技能,也能間接的引導學生的能量到某個的興趣和領域之中。[4]
(四)高等教育的發展
18世紀,德國地區的大學改革較少,但到19世紀之后,高等教育領域經歷了較為重大的改革,這些改革甚至影響了全世界范圍內的高等教育發展,而提到德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則不能繞開洪堡對大學的改革。
在洪堡的改革下,柏林大學秉承學術自由的精神,將學術研究作為學校的核心任務之一,設立研修班(seminar),以培養學者而非培養中學的教師作為目標,并調整原有學院的研究與教學內容——神學院轉變為研究一般宗教科學的學院,法學則不再只是講有關自然法和現行法的法律格言,而研究法律發展的科學問題;在柏林大學建立后的十幾年間,許多參照柏林大學的模式、專注于科研與教學的新型大學得以建立,比如波恩大學和慕尼黑大學。[14]
盡管在1840年至1870年間經歷了一些發展與改革的停滯,但德國的大學在1860年代之后重新走上快速的發展道路,在20世紀初期,多所大學的經費、學生人數以及教師人數與19世紀中期相比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14]更加具體地講,德國的大學在19世紀后半葉經歷了以下兩個方面的顯著變化:(1)大學教育內部結構的變化,即為適應工業化發展需要而出現的各大學各院系的規模的調整:神學曾經是德國各大學中最大的學科,1870年時下降到了16.4%,1914年時則進一步下降到了9%。法律學科在1870年時還擁有學生總數的24%,由于就業市場過剩,到1914年時則下降到了16.5%左右;(2)新型大學的出現,一方面,是新創立的綜合性大學,如1901年建立的法蘭克福大學等突破了傳統學科的設置模式,新設了自然科學、經濟學等學科,以適應經濟技術與社會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則是商業及技術高等專科學校的建立,它們常常是由綜合技術學校、技術專科學校(technischeFachschule)、工商業研究院等發展而來,并建立在一些商業較為發達、技術較為先進的城市。[15]
德國聯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將德意志地區的教育發展的特點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1)在歐洲乃至全世界范圍內較早引入面向大眾的教育義務;(2)學校形式的規范化以及畢業證書和學位的引入,且畢業證書隨學校形式的不同而有差異,而這些證書與特定的職業發展路徑、培訓路徑及要求聯系在一起;(3)教育系統中較為嚴格的“高級”學校與“低級”學校之間的區分,前者主要針對社會貴族和精英的子女,而后者則面向大量普通民眾的子女;(4)20世紀早期引入中等學校的形式。
概括來說,經濟技術的發展、國家在制度和政策方面的改革以及人們對于社會問題的回應共同構成了德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教育模式演進和變遷的主要動力,它們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和機制推動德國的基礎教育、中等教育、職業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在并不算長的時間里經歷了較為迅速的變化,而包括教育目標、課程內容、教育方法以及教師培養路徑等多維度多方面的教育模式的改變,對于德國社會的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也反過來起到了一定的影響。
三、教育模式演變對城鎮化進程的影響分析
(一)教育推動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
盡管教育對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動作用看上去較為間接,但是實際上卻至關重要。德國作為資本主義世界后起的工業強國,在18世紀之前的發展其實落后于英法等傳統強國,但從19世紀開始,德國的工業發展速度快、城市改革徹底,僅用幾十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城市化的進程,而在此過程中,科學技術和人口流動障礙的消除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教育在推進科學技術進步和消除人口流動障礙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其實,教育在工業化過程中的作用并不是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簡單,實證研究顯示,教育在英國工業革命早期的紡織工業中作用其實幾乎沒有;然而,在普魯士工業化的趕超過程中,教育對于非紡織部門的積極效果則是非常顯著的;在洪堡對于普魯士的教育改革中,以培養大量公民獨立理性思考能力以及負責任的行為為目標的普通基礎教育,對于應對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改變具有重要作用。[16]
高質量的基礎教育與職業教育有力的推動了德國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不斷提升,一個重要的指標在于德國出口總值與出口中工業產品所占比重的變化,與1872年相比,1914年,德國的出口總值提高了超過30倍,而工業品占比則從38%提高到63%;德國在這一時期所經歷的大范圍的、且其他國家無可匹敵的工業擴張主要是由于其工人的競爭力,大量初具文化知識和掌握了初級勞動技能的訓練有素的勞動者,與技術人員一起組成技術梯隊,大大加速了德國工業的發展,也給德國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了極其深遠的影響。[17]
在美國經濟史學家理查德.蒂利看來,德國的中等及高等教育機構,尤其是職業學校、技術學院和大學的自然科學和工程方面的院系培養了大量的受到良好訓練的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師和技術工人,而大學的研究則轉化為適于產業應用的技術知識,德國培養的各級各類人才以及科研文章在世界范圍內具有一定的領先位置,這不僅在化學及電氣工程等涉及科技水平較高的部門如此,在許多其它產業部門也是如此,教育的推動作用顯著。[18]
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中等教育與職業教育的作用在推動城鎮化與工業化進程中的作用特別顯著,許多杰出的地方工業家并沒有在大學接受過高等教育,且直到1860年,他們也沒有讓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強烈意愿。[19]
總的來說,德國政府把教育當作振興國家的手段,力求整個教育體系從內容到方法都與社會的近期需求及國家的發展相結合,讓各類學校遠離舊教育的宗教目的,致力于培養現實生活中的有用人才,從而為提升德國企業的競爭力做出了貢獻,從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與技術進步。[20]
(二)教育對社會結構的作用
教育對于城鎮化和工業化的作用并不止于培養勞動力方面,教育系統對社會結構的塑造和改變也從側面實際影響了德國的城鎮化與工業化進程。
在德國城鎮化的過程中,教育系統對社會結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教育機會的擴大使得大量農民和工人等社會下層勞動者子女受到更多的教育,從而提升其社會地位;(2)優勢精英階層通過教育系統類型與層次的區分,實現了對學生的篩選,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其優勢地位,教育系統在這個意義上起到的是對社會結構的穩定和固化。
在1800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各級各類學校的學生人數在總體上呈現持續的增長,教育機會面向大眾的開放在這100多年里的多數時候都非常顯著,城鎮化過程中大量農民轉變為工人,他們的子女的教育機會不斷的改善,越來越多的人能夠進入較高層級的學校,教育系統的整合功能得到了較為充分的體現;與此同時,由于教育系統內部結構與層級的清晰劃分,教育系統的分化功能也能通過數據得到驗證。[21]
教育系統對不同學生的分化反映了德國教育系統的一個核心特點,即學校系統、職業系統與就業系統的緊密聯系,這直接反應在國民學校(主體中學的前身)、實科中學和文法中學的三層級的學校系統中,且學校系統的這種層級結構與階層分明的社會結構又密切相關。[9]教育系統所引起的社會階層的分化反映在了社會流動性上,德國非熟練工人與臨時工向社會上層流動的空間較小,而熟練工人向上的流動空間則較大。[22]
在高等教育中,同樣可以既看出教育機會不斷擴大的趨勢,也能看到教育對社會階層結構的鞏固及固化作用。對德國大學學生的家庭背景的統計數字反映,一方面,在1840-1870年代,許多高校中第一代大學生占所有大學生的比例在明顯提高;另一方面,其父親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進入大學學習的概率要明顯高于其父親沒有讀過高等教育的學生,比如,1840年代符騰堡地區的大學新生中的近60%都有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父親。[23]
由此看來,19世紀及20世紀早期德國的教育發展與模式變遷對社會階層結構起到了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通過提高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規模和人數,向大量普通民眾提供了提高社會地位、獲得穩定職業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因教育系統與職業系統、教育結構與社會結構的緊密聯系,而在很大程度上對社會階層結構的固化和再生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教育系統對社會結構的影響和塑造,德國城鎮化進程高速推進的階段較少受到社會革命等動蕩的干擾,從而進展較為順利。
四、德國城鎮化與教育模式演變的特點及啟示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概括歸納出德國城鎮化與教育模式變遷互動關系有以下四個方面的關鍵特征。(1)城鎮化的進程與教育模式的變遷聯系緊密且有明顯的互動效應,一方面,城鎮化構成了教育模式變遷的主要動力之一和最重要的時代背景;另一方面,教育模式的變遷也對城鎮化的進程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2)城鎮化進程中教育模式的變遷是全方位和整體的,正是基礎教育、中等教育(尤其是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全方位的變化和改革共同推動了城鎮化進程中的技術變革、經濟進步及社會變遷,僅靠單一層次單一類型的教育改革難以適應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需要。(3)教育模式的變遷對城鎮化進程的既在經濟方面有推動作用,也在社會及政治層面產生重要影響,一方面,教育模式的改革與教育內容和目標的變化為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提供了大量高素質的勞動力;另一方面,教育系統的結構調整也為在社會轉型時期保持社會結構的相對穩定、防止社會動蕩起到了重要作用。(4)國家權力的支持和介入對于教育模式的變遷起到了重要作用,且這種作用在城鎮化進程中得到了發揮。19世紀上半葉,普魯士的教育普及、職業教育體系的早期發展以及新型高等教育機構的興起都與國家權力的介入密不可分,這些教育模式方面的變化為德國在當時的國際競爭中趕超英法等傳統資本主義強國提供了重要的幫助。
我國目前仍然處于城鎮化進程之中,德國城鎮化進程中教育與城鎮化之間的互動關系對于我國的城鎮化發展以及教育改革都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筆者在前文論述的基礎上嘗試概括梳理以下三個方面。
1.應促進城鎮化過程中不同類型和層次教育的協調均衡發展。城鎮化進程是一個涉及面廣、影響因素眾多且內在關系非常復雜的過程,其中各級各類教育能起到的彼此不同但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響,在此過程中應關注不同類型和層次的教育的均衡協調發展,使其分別發揮自身的作用,以有利于城鎮化進程的有序推進。
2.應發揮教育在城鎮化進程中的推動和穩定作用,一方面,通過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等途徑培養不同類型及層次的高素質勞動者;另一方面,也應通過合理的教育資源分配和教育結構安排來滿足不同群體的教育需求,以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
3.應注意結合運用市場手段及行政手段來發展教育,以達到教育供給的最佳配置。基礎教育與職業及高等教育分別屬于公共物品和準公共物品,要在較為有效的提供優質教育資源的同時保障民眾的基本受教育權,一方面,應充分調動多個利益主體的參與和投入教育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則在市場失靈的領域中進行合理的制度設計和公共資源投入,從而在運用市場手段與行政手段之間保持合理的平衡。
[1]申曉英.城市化與社會變遷——以19世紀初至一戰前的德國為例[J].德國研究,2004(2):32-36,78.
[2]Von den Driesch,Johannes&Esterhues,Josef,Geschichte derErziehungund Bildung[M].Paderborn:Ferdinand Sch?ningh,1961:176.
[3]徐繼承.德意志帝國時期城市化研究(1871-1910)[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2:77-80,87-89,118.
[4]Gonon,Philipp,The quest for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Georg Kerschensteiner between Dewey,Weber and Simmel[M].Bern:Peter Lang,2009(42),72-74,76.
[5]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Deutsche Bildungsgeschichte-eine Zeitleiste.[2013-09-09].http://www.bpb.de/gesellschaft/kultur/zukunft-bildung/145249/geschic hte-des-bildungssystems.
[6]邢來順.略論19世紀德國教育的發展趨勢[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1):70-74,128.
[7]Universit?t GH Essen.Entstehung,Struktur und Steuerung des deutschen Schulsystems.Skriptum zur Einführungsvorlesung in den Studienbereich ?D“.2000:7.
[8]王天一,夏之蓮,朱美玉.外國教育史(上冊)[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194,196-197,196-197.
[9]Drewek,Peter.Das gegliederte Schulwesen in Deutschlandim historischen Prozess.Ans?tze,Quellen undDesiderate der historischen Bildungsforschung.Archivpflege in Westfalen-Lippe 83.2015.
[10]張斌賢,王晨.外國教育史[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3:271.
[11]王天一,夏之蓮,朱美玉.外國教育史(下冊)[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63.
[12]凱瑟琳.西倫.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國、英國、美國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經濟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6-43,48-49,51-53.
[13]Greinert,Wolf-Dietrich,Das deutsche System der Berufsausbildung.Transition,Organisation,Funktion.3.Ueberarbeitete Auflage[M].Baden-Baden: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1998:85-87,75-76.
[14]弗.鮑爾生.德國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25-128,129-131.
[15]邢來順,吳友法.近代德國工業化過程中教育事業的發展[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6):99-105.
[16]Sascha Becker,Erik Hornung,Ludger Woessmann.Catch Me If You Can:Education and Catch-up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Discussion Paper No.4556.November 2009.Forschungsinstitutzur Zukunft der Arbeit.2009.
[17]Dawson W.H.,The Evolution of Modern Germany,London,1915:148.//徐旭華.德意志帝國城市化影響因素分析[D].蘭州:西北師范大學,2012:74.
[18]Tilly,Richard H.:Industrialization as an Historical Process,in:European History Online(EGO),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uropean History(IEG),Mainz 2010-12-03.URL:http://www.ieg-ego.eu/tillyr-2010-en
[19]霍布斯鮑姆.資本的年代1848-1875.[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50.
[20]姜麗麗.德國工業革命時期的城市化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08:27-28.
[21]Nath,Axel.Bildungswachstum und ?u?ere Schulreform im 19.und 20.Jahrhundert.Individualisierung der Bildungsentscheidung und Integration der Schulstruktur.Zeitschrift für P?dagogik,49:1,2003:8-33.
[22]Klaus Tenfelde,Reviewed work(s):Town in the Ruhr:A Social History of Bochum,1860—1914 by David F.Crew,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5,No.3(Jun.,1980).轉引自:徐繼承.德意志帝國時期城市化研究(1871-1910)[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2:11.
[23]Fritz K.Ringer.Higher Education in Germanyb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967:123-138.
李俊,男,同濟大學職業技術教育學院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政策、比較職業技術教育。
G719
A
1674-7747(2017)28-0029-07
[責任編輯 張棟梁]